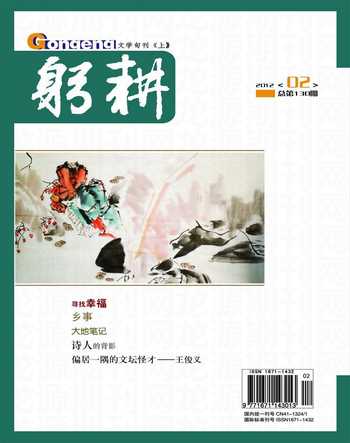银元
樊有堂
三宝气急败坏地掏出手机给大宝打电话:“大哥,我是三宝呀。你现在在哪里?东坡地摘棉花。快点回咱老院吧,出大事啦!咱爹埋的银元被人挖走了,快回啊!”三宝打完电话,内急,连忙进厕所方便。便后快步往外走,走到桂花树前,右脚使劲儿跺地面。脸色如猪肝,浓眉拧成两根麻花,铜铃般的眼球胀得要蹦出来。
他又急又气,烦躁得很哩!
他能不又急又气吗?女儿殷姣开学上高一需要两千元,儿子殷好考个三本需要一万六千元,妻子赵兰偏偏在这时候患脑溢血,已经花了一万二千元,往后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家里积蓄少,妻子治病已经借亲戚四千多元,这后边的开支咋办呢?清明节给娘上坟时,爹告诉他们兄弟三人,爷爷解放前做洋布生意,攒了一百块“袁大头”,算是作为传家宝留给他,他把这一百块银元装在坛子里埋在院内桂花树下,等来年春节把它起出来,给他们三兄弟分分,各保存各的,把这银元代代传下去。现时,他急用钱,他想找爹商量,让爹早点起出来。他听说城里古钱币市场上一块能兑五百多元,他想换现钱,管什么传家宝呢,救急要紧吧。可现在这银元不翼而飞,真让他气急攻心,坐卧不宁!
三宝抬头看天。乌云黑网似的罩过来,片刻,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像魔鬼在施展魔法一样,使院内变得又昏又暗。一阵凉风吹过来,他不由自主打个冷战,浑身哆嗦不止。
“嘀嘀”两下电动车铃声把三宝的哆嗦止住。他慌忙往大门口走,迎接大哥。
大宝一脸严肃肃地推车进院,支好车,缓步走到桂花树前,“你啥时候发觉的?”
“我刚从医院回来,到这院里就看见啦!”
“没事儿你到这院里干啥呀?”
“我想看看咱爹回来没有。”
“咱爹不逢年过节一般不回来,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想先看看,然后……”三宝欲说又止,索性把头埋下来,不看大哥。
大宝知道三宝想说什么,没有追问。他仔细看看现场,然后对三宝说:“你去把你二哥叫来吧!”
“我不去,俺俩不说话。大哥,说心里话,我真怀疑是他两口子偷偷挖走的呢!”
“啥见证哩?你去吧,你是弟,他是哥,你去找他就说我叫他来的,他不会让你难堪的。这事不能往后推啊!我刚才在地里给爹打电话,他说他也没挖,这就麻烦了。”
“那中吧。”
三宝极不情愿地推起大哥的电车往大门外走,心里开始翻腾起和二哥的恩恩怨怨。
他和二哥相差三岁,记事起就是二哥欺负他打他。他每向父母告状,都会招致二哥更重的打,气得他多次发誓长大后非报仇不可。后来,张庄的黑蛋打他,二哥揍了黑蛋,这事儿才算摆平,他从此不再对二哥耿耿于怀。二哥和他一前一后结的婚,二嫂说他屋里的家具好,就多次带二哥找爹妈闹事。妈心肠窄,为此气成肝癌,驾鹤西去……八年前分宅基地,二嫂抓阄后又赖着不算,他让二哥表态,二哥死猪般不吭声。他气得指头戳到二哥的鼻尖上,骂二哥是“肉拧头”。结果和二哥打一架,双方头破血流。从此和二哥二嫂楚河汉界般隔开,井水不犯河水。今年清明节下午,舅父和爹召集他们三兄弟三妯娌商量轮流管爹饭的事,二嫂不论理,说爹在三家干活出力不一样,她家出点钱可以就是不轮流管饭。舅父怎么劝解她都不同意,并且站起身和舅父大吵。二哥又是看着不管。他实在忍无可忍,就和二嫂争辩,谁知二嫂变本加厉,嘴里不干不净起来。他气得上前推搡二嫂一把,捅了马蜂窝。二嫂趁势歪倒地上又哭又骂,骂他是狗娘养的野杂种,黑心歪尖坏红薯;骂二哥是个熊包蛋,鱼鳖虾蟹都敢欺负。二哥猛然站起身,往他跟前窜。多亏大哥抱住,才避免一场血战。舅父气走了。爹气得第二天就住到张庄姐姐家。他童年时的“仇敌”——张黑蛋姐夫大度地赡养爹,令他对姐夫和姐姐肃然起敬,也使他和大哥惭愧不已……
“你有啥事?”二宝在村头修理铺石棉瓦棚下搓着油污的双手问三宝。
“大哥让我叫你现在就回老院,分咱爹埋的银元哩!”三宅撒谎,没有直说。
“那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就到!”二宝木着脸,不阴不阳。
“挖走没挖走还不一定哩,咱挖挖看吧。”大宝面对两位弟弟,低声沉沉地说。
“肯定是挖走了,这新埋的土又鼓又虚,明摆着哩!”三宝边说边睃看二哥。
二宝不吱声。他从小到大就不爱说话,天生有“大将风度”,可惜连个民兵排长也没当过。这时,他从大哥手中拿过铁锨,麻利地开始挖土。挖啊挖啊,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斜着挖到桂花树底部下面,约有八十公分处。虚土全部掏出,空空如也。
大宝木然地站着一动不动,眼神黯然失色。
二宝埋头填土,一锨比一锨慢,像是正在盘算主意。
三宝脸色铁青,走到院内石板前,一屁股坐下。两眼越瞪越大,越瞪越红,样子可怕得很哩!
一阵闷雷从远处响过来,轰隆隆,轰隆隆……天上的黑云压得更低,仿佛站到屋顶就能抓它几片。黑云和黑云连接处的上部不时掠过一道又一道次黑云,使人感到苍穹深不可测,多变怪诞。
二宝填完土,用脚使劲儿踩,踩出决心:“哥,要是没有别的事,我走啦!”
大宝悠悠地答道:“别的没事呀!”
二宝干脆果断地说:“那我就走啦!”说罢,转身抬脚就走。
三宝急了,站起身,大声吼道:“你不能走!”
二宝扭转身,怒视三宝说:“咋,你有啥事?说!”
“这银元莫非就是你挖走的,也不说个一二三就走了,恁轻巧!”三宝很恼火地说。
“咋,你怀疑是我偷的?我还怀疑是你急用钱,你偷的哩!”二宝反唇相讥。
“我不是那号人,我才不会偷哩!”
“谁是那号人?那号人脸上有字吗?”
“你就是那号人,你脸上就有字!”
“因为你自己是那号人,所以你才把我想成跟你一样也是那号人哩!”不爱说话的二宝嘴并不笨,唇枪舌剑,毫不相让。
“你放屁!”三宝缺乏事实证据,斗不过二哥的嘴,被噎得脖粗脸红,只有拿出杀手锏,放粗话。
“我放屁,好啊,你小兔子长大了,敢骂我了,让大哥作证,我怕你中不中,我走啦!”二宅说后扭头就走。
大宝站着没动。他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把头仰向天空,望着黑云发呆。
三宝突然一个箭步窜上去,伸手抓住二哥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想走?没门,说清再走!”
二宝半转身,“啪啪”给三宝两个耳光子,并趁机猛往后一挺,挣脱三宝。三宝不说话,瞪着猩红的双眼,一个黑虎掏心拳照准二哥直捅过去,把二宝打得往后倒退几步,险些跌倒。二宝打架哪里吃过这样的亏!他迅速稳住脚步,猫起腰,握紧双拳,迎着三宝,也冲了上去。三宝躲过二哥的拳头,顺势贴近他的身子,双手抓住了他的臂膀,使二宝拳脚施展不开。接着,兄弟俩扭打在一起,随之双双倒地,在地上翻滚着……
大宝急忙跑过来,弯腰拉已经压在二宝身上的三宝。可哪能拉得起呀!三宝不松手,死死压住二宝,并抽出右手猛打二宝的脸。二宝也不松手,用劲挣扎翻腾,险些又把三宝翻压下边。两个家伙拼了命,谁也不让谁!大宝看三宝下手重,就大声说:“别打啦,银元是我挖走的!”
“真的假的?”三宝松手,仰脸问到。
“真的!”大宝一脸认真地说。并且显出惭愧的样子,把头低下去。
三宝缓缓站起身,拍拍裤子上的灰土,嘴角浮出一丝苦笑,生涩地结结巴巴说:“不……不可能吧,大哥,你不是那号人,你是不是……为了劝……劝架胡承认哩!”
大宝一本正经地摆手说:“不,不!真是我挖走的,我心小,怕万一被别人挖走,咱兄弟可破大财了!这一百块银元现在就藏在我家,你俩放心吧。”
二宝也慢慢站起身,一脸惊谔。
“那……”二宝三宝同时嗫嚅。
大宝用手理理头发,显然理出了事情的头绪,不紧不慢地说:“明天早上我去张庄叫咱爹,上午九点咱都到老屋来,就在这里分银元……”
天空突然响起一声炸雷,打断大宝的话。随之隐约听到远处有风雨呼呼声。顷刻间,附点噼噼叭叭砸下来,毫不留情地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三兄弟匆匆散去,消失在茫茫烟雨中。
第二天上午,阳光灿烂,空气清鲜。村民们都在屋顶上晾晒棉花、玉米,谁也不愿错过这秋日金贵的太阳。棉花的银光和玉米的金光以及农人笑脸上荡漾出的红光交相辉映,映出了一幅金秋农家甜美的生活画卷。
殷家三兄弟今天虽然和大家一样被霞光万道的朝阳沐浴,但是他们却高兴不起来,各自揣着难以名状的心绪,神情凝重地往老屋走去。
殷明牛老汉早早在屋等候。他看上去不像七十多岁的农家老人,腰杆很直,精神矍铄,斯文秀气,举止大方。兄弟仨陆续进屋,跟爹说些问候话,坐定。
大宝开门见山把昨天下午三宝发觉银元被挖,二宝三宝争吵打架的事儿一股脑儿向爹诉说一遍。最后,他十分沉重地说:“爹,都怪我财迷,不该偷偷挖走银元,更不该把这银元交给他大嫂保管。现在她死活不拿出来,还不准我承认,我也没办法,只有瞒着她把这银元折成钱,给二宝三宝分分,你说中不中?”
“折多少钱呢?”爹脸色很难看,但话语柔和,不紧不慢地问。
“折一万五千元,咋样?我给二宝三宝每人五千元。”大宝一脸无奈,话语诚恳。
“不中,不中!”三宝首先大声反对说,“折五万元也不多,古钱币市场上能卖六百元一块,要是有特殊版的,没准儿一块就值多少万哩!”
“折啥钱呀,慢慢做我大嫂的工作,咱还是分银元吧!”二宝一改往日的寡言,从旁插话。
大宝板着脸说:“折钱太多是不可能的,分银元更是不可能。我就是再让一步,最多也只能折两万元,否则就不再说了!”
“你论理不论理?”二宝三宝异口同声。他俩结成同盟,变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我咋不论理啦?你大嫂把银元藏起来了,要想叫她交出来,除非打她杀她,你们说咋办?要不这样吧,我折的价和三宝折的价都不算,咱们一起到银行问问,白银一克多少钱,我听说一块银元是二十六克,有多少算多少,中不中?”大宝不温不火,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你,你……赖皮!”三宝怒不可遏,站起身,指着大哥说,“真没想到啊,大哥呀大哥,你变恁快!我平时除了把你当哥敬,还一向把你当正人君子,尊重你,抬举你,原来你却是个伪君子!”
“给我坐下!”爹威地怒视三宝说,“你坐下慢慢说,理是说明白的,不是吵明白的骂明白的,更不是打明白的!你难道不准你大哥说话吗?”
“爹,我大哥就是不论理了,反正我就是要银元,折钱多少我都不同意!”二宝态度十分强硬。
“二宝,你别逼人太甚,想分银元办不到!”大宝一口回绝,显得有些蛮横。
“嘿嘿,”三宝冷冷一笑,阴阳怪气地说,“大哥呀,我的亲亲的大哥呀,你是不是逼着我翻脸哩?那就别怪我三宝不认你这个大哥啦!”
大宝没吱声,把头埋下去。头越垂越低,越垂越低,嘴巴几乎抵住膝盖。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流出来,滴落在地面。
一阵难熬的沉默。屋内静得能听见院子里的蟋蟀叫,“唧——唧——唧”烦死人了,该死的小东西!
殷老汉站起身,缓步走到西间锅台前,弯腰从柴灰堆里摸出个黑塑料薄膜裹缠的包包,抖抖灰草,用手拍打两下,回到正间,把它放在面前的木桌上。
大宝哭得很专注,似有满腹委屈,没抬头。二宝三宝都睁大眼睛看着爹,不知道老人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心却莫名地希冀发生点什么奇迹。
爹重新坐下。手指着黑包包,神色严峻地说:“二宝三宝呀,你大哥像个大哥样儿,会事,厚道,能吃亏!我看他是怕你俩相互猜疑酿出大祸,才承认是自己挖走银元的,实际上银元在这里面呢。你俩逼鸭子上树,他往哪儿弄银元给你们分啊!”
大宝猛地抬起头,泪水悄然止住,心里咯噔一下,像突然打开一把锈锁。二宝三宝眼看直了,如梦如幻。肚子里却如咽下个苍蝇,很不是滋味。
爹叹口气,把缠在黑包包上的尼龙线解开,“哗啦”一下把银元全倒在木桌上面,环视他们一眼,指着银元说:“兄弟情应该比这东西贵吧!我告诉你们,我根本就没有把银元埋在桂花树下。桂花树下的土是我大前天回来后心情郁闷故意挖着玩的,我没见你们就走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考验你们兄弟三个,看你们如何对待亲情和金钱的,让你们想想怎样做人才正确哩!即使昨天三宝不往桂花树下看,我以后还会让你们看,这银元被挖走了,让你们都表现表现。不过我跟你们说明,这银元只剩下七十五块了,那二十五块送给我闺女和黑蛋女婿做纪念啦。他们待我好,不仅管吃管喝管看病,而且还管零花钱。我要打破农村财产传儿不传女的旧习惯,我想你们不会不同意吧!”爹说罢,把银元按每份二十五块分好,让他们把银元拿走。
大宝看着爹,指指三宝说:“爹,三宝眼下急用钱,我那一份不要了,全给三宝吧……”没等大宝说完,二宝红着脸插话道:“爹,我这一份给三宝顾急也中,你还保管也中,我们没有赡养你,心里很不好受,咋好意思分银元哩!”
三宝心头一阵滚热,眼角潮湿,泪水随之溢出来。他哽咽着说:“大哥……二哥,这银元你们不……不要,我更不能要!我的困难慢慢解决……我的意见让咱爹把银元换成钱,以爹的名义把咱村西小河的桥修好……给咱们留个大的纪念吧!”
殷老汉抬头看看三个儿子,微微一笑说:“我看这样吧,银元我还暂时保管,三宝的意见我考虑考虑……”
这时,三宝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打断了爹的话。他摸出手机,摁了接听键,儿子殷好焦急的声音传过来:“爸,我妈病危,需要马上做手术,医生让你快点儿来急诊室!”
“好,好,我马上就到!”三宝答应一声,急忙跟爹和两个哥哥打招呼,然后转身就往屋外跑。
殷老汉吩咐大宝二宝回家拿钱往医院,帮三宝度过难关。大宝二宝爽快答应,匆匆而走。殷老汉坐着没有动,两眼直直地盯住桌面上的三堆银元:这东西应该怎么处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