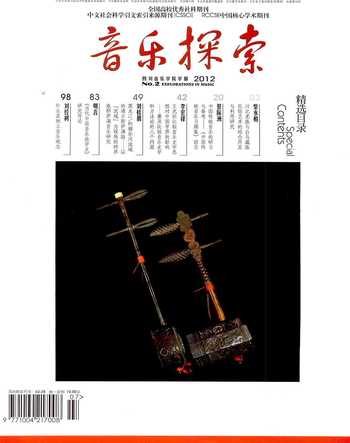她在民歌的海洋流连忘返
罗天全
摘要:方妙英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她在民族音乐学、音乐创作和音乐教学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笔者只能挂一漏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她的楚地民歌研究成果。一、楚宫、楚徵、楚羽体系民歌三声腔研究;二、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研究;三、湖北五句子歌及其变体研究。
关键词:方妙英;楚地民歌;三声腔;哭嫁歌;五句子歌及其变体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方妙英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随后在武汉音乐学院执教逾30年,1984年调入厦门大学筹建并主持音乐系工作。从教50年以来,她在民族音乐学、音乐评论、音乐创作和音乐教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是一位音乐理论功底深厚、音乐创作才能突出、音乐实践经验丰富、音乐教学成就突出的资深音乐家。
1959年,方先生撰写了从事民歌研究的首篇学术论文《江汉平原上的薅草歌》,并于同年6月在《人民音乐》发表。其后,先生便将从事音乐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民歌这片肥沃的田野,并与其结下了难分难解的终身情缘。
尽管方先生对中国民歌的研究是全面的和系统的,但由于其所处地域之限,她在民歌研究中对楚地民歌的研究最为深入、透彻而系统。她在武汉音乐学院执教期间,走遍了湖北省除神农架外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了解楚地山河和楚地民风,对楚地民歌情有独钟。自1959年发表《江汉平原上的薅草歌》一文后,便将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那远古的遗声。
先生撰写了研究楚地民歌的学术论文主要有:《江汉平原上的薅草歌》(《人民音乐》1959年第6期);《绚丽多采的湖北民歌》(《湖北广播》增刊,1980年11月);《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中国音乐》1982年增刊);《楚歌三唱》(《音乐爱好者》1985年第2期);《论鄂西土家族哭嫁歌》(《黄钟》1987年第4期);《论楚徵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民族音乐学论文选》,上海音乐出版社1988年出版);《楚声赶句子音乐结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论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黄钟》1997年第2期);《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1999年4月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等。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方先生的楚地民歌研究成果:一、楚宫、楚徵、楚羽体系民歌三声腔研究;二、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研究;三、湖北五句子歌及其变体研究。
一、楚宫、楚徵、楚羽体系民歌三声腔研究
楚地历史悠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远古长阳人曾经在这里栖息。这里是楚人的家乡,也是巴人的乐土;这里是屈原、昭君的故里,也是土家族生存的家园。先民们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用勤劳的双手开天辟地、斗恶驱邪,创造了属于本时代的美好生活。
楚人诚挚纯真,忠信好义,无畏无惧,乐观向上。
楚声源远流长,灿烂辉煌。
楚地民歌自成一体,别具特色。
先生深谙此道。她将楚地民歌归纳为楚宫、楚徵、楚羽三种体系,并进行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论楚宫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论楚徵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和《论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三篇力作。先生先后在20多年间,足迹遍及江汉大地、荆楚山川,在数以万计的楚歌中,至少对111首民歌作了科学的排队、详尽的考订和仔细的分析,从个性中找出特征,从共性中探求规律,并在文中列出了100首民歌的谱例,进行有说服力的佐证。
“三声腔”在湖北荆楚、鄂中、鄂西地区民间又称“三音歌”,是楚宫、楚徵、楚羽体系民歌音乐思维的核心。
楚宫、楚徵、楚羽体系三声腔是楚地的主要声腔。它们的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变化丰富,个性独特。
“楚宫体系以‘宫、角、徵三声腔为核心,通过‘商、‘羽音的装饰和独立运用,分别形成自己独特的‘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调式,它不同于其它的汉族五声调式。”“楚宫体系音乐发展手法最主要的特征是充分运用各种声腔的色彩性对置交替手法,通过同宫系统平行调式声腔的对置交替,向上、下方五度外宫、属宫和下属宫系统,以及大、小三度外宫系统的声腔进行色彩性的对置、交替来烘托有着接近大调性色彩的‘宫、‘角,‘徵三声腔。”
楚徵体系三声腔为“徵、宫、商”,其骨架以四度音程为基础,在该三声腔中,自然音列的旋律音程由连续四度进行排列而成。其装饰手法多样而复杂,它既可运用正音“羽、角”进行装饰,也可运用偏音“清角、变宫、变徵、闰”进行再装饰。此外,楚徵体系三声腔向上、下方四度音程引伸和扩张,使楚徵体系民歌更具本地区风格。
楚宫体系三声腔和楚徵体系三声腔中由于两者都含有“宫、徵”两音,差异只有一音,因此,在这两种不同体系的声腔中,还可以进行同宫系统和非同宫系统的色彩性对置和交替运用。它们均属单一三声腔体系。
楚羽体系是单一三声腔和双三声腔的复合体系。楚羽体系的单一三声腔以“羽、宫、商”三声腔为核心,运用“角”、“徵”音进行装饰。楚羽体系的双三声腔可有两种类型的嵌接类型,即相同结构的嵌接和不同结构的嵌接。此外,先生还对同一结构内三声腔在声腔上的对置、变音的选择运用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论述。
先生认为,楚声有一定的艺术规律。如楚宫、楚徵、楚羽三种不同体系的民歌音乐思维既有它们独特的个性,又有相通的共性。“楚宫、楚徵、楚羽三个不同体系的民歌音乐思维均源于各自不同的音乐审美意识,它们的旋法、结构、调式、调性以及演唱、帮腔、伴奏等风格都被各自本体的艺术规律所制约,被声腔的框架结构所主宰。每一体系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到历史的、时代的社会习尚和审美情趣的局限。各体系有它自身的长处,也会有不足之处,但绝不存在精巧和粗浅之分。……楚宫、楚徵、楚羽都是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创作才智的艺术结晶,它们各自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与顽强的生命力。”
楚宫、楚徵、楚羽三种体系的民歌在楚文化的长期哺育下,广泛地吸收了其它姊妹艺术的滋养,逐渐发展成深受当地人民喜爱的瑰丽奇葩,在民歌苑中散发出沁人的芳香。
二、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研究
“哭嫁歌”是我国土家族的一种民族习俗,也是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土家族分布在湘鄂川黔边。湖北土家族则多居住在鄂西恩施、五峰、咸丰、长阳等地。土家族聚居区素有歌山花海之美称,其哭嫁歌尤具特色。姑娘出嫁陪唱“十姊妹”,而男家接媳妇要陪唱“十兄弟”。十姊妹和十兄弟合称“姊妹歌”,土家人谓之“哭嫁歌”。先生对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研究多年,于1987年撰写学术论文《论鄂西土家族哭嫁歌》,并在同年由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发表。
土家族有“歌丧哭嫁”的传统习俗,视“哭嫁”为美德,常以是否善哭来权衡姑娘的聪慧才智。哭嫁时间长短不一,短则七天或半月,长达一月。当新娘被亲哥背上花轿离开娘家时,“哭嫁”达到高潮。
先生在文中列举了21首哭嫁歌的谱例进行深入研究,其丰富的资料、翔实的内容、透彻的分析、独到的观点让人莫不信服。她将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的歌腔功能划分为“抒情悲歌”和“抒情放歌”两类,“第一类是以哭代唱,唱中有哭,边哭边编的抒情悲歌;第二种是以唱带哭或只唱不哭的长诗结构式的抒情放歌。”抒情悲歌即“堂外哭嫁歌”,抒情放歌即“歌堂哭嫁歌”。
堂外哭嫁歌是一种抒情悲歌,多在后堂或姑娘房内,由少数人唱。节奏感不强,旋律性稍差,哭多于唱。堂外哭嫁歌的音调取自鄂西土家族音调,如薅草锣鼓、山歌、小调、摇儿歌、灯调等。
歌堂哭嫁歌是一种抒情放歌,它有两种形式,即“陪十姊妹”和“陪十兄弟”。陪十姊妹是一种以集体演唱为主的形式,唱多于哭。陪十兄弟的内容与陪十姊妹相似,有一人独唱、两人对唱或一领众帮等形式。
鄂西土家族哭嫁歌具有古朴而神奇的色彩,散发着沁人肺腑的芳香。在学术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推介下,这块深山中的瑰宝终于走出大山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先生于此,功不可没。
三、湖北五句子歌及其变体研究
先生对湖北民歌中独具特色的“五句子”、“赶句子”、“穿号子”的研究尤为深透。她在这方面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主要有《楚歌三唱》、《楚声赶句子音乐结构》和《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等。
在这三篇论文中,先生举出21首曲谱为例,主要考察并详尽研究“湖北五句子歌”及其变体“湖北赶五句”、“湖北穿五句”等三种形式的湖北民歌。
楚地盛产五句子。五句子多为山歌或秧田歌,其内容多为纯真、纯净、纯善的情歌,“喊起五句子,隔山隔岭也传情。”全曲因以五句唱词组成而得名。民谚曰:“亲嘴要亲第一口,五句子要听最末声。”方先生认为,“第五句往往是精彩的点题,常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特别动人。”它是艺术情趣之所在、作品意境之升华,故有“五句山歌五句单,四句容易五句难”之说。五句子的歌词多为七言,有独唱、齐唱和对唱。五句子的结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由两个上下句组成,最后结束句点出主题。另一种是五个句子有机联系在一起,共同塑造一个完整的音乐形象,最后一句也是最精彩的压轴,令人神往,回味无穷。五句子的曲体结构有平腔五句子和高腔五句子之分。平腔五句子还有“规整句式”和“不规整句式”两种形态。
“湖北赶五句”是五句子的变体之一。“赶句子”有“二句赶”、“三句赶”、“四句赶”和“三、四句赶”四种形态。其中,“三句赶”和“四句赶”最为常见,也最具楚声特色,是“湖北赶五句”的主要形态。赶句子是一种特殊的非方整性结构,它既有词格结构对称、音乐结构不对称的形式,也有词格结构和音乐结构均不对称的形式。
“穿号子”是五句子的又一变体。方先生认为,穿号子是以五句子为基础,运用民间传统的对歌方式,进行穿插、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独特曲体。整首歌曲围绕一个中心主题,以副歌(梗子)穿插正歌(叶子),从而形成一种丝丝入扣的艺术构思。穿号子因地域不同而又有穿五句、穿句子、穿歌子、穿号头等称谓。
穿号子在现场演唱时可一领一穿、二领二穿、一领众穿,也可以男女分别领穿。其词体可分为“号儿词”与“歌儿词”两部份。其中,号儿词在民间被称为“梗子”,相当于引歌或副歌部分;歌儿词被称为“叶子”,相当于正歌或主歌部分。穿号子的结构类型有“单号儿结构”和“双号儿结构”两种。
号儿词大致有三种模式,即:传统基本模式;在五言四句中插入衬词或衬句的模式;在五言四句中插入衬词、虚词说白,或对白的模式。
单号儿的穿插方式与结构形态可分为五种,即:“亮号儿全梗分句正穿”、“亮号儿全梗分句变化正穿”、“亮号儿全梗整穿”、“亮号儿半梗整穿”、“无号头直穿”。先生对该变化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列谱为证。这比她于早年在《楚歌三唱》中提出的“亮号儿正穿”、“亮号儿倒穿”和“直接亮号儿”三种形态更为系统、更加详尽、也更有说服力。
双号儿结构比较少见,穿插技巧比较复杂,接唱帮腔难度较大。方先生在文中以鄂西南鹤峰土家族双号儿《白布包的底》的曲谱为例进行分析,“双号儿是在穿五句单号儿中间再穿一个五句子。即前面的单号儿在进行到第二句正词后直接再穿插一首五句子歌,然后再接上前面单号儿的第三句正词。换言之,也就是在单穿五句中再套穿一个五句子形成双号儿。后面的第二首五句子必须与前面所亮出的号儿词和歌词的中心思想紧紧扣住,使主题更为深化,更具艺术性,成为整首双号儿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对湖北五句子及其变体的研究情有独钟。1999年4月,她以70岁高龄参加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新作《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远不说她在1964年出版的《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中即对五句子及其变体有过详细研究,就从1985年发表《楚歌三唱》算起,也已有15年之久。其间,先生的研究从未停息,并于1988年发表了学术论文《楚声赶句子音乐结构》。从1999年发表的《华夏楚声穿号子结构艺术》中可以看到,先生对五句子的研究厚积薄发,并臻于完善。
两千多年前,楚国诗人屈原驾轻就熟的骚体就是一种非方整性结构的诗歌,与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诗经》相比较迥然有别。五句子歌及其变体主要流行于鄂西一带,这里正是屈原时代的楚国故地,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真正的远古遗声?!
先生认为,“‘楚声是灿烂楚文化中的一颗瑰宝。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形成具有荆楚人民所独有的创作构思与艺术风格。它从词格规律、声腔运用、调式转换,结构变化以及演唱方式等方面都集中地展示了这一地区人民的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和音乐思维;从而使它与我国其他地区的民歌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与艺术造诣。另一方面伴随着历史的前进和长时期的对外音乐文化交流又不断地注入了新的因素,赋予新的色彩,使楚声具有更加旺盛的艺术生命力。”这真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道出了楚地民歌的艺术特点之真谛。
先生长期从事民歌研究和民歌教学,但从不满足于停留在字里行间、谱面分析或视谱演唱。我和先生有缘,曾有幸听她授课,那绝对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艺术享受!她在课堂上能随时背唱大量的民歌,就好像入乡随俗似的唱啥像啥,从东到西、纵南横北,既没有地域和民族的限制,也没有风格和体裁的约束,加上自己一手流畅的钢琴伴奏,顿时让人听到歌中蕴含的乡音和乡情,感受到无尽的乡思和乡趣。
先生丰富的实践给她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她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自己辛勤探索、逐渐积累起来的,是用自己毕生心血浇灌的果实和结晶,绝无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甚至信口开河之嫌。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严谨的、严肃的,具有独立的学术观点和独到的学术见解,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被学术界广泛地采纳和沿用。
在我的眼中,先生是一位民歌研究的奇才和女杰。几十年来,她在民歌的天地熏染浸润,她在民歌的田野辛勤耕耘,她在民歌的海洋流连忘返,她已然把握了民歌中那迷人的神韵!
责任编辑:陈达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