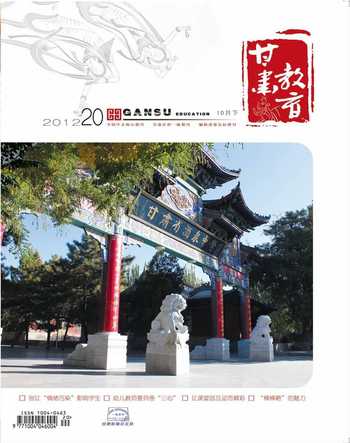古代诗坛鸳鸯鸟秦嘉和徐淑
封立
在通渭县榜罗镇附近的秦家坪,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合葬墓,里面安睡的是一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其少见,在甘肃古代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诗人夫妻——秦嘉和徐淑。
秦嘉和徐淑都是东汉汉阳郡平襄县(今甘肃通渭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活在东汉桓帝(147—167年)前后。据《通渭县志》记载:“秦嘉,字士会,桓帝时为郡吏,岁终为郡上计簿使赴洛阳,除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徐淑,秦嘉妻,天性聪明,有才识,长于诗文……”这对才子才女婚后感情甚笃,美满幸福,不忍分离,秦嘉到郡治任职时夫妻携手同往,然而徐淑不幸得病,为了不影响丈夫公务,不辞而别回家乡疗养。两地分居,山重水隔,夫妻二人只能书信传情,诗文寄意。秦嘉客死他乡后,徐淑肝肠寸断,悲痛欲绝,亲往扶柩以归葬。当兄弟逼她改嫁时,她毁形不嫁,哀痛伤生,抑郁而终。秦嘉和徐淑不仅是珠联璧合、情意相投的恩爱夫妻,而且都是富有才情、心存灵犀的多情诗人,他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因为他们的诗文赠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相传秦嘉和徐淑的诗文作品有二百多首(篇),但流传下来的不多,仅存诗文12首(篇),除徐淑《为誓书与兄弟》外,都是夫妇间往来叙情之作。
秦嘉率性自然,是一个清醇的文学之士,他虽身为上计掾、黄门郎,却不沉溺功名,不看重浮华,关注的是自己的情感世界。从他的《与妻书》“不能养志,当给郡使……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惨少乐”中可以看出,秦嘉的理想、志趣根本不在风尘利禄之中。他对能娶徐淑为妻,觉得非常幸运,在描写婚礼的《述婚诗》中,“君子将事,威仪孔闲。猗兮容兮,穆美其言……神启其吉,果获好逑。适我之愿,受天之休!”真情真性,情致博雅,字里行间洋溢的都是喜悦和幸福,毫不掩饰对妻子的赞美、钟爱之情,以及自己珍惜爱情,希望天长地久、永远相爱的愿望。这在以含蓄、自谦的中国古代诗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秦嘉的诗歌,一反汉代铺张恣肆的风气,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从个人情感落笔,让诗歌文质兼顾,婉转动情,开婉约诗之先河,不仅语言朴实,情真意厚,缠绵凄怆,而且在语言的通俗化、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生活化方面,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赠妇诗》三首,其一写即将赴京之际遣车迎妇,妻子因病不能前来,面对“空往复空返”的车子,惆怅不已,“临食不能饭,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其二从自身的“少小罹茕独”的身世说起,写夫妻离多聚少,天各一方的思念之情,“把人间平凡的夫妇之情,用平易和缓的笔调叙出”。其三写启程赴京时以礼物赠遗徐淑,遥寄款诚。“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一句承前启后,把诗人的情绪和赠物的思绪相牵连,让诗歌的叙事和抒情合二为一,体己中见伤感,豁达中含辛酸,充满着感恩和温情,尤其对妻子的爱,总觉有一种不对称的亏欠,表现在诗中为“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这是标准的中国式爱情和古典型的夫妻所特有的心理流露。
徐淑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深厚文学功底的女性,一生为情而活,为情坚守,为情发光。她的作品虽多用骈文写成,但立意高远,气韵飞动,至情至理,酣畅淋漓,尤其是书信体散文,文约义丰,语言朴实,感情充沛,用典工丽,一扫汉赋堆砌铺陈的陋习,事事细节,处处生活,堪称书信中的上乘之作。《答夫书》婉转动人,一叠三叹,文辞华美,希望丈夫以孔子不耻“执鞭”为榜样,积极上进,建功立业。还引用《诗经》中“谁为宋远,企予望之”的句子,表明自己与丈夫虽然分隔两地,心中无时不在思念的纯真情感。同时徐淑也是一个大胆直言的女性,敢于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又报嘉书》中她对秦嘉“敕以芳香馥身,寓以明镜鉴形”的“关切”进行了直言反驳,以为“此言过矣,未获我心也”,并以“素琴之作,当须君归;明镜之鉴,当待君还”为誓言,表达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诚不二。尤其是当丈夫亡故,兄弟把她像财物一样再许他人时,她内心油然生发人的尊严、自由和对爱情的权利,促使她做了最激烈的反抗。面对兄弟的威逼利诱,她愤怒地作《为誓书与兄弟》,驳斥他们的丑恶行径,表明自己“杀身成义,死而后已”的决心,展露出女性人格美的光华。徐淑的诗作虽仅存《答夫诗》一首,但形式独特,具有五言骚体的典型特征,是“四言诗体与五言诗体的集合体、结晶体,是五言诗体发展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活标本、活化石”。
秦嘉和徐淑以诗文赠答,抒情寄意,开创了中国赠答诗体和婉约诗体的先河,是中国古代文苑中的一朵奇葩,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的说法,是最中肯和公正的评价。
编辑:马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