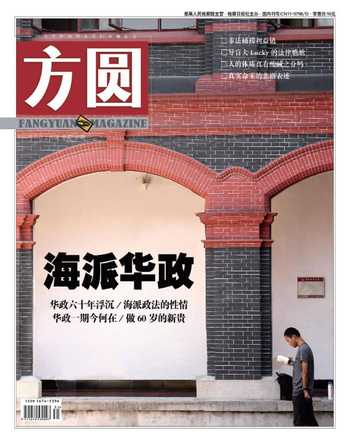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徐则臣
【√】“和平”一词有了确切的含义。有答案了,我给朋友发了条短信:游走街巷,卖葫芦丝
汉字很奇怪,你问天下是否太平时,我觉得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你若问世界是否和平,我觉得它离我很远;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围在你身边而世界必定远隔重洋。
基于对汉字的褊狭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觉,在谈论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动荡和威胁时,我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为我的生活目前比较安稳;而千里万里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经受考验,反动和杀戮每天进行。谈论后者,我常常觉得“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知,那里打起来了,那里也打起来了,那里还要继续打下去;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打”字,于我大多时候只是一条讯息,看完就完了。
这两年,我祖父总把“世界和平”挂在嘴上,动辄跟我谈国际形势,提醒我哪里“不安全”,哪里又“紧张”了。祖父久居乡野,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南京,离家一千里地。现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动范围以家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以内,到镇为止,因为没什么事需要到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去办。祖父每天看电视新闻,世界上哪个角落稍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因为我在北京,他连北京的天气状况也能报得出来。
这几年出国比较多,出门前我会跟祖父告个别。他就在电话里说,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一定要去吗?前天又有恐怖分子劫机,飞机能不能不坐?欧洲经济危机很严重,社会不太稳定,晚上别一个人往外跑。如此等等。我就宽慰祖父,我只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谈文学,又不是打仗。
祖父教书之前被抓过壮丁,让他拿枪去杀人。那时候国共内战,日本鬼子也骑着高头大马在我家乡乱转,因为认得几个字,祖父被委以一个小头头的职务。可他杀鸡都下不了手,哪是拿枪的人,扔了家伙跑庄稼地里躲起来了,天黑前不敢从高粱秸捆里露出头。这事后来成了祖父的罪证之一,“文革”时被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和游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一头从二楼上扎下来。还好命没丢掉。此后他被从学校里揪出来,成了猪倌,每天和几十头猪打交道。
七十岁以后,祖父很少再提过去,他开始关注“世界”。孙子辈的已经开始在外面跑,出门念大学,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出国;他希望能为我们这一代人想象出一个安稳、宁和的环境——只能是想象,因为世界每天动荡,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劲儿。尽管他不提过去,但过去肯定一直都在,那个时间里有他对“和平”最切身的体认。也因为这个体认,他会本能地将风吹草动的当下“世界”与他的过去迅速建立起联系,世界于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惧与杀戮之事都让他警醒和惊惧。他都要在出门前提醒我。
若干年前,父亲跟我说,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惊,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祖父碰过二胡,一次都没有。我问祖父,祖父说,忘了,不会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如果从战场归来,你最想干的一个职业是什么?我把自己硬塞进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里。仔细想了,还是想不出。回家时坐车横穿北京,看见车窗外一个卖葫芦丝的男人在路边走,脖子和肩膀上挂满自制的葫芦丝、笛子和箫。他走得缓慢,低头吹着《月光下的凤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调谦卑,而曲音欣悦祥和,给我一种劫后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似乎想象里的视野也开阔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和平”一词有了确切的含义。有答案了,我给朋友发了条短信:游走街巷,卖葫芦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