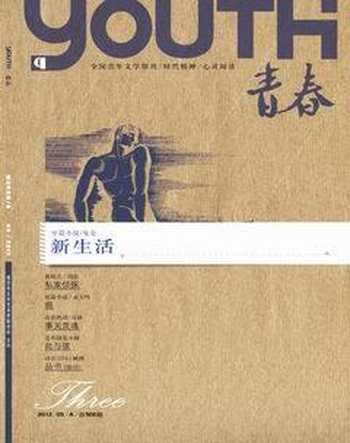此与彼
在途中
我正在叙述的风景或经历与记忆似乎无甚关联,但它们确实是从车窗外向我涌现、延伸,并从一个冬天进入到另一个冬天。它们在不同的维度上与车厢相对:平行或者交叉。它们在缄默、呼吸、枯干、流淌……事实上,你无法看清它们:哪些离你远,哪些离你近,哪些已经或正在消逝,哪些消逝的至今尚未到达。倘若情形不是这样,那么现在,它们在车窗那边同样能看见我。
我正在离开什么,并且打了一个喷嚏,冬天因此得到一次证实。小小的铁皮盒一旦安上四个轱辘,它们就能跑,就能带着我兜圈子:由A至B,然后像倒带那样由B至A。一个空间在另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必定像抽屉或风箱那样来回运动。只是我很久没出过门,衣服穿得少了点。但思想似乎并不怕冷,它进入冬天,而冬天本身就类似一种抽象思维:冷峻,坚硬,水落石出。
我必须去B城,为一件很功利的事。但是上车后,我对去B城突然感到茫然、虚无,甚至对自己也感到陌生,周围的一切随之变得像跑光的底片一样无意义。这种情形类似《旧约》时代,上帝对犹太先祖说:“你必须去耶路撒冷,你不能去耶路撒冷。”问题是,我已坐在中巴车里,并且正在叙述它。
冬天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麦当劳化的不断膨胀的世界,雪下得肯定越来越少。但云层好像比先前更低一些,更暗一些。田野里有人,有草堆,也有麻雀,还有石头一样的白色之物。显然,野鸽子在飞。很多年我都没见过它了。我想起,圣灵在《新约》中呈现为一只鸽子。那么,野鸽子似乎应介于圣灵与性灵之间,因为它多了一些大地的野性和土味。
坐在我左前方的司机一直在调整速度。车门旁那个胖女人是收费的,她正与乘客——一个很瘦的家伙——为几角钱脸红脖子粗地讨价还价。细节着实很生动,但对它进行写实主义描绘已无必要。同行的C告诉我,他小时候在这一带呆过,那时他的外婆家有好多好吃的,还有一个水竹编的蝈蝈笼。有一年发大水,他差一点掉到水凼里淹死。我也向他唠叨点孩提时代的事儿。可是回忆只能使我接近叙述和叙述中的风景,而不是过去的那个我。
绵延不已的树林后面是同样绵延不尽的江水。那伪装成灰绿色的皱巴巴的表面随意晾挂在没有叶子的枝桠间,如同婴儿的尿布,几乎没有一点儿光。而在江水后面,那淡入淡出的依旧是树林,是分不清此岸还是彼岸的防护林。显然,树林反向而驰的速度比江水更快一些。有的时候,前边突然出现一大片被忽略的、缺口似的空旷,无遮无拦,仿佛是大水的入口处,没有鸟影,也没有草迹。车身顿时猛烈摇晃了一下。
不用说,在这个忽地转亮的瞬间,我经历了它们以及想象中大片大片的芦苇。车子好像停了几次,下去几个人,也上来几个人,都照例要摇晃一下,然后扶住什么。车厢内的人也并不见少。尘迹和雨痕沾满玻璃,乍一看去,像是谁随手胡涂乱抹留下的。
堵车还是发生了。一个长蛇阵足足被阻挡了一个小时,并且每个乘客还掏了一元钱。在经过事发地点时,我看见许多人,其中一个老头在大声责问,一个老妇在路边呼天喊地:他的儿子刚从南方打工回来,晚上竟被车撞死,可肇事车早已逃之夭夭。此地段介于两县交界,因而两地互相推诿。那老头看上去有点像悲伤的约伯。约伯尽管“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兢”,但他还是比一般圣徒多了怀疑反问的精神。他责问神:“恶人的灯何尝熄灭?……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他所作的,有谁报应他呢?”
换言之,上帝一思考,人们是否也会发笑?
后面有人接连打了几个喷嚏以及哈欠,可是依然没有看见结论。刚刚逝去的景物好像又在前方出现,只是夹杂着几只不知从哪儿来的山羊,白的和褐的,在形同虚设的大堤上啃草——但草色与土色几乎没有区别。
我昏昏欲睡。C则横躺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一声不吭,谁知道他做着怎样的好梦。爱伦·坡说,当他想知道一个人当时的思想时,他就根据这个人的脸画出其轮廓。而车厢内的光线越来越微暗、昏黄,他脸部的轮廓大部分沉浸在斑驳模糊的阴影中。然而,窗玻璃仍如牙齿似地格格打颤,不一会儿,它颤开一道细缝,刀片样的风猛地刮过我的下巴。窗玻璃随即被后面的手再次关紧。看来,越是通明无碍的地方,越是布满看不见的缝隙。
我知道我不能想得太多。如果想得太多,那么它会像下面的轮胎随时都可能爆掉。可是我感到一股莫名的回风,吹得后脑勺生疼,仿佛一种更大的思维的漩涡让我置身其中。它们看不清我的脸、眼睛以及正在伤感的鼻子。这就是久违的冬天吗?舍斯托夫说“人应该怎样同上帝争吵?”而弗罗斯特却说:“同世界进行一次情人的争吵!”那么我是喜欢上帝的世界,还是喜欢情人的世界?
在没到达目的地时,车厢内几乎已空空荡荡。我和C,还有几个脸皮紧绷的乘客,都一律成了剩余者。颠簸的车身使我想起乡下的簸箕来。现在轮到它们不停地旋转、簸扬:光阴和痴梦像稗谷一样飞逝,只剩下一片惘然……
下雨了,雨点小得无法辨别,只见前方的刮雨器在左右划弧。柏油路已黑得有点闪闪发光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差点使C从座位上摔下来。因此我不得不暂时停止叙述。不过雨意仍在持续,我的头发被它弄得有点潮湿了。
四月
四月的某一天,R君打电话约我去石塘湖。于是骑自行车至开发区,转乘3路小中巴。风挺大,一波一波地从车窗口猛烈地灌进来。坐在我旁边的小女孩将车窗拉上,我将前面一扇也拉上,但又被前座的妇女拉开,她说她晕车。这样小女孩就低下头避风,而我的眼睛吹得都快睁不开了。
春天的行进速度在开阔的郊野呈现出节奏感。油菜花基本谢了,密密地结满了青虫般的细荚儿;桃花也看不到了,她刚怀上小青桃儿;而白豌豆花和紫云英开得好不热烈,丝绒一样的土黄色丸花蜂嗡嗡地飞着;蒲公英已撑起了绒毛伞,等待着与谁远走高飞。冬天遗弃的所有的枯寂旷野,现在全被茂密的草们占领了。看上去一切都是野草,包括风中俯仰的大麦和小麦。在低黯的时间深处,除了草你还能看见什么?草是最让我兴奋和痛快的。但嫩草因落上一层浓浓的露水而泛着银灰,在朦胧的水汽还没有散尽的土坡上,它们还透出幽暗的蓼蓝色。
不一会儿,石塘湖打埋伏似的从车的右前方闪了出来。与水接缘的一刹那,你感到这一路揉搓着脸的风便来自那湖水深处。空间的秘密就是这样,你只能在里面翻动它的页码。远远看去,石塘湖的狭长水面就像一条宽阔的河流,波平如镜,而大龙山脉如水墨画悬于其左岸,墨赭交错,气韵浑成。
到达石塘嘴站,我和R君就下了车。远远看见水上游乐场上空飘浮着不少风筝,场内也装饰着各色各样的风筝。原来是潍坊的一个风筝展。风筝起源于中国,据说春秋时鲁班仿照飞鸟制作了第一个风筝,叫做纸鸢。进去后,我们凭票摸奖,R君摸到一个黄色乒乓球,得到一个蝶状风筝。而我手气不好,只摸到一个白的。阳光的确很媚人,暖融融的。湖上的游艇飞速行驶着,有时转着圈儿激起不小的水花。R君开玩笑说,这儿适合带一个情人来度假。我摆弄着他“摸”来的风筝说:就像这蝴蝶风筝,可以放飞得很高。我注意到,有个中年人放风筝的动作很熟巧。那是复线风筝,一对儿,像海上的军舰鸟忽上忽下,灵动飘逸,不时发出“格棱格棱”的清脆响声。R君弄了半天也没有将蝴蝶升起来。我过去帮他摆弄,也没有成功。
这时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声,那是附近飞机场上的“银燕”正在起飞。当它掠过风筝的上空时,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好像达达主义那不可思议的意象拼盘。飞行员大约也能看见下面游曳着彩鱼般的风筝,但他不可能听见风筝“格棱格棱”的响声。
有个小伙子在放鲤鱼风筝。我走到他旁边看他摇着线盘。然后我借机把他的摇盘拿过来,玩了一下,感觉线那头的拽力还真蛮大的。他指着那个中年人说,这个潍坊人放风筝几十年了,技术了不得。那个中年人正好过来了,风筝像他家养的一般尾随着他。我跟他随便聊起来。
他说这儿的风不行,风被大龙山挡住了,下面的风向不稳定。这时他的双鱼风筝慢慢落了下来。他说,这种风筝落地时弄不好会碰伤人。我感到惊讶不已:这么轻飘飘的东西,能有这么大的冲剌力?R君在那边叫我,他摸来的那个风筝放起来了。但那蝶太小了,丑小鸭似的,看上去太一般了。接下来,我只见潍坊人的口型在变化,巨大的钢铁轰鸣声将他的声音吞没了(类似磁带上的声音被彻底洗掉了,这就是说他的声带成了空白带子)。突然丧失嗓音令他措手不及,接下来的是沮丧和惶恐。他抬头狠狠瞪了一眼那掠过头顶的“银燕”。我也跟着狠狠瞪了它一眼。它低得似乎跟那飞得最高的蜈蚣风筝擦翅而过(为什么非要注意它?是因为这个会飞的钢铁家伙在闪闪发光么?)。一种极不理解的、困惑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
他说,“最…最…厉害的…风筝是把…人…带到空中去。”他边说边望着天上。我问他可曾见过?他说他亲眼见过一个人被突袭的强风带到空中。“那…那…个风筝…约有…四十平米…大小。”他又抱怨地望了望天上,“在它缓慢下降时,那倒霉的家伙因失误线没抓牢,结果从二楼高的空中掉下来,幸好下面是松软的盐碱地,摔了个粉碎性骨折,捡了一条命。”那亮家伙早飞走了,但他却尚未从轰鸣中恢复过来。这时,一阵清淡的湖泥味从波面上吹过来,几只小灰雀儿落在浅岸处,不时啄着湿泥里的草虫。
树林重新发出香气来
翱翔的云雀随身
举起了天空
天空对我们的肩膀有点重
这是里尔克《写于一个四月》中的句子。但这儿似乎没有发出香气的树林,而肩膀上的天空让我感到越来越重,风筝也无法减轻它。当然,这是另一个四月,不是一九○○年里尔克的四月。
离开石塘湖时,正午的阳光变得强烈了,而风力却变小了,柔柔的——那真叫“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了(忽想起李叔同年轻时所作的一首歌词)。我便是那“春人”么?回头再看湖边那一溜彩旗,它们无精打采地抖着,似乎并不认我为“春人”。但它们是我重新插好的——刚才有一面红的和一面绿的,被风刮倒了。在我靠近它们时,风把那一团鲜艳欲滴的柔滑吹拂到(准确地说是泼到)我的脸上。那一刻我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至少我有二十多年没这么近地靠近它们了。广场上那一片绸质的飘抖声和红欲透胸的亮丽,还有那银燕的轰鸣声,曾是我少年时代所耳濡目染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二十余年来,两手空空的我仅仅走在一条逃避它、远离它的草径上。
杜拉斯写一个孩子放中国风筝的场景,给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有风的黄昏。别的孩子都在沙滩上打球玩,放风筝的孩子却一动不动。后来她发现,这个孩子“两腿瘫痪,瘦得像细木棍似的……。别的小孩都已经走了。只有那个孩子还在那地方玩他的那个风筝。”她为此感到焦虑不安。“天黑之前,肯定会有人跑去把孩子带回来。天空上飘扬的风筝指明他所在的地点,那是不会错的。”(《物质生活》)
这场景简直无法言说。然而,不经意间却被孩子和他的风筝说出了。
中午在R君的同事苏某处吃饭。他在桥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家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我感到纳闷,这条小小的河何以叫做六零六河?我从来没听说过以数字命名河的。后来向主人打听才弄清:这儿原本没有河,六十年代修筑飞机场时部队挖的,因为战备隐蔽的需要,河的名字也以部队的番号命名。但现在它的确像一条河了,像模像样地潺潺流向石塘湖了。我在浓荫密布的河岸徜徉了一会儿,感到几分惬意(飞行员们必定在午睡,谁知道他会不会把蜈蚣风筝梦成蜈蚣?)河上相隔不远有两座桥,新的和旧的,刻着同一个河的名字:“六零六桥”。因此我也记下了它们。
无弹奏轰鸣
尽管我不止一次地进入柴可夫斯基和贝多芬的钢琴旋律,但进入乐曲之王的强大载体——钢琴那巨大而精巧、但被拆散开来的物质结构时,我还是被它强烈的轰鸣声搞得晕头转向。它像一匹烈马被分割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被固定在专门的车间制造,各种零件的加工由不同流水线上的技术人员来操作。事实上,钢琴的构件在这儿不知被放大了多少倍,一个“马腿”或“马屁股”就要占据一个巨大的厂房。
此刻,我就穿梭在北方某钢琴厂的一个车间里。听觉告诉我,能迸发出莫扎特天堂般乐曲的物质性钢琴,它的源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噪声,钢琴似乎正是由这形形色色的被刨光的噪声零件组装起来的。我首先感到的不是自身的渺小,而是一种被沉默状态。“你不沉默,我强迫你沉默。”一种类似胶布那样的透明之物封存了我。我甚至感觉不到心跳在何处。但我可以开口说话。我试图喊流水线那边的女儿时,结果一张口,声音就仿佛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
时间呆久了,我感到我的存在也被拆卸成一堆声音的零件,比细小的簧片还小,简直是一堆无用的、蜷曲成团的金属刨丝。它跳荡着,快要飞到空中去,与那声音的无用的碎片缠裹在一起。我第一次经历了被声音剥夺后惟余空壳的感觉,类似于掏空后的红色蟹壳被丢弃在餐桌上。
但冼星海塑像就站立在厂房前的寒风中,是他而不是我能更久地站在这儿,日夜倾听着这混杂的噪声的碎片。
当然,我随时可以逃离这儿,或者躲到外面抽一根烟,可我没有。也许我要体验的正是这种感觉。坚韧的物质结构在震响,在整合,一只声音的巨兽在显示它无所不在的锃亮和强悍。
当作曲家的脑海中游弋着无数音符的小蝌蚪时,这儿也在孕育着、堆叠着、打磨着各种声音的零件。这是两个平行存在的看似毫无关联的存在事实。人们一般认为巴赫的赋格曲《十二平均律》极为精确,我发现这儿的每个零件也同样精微到忽米。你不能不承认,在这一点上,物质的精密结构正在为形而上的飘扬提供了良好的基点。
在车间到车间的间隙,我感到北京年初的寒风那有力的击键,敲击着槐树和白杨树那枯掉的和没枯掉的部分。我稍稍停顿了一下。我的砂眼在风中又流泪了。北京的风和风中的砂粒哦,在巨大的厂房之间辗转并呼啸着刮过。
最后,我们一行人来到调试车间,仿佛进入了高潮。这儿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因为至少有几十架揭开琴盖的钢琴同时在接受检测,而每一架钢琴上又有几十个小钢槌在连续敲打金黄色的琴弦。当然,若听一架钢琴调试,我想它敲击出的声音是十分清刚有力的。问题是,那么多的钢琴同时各弹各地机械反复,简直是不断切削着一堆堆声音的金属刨丝。只不过有一些银白的碎屑,掉在我的身上就哑掉了。
这儿所有震荡着的钢琴都处于“无弹奏”状态。调试师们在其间走来走去。所有的钢琴上都没有那双优雅的、白皙的手。为什么在这儿我感到噪声中的“无弹奏”,而在其他地方想都没想过?我想此刻不是我,而是我的思维被吸附到肯定它同时又否定它的漩涡之中。这种在内部对抗着的强大力场,比它表面的轰鸣更令我震动不已。
因此我目击了这样一个潜在的事实:它们正被一双无形之手摆弄着,敲击着。也可以说,它们此刻正是被“无人”弹奏着。“无人”也是一种人。他可能是无数的、集合的人,也可能是空无所有的人。那么我时常受到的窥视和挤压,肯定有一部分与这个“无人”相关。
“无人”你干得多棒呵!你到底想把我怎样?
它们正处于被缺席状态。被缺席,意味着一种灵魂、一种可能尚未出现。后来我想到,当我被沉默时,我周围的琴槌舌条般地热烈卷动着。是谁让我无法沉默,同时又无法言说这苦痛?言说,仿佛是在一个时代“小商贩般的正常智量之上,添加了一个过重的阑尾”。
无庸讳言,我喜欢那巨大而明亮的三角钢琴。在我的感觉中,它一直处在午夜的黑暗大厅,静静地等待某个人来弹奏它。它其实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急流暂时凝固在那儿。当然肯定会有一个人来溶化它,激扬它。不管它蒙上了多少灰尘,冻结了多久,都会有一个人带着他生命的全部热度向它走来。
他要为这黑暗空旷的大厅献上一支曲子。
而这,正与写作者的命运和境遇庶几相似:他在黑暗中无声地说话。因此当下我关切的是,在写作本文时,我是否也会处在一种“无写作”状态?我的手是否只是庞大而空虚的“无人”的一个小指头?
红·绿·白
我一直试图搞清楚,古今艺术家何以对墙上的斑点情有独钟?比如沃尔夫就有一篇意识流小说叫做《墙上的斑点》,而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曾对学生说,“要是你们注意地看着旧墙壁上的脏东西或某些碧玉的五彩缤纷的色彩,就有可能在那里面看到各种各样景色的创造和再现”。真够神奇的哦。看来,这种观察方法可以成为一种传统了。
我不禁想起自己住的红房子来。那陈旧而斑驳的石灰墙上,形状不一的奇异的雨渍和色斑随处可见,勾人浮想联翩,包你想什么像什么。学画画的就该到这儿来观摩。不过,最近它被拆掉了。据隔壁老校长讲,七十年代建这所房子时,他带着师生从水塘里将木料捞上来扛到这里。房子做得极简陋,空心墙,木结构,起初是做学生宿舍用的,后经多次修修补补,便成了当时不算最赖的教工配套房。不妨说,它属于一种难得的夏暖冬凉型,屋檐边那几块斜倾欲坠的大灰瓦,随时都在考验你从容出入的雅量;那昏暗而陡的楼道,顶层天花已剥落数处,裸露出瘦骨伶仃的“鸡肋”来;其上唯一的灯泡尘网密布,它似乎看破红尘——因阅尽蜗居者脸色而黯然无光。
至于下起大雨,它还兼具古代滴漏的功能。它虽屡经翻瓦,浇柏油,可漏雨的秉性坚定不移,且呈一种流动状态:这儿检修好了,那边又漏;墙与顶的夹角洇着发黄的斑迹,天花坠而不塌,只是时辰未到。那浸蚀于天花中央的水渍,望久了倒是一幅变幻着的野兽派画作:一只污黄的怪物或大或小,那霉变部分生成它的毛发,如《神异经》里的讹兽,“其状若菟,人面能言,言东而西,言善而恶,其肉美,食之言不真矣。”
这座旧楼究竟算不算“危房”,完全在头头们嘴皮怎么说:向上要新建项目时,它是摇摇欲坠的危房;房改时,它合乎红头文件的配套房标准,租金与新建的单元房一样照收。但在一般场合,它习惯上被称作“红楼”。因此,居者的梦便可以美其名曰“红楼梦”。
在周围后起的建筑之间,它慢慢趴下去,皱缩着,呈现出被时光的炆火烤熟的河蟹色。有意味的是,我也是河蟹一样的寄居者:在蟹壳般的空心墙内生息,蜗行,进进出出。
我记起冬天走廊里持续到下午五点钟的阳光,暖融融的,无遮无拦,被条被晒出一股阳光的好味道,一直漫延到睡梦中。尽管周遭一片枯黄、萧瑟,但楼下栀子树绿得沁人,充溢着那清莹且白的柔细之力。
红楼终于被拆掉了。它先是整个地被搬空了,从来没有这么空地空过。只剩下斑驳的奇异的墙壁。还有,寄居者的痕迹一点也没减少。在我最后一个搬走时,楼下院子里的藤网上还挂着无主的葡萄,还有几柄绿叶在风中颤摇,而一棵臭椿上则吊着隔年的老丝瓜儿。
当“废墟”真的出现时,红楼已成为一个词。成垛的红砖、门楣和窗框、斑驳的内壁,以及锈铁管、屋椽、烂铝线、牛毛毡、破瓷、一只拖鞋,与满目狠藉的碎砖瓦屑混成一片。但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一个寄居者的重临而变得迷离起来。秋雨无法在子虚乌有的瓦檐逗留、滴嗒。它匆匆穿过这一角“空”出来的空间,淋湿了他无法返回的“原处”。
红楼被拆掉后,我曾去找寻楼下那株栀子树。尽管我知道它肯定被砍掉,或者被挖走了,但我还是想来看看。这棵栀子树根深叶茂,比一个人还要高,很有点卓然不凡的丰韵。每年初夏时节溢出淡淡的清香,与这座红楼日益衰败下去的气息混和在一起。
显然,它无法改变这种衰败,这种陈腐,却只能反抗着,抵消着,以清莹且白的柔细之力。它已数易其主。乔迁者大约都动过移走它的念头,但最终都不免“怜香惜玉”起来。现在,在它所在的地方,空空如也,只遗下一个断根残须的深坑。
现在我终于有点明白达·芬奇没说完的话了,他说:“要是你们注意地看着旧墙壁上的脏东西或某些碧玉的五彩缤纷的色彩,就有可能在那里面看到各种各样景色的创造和再现,看到混乱的争吵和种种精神姿态,看到稀奇古怪的人物形象和变幻莫测的服装以及大量的其他事物。因为精神在这混乱之中受到激励并在其中发现了不少新创造。”呀,实在妙极了。
浮现
年底的雾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我起得并不算早,雾像对面人家的花猫已悄悄窜上这边院墙。抬头一看,香樟树被弄得一头雾水。拉垃圾的板车在雾中变得有点诡秘,仿佛装满了珠宝,急匆匆的,让人猜疑。这是冬天的雾,压得低声低气,又清冷,又干燥。
雾还是让我想起多余的没有散掉的烟尘,它们积压在那儿,到年底必须做一次小结。现在我目击了这次清理的过程,它们好像还带有硫磺的味道。
老实说,近几年我对下雨很发怵,因为我挺厌烦雨搭子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不知从哪儿钻出来那么多雨搭子,像雨的放大器,布满了我的住宅楼,一个劲地聒噪不已。我经常套上雨披去上班,出门时却发现雨早停了,而雨搭子依然像老太婆那样喋喋不休!
雾看来还是挺可爱的,无声无息,迈着猫步。仅仅一会儿,世界便变得比我想像得要轻。是孩子们上学的时间了。一个绿孩子在我前面晃动着,蓝书包在他屁股上一颠一颠,这与湖边老太婆们的红色扇舞形成对照。在雾中,我经过的那些确切地点都成了“某处”,而我自己,则毫无例外地成了“某人”。
某人正在走向某处,只有树们站在原地。这并非是说树们不在走动,没有它自己的速度。比如,一些树依然垂挂着紫色或红色的小圆果,一嘟噜,一串串,而另一种树则开着一点也不显眼的花,看上去跟嫩叶差不多,你靠它很近时才闻到一缕清香;至于那些落光叶子又满枝绿苞的树,似乎一直站在自己的拐弯处,任凭想像而自枯自荣。我当然叫不出这些树的名字。它们属于正在沉默的大多数中的“某一株”。
让我惊讶的是寻常见惯的悬铃木,那满枝微酡的枯叶子,此时仿佛一树斑斓的花朵。它们是向下的,慢慢收缩着往日的狂放和青葱。其中一片慢慢落了下来,一点也不飘,它碰到下面的树枝,翻转了一下,又擦过另一片叶子,触地的一刹那,充满了那种幽远中持续到来又忽地被打断的声响。它似乎承受不了一点暖意,或者微风的抚摸。脆弱到极限的坚韧,这怒放着的凋零,是这个有雾的冬天为我掠过的神圣多余的美。
我有点诧异,为什么在雾中,我却感到了另一种清晰?
冬雾中的鸟比平时多了不少。一只鸟融化了翅膀,但它在飞,鸣啭声水滋滋的,像落叶重新飞回了枝头。我发觉鸟儿们具有盲目乐观的特点,它们在雾中飞得很低,叫声中含有更多迷漓的成分,不像躲在《诗经》中的斑鸠有那么多桑葚可吃,它们只能吃雾气。
还有一些鸟,晕乎乎地呆在疏枝上,一动不动。乍眼看去,它们几乎成了光秃秃的树木想像出的若干果实。“你拥有那么多的种籽,却只有那么一点儿泥土”。贝纳丹对卢梭说的话,大约也可以对这些树说。谁知这时鸟们忽啦飞走几只,碰落的水珠嘀嘀嗒嗒的,当然会有鸟粪滴落下来,加上雾中传来的铃声、喇叭声,就足以证明世界的秩序依然是醒着的。
除了深夜的亡灵,所有的人都活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为什么从我身边擦过的人都行色匆匆?“你的梦呓象公文包里夹着的一声猫叫”。当然,鸟粪里也可能有野草籽,它们可以在我抬头才能望见的高耸入云的高压铁架上发芽、疯长。现实和虚构有时难以区分,正如一扇关不上的旧窗户,夏天的烈日使它歪向一边,连绵的梅雨又使它翘向另一边。“道路在雾中”,这是米兰·昆德拉的判断。其实,雾原本就属于没有路的路。
一个人突然向开阔的水面拚尽全力吼叫,——噢嗬嗬嗬——,无意义的、动物式的吼叫,然后屏息运气,再发力,叫声不断撕开雾的帷幕,似乎要让那外面几代观众都听见。据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法。但我看不见他那拼力豁开的嘴巴。哦,他像不像蒙克《呐喊》中那个站在桥上的家伙?一个人在雾中,也许能通过吼叫来证实他的存在,但我从来没有试过。如果我也这样吼叫,我会感到害羞,不好意思地红脸。我已习惯于温文尔雅的说,克制的说,转弯抹角的说,言不由衷的说。据说练声带也有门派的不同:既可练报告式的声如洪钟,也可练蚊子式的柔腔媚声,“嗲嗲嗲——”。一般都是兼练两种或多种。只练一种有成“公鸭”或“鹌鹑”的危险。
“你的喉结太大了,所以不太……”这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有点感冒了。一辆赛车冲到我跟前猛地刹住,还没看清那张脸,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倒是一则“包治结巴咀(嘴)”的广告被我看见,大红漆字的下面是带区号的电话号码。那弯弯扭扭的字体让我感到他“结结巴巴”的痛苦。无法言说的痛苦该是怎样一种痛苦?一个城市的结巴佬们能被外地郎中如此关怀,应该感到无比幸福才是。我想给这个家伙挂个电话,我想找到他,我想观摩他很卫生的口腔,鲜艳的牙龈,舌头怎样优美地卷动。我还想问问他是否“包治”说话太“流利”这种病。
这会儿,一所家庭幼儿园的铃声,响了。接下来的是,一个大人粗哑的嗓音,高声放牧着一大群鹅黄的童声:“妹妹你坐船头欧,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荡荡悠悠……”在该拐弯的地方,整个地乱了套了,小鸭子们咬不准那个斗大的“爱”字。
一切都在重新开始,而我正站在“某处”迷迷糊糊。雾将未知的雪气与自身混和在一起。那么,比冬雾更灰白的是路,还是大排档里的“狗不理”包子?我想我正置身在它们中间,走走停停。我感到了坚硬和虚弱。一个人正在飘零的部分,却宛然悬挂在那儿,不见其少。当然,时间尚未施加最后的压力,我似乎还可以在“是……呢,还是……”之间徘徊,优柔寡断。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