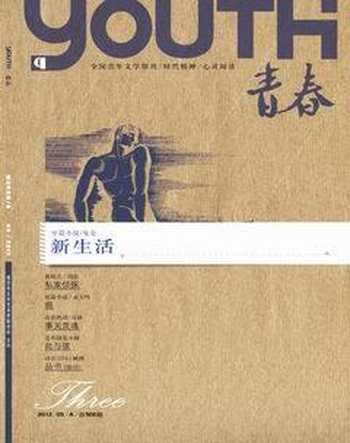穿青衣(组诗选六)
穿青人
◎ 徐源
穿青人,一个神秘的未定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西南、黔南五个地、州、市所属二十多个县,第五次人口普查约六十七万人。
遗失的三把头
第一把 是我们朝拜的天
要梳在高贵的头顶 把五显挽成叛逆的椎
第二把 是我们安身的地
要梳在神圣的脑后 弯曲如躬耕的犁铧
第三把 是我们的今天
要梳在艰苦的额头 露出深浅不一的纹
没有镜子 让我们看到自己 回到过去
那些腐蚀在风雨中的脚印 无人收藏
刻在骨头上的痕迹 歪歪斜斜
终不成一个能记载的字 我们将到哪儿
去寻找埋葬在高处的祖先
没有尸体的祖先 只有一捧厚重的泥土
在空旷的时间 对着厚重的大地
喊得撕心裂肺
哦 这一个梳着三把头的民族
身披夜晚 提着马灯和头颅
向着黎明的寨子走去
穿三节两袖衣的外祖母
穿三节两袖衣的外祖母
腰拴青色大带 脚套细耳草鞋
手提镰刀 要去对门岩上
割一背茅草 铺在漏雨的椽条上
在房顶腐烂的阳光
她揭下拖进圈里 重新变成粪
变成来年春天的苞谷苗
在闹饥荒的年月 她挖野菜的锄头
入地三尺 掘进日子深处
半碗面和一锅水 喝进肚子里
咕嘟直响 像一首清苦得单纯的歌谣
岁月虚弱的影子在里面晃荡
穿三节两袖衣的外祖母
总在揭不开锅的时候 从牙缝里
挤出一点维以生存的粮食
把一日三餐熬过去 把所有的艰难
在儿女面前 应付得自如
穿三节两袖衣的外祖母
想起沉封在坛子里的往事 心怀感恩
像打开多年的老酒 温馨扑鼻而来
她指着肚子上那条隐隐的疤痕
这是用米草绳勒紧肠子留下的胎记
整整拴了三年 她说话时
语气变得满足 骄傲 只有她才有这种权利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又三年
终于锻造了那个时代的胎记 那一辈人
看着鼻子就酸的胎记 醒示子孙后代的胎记
牛王节
一生忠于土地的 不只是我的祖辈
不只是贫瘠中昂着头的庄稼
这些苦守的岩石 不厌的天空下
刀耕火种的年月
这牛 生于犁铧之上 长于犁弯之中
累死于犁绳之尾 它翻阅过的土地
是一本无字的经书
让一群穿青人
在上面去寻找答案
生而息
息而生
必须把它的头骨放在最高贵的位置
超过我们的灵魂 这一生
忠于苦难的太阳 让子孙
在一犁新鲜的泥土里
发芽 拔节 成长一片明亮的春天
生命之树
我落地而生 长得瘦小
在襁褓里吮吸着未知的命
需要一棵花树 让灵魂在上面
寄生下去
栽在右侧的菜园里 栽在三岁
我多病苍白的春天
栽在我差点就离开这个世界的零晨
鸡叫一遍 树形成
在一阵山歌的风水中
获得一把锁住生命的铜锁
日子在它的枝上 长出了
新的叶 两三小片 多么拮据
每天早晨 我去看它
看我自己的另一半 看阳光
忽略过的背面 颜色浅一点
树在 人在 将要消亡的誓愿
于尘封中萌动着身子 掀起灵性
我很高兴还能像它一样
抓紧一把泥土 看着这个凸起季节
逐渐显现出人生的面孔
用一把时间 涂抹在粗糙的爱上
我终于穿过童年了 童年被抛弃在荒草里
穿过青年和中年 穿过暗流的藕粉
暗流的鸽哨的叹息
在淡泊世态的眉毛间 穿过所有
在我的村子里 一个人对应一棵树
多为果木 老来砍下
做一个枕 放在自己的棺材里
这是肉体与灵魂重合的时刻
畏惧而神圣 骚动而沉寂
闭上双眼 返还到神的子宫里
再去酝酿来生的艰辛和幸福
救苦解结
把腰弯得再低一点
为了我们逝去的亲人 守护凡体
超渡亡灵 也为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
看春夏秋冬的轮回 救苦——
一本经书的长度 穿青老道士
额纹的长度 一生的长度
手握佛香 绕着老屋 绕着自己的根
把家门前的路 踩得更加深陷
望山裙在风中 载不住
流连忘返的魂魄 昔日的笑脸
我们的身前 是活着的光阴
我们的身后 是活着的影子
倒着走回来 拾起所有的悲伤
回到起点 拉掉棉线的活结头
改变死去之人的命运 他升入天堂
让我们移动 在黑白之间
在停止与继续之间 移动
把腰弯得再低一点
我们手持应红幡 身着青衣
摸着身上的每一根骨头 不知安装于何处
多么的卑微
在这条路坎坷的地方
为我们逝去的亲人救苦
为我们朦胧的命运解结
以蛇为亲
我的奶奶走了十多年
今天 她第一次回来 她的灵魂
附在一条菜花蛇上 爬过门前
太阳底下晒着的大豆秸
爷爷叫齐他所有的孙儿 十多年
我们都长大了 爷爷的胡子
也白了一根又一根
我们站成一排祈祷她的庇佑
她爬过曾走过的小路
十多年前割过的青草 如今还在生长
十多年前的庄稼和现在一样
她喊过的那一声 蚕虫还在重复地叫着
她伸出舌头 去亲吻泥土
最后爬过石砍脚 走了 她是不忍回头
爷爷点了三柱佛香 插在路口
轻念着奶奶的名字
我们是多么的相信
内心深藏的爱 在爷爷眼中
走动着十多年前的
贤妻良母 十多年来的风
吹乱了他的头发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