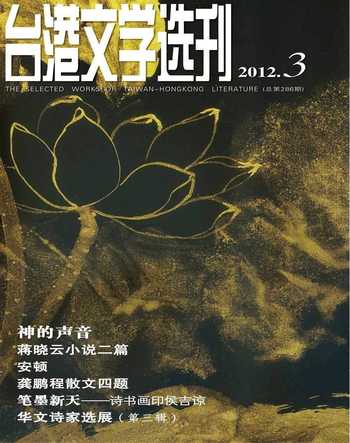安顿
陈若曦
张连昭惠的独子丧身车祸,让老妈痛不欲生。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壮,不料没打声招呼就走了,任谁也是难以承受。不是女儿伙同侄子拉着,她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
“走的怎么不是我呀,你叫我晚年依靠谁呀!”
老泪纵横的恸哭,道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使得亲友也一掬同情之泪。
不幸中的大幸是,娘家人总动员也似的从各地赶来冈山,抢着代昭惠办理一切丧葬事宜。弟弟亲自挂帅指挥,连八十岁的老哥也由孙子搀着上门慰问,侄子们更是一呼百应,抢着披麻戴孝,把丧事办得隆重又体面。其间种种孝悌友爱之情溢于言表,差堪弥补她丧子之痛了。
儿子入土之日,她叫外烩师傅来家,办了两桌海鲜料理款待娘家人。席间,她率领两个女儿,让媳妇牵着两个孙女儿,一起以茶代酒向亲戚举杯道谢。
老哥谦让说:“你嫁到张家,但仍是连家人,自己人理应互相照顾嘛!”
弟弟问她:“阿姐,这几个侄子待你不输亲儿子吧?”
她由衷地点头表示感谢。
老哥说:“父母不在,兄嫂的家就是你的娘家了。几时来大甲散心吧,我让小辈的开车来接你。”
侄子纷纷表示:“姑姑几时去?来一通电话就行了!”
如此亲情,不但老妈,连两个嫁到外地的女儿也感动得眼眶湿润了。
“真应了‘塞翁失马的说法,没了哥哥,倒发现舅舅和表哥这么好,让我远在台北也放心多了。”大女儿美慧启程回台北时,感到十分安慰。
小女儿美智表示:“比起台北,我住印尼是更加鞭长莫及了。”
她因此也叮咛老妈:“到底血浓于水,妈没事就多去舅舅和表哥家走走才好。”
“娘家嘛,”昭惠欣然答应,“以后只要有请,必到就是。”
终于,回来奔丧的女儿和孙女儿陆续离去了,家中又恢复了白天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守门的日子,而晚上则剩下婆媳俩,令人倍觉凄清。这时哥哥来电话了。
“大甲妈祖去新港进香了,回来要大拜拜,你来看热闹吧!”
弟弟亲自开车来接,她带着回娘家的心情,欢欢喜喜地赶热闹去了。
妈祖绕境进香是大甲的盛事,家家备了丰盛的牲礼祭拜,并大宴外地来的朝觐客。连家在镇澜宫附近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因门面很小,流水席直摆上街边,食客和香客川流不息,益显得人气旺盛。昭惠多年不曾参与这种盛事了,身处其中,感染了一份喜气,似乎又捡回了儿时逢年过节的兴奋,整天乐淘淘的。
大哥留弟妹俩过夜。次日一早,儿孙辈都还在睡梦中,三个老人已经坐在铺子里泡功夫茶了。
尽管铺门大张,然而经过了一个日夜的锣鼓喧天和爆竹轰炸,街道过度疲劳似的还沉睡不醒。
闲话了一回家常,哥哥忽然提起:“阿惠还记得桃园老家的房子吗?”
她当然记得。父祖都是耕种之家,农舍和菜地外,还有池塘养鱼,牛棚和猪栏也齐全。它是连家三兄妹生长的地方,即使自己南嫁到冈山,对老家还是念念不忘。后来生儿育女了,外公外婆的家更是孩子们爽心悦事之地。父母相继撒手西去后,她再没回老家过,只知有位远房的阿童叔住着,兼代连家看房子。
“好久没回老家了,”她念旧地问起来,“阿童叔还在吗?”
弟弟告诉她:“童叔过世一年了,房子一直空着。”
这时老哥呷一口茶,清清喉咙后,对妹妹说:“你我到这把年纪了,知道生命脆弱且无常,有些事不早些处理怕临时会措手不及……你说是也不是?”
谁说不是?儿子开车去花东游览,光天化日之下一辆沙石车冲过来,撞得人车齐毁,什么后事都来不及交待,一刹那便天人永隔了。生命的无常,还有谁比她体会更深刻呢?她不禁欲语还休地喟叹了一声。
“阿惠,爸妈去世多年了,这小小的祖产一直没有处分,只怪阿哥偷懒……好歹现在做个了断,我们这一代人也就安心了。”
老哥以缓慢深沉的语调说到这里,弟弟接过口说:“大哥的意思是,祖产再小,也要留在连家,由连家子弟来继承。这样做,也合乎我们台湾人的风俗。”
哥哥边听边连连点头称是,当即接下来表示:“我们这把年纪了,也用不到这点家产,不如早点让给小辈的,他们拿去做本,给姓连的挣出一片天,大家晚年都有依靠,也都有光彩了。”
说到这里,老哥口气一转,严肃认真地问她:“阿惠,你能不能放弃你名下的继承权,把它让给你这些侄子们?”
兄弟俩四只眼睛齐刷刷盯着她,目光灼灼,让人不胜招架。尤其是大她十岁的老哥,儿时颇敬畏他三分的,如今白发稀疏,满脸犁不平的皱纹,风烛残年的人,委实不忍心和他争执抬杠。
真的,她也七旬高龄,生活无忧,何必去分那一点祖产呢?仅有的儿子走了,媳妇有工作,如今又获得丈夫的赔偿金,生活很有保障;两个孙女儿一个留美,一个念台中商专,将来全要嫁到别姓人家去,为她们操心未免多余。嫁出去的女儿也是各自有命,美智的夫婿且是印尼富商,更不必锦上添花了。几个侄子留在台湾打拼,照顾他们等于是照顾自己的晚年,又何乐而不为呢?
“阿哥,我当然愿意。”
大哥一脸的皱纹登时波浪般舒展开了。他宽慰兼友爱地表示:“我早知道阿惠是念家顾家的人。难得来一趟大甲,不如今天就把手续办了吧,嗯?”
弟弟应道:“那是最好了。”
老哥就带着两人到庙口吃早点,然后敲门叫醒一位熟识的代书。代书匆匆洗漱了,便领着他们上办公室,取出事先备妥的文件,让她签名盖章,放弃所有房地产的继承权。
弟弟还要赶回农会上班,这天办完事就开车把昭惠送回冈山了。
“阿姐,你就把侄子当儿子吧,今后有什么事只管找他们!”
分手时,他一再叮咛着。
这些侄子也真有心,昭惠回家不久就接到高雄的侄子来电问候了。老人家盼的就是这种嘘寒问暖的关怀,登时感到贴心之至。
事实上,她也是这时才体会到老人的寂寞。一向和媳妇沟通不佳,倒也从不吵架或拌嘴,就是彼此没多少话说。儿子在时尚不觉寂寞,饭桌上老人总还插得进两句嘴,现在婆媳却常是对坐无语,竟感到空气凝重得可以拧出水来。眼巴巴等着小孙女假日回家相聚,但小姑娘忙于找同龄朋友,一日三餐都难得在家吃,妈妈都拿她没办法,遑论祖母了。
经过丧子的打击,她的健康耗损不小,精神大不如前。精神不济,风寒竟乘隙而入,一场感冒竟让老人家躺倒半个月。以前生病都是儿子带她看医生,如今是媳妇代劳了。然而两趟医院跑下来,媳妇透露口风,她全勤的年终奖金泡汤了。老人听了内疚不已。向来身体硬朗的昭惠,第一次惊觉老人生病的恐怖和无奈。
她想起侄子们。然而最近的是大甲的侄子,开车也要两小时,怎么也不忍心叫他撇下生意,来回花上大半天只为了带她看病。数一数侄子倒有五位之多,可惜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一位老邻居来看她,闲聊中说起某人住进一家老人安养院。
“才半身瘫痪就被不孝的儿子推到安养院去,这老人够歹命的啦!”
邻居在感叹之余,不忘安慰病人说:“媳妇这么孝顺,阿惠你真有福报耶!”
“她八小时上班,回家还要照顾我,难为她了。如果安养院办得好,我也不反对……”
“你别开玩笑了!”邻居不以为然打断她,“安养院办得再好,哪里比得上住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呢?”
昭惠一时默然。近年来媒体常有各式各样的老人院广告,有些房子盖得美仑美奂,医疗和娱乐设施齐全,地点也在风景区,但据说入住率不高。她知道,家人和老窝是令人难以割舍的。
“要是住在台北就好了,”她折中地表示,“听说台北有老人日托中心,白天可以上班似的去那儿待上一整天。”
“那也不好,七老八十了还要天天上班,多累呀!”老邻居离去前,谆谆告诫她:“什么安养院之类的,你可千万别在媳妇面前提一个字才好!”
邻居的好意,她笑笑表示领情。别说是儿媳了,就是朋友间也等闲不提的;安养院一词,对老人而言几同禁忌。
和女儿就不同了,她可以开怀畅谈,甚至百无禁忌。
“要是老生病,我想不如去住安养院算了。美慧帮我打听一下,台北附近有什么好地方没有?”
她有意以退为进来试探女儿,结果反应不一。美慧因为婆家人口复杂,无法接妈妈同住,真的去打听了安养院。不久,她告诉妈妈,等级很多,选择也不少。最高级的一家设备新颖齐全,食宿等同五星级旅馆,预交押金四百万外,每月生活费一万元;其次等级递减,收费亦然;也有佛教团体办的,连寺庙和和尚也一应俱全。
她劝妈妈:“尽量和嫂嫂住,实在不方便了才考虑安养院吧。”
美智则相反,热情地邀请妈妈去住。
“妈还没来过印尼,阿宽人很厚道,泉州话你也听得懂,来住住看嘛!”
老人家相信,人与人能沟通最是要紧。阿宽是女儿离婚后改嫁的女婿,父辈自福建移民去泗水,会说闽南语。他刚过六十大寿,前妻的儿女多成家了,只有小儿子同住,而他在雅加达念大学,听说假日才回家。此外就是两人婚后生的四岁女儿婷婷,算来家中人口简单,再空降个丈母娘,应该不嫌太挤才是。
“好吧,去印尼的事,等我感冒好了再说。”
然而美智却给长荣航空公司打电话,先为老妈买好一个机位。盛情难却,感冒也不药而愈,昭惠便整装出发了。
老妈觉得自己步履健壮,长荣机上供应台湾菜,空姐也操国语闽南语双声带,自己完全可以单独旅行。媳妇却不放心,托航空公司找到一位同机女客,机位划在一起,请她就近照料老人。
五位侄子里,有三位赶来送行。大甲的侄子代表他老爸和众兄弟,给姑妈送上一个红包。
“姑妈,我们祝您旅途愉快!”
昭惠接到一个饱鼓鼓的红包,内心一阵感动,眼泪差些夺眶而出。活到这么大了,这还是头一回出门有人送礼以壮行色呢!
飞机起飞后,她把红包打开,数了一数,竟有三十张千元大钞!
同座的女客向她恭贺,并说:“侄子对你这么好,儿子想必更好啦!”
“我没有儿子,他们就是我儿子了。”
飞雅加达途中,她心花怒放,身子有如气球升空,一路飘飘然。
美智来雅加达接机,和老妈住进一家五星级旅馆,房内供应鲜花水果。旅馆地处首都最先进也最漂亮的马路上,四望全是摩登建筑,车水马龙,繁华极了。
“美智呀,饭店横竖是睡觉的,何必住得这么豪华呢?”老妈觉得心疼。
“阿宽要我们住两天,让妈好好地逛一下雅加达嘛。”
一天逛下来,老妈就觉得雅加达人多车挤的窘状,和台北如出一辙;尽管街道宽阔,但公共汽车竟在街心停泊落客,交通之紊乱远超过北高二市。此外花繁树茂,天然资源显然比台湾富裕,清真寺庙更洋溢着中东的风情。怪的是,她看到许多华人面孔,但即使到了华人聚集的中国城,也见不到一个方块字招牌。
“妈,我们在印尼生活很舒服,赚钱也容易。美中不足的是,当地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非常敏感,刻意打压。这里不许办中文学校,中文书报也禁止进口,只因为欢迎台商来投资,才略微打开一个小缺口而已。”
原来八十年代印尼欢迎台资,几经交涉才允许台商办了一个小小的“台北学校”,是中文补习班性质。美智随前夫来印尼经商时,两个孩子都读过这个学校。
她抱怨说:“孩子们被他们老爸送去美国念书后,中文都忘光了,现在给我来信全是英文!”
“不要怕,他们将来回台湾做事,中文三两下就捡回来了。”
昭惠对孙子很有信心。倒是听了女儿说到本世纪几起排华案件,不免惊心动魄。
“当地人为什么这么讨厌中国人呢?”
“马来人不会做生意,竞争不过中国人,因嫉生恨呗!”
原来华人的人口只占印尼的五个巴仙,但掌握了七成的财富,招致嫉恨自是意料中事。昭惠觉得,女婿一家简直是坐在火山口上,奇怪女儿竟无知觉。
“妈妈,你放心吧,每次排华事件之后,印尼经济一定跌落谷底,相信苏哈托总统不会这么笨吧。”
信佛的昭惠还担心:“到处都是清真寺,你和阿宽不信伊斯兰教行吗?”
“没办法,中国人吃惯了猪肉嘛!”
美智说,当地人一手拿经书,一手握剑,自己很团结,但对外教包容性很低,华人不肯信他们的教,确是得罪了当地人。
“我们家的佣人全是马来人,有些事得尊重他们的习俗,只好自己动手。”
昭惠常听女儿说,再婚的刘家是泗水的大姓之一,果然居家很有气派,楼房高耸,庭院大得像个小高尔夫球场。一家四口就雇了四个仆人服侍;有一个女佣还是从婷婷出生就一手照料到现在,如今仍是她的专人保姆。
昭惠奇怪:“你又不上班,干嘛要雇这么多佣人呀?”
“印尼人工便宜嘛!佣人的数目也攸关社会地位,雇少了也没面子。”
“虽然这样,”她告诫女儿,“四岁的孩子还用保姆,小心宠坏了孩子!”
女儿只是笑笑:“阿宽前妻生了三个儿子,老来才有个女儿,还嫌宠不够呢!”
阿宽皮肤黧黑,偏喜穿玄色唐装,显得清瘦而严肃。他继承祖传的粮米生意,如今店务交给儿子经营了,闲暇用来打高尔夫球,生活过得很悠闲。他不但娇宠幼女,对妻子也带三分宽容,因此在昭惠眼中,夫妻倒像父女,但一家三口站在一起,简直像祖孙三代。
“我家房间多的是,欢迎你住下来。”
女婿很客气,但是对待佣人很严格,头一餐饭就让昭惠感到不好消化。
佣人上完一道道菜后,阿宽接过一只盘子,亲自用筷子拣了几样菜,然后把盘子交给妻子,让她拿去放在门外边的地上。当一家人就餐时,佣人垂手伫立门外,木头似的一动不动。
昭惠悄声问女儿:“门外那盘菜是喂狗的吗?”
“不是,赏给佣人吃的。”
昭惠一愣,半晌转不过神来。
饭后上甜点时,昭惠想喝茶。茶壶在桌子正中央,举手之劳而已,她就伸手去取。不料女婿阻止她,却改用马来语呼喊门外的佣人。佣人立即走来,按主人的指示,绕到老太太身后,恭敬地倒了一杯茶。
女儿叮咛她:“佣人闲着也是闲着,有事让他们做吧。”
老妈唯唯诺诺,但心里颇不以为然。
饭罢,男主人一站起身,婷婷的保姆立即进来,牵着小女孩的手出去了。三个大人鱼贯而出后,门外的佣人才进去收拾餐具。
昭惠出门走得战战兢兢,惟恐踩到了地上那盘菜。
“待佣人这样……不大宽厚吧,美智?”
母女俩在一起时,她悄悄提了一句。
美智只是无奈地笑笑。
“刚开始,我和阿宽也为此拌过嘴。他不要我纵容这些马来人,说我会破坏他的家规……婷婷生下来后,我才习惯下来。”
“阿弥陀佛,众生平等嘛。”
美智听到老妈念佛号,赶紧辩解说:“台商对马来人都比较好,结果怎么样?凡是给台商家帮过佣的人,当地华侨都拒用,说是被我们台湾人宠坏了!”
昭惠除了再唱一声“阿弥陀佛”,也没话可说了。
住下来以后,美智带妈妈到处游览。比起台湾,印尼天然资源的富庶令人赞叹,但是乡村的落后和贫富悬殊也让昭惠吃惊,民不聊生,而失业者沦为乞丐的比比皆是。这么富有的国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穷人呢?昭惠正在感慨时,雅加达发生了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件,抗议政府贪污腐化。
阿宽对政局并不悲观:“印尼政局一向受军人控制,苏哈托总统贪污腐化,也该撤换了。”
泗水远离首都,一时还感受不到政局的脉动,但昭惠却萌生了还乡的念头。养尊处优的生活替代不了冈山老家的活泼热闹,她怀念老家的亲友和事物,譬如可以无限转台的台湾电视即是一例。
“阿嬷不要走!”
婷婷和外婆学了好些闽南语,对她依依不舍。昭惠凭着比手画脚,也和马来佣人熟识了,还学会享用酸辣的印尼菜。几个佣人对她颇有好感,都用肢体语言表示挽留。女儿最是舍不得了,劝阻不成便动员夫婿挽留她。
“印尼很多地方像台湾,你会越住越喜欢的。”
阿宽并如数家珍地告诉岳母:“我们都是海岛,气候很像;十七世纪的时候,两地都被荷兰人统治过;你们台湾的耕牛还是印尼运过去的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印尼也吃过日本占领军的苦头,我父亲还见过台湾来的志愿兵……”
昭惠没有反驳,但思乡情切,夫妻俩拿她没法治,只好送她上飞机。
回台湾没两天,印尼政局急转直下,苏哈托总统被轰下来了。不久,雅加达发生暴动,印尼政府纵容暴民劫掠华商,焚烧房屋,殴打华人并强奸华妇。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台湾报纸每天都在头版报道,看得昭惠惊心动魄。
弟弟刚听说她住不惯印尼时,曾笑她“有福不会享”,这时改口来祝贺了。
“阿姐,幸亏你早回台湾,逃过了一劫!”
“就是呀,以后女儿怎么说,我再也不敢去住了!”她想想都还害怕。“印尼穷人太多了,那贫富悬殊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爆发耶!”
她劝女儿回台湾避避风头。美智却说丈夫相当镇静,他估计政府不会让暴乱扩大;据说阿宽的父亲经历过一九六五年的反共政变,那场动乱华人被杀的至少在三十万人以上,但刘家只被抢光店里的大米,人丁毫发未伤。
“阿宽说,问题都出在雅加达,他是宁死也不住雅加达。七十年代他在那里跑生意,赶上学生示威和贫民区暴动,也是烧杀劫掠……哎,华人真倒霉!”
“好多台商跑回来了,你不妨做个准备,有备无患呀!”
老妈惟恐提醒不够,又强调说:“我很想念婷婷,带她回来让我看看吧!”
“好吧,我去订两张机票。”美智勉强答应。
这话说过没两天,忽然通知美智和女儿来台湾了。原来骚乱扩向外地,泗水人心惶惶,刘家的园丁偷了东西跑掉,阿宽这才同意妻女暂时来台避险。
美智返台,大大丰富了老妈的生活。她去台多年,对家乡的景物备感亲切,不时带着祖孙俩出游,垦丁、南横、溪头……都留下三代人的足迹。
一辈子劳碌的昭惠,难得如此游览山水,不禁老怀大开,抚着一花一木都会感叹:“不用去外国了,台湾也很美呀!”
有一天早上,在杉林溪小木屋的停车场上,昭惠碰到一位老乡,小时候一起采茶的阿珠姐。十几年没见面了,两个老人兴奋得把臂攀谈起来。
“你一个人来吗?”昭惠问她。
“不,孙女儿请我参加她们公司的旅游团。”
阿珠指指场上停泊的一辆游览车。
“哇,你真福气,有孙女儿可以依靠了!”
“哪比得上你呀,阿惠!”阿珠说着,透露出一副“你别装假”的神色。“你现在大发了,可以成天到处游山玩水,才真正令人羡慕死啦!”
“哪儿的话,人老了就跟没脚似的,难得美智回来,才能带我出来走走。”
昭惠不想解释,其实是印尼暴动,母女俩因祸得福的缘故。
“唷,美智这么孝顺呀!那是当然了,你现在身价百倍了嘛!”
老乡眯起了浑浊的眼睛,嘴角似笑非笑,话里颇有揶揄的口气。
昭惠莫名其妙,一时不知怎么接腔。
“哎,我服你了,阿惠。”
阿珠放弃似的,改以淡然的口气问她:“我一直很好奇,你们那片靠近飞机场的地卖了,究竟分给你多少钱?”
昭惠瞪着阿珠:“地卖了……真的?什么时候……喂,你知道卖多少钱?”
“骗人傻瓜呀!”阿珠口气不悦了。“地价谈了一整年,你怎么会不知道?喂,没有你盖印,土地哪能过户?”
昭惠一把抓住对方的肩膀,急得快跳脚了:“真实的,骗你就给雷公打!”
阿珠尽管啧啧称奇,还是张开手掌,比了四根手指说:“厝边的人谁不知道,卖了四亿元哪!”
倒是昭惠自己像被雷公击中一般,嘴巴震开老大,心差些蹦出口腔,身子则是摇摇欲坠。
“妈妈!”
恰好美智走出小木屋,见状连忙跑来搀扶。
阿珠看到这种反应,吃了一惊,撑开的手指半天缩不回来。
“你怎么了,妈妈?”
美智口里喊着,目光却瞟向老妈身旁的人。
阿珠怕她误会,连忙解释:“你就是美智吧?没什么啦,你妈不知道卖老厝的事……你扶她进去,用万金油擦擦额头……不好意思,我们要回去了。”
这时游览车传来马达发动声,老人乘机抽身。
“再见了阿惠,什么时候到桃园玩,记得找我啊!”
“喂,喂,你是……”
美智正想留住这位惹事的老妇,但昭惠已然回过神来,立即牵住女儿的手,示意她不要追问。她让女儿牵着回到屋里,坐下喝了一口水,缓过气来后,才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出来。
“妈呀,你真是老糊涂啊!”
往后的一段日子里,“老糊涂”就成为女儿和媳妇的常用语。
大女儿尤其埋怨她轻易放弃继承权。
“这样的大事,你怎么都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呢?现在男女平等,女儿和儿子有什么区别,你就不把我们的权益放在心里呀?”
美智则是遗憾老人家脑筋少了一根弦。
“你不管多少遗产,先拿到自己手里,以后爱怎么花用都是你的自由,送女儿、送侄子、捐给慈善团体,都随你挑嘛!”
平常话不多的媳妇也一反常态,借小姑的耳朵数落婆婆。
“儿子不在了,不是更该疼惜没父的孙女儿吗?住在一起十多年,亲情反倒不如一年难得见一回的外姓人家,说来谁会相信呀!”
她还泪汪汪地哭诉说:“你哥哥说走就走了,可怜留下这两个孩子,谁来帮我栽培呢?如今家里是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这个家要靠谁撑持?哎,说来说去还不是你嫂子命苦,敢怨谁呀!”
这种种怨怼和责怪,听得老人心乱如麻,觉得自己果真草率愚蠢,十足是愧对子孙的罪人。半年来刚结疤的丧子之痛,顿时被这种自怨自艾撩拨得鲜血淋漓。她很后悔,当时应该设法撞死在棺材上才对。
备受悔恨的煎熬,从溪头返回冈山不过两天,老人家已经眼眶深陷,颧骨凸出,一副大病未愈的模样。
还是美智随夫出外经商,到底见多识广,先从自哀自怨中站出来,作亡羊补牢计。
“舅舅他们明明是谈妥了卖地的价钱,这才逼迫妈妈签字放弃,我们可以告他们欺诈!”
昭惠听到打官司,期期以为不可:“兄妹到这把年纪了要打官司,岂不让人笑死!白纸黑字的文件,逼迫也说不过去,而是……”
她不忍心点出“诱拐”两字,其实是兄弟乘人之危,在她感情最脆弱的时刻,加以连哄带骗所致。
美慧比较实际:“不打官司也要讨回点钱才行!”
要得到吗?老妈很犹豫。祖产卖了这么一笔天文数字,如果兄弟有良心,给她出去饯行的红包,便不该是区区三万元。台湾俗话“人是亲戚,钱是性命”,这种视钱如命的兄弟,怕是早无手足之情了。她深感悲哀,台湾人几时变得这么唯利是图了?
媳妇和女儿却都心有不甘,老妈最后只好让步。
“送出去的东西照理是不能讨回的,你们要能找到一个好的借口,不妨试试看。”但是她警告她们:“愿意给多少但凭他们的良心,别指望太多了。”
为了找理由,台北和冈山的电话打了一整个晚上,终于让媳妇想出了个点子。
“妈妈不是托美慧找过安养院吗?最好的一家要预交四百万元,就当要给妈妈筹这笔钱,如何?”
美智觉得可行,当下拍板说:“行,就要一个百分点好了,四百万!”
众人公推她出面交涉。电话打到大甲,请舅公来接。寒暄之后,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阿公家那片旧厝和土地,听说卖了,是不是?”
“是卖了。”舅舅嗓门虽喑哑,却不含糊。
“请问卖了多少钱?”
半晌没回应。美智再问一声,他反说:“你问这个做什么?”
“妈听古厝的人说,地卖了四亿元,是不是?”
舅公没否认,而是嗯呀嗫嚅了一番才表示:“没有实得这么多了,是你小舅过手的事;不过我知道,这年头办事都要打点红包什么的……”
老人迂回了半天,总是避重就轻,美智只好单刀直入地打断他:
“大舅,妈妈为了照顾几个亲侄子,慷慨地放弃了祖产的继承。现在妈妈碰到实际的困难了,为了清静,也为减轻我嫂嫂的负担,她想住到安养院去。”
接着美智介绍了一下安养院的设备和收费,说明四百万就可以让老太太高枕无忧的理由。电话那端,始终静静听着没有回响。
“四百万对四亿来说,仅是一个零头而已,但是妈妈就可以安度晚年,我们做女儿的也放心了。舅舅,你能不能和表哥他们商量一下呢?”
老人家沉吟良久才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笔钱都分出去了……且让我和你小舅说说看吧。”
美智谢了他,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般挂了电话。
然而等了一个星期,大舅杳无回音。她打电话去,挂通了却是录音。她留了言,也仍是没有下文。
昭惠觉得蹊跷,于是亲自打电话,结果也是石沉大海。她打电话到弟弟家,也是电话录音。打给几个侄儿,效果相同;姓连的忽然全置备了先进的电信设备,不再亲自接电话了。
昭惠又气又伤心:“不知真相还好,如今亲戚反成了路人!”
美慧气不过,打算亲自去大甲找舅舅理论。
老妈坚决制止:“别再提遗产的事啦!这种亲戚丢掉也罢!”
大家果然噤声。媳妇也没有多话,做婆婆的却避免和她正眼相对,那一份愧疚感压得人抬不起头来。尽管美智带着婷婷天天逗着老妈说话,她却消沉下来,胃口也大不如前了。厌食加失眠,几天下来人就瘦得像根枯萎的稻草。
八月底,阿宽来电话,说印尼已大局底定,要妻女回家。老妈听到女儿要走,一时老泪涔涔,生离死别似的难以割舍。
“妈,你还是来印尼和我住吧。”女儿邀她。
她摇头了:“我愿意留在台湾,住安养院。”
她不仅说说而已,而是十分坚持。这年冬天,美智和嫂嫂合力筹出了四百万,送母亲进了淡水的安养院。美慧每周去探望她,其他人定时给她打电话,听到老妈说她“天天在度假”,大家才放心。
儿子做周年忌时,昭惠搭火车回冈山主持家祭。媳妇看到婆婆头发雪白,脸色红润,精神尤其活泼,大有返老还童状,一颗愧疚的心才放了下来。
“谢谢你们的孝心,”昭惠说,“让我晚年过得这么平安舒适。”
她没说出来,其实也感谢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的贪婪,她反而有个安适的晚年。
(本专辑为本刊特约稿)
·责编: 宋瑜 马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