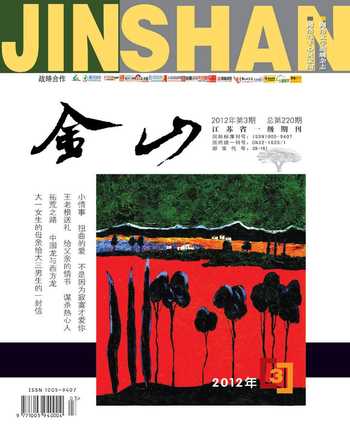樱桃树上的斧头
余欢欢
这里是中国的一个小镇,繁华的城里的一个毫不出色的一块格子镇。
这里是南方,并不沿海,地理模样如一顶倒过来的破斗笠。她的住址就在斗笠的最边缘区域。
大波浪,红嘴唇,红指甲,不可或缺的香烟。书桌上一本屠格涅夫精装版的《初恋》,仰面翻至两百零八页,她的手机就压在左边的页面上。她不喜欢电话,有时候甚至极其讨厌,在极度紧张的压抑的时候,她时常有晕倒的倾向。她对香烟有一种病态的着迷,一天抽二十多根,至到上腭发麻。香烟是个好东西,一开始,她还仅仅是喜欢看男人抽烟,看男人的喉结在抽烟时抖动的性感模样。后来有人推荐她抽一种叫做DJ-mix的苹果味的香烟,她逐渐找到了抽烟的快感,那会让她过敏神经的跳动、淋巴液的环流和动脉里的舞蹈,所有的程序都慢下节奏,渐渐静止。
每当夜晚,她就坐在那张早已污迹斑斑的红皮沙发上,想着一些无边无际的事情。古牧犬从椅子的下面,探出自己的头,像只乌龟看着绿色的房子,厌倦又新鲜。她每天都窝在这样的巢穴里,不声不响,然后每天为自己做一个决定。她就像是一只食欲不振的软体兽,坐在那里,无精打采,但她又不自禁地逼迫自己去完成一件又一件毫无指望的事情,她想搬离这里去寻找一个更好的归宿,可是下了决心离开这里,却不知该走向哪里。每次想到这里,她就想抽烟,一抽就无法停止。抽烟的时候,她是那么安静、美丽、优雅。她的眼睛大而有神,面颊晶莹如玉,鼻子微挺,如天鹅般优美的脖颈上那根铂金项链泛出柔和的光泽。
她坐在沙发上,看着蜷缩在椅子下的黑白毛色的英国古牧,它老老实实地呆在哪里,不吵不闹。很久很久,她就这样保持一个思想者的状态看着,留在这里。她说,不离开,只是为了更好地去发现另一个自己。去发现还是去找回,她自己也不清楚。现在的她依旧保持着当初的那份迷人,过去的她,纯白孱弱倔强;现在的她,妖娆诡异神秘。
自由,因为自由。对任何一个深深迷恋她的男人来说,希望她一生一世本本分分地为人妻子就好,可是她说,我做不到。其实她自己也不确定,她总是在变,只是她更加害怕有天她变得身边的人接受不了自己,而不是她自己。
她出席各种奢侈场合,然后不停地满足自己去挥霍。她喜欢一切诱人的东西,她自己也想和这些诱人的东西和平共处。她通过浓妆、香烟来引诱自己走向自己要到的边缘,但是她绝对不是那种活到绝望的女人。
那日,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灯下写作。她抬眼望去,这小镇,没有一点的诱惑能让她走出去,但是她就是这么一个安土重迁的女人,不喜欢却不离开,喜欢也不靠近。这里是个并不富裕的小镇,正如她曾经在书中告诉别人的,她的住处就处在破旧斗笠的最边缘地带,她的屋前种着一棵樱桃树。这里虽然谈不上是个好地方,但是生态环境不错,樱桃树长得很好看,如果不是地域的限制,她真想把这里变成一片樱桃园。
关于樱桃园的梦想,她也从来不跟外人提及。多年前,这里也曾住过一个男人,是位个性很温和的美术家,喜欢剪花修枝的一类事情,樱桃树就是他那时候栽种的。多少年了,她也记不清了,也不想用力去搜索,只知道这树死了她又种,种了它又会死去,她喜欢吃樱桃,所以每年在樱桃树结果之前,她会很细心地呵护它。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感觉像是一场仪式,必须在某个季节前好好完成一样。后来樱桃就渐渐地成了她生命中任时间如何推移都无法泯灭的入木三分的符号。
因为记忆里好像有人告诉她,樱桃代表珍惜。为什么她也不是很清楚,听说是樱桃的英文“cheery”和英文珍惜“cherish”听起来很相似。他时常以自嘲的口吻说,我只是一个画匠,偶尔干干花匠的活,哪里能娶到你这样顾盼生姿的才女呢?他每次都这样说自己,但是在当地,他虽然还不是很出名,但已经算是个不小的人物了。而她呢,的的确确只是个写手。后来他有了机会,出了国以后更是名声远扬了。曾经还心潮汹涌想同他一起共事的姑娘,在他的光芒里,越来越暗。她也愿意这样越来越暗,暗到他看不见,最后她以为他忘记了这么一个人。关于他的行踪,她了然于心,他是大人物,她明白。该怎么做,她自有分寸。
只是没有合适的替补,她的感情才会空白到现在,尽管她的意识里,并不认为他就是最好的。他走的时候,没有交待。她的思绪都一片混乱,在期待什么?她只是倔强地想往前走,一直往前,离他越远越好。
现实生活中,她还是一个很本分的女人。说她俗不可耐也罢,她就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用奢侈品粉墨自我的女人,她喜欢这样,妖艳。外表的夸张尺度,让她看似是个放荡不堪的女人,她并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只有这样,一旦被认定,她放肆的尺度就会被接受,但是她的骨子里,是个干净的女人。
她是个病态敏感的感觉派,她想好好爱一场,但是天生的恐惧总是让她退避三舍。她和男人的关系就像是一场捕猎,高手斗法一般。她有耐心,喜欢静观其变。这让围绕她身边的人都很不喜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男人受不了这种漫长的考验,女人受不了这个单身公害。
她的思想尤其花哨,每次写作的时候,她脑子里总是想起街头卖唱的歌女、舞台上黯然的戏子,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她就活在这样的幻想和文字形象里。她总是觉得自己和这些戏子歌女差不多,都是在这样形式的世界里找一个位置,让别人允许,安分老实地呆在那里。
电梯里,她极其讨厌这小空间降落时短暂几秒的晕眩感。有时候,她低头看着自己,在门自动闪开的那一刻她才是真的降落——到底,他没有出现。
电影院里的情侣们,女人几乎都是左手鲜花,右手男人,而她的手里,只有一张电影票。她连续看了五场电影,她喜欢这种视觉持续的刺激。
凌晨的小镇,半苏半醒,她看见这里的建筑变得陈旧和堕落了。她总是觉得自己会在这样奄奄一息的天空里,悄然死掉。
这样的日子寂静漠然地流淌了三十多年,人心中最深的咒语不是施蛊以后的各种妥协和摆布,而是年久日深保持了懒于动摇的惯性。这时候,她已经四十多了,度过了女人最美好并即将度过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年华,她训练有素地吐了一口烟,眼里泅着像泡沫样的浅浅的泪花。
在年华即将老去之前,她应该做些让她不留遗憾的事情吧,她想。
在几个小时的辗转之后,她到达中心艺术区,那里有他的作品,一一陈列在橱窗里,这时候,情绪瞬间冲进她的鼻梁、额头,一阵酸。她看见了他,他像一小团芥末,就像她眼前看到的那样,青绿的颜色,在精巧的小碟子里铺成一朵柔弱的花,很清纯,还有一点骄傲,让人最心底的琴弦产生一丝波动。人生这样复杂,可以让人难以忘怀一生,抑或是死不瞑目,可以仅是某个云淡风清的下午,在樱桃树下,她未等到那个人,如此而已。
她并不知晓,只因这个理由,她便开始忌恨他。他也看见了她,两人就这样互相瞪视,或是为了观察对方,却变做互相比试的局面,都试图用眼神迫使对方低头。他直愣愣盯着她看,她并未回避,也瞪着眼睛看着他,毫无一般女人的温柔羞赧。音乐换了几首,她不知道如何摆脱尴尬。他叫了身边的人约她在贵宾室见面。
他暗中吁了口气,看见她低了头。他向侍应生要了一支雪茄点燃,烟雾渐渐散开,在两人间萦绕不散。她也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他的表情里没有惊诧她的变化,这些年,他应该也见过各种女人。
终于,在雪茄燃掉已过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取下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看了她一眼,但她冷眼相回。
他说:“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吧?”
她听得出来,这句话不是在征求,仅仅是下个通知。她此时才明白她的地位,她只是圈养多年的情人而已。
“我很注意,我没有再打扰你。”她猛吸了一口烟,嘴唇却在抽搐。吐出烟雾的时候,她的嘴里发麻、苦涩。
“我很欣赏现在的你——的画。”她说,“但是我想,所有美好的艺术形式都应该有一个与之匹配的艺术家。”
“唔。”他若有所思地点头,嘴里叼着烟有心无心地应着,一边给她倒酒。
她不知道现在的自己该怎么全身而退,她一定是脑子热过头才找到这里,情绪埋藏成地雷在此时爆炸,所有的风险,都一一袭向她。她一心想要防备,此时,她打心里希望他说些“她是个不要脸的女人”之类的话,她才能适应现在这样的羞愧,她想浸入酒杯里,尝一尝醉生梦死的滋味。他是一个很斯文有礼的男人,最终没有说出羞辱她的话来。年纪是相当好的数字,他还年轻,她老了。
“谢谢你来看我,我明天就要走了,能赏脸共进晚餐吗?”
她没有抬头看他的表情,只是低头看自己手上的指甲油。他其实也在看她的手,指甲油有点花了,除了那种刺眼的红,她的手上还有一块难看的疤。那疤是不久前不小心被剪子戳到的,因为她总是走神。这次他的请求,她是可以拒绝的,但是她一时没有想好拒绝的理由,却又怕拖延的沉默让彼此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她一声低声的简洁的单音节算是应允了。
仪式似的晚餐以半陌生半亲切的方式在两人简洁的对白之后结束。他还记得她喜欢吃的那几道菜,不加醋和不加辣椒的酸辣鱼,不吃西红柿和香菜。她似乎还感动这些细节。她感觉他在看着他,他深黑的睫毛抵消了面部的苍白,她暗暗低下头,去逃避自己那张苍老丑陋的脸(如果没有浓妆层遮掩)。多年的孤独让她养成购物癖和香烟瘾,一面作践自己,一面心疼自己。她需要被爱。他还是一个温柔的男子,尽管她看穿了他的虚伪。他离开座位走到餐厅之外,她的角度不偏不倚地看清了他的一言一笑,并且准确无误地猜测到他电话那头的缠绵。她把心里想好的话吞了回去,情绪在这一瞬间坍塌,所有的念头在这一时刻发生着质的变化。
她回到了斗笠式的地域,她想过回自己想要的那份生活。几个月以后,她试着去调整,她亲爱的古牧嗅着浸在水里几天未洗的袜子,她的写字台蒙尘多日,还有墙角那厚厚的蜘蛛网,她都想一一去处理,但现在的她,更需要一个氧气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