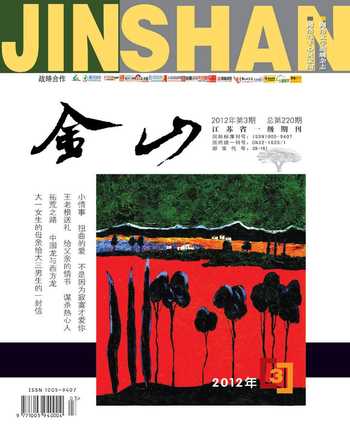太多往事在深夜里徘徊
董晨鹏
金敏华希望我写一篇有关刘青的文字。其实不用他说,我也会写的。刘青走了4个月了,但我仍然不能静静地坐下来面对她已经流逝了的过去。不需要哀乐响起,也不需要放一曲“长亭外,古道边”,深夜独自打开电脑,点击开相册,抚摸着柔软的记忆,如同握一把苍凉于手,我百感交集,泪流满面!
很多人一直以为人这一生,要走很长的路,其实,人世间只是天堂和天堂或者地狱和地狱之间一艘窄窄的渡船,我们只不过是渡船上的一个乘客而已;甚或只是一片飘落的雪花,雪花落地即无花。2011年9月12日的《深圳特区报》刊登了这样的一则讣告:“深圳报业集团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青同志……终年43岁。告别仪式已于9月11日下午3时在长沙市明阳山殡仪馆举行。9月12日上午10时于长沙金陵墓园举行树葬。”这种哀荣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享有的,但即便享有这样的哀荣,属于我们的时代亦如同雨后的彩虹,美丽而薄如蝉翼,轻轻的一阵风,就消逝在永恒的虚空之中了。唯有生者的追忆,才能留住逝者仍然在我们生命中行走的灵魂。
1968年2月11日出生于长沙的刘青是我们这批同学中岁数比较小的,但她却显得比别的女孩成熟,待人接物分寸感掌握得非常好,脸上总是挂满了灿烂的阳光。她的美是一种大家闺秀的端庄。她的情史很单纯,我一直以为刘青最应当担任的角色是贤妻良母,但命运似乎太会捉弄人,她的事业发展远远比她的家庭生活要丰富多彩,她不仅没有把和老金的爱情故事坚持到底,也没有做过母亲。我一直认为为人父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具升华色彩的关键事件,这件事能让我们更好地学会感受和分享,去品味幸福的另一面。
60后的我们这一代人,承载着中国太多的历史重荷,踏上社会后,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让我们常常在事业的优秀和生活的快乐之间犹豫不决。其实,最优秀的人不一定是最快乐的,而最快乐的人不一定最优秀,但一定是最幸福的。幸福的一面是追求,是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另一面则是给予,是充满爱和温暖的情感积淀。追求意味着我们要有梦想和创造,给予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感受和分享。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梦想和创造上,努力去做一个对社会而言最优秀的人,但我们去努力和亲朋好友感受和分享了吗?真的是少之又少,因此,快乐虽近在咫尺,却又远若天涯!老金和刘青似乎也不例外。
老金是浙江人,大学里跟我这个江苏人关系更近些。他跟刘青究竟怎么走到一起的,我至今也没有问过老金,但我知道老金绝对是那种对女人体贴入微的男人。我现在想想,是否是1988年我们在上海新闻单位的3个月的专业实习成全了他俩?由春到夏,我们眼中的桃树从灼灼其华到有蕡其实,再到其叶蓁蓁,老金和刘青的心中是否从那时起就已经有了“之子于归,宜其家人”的情愫?
1989年夏天毕业之后,老金和刘青都去了深圳,再后来就听说他们结婚了。2009年五一节,我们毕业20周年返回母校,烛光晚会上,老金和刘青各自端坐于一隅的黑暗之中,我这才知道两人已经分道扬镳。
据说从武汉返回深圳仅一个月,刘青便在体检中发现肺部有癌细胞。
刘青虽常驻上海,她却从来没有到我所在的城市来过,似乎总有忙不完的事情。我每次到上海办事也是很匆忙,几乎总是上午去下午回。那次要不是在上海过夜,我也不会想到打电话请刘青过来吃顿饭。我们常常会后悔,后悔每一次都与最后的机会擦肩而过。我们为什么总是不愿意放慢一点节奏,为什么总是以为将来一定会再有与亲朋好友见面说说话的机会呢?
2011年9月12日,中秋节的中午,在岳母家吃饭的时候,我发一短信给金敏华,祝他中秋快乐。老金很快回短信:“十日凌晨三点二十五分,刘青走了。昨天大家为她送行。我下午回京。”我黯然神伤,发了一会儿愣,然后打电话给老金,问怎么当天没人告诉我?老金说正好在中秋前夕,大家都很忙,就由长沙的同学做代表了。老金告诉我,参加刘青追思会的正好是99个人,在长沙的阿轸、缵吉、令军、老易都去了。我心头隐隐作痛:宿命般的九九归一,是天使传递给我们刘青已平安抵达天堂的讯息吧?
天堂在我们的梦中,真正的天堂在我们的怀念之中。怀念构成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怀念,我们的过去就是一片苍白的荒漠。我们用怀念留下我们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痕迹,同时,也留下了我们自身生命运行的那条与众不同的个性轨迹!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同学,刘青其实是我们生命本身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只要她还存在于我们的怀念之中,她的生命其实就仍然还在尘世间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