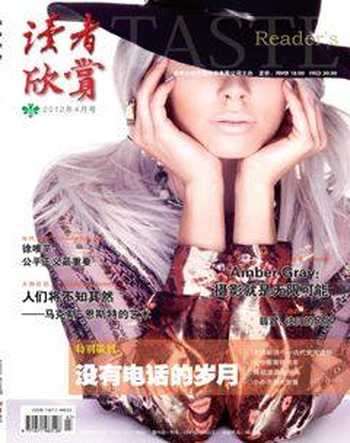古代如何民意评官
完颜绍元
“群众满意度”并不新鲜,民意评官早在汉魏时代就出现了。古代如何考核官员?民意测评有怎样的分量?官员对民意考评的态度又如何?
汉魏时代就有了民意评官
年终岁末,各地官员总结会、考核会、评价会如火如荼。近年来,在官员行政考评中突出民主,重视民生,强调民意,适当提高“群众满意度”权重,运用“民意”指挥棒,被认为是考评机制的一大进步,媒体则有“以考评模式突出亮点”相称的。其实这个亮点并不新鲜,民意评官可以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传统了。
往前追溯,民意评官的源头当是汉魏时代的乡议选士制度,就是从最初的选拔官员要听取群众评议,逐渐发展到考核官员时也要参考群众评议。当时,有很多基层官员因为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而飞速升官。比如,《汉书·循吏传》中,朱邑就是因为受到群众拥戴,由乡干部一下子升为太守卒史;召信臣也因为得到了群众的好评,由上蔡县长直升到零陵太守。
反之,也有很多官员因为群众评议太差而丢官。汉成帝时,高陵县令杨湛和栎阳县令谢游都是极其贪婪狡猾之人。丞相薛宣封“吏民条言”给杨湛,给他施加压力,让他自动辞职;发公函给谢游,开门见山地说:“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群众对你这个栎阳县令很不满意,都反映你施政无方、法令繁琐苛刻。于是,谢游的乌纱帽也丢了。而“吏民条言”和“吏民言”的内容,正是指群众对两个县长的批评、揭发、举报。
刺史考核官员先做问卷调查
古代没有电台、报刊之类的公共传媒,也没有可以让民众自由交流的互联网,所谓民意评官的方式,大体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
自上而下,就是上起中央,下至州郡,都要定期派遣使臣、风宪官员等,分级分区巡行视察,听取群众对各级政府吏治官风的评价。
西汉的时候,刺史巡行郡国,每到一地,必定先去官立学校,就当局施政得失等问题让学生填写问卷,然后以官驿为临时办公地点,通过调阅计簿文档、分头察访询问等途径了解情况。为防止受蒙蔽,刺史总是把会见当地长官、当面听取汇报之类安排在最后。
汉成帝时,朱博任冀州刺史,负责常山、巨鹿、真定、中山等10个郡国的巡视。朱博上任没多久,就在巡视途中被四五百名群众包围在某县的官驿里。这些人都是来举报当地官吏的。这种方式为以后历朝所继承,邓小南所著《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一书中称,唐宋时期的中央使臣、监察官员在巡行考察地方吏治时,都很注意搜集群众意见,有人将之概括为“欲考吏治,莫若询诸民言”,要想对官员进行考核,最好的办法就是征求百姓的意见。
唐高宗时,监察御史郭翰巡视陇右,当时狄仁杰任宁州刺史,治理有方,“风化大行”,所以郭翰进入宁州境内后,沿途不断收到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的表扬信,都是赞美狄仁杰的。郭翰对州政府派来接待他的官员说:“进入州境一看,便可知施政绩效了,我愿意成全你们领导的美政,用不着再待下去给你们添麻烦了。”于是告辞而去。
得到百姓表扬,方能驰骋官场
自下而上,就是群众可以通过向各级官员或风宪官投书献状、当面陈述等方式,主动表达他们对本地吏治官风的看法和意见。在正统史家眼里,两晋南北朝多数时段的政治远比两汉乏善可陈,但后世常见的一些民意评官的形态与取向,多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比如,此时期逐渐形成了联名具状的民意表述方式。萧梁初,永阳郡百姓何贞秀等154人联名给湘州刺史递状,从15个方面表彰本郡长官伏暅治理有方,刺史再将文状转呈中央。还有一位历任多地州、县长官的何远,每到一个地方任职,总有群众给上级递状,说他这样好那样好。
又如,后来逐渐发展为民意评官主体形式的“举留”,当时雏形已现,就是那些表彰性的联名具状往往在官员任期已满或因其他缘故(如丁忧)即将离开现任职务的时候出现,而且总是将递状目的直截了当地归结为希望某官留任现职的诉求。从史书记载看,凡被群众具状好评的官员多能获得回报,如前文所举的伏暅被提拔为新安太守,何远不仅被越级提升为给事黄门侍郎,还得到皇帝专门发诏表扬。
在传播政声、增加美誉之外,很多时候群众的好评还有保官的作用。北宋真宗时,刘随任永康军判官。他兴利除弊,减轻民众力役负担,严禁政府人员借马市勒索少数民族,可以说为老百姓谋了不少好事,当地群众都称其为“刘父”。但最后他却因为拒绝上级请托,被人冤枉,以至于官位不保。当本路监司相继来永康察访巡视时,数千少数民族群众拦马质问:“我刘父何处去也?”并大声齐喊:“还我刘父!”本路监司再三抚慰,数千群众方才散去。监司把情况一一汇报给中央,洗雪了刘随所受的冤屈,让他官复原职。
史料中有不少借助乡亲父老美言而得彰显的县令。唐宣宗时,醴泉县令李君奭任期已满,全县数十个父老代表民众向上级州府具状要求他留任后,因为不能确定是否如愿,又一同去庙里设斋求佛,恰巧遇到来此打猎的皇帝,就跟皇帝讲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其后,有关部门两次拟定接替李君奭的人选,皇帝都不予批准,使李君奭得以继续留任。一年多后,怀州刺史出缺,皇帝亲自点名:“醴泉县令李君奭可为怀州刺史。”
又如南宋前期,杜颖以弋阳县丞代理永丰县令。过去永丰的税粮征收在本州所属六县中一直名列末位。杜颖到任后,不许吏役借课税扰民,禁止过去抓捕违期交税者的做法,而是与百姓约定让其自行缴纳,并且体谅百姓的困难,一再宽限日期,于是百姓非常感动,争先恐后地去交税,最终得以完成指标。等到他代理期满将要离任的时候,老百姓们都纷纷向州领导表示感谢,感谢他派来了这么好的县令。州领导郑汝谐因此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考评,为他未来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因为群众意见太大而导致丢官的事例也有。如北魏的郦道元,就是那位撰写《水经注》的著名学者,在任东荆州刺史时,“威猛为治”,当地民众向中央指责他施政苛刻严酷,结果被就地免职。
百姓组团来京考核官吏
纵观历史,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代前期,可以说是民意评官最为活跃的时期。朱元璋要求“户户有此一本”的《大诰》(明太祖亲自制定的刑法)中明确提出,凡各地“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都可以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评官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当面告诉皇上:本境官吏“为民患者有几人,造民福者有几人”,朱元璋必定根据民众评议,表扬好的,降免差的,乃至惩办有罪的。
明代前期,许多因违纪犯过而受惩处的官员全靠民众好评才能被解除处分。对此《明史·循吏传》特别强调说:太祖立重典从严管理官吏,州县守令常因小过而受惩,甚至被关进监狱,但如果听到群众对他有好评,就会让他官复原职,有时还给予奖励。如洪武中有定远知县高斗南、永州知府余彦诚等一批州县官员,有的因为犯了公务过失,有的受连坐牵累,先后被罢官。可是当地人民都说他们是好官,把他们的施政善举一一列出来,皇帝就让他们官复原职。灵璧县丞周荣受某案牵连,被逮入刑部,年老乡绅成群结队地来到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最终皇帝传旨释放周荣,脱囚衣、赐官服,由礼部出面宴请他和年老乡绅后,送还原任。周荣不久便从副职转为灵璧知县,后来官至河南左布政使。
据清编各省通志及《明史·循吏传》的有关记载可知,从那时起,许多地区民意评官蔚然成风,写出了古代官员管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永平府乐亭县主簿汪铎和县府工房书吏张进等借劳役“设计害民”,索取贿赂,当地父老赵罕辰等44人以《大诰》为据,结团赴京。汪铎得知,快马加鞭,赶了40里路追上大家,再三求情说:“我14岁进学,吃尽灯前窗下之苦,好不容易熬到现在这个职位,你们千万饶了我,别坏了我的前程。”由此可见地方官吏对负面民众评议有多害怕。
“民意代表团”也能造假
不过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大体制下,民意评官要想得到良好发展,特别是在指摘违失、弹劾罢免方面得到突破,根本不可能。所以凡是遵循体制认可程序进行的民意评官,大多是颂扬循吏德政,并且逐渐演变成地方官员利用民意评官争取期满留任的有效手段,这就是前面已提出的每当官员将离任时出现的“举留”。
宋代群众举留长官的层级和形态很多,有向州府举留知县的,有向监司举留知州的;有的举留不是写材料向上汇报,而是采取拦道、越诉、举幡、击鼓等形态,相当“雷人”。如宋高宗时向子忞守衡州,时逢大旱,衡州米价一下子蹿升到每斛一万五千钱。向子忞急忙遣人分赴各粮食丰收地区抢购粮食,以原价摊分路费出售,每升为六十钱,这批价格适中的粮食救了很多百姓。但此举严重损害了原本想趁机发一笔横财的富豪乡绅的利益,于是这批人也来“民意评官”,最终导致他罢职。消息传出,“士民相与群聚”,一起拥到衙署前,敲击给老百姓鸣冤喊屈用的登闻鼓,称“愿举留”向子忞。现场情况是群情激奋,“鼓为之裂”,吓得提刑忙以巡视为名趁夜登舟逃走。
正面性的民意评官如此“给力”,往往能给当事人换取名利双收的实惠,所以官秀民意的故事也不绝于史。唐高祖时,并州总管李元吉在任上胡作非为,中央收到其副手宇文歆的如实反映后,召他去京师。与此同时,李元吉也秘密召集百姓前去为他说好话,估计这个“民意代表团”赴京举留的费用都由并州府财政埋单。
明太祖时,河南府新安县主簿宋圮因违法乱纪被朝廷拿去配合调查后,与其“同恶相济”的该县典史李继业为救同伙,也为自救,居然想到了打民意牌,于是召集地方耆老刘汶兴等13人开会,要他们去南京向有关部门为宋副县长说情。刘汶兴等人说不敢去,李继业马上以今后上交公粮时刁难他们相威胁。刘汶兴等人害怕,便说去是可以去,但是没盘缠。李继业说,那你们明天来找我吧,我给你们盘缠。等这13人第二天来领盘缠时,李继业却在官府装病,躲在里面不出来见人,只是让人传话说,官人今天病了,你们自己先去吧。因此各人自备盘缠,赴京去说违心话。真相被揭穿后,连累被胁迫的刘汶兴等人也受惩罚。尽管如此,这类“民意秀”始终不绝。宣宗时永宁县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求当地耆老给上级写信为他唱赞歌并乞留任;还有汉中府同知衙门的吏员们给上级投书,开列同知王聚种种政绩,推荐他出任知府,后来得知这是老王设宴请客求来的。
唐代官员考核指标
一是标准明确、分类考核。唐代官吏考核标准分为通用标准和职务分类标准。通用标准是“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是对所有官吏的共同要求。
唐代把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宗教等各方面官吏的职责分为27类,作为对各种不同官吏职责的职务分类标准是“二十七最”,这实际上制订出了每一类官职的考核标准,用以考核各类官吏的才能,较之前代,唐朝的考绩制度甚为完备。
二是德才结合、等级分明。唐代把考绩的优劣、好差划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二善为中上,无最一善为中中,职事粗理、最善不闻为中下;受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
三是范围广泛、量化考核。唐代的考绩范围广泛全面,对九品以外的流外官也制定了考核标准,即“清谨勤公、勘当明审为上;居官不急、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数有愆犯为下;背公向私、贪浊有状为下下”。这样按品行、才能功过分为四等来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