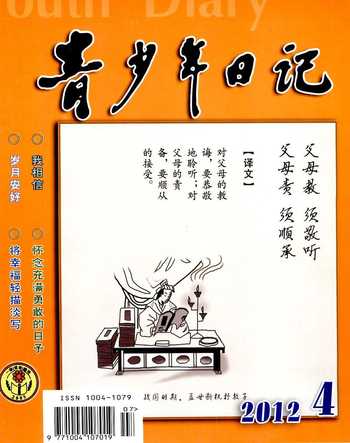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蔡海雁
3月6日晴
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年冬天,雪特别大,天特别冷。
肆虐的狂风像一头受伤的野狼,高一声低一声地嚎叫了一整夜。极不情愿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裹上早已冻透了的棉衣棉裤,立刻感到彻骨的寒冷。定定地望着早已打好的行李卷,不争气的眼泪一个劲地在眼窝里打旋。“我还是别去上学了,行吗,妈?”“不行,”妈一边把手里的柴草扔进灶膛,一边回过头来,“不上学,长大了……”一股浓烟从灶膛里喷出来,呛得妈咳嗽了老半天,“不上学,长大了能有什么出息?”
含泪咽下大半碗热汤面,我在兄弟们的簇拥下,冒着漫天风雪上路了。妈抹着眼泪,颤微微地把一个花布包塞到我手里:“拿上,这是你的学费饭费,出门在外不比家里,该花的钱别舍不得,钱不够了,写封信回来,再给你寄。”我接过沉甸甸的花布包,我一下子感到自己长大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开始在心底升腾。我知道,这个小布包里的那一叠面值不等的纸币,是那头不肥也不大的年猪换来的;我知道,妈所谓的“再寄钱来”,指望的还是喂大墙角的那头连走路都打晃的小瘦猪;我更知道,为了喂大那头小瘦猪,妈还要付出许多汗水。
走在几乎无人涉足过的雪地上,妈又把连日来说过八百遍的话重复了两百遍。说来说去,无非还是那两句话——好好学,长出息。妈每说一遍,我都郑重地点一下头。走着走着,妈突然停住脚步:“江,你的新鞋呢?怎么不穿?”“我穿不惯,还是……还是旧鞋舒服。”
“胡说!”妈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鞋,“你瞧瞧,脚趾头还露在外面……”一面说着,一面把挎包打开,“新鞋呢?快找出来换上!”我哑然一笑:“别找了,妈。我把新鞋给老三了——我穿不上……太小了。”“都怪我,那双鞋差不多做了一年,鞋不长脚长,哪能不小呢?”妈站起来,眼角眉梢挂满了苦笑。
不知不觉间,熟悉的草舍熟悉的村庄走出了我们的视野。我再一次劝妈别送了,妈为我拍去身上的雪花:“好好学,长出息,别想家。”我含泪点头,迎着风雪,走向远方。过了许久,我回头一望,亲爱的妈妈还默默地立在风雪之中。我放下挎包,立正站好,给妈深鞠一躬……
此后,我一次又一次把足迹叠印在熟悉的乡间小路上,妈也一次又一次地把我迎回送走。到1981年初秋妈再次送我的时候,我的书包里已经装入了一张中等专业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此后,在乡中学任教多年的大哥白天当老师,晚上当学生,硬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闯出一条路,步入师范学校的大门。
此后,两个弟弟发奋苦读,金榜高中,一个和大哥一样,当了人民教师,一个和我一样,投身蓝色税海。
小弟结婚时,我们兄弟四人相聚。酒酣耳热,小弟问我:“这些年在外奔波劳顿,最难忘的是什么?”我说:“是妈那两句话——好好学(后来变为好好干),长出息。”大哥和三弟相视一笑:“兄弟所见略同。”于是,大哥提议,我们四人来到母亲面前,毕恭毕敬地敬了四杯酒。妈喝了酒,一一嘱咐我们:“好好干,长出息。”
好好学(干),长出息,两句普普通通的话,整整激励了我20年。这些年,我看了许多书,听了许多报告,起草了许多领导讲话,但是,没有哪部书哪个报告哪篇讲话能像妈妈那两句话那样让我自励自省自强。在许多同学耐不住学校艰苦的生活条件哭着飞回父母的羽翼下的时候,是妈那两句话让我留了下来;在繁重的工作任务接二连三地拥来几乎将我压垮的时候,是妈那两句话让我咬紧牙关挺直腰杆;在物质利益向我招手糖衣炮弹向我袭来的时候,是妈那两句话让我不为所动。这些年,我一次次变换工作单位,从税务所一步步地来到省局,靠的是个人努力,而个人努力的动力,正是妈妈那两句话。曾有人向我求教“调动秘诀”,我写给他一句话:“夜夜想起妈妈的话”,求教者大惑不解,我哈哈大笑。
妈妈的话,简单明了;妈妈的话,博大精深。读妈妈的话,读的是人生;实践妈妈的话,实践的是理想。得意的时候,想起妈妈的话,就不会迷失脚下的路;失意的时候,想起妈妈的话,就会擦干眼角的泪,悲壮而坚定地上路;迷茫的时候,想起妈妈的话,就能找到北斗,看到朝阳。
夜夜想起妈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