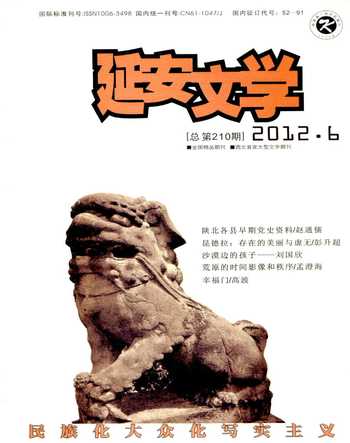赶集记忆
王彩利
一个油饼儿,一根冰棍儿
父亲是务实的庄稼人,但也做点小买卖,比如买几只羊,或一头小毛驴或小牛犊,等过段时日牲畜涨价了,就赶到集市上卖了,赚点儿小钱。所以,赶集是父亲生活中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上小学时,是父亲带我去赶集。每次赶集前,都得提前跟母亲“预约”,然后经母亲三天两头念叨,父亲才在一个他没啥生意的集日,赶着驴拉车带我去。一早上,父亲先去山里劳动两小时,回家吃过饭,给驴饮水,用笤帚刷扫一遍驴身子,察看车胎是否需要充气。一切准备好了,父亲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又在驴拉车中间放上一块干净的棉毯子,让我坐上去,车前面空档处放一个尼龙包,那是父亲给自己备坐的。把平车套在驴身上,牵住驴缰绳,手一扬,喊一声“啁啾”,毛驴就迈步起程了。坐着驴拉车,我风光无限地走出村子时,同龄孩子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快乐、骄傲,胜过现在坐飞机去北京。山路逶迤、颠簸,父亲一直叮嘱我要两手抓住车辕,坐稳扶好,小心掉出去。但我没在意,倒喜欢颠簸的感觉。天高云淡,赶集的人陆续前往,也有赶驴拉车的老农与我们朝同一方向奔跑。
翻过一座山,越过一道沟,穿过两个村子,就望见小镇集市了。听到汽车鸣笛,我心跳加速了,想去小镇的旧书摊买几本小人书,去小杂货铺买一支价值昂贵的英雄钢笔,而最想买的是旧街旁边土炉子上烘烤的喷香的油饼儿,以及用棉毯子盖着的木箱子里的冰棍儿,这才是我日思夜想赶集的真正目的。
走到油漆马路上了,小镇近了。“爸爸,到了!到了!”我这么喊着,没把父亲喊“醒”,倒是喊得毛驴跟着我激动,高翘尾巴,“嗒嗒嗒”小跑起来。父亲狠狠向后拉了一下手里的缰绳,吆喝:“眼睛看路走,别跟着小孩子胡闹。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混帐东西!”那时埋怨父亲小看我,将我与毛驴相提并论。现在想来,是父亲爱我,拿我的过错训斥毛驴。毛驴跟着他一年四季赶集,而我偶尔去一次,激动是情理之中,但毛驴就应该像他一样,稳重谨慎。
到小镇了,在牲畜市场里,父亲悠长地喊一声“驴——”,毛驴便停住脚步。父亲让我从后面慢慢往下溜,而我站起身,腿一抬,跨过车辕木就跳下来,脚趾骨碰在车盘上了。我身子一沉,蹲下来,按住碰伤处,泪花在眼圈边打滚。父亲丢开毛驴,急忙蹲下掀开我的手,按住脚趾骨反复揉,说:“你还不及毛驴懂事,有多大本事了就翻车辕了?我就晓得你麻烦不懂事,不想带你来。你妈天天怂恿我说,让带你走一回去一趟。这不?就出事了。”“爸爸,我不疼,没事。”我掀开父亲的手,想站起来。“皮都擦掉一块了,还不疼?”“不疼了,真不疼了。”我真的不疼了,因为我闻到油饼儿的味道了,口也渴了,想吮一口冰棍了。
“爸爸,去旧书摊给我买小人书。”与母亲“预约”赶集时,我郑重“承诺”:赶集我只买小人书,不买吃的。为了兑现诺言,我就撒谎。因为去旧书摊要路过卖油饼儿的,而且书摊老板就兼卖冰棍儿。父亲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一边把毛驴拴在一棵老槐树上并卸下平车,一边诡秘地说:“先去前街粮市上转转,回头再给你买小人书。”我心里刹那凉了半截,因为去粮市与油饼儿冰棍儿沾不上边儿啊。我挤出了一丝笑——不好意思的那种,也挤出了一句简短而不好意思的话:“爸爸,我渴了。”父亲又诡异地笑了,说:“我想你也饿了,走,咱先去买个油饼儿,再买根冰棍儿,小人书就靠后吧。”我知道父亲是在故意逗我,因为他一准看穿了我的心思。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马上就能解馋了,这是最重要的。
父亲打开的确良白手绢,抽出两毛钱,递给正在揉面的卖油饼儿师傅。师傅挑了一个刚从炉中拿出的热油饼儿递给我,又给父亲找来五分钱。父亲接过说:“走,拿这五分钱买冰棍去。”
我一手拿着油饼儿,一手举着冰棍儿。一口油饼,一丝咸咸的油炸葱花香味热滚滚地漫进喉咙,来不及细嚼,就被我咽下去了;也不忘记滤一口冰棍儿,冰凉凉,甜滋滋,沁人肺腑。就这样,我咬一口油饼,吮一下冰棍,逍遥地逛着旧街。当冰棍儿与油饼一齐下肚后,旧街也逛完了。我感到腿困了,想坐下来歇歇。
于是父亲把我带到拴毛驴的牲畜市场上,让我坐在平车上等他,嘱咐我不能乱跑,他去粮食市场转转。这次我稳稳坐在平车上等父亲,等着等着竟在平车上睡着了。醒来,太阳偏西,已是半后晌了,赶集的人流向东西南北分散。父亲也给毛驴套车启程回家了。我满脸灰尘,恋恋不舍地回望着像发过洪水的小镇集市,期盼着下一次赶集的日子。
追随“歪辫队”
最初在乡下教书的日子里,赶集曾是我生活中一味调料,是我释放郁闷的唯一途径。而这途径与“歪辫队”有关。
我教书的村里有六七个女孩,逢集日,一律穿着偏襟子枣红上衣,黑蓝喇叭裤,一根长长的辫子不在脑门正中,却偏到脑门左侧,辫根儿扎一方花手帕,身上斜挎着白色小皮包,骑着飞鸽轻便自行车,两手托前把,慢悠悠,一摆溜地在乡间小路上行进着,花枝招展的,招惹着前村后庄小伙子灼热的目光。久而久之,这一摆溜女孩有了一个别致的名字——“歪辫队”。我心里对“歪辫队”是满满当当的羡慕——羡慕“歪辫队”女孩的漂亮,佩服她们的勇敢、超前。她们是一柄划破乡野落后封闭的利剑,冲击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封建保守的心灵。
然而,羡慕归羡慕,自己却天生笨重懦弱,无法成为“歪辫队”的一员。我索性就追随“歪辫队”,当她们忠实的粉丝。逢集日,我尽力找机会,尾随着“歪辫队”赶集。一路上,我与她们始终保持一段距离。当快走到公路边的时候,“歪辫队”停下来,蹬支架放稳自行车,弯腰拍拍裤子,抬头翻翻衣领,再从包里拿出小圆镜和小梳子,对镜梳梳额头前面的刘海儿,摇摇头,意在抖落尘土,之后将圆镜、梳子装进包里,精神焕发地跨上自行车挤入赶集的人流。走到集市上,先寄存自行车,然后沿着旧街逛,去杂货铺买五色花线、鞋垫花布、绣花针之类物什。路过化妆品店或手饰商店,一定得进去看看。遇着价格实惠的,就买下;价格贵的,拿起看看,再放下,心里会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我现在买不起,将来一定有一个男人买来送给我。女孩子就这点强项,把实现不了的梦想可以寄托给未来的丈夫。即使实现不了,但美好的幻想完全可以消减当时的失落。
“歪辫队”终究是一树花,好景不长就“凋谢”了。在赶集的路上,被后生们滚烫的目光灼晕了,跌进了后生们的怀里如痴如醉,享受着青春的欢乐。待醒过来,就要“秋收”了,才明白该有婚姻了,于是开始物色媒人,提亲,订婚,结婚。为人妻后,很快就做了人母。
“歪辫队”解散了,我有种“物是人非”的失落感,赶集的次数也日渐少了。但每逢集日,仍坐卧不宁,魂不守舍,人在学校,心却跑到小镇的书店、服装店、老式照相馆,跑到人头攒动、人声吵杂的街巷中。
赶集已融入我的生活。村里人曾贬嘲“歪辫队”:“集集赶集集到,一集不赶不热闹。”而我是“一集不赶魂丢掉”——我得继续赶集。
每逢集日,多数是上课时间。我往往提前给学生上完课,吃过饭,上午一放学就骑自行车奔往小镇,赶下午一点钟上课再匆匆回到学校。有时赶集连一毛钱的东西都没买,且灰尘满面,但神清气爽,连日来的郁闷与疲惫荡然无存,之后又精力充沛地投入到繁忙的教书工作中,但私下里却忍不住默默掐算着下次逢集的日子,也思虑着我该穿怎样的衣服梳怎样的发型穿过拥挤的集市。
赶集,与爱情相逢
夏日雨后初晴,明知道路泥泞,会有陷进泥坑的危险,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去赶集,因为赶集已成习惯了。
果然,自行车行到一拐弯处,看到有车辙滑过的痕迹,我立即刹车。但晚了,自行车歪倒,车轮陷入泥浆。我急忙跳下来,一看还好,没陷进去,只是裤管沾了不少泥。我使劲从泥浆中往出拽自行车,但太沉,只好坐下来等待赶集的乡亲“救援”。不多时,一阵摩托鸣笛声由远而近,我心中惊喜——喜的不是等待到“救援”了,而是可以见到一辆飞驰电掣的摩托车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难得见到摩托车,偶尔见到摩托车飞一般从身边滑过,望着摩托车屁股冒出的一溜蓝烟,心中说不出的羡慕向往,幻想我未来的夫君如果也骑着摩托车带我坐在后面,那多风光啊!
摩托车过来了,但不是飞奔来的,而是慢腾腾的,渐渐停下了。摩托车上的小伙子下来了,穿着蓝条码褂子,裤管上也沾了泥。
“是不是自行车陷进泥浆了?”
我有点害怕:他停下来想干什么?
“嗯。你的摩托车也走不动了?”
“不是。我是想帮你把自行车拽上来。”
他一只手拽着自行车前把,身子稍微躬了一下,似乎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自行车从泥浆里拔出来。
小伙子骑上摩托车走了。我看到车后面挂着一块方形铁牌,上面写着“扬子江摩托”,我牢记于心,开始暗暗策划一场惊心动魄的恋爱。
此后在赶集路上,我开始留意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找寻写着“扬子江摩托”的牌子——只有找到它,我的恋爱才可能成功,才有可能惊心动魄。走到集市也不再无聊瞎逛了,而是留意一个穿蓝条码褂子的小伙子——我坐摩托车赶集的伟大梦想就得靠他来实现。偶尔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竟如此脸厚,小小年纪竟用如此“城府”来算计一个陌生男人。现在想来,反倒觉得欣慰:“脸厚”也好,“城府”也罢,那是我曾经热情拥抱生活的见证。
我赶集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扬子江摩托再也没有出现过,蓝条码褂子也不会出现了,因为风情夏季过去了,我都穿着毛衣赶集了。我后悔当初没问“蓝条码”是哪个村的,如果知道他是哪个村我就一定能将他搜查到。但晚了,换个目标吧!可下一个目标在哪呢?我现在的目标是飞驰电掣的“摩托车”,不是撒遍满街的“自行车”。
又一个夏季。学期末,我步行带领六个学生参加学区统考。恰逢集日,考完试,已是中午,烈日当空,又饿又渴,就与学生一起坐在地摊上吃凉皮和油旋,又买了一瓶五毛钱的汽水放在跟前,噎着了就喝一口。因为饿了,学生狼吞虎咽,我也全然不顾自己身为人师的文雅形象。很快就潦草吃完了,仰头喝汽水时,突然发现对面的木矮凳上坐着一个吃凉皮的小伙子,他一边吃一边向我这边看。他的吃相比我文雅,发现我注意到了他,就冲我笑。我觉得面熟,但想不起是谁,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也假惺惺回报以微笑。
他停下手中的筷子,问我:“你也赶集了?”
“嗯。”我的回答简短而没有温度。
“你认得我不?”他显然对我的冷淡开始质疑。
“很面熟,但想不起来了。你是哪里的?咱们在哪见过?”
“你的自行车曾经陷进泥浆里谁帮你拽出来的?”他说完得意地笑了,幸灾乐祸似的。
我的脸“唰”地红了。生活真能捉弄人啊,寻你寻了千百回,暗地里为你美丽了千百次,你却躲在我看不到的角落里。没想到,就要把你彻底忘记了,却在我最为“落魄”的时候,你奇迹般地出现了。
“记得,当然记得。那次你穿着蓝条码褂子,骑着扬子江摩托车。你今年比去年更帅了,所以我认不出了。”为了挽回我的“狼狈”吃相,拍了一句马屁,希望听到他对我的评价。但他只是笑笑,没言传。我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站起与老板娘算帐时,连同他吃的凉皮钱一并结算了。
“怎么能这样?你让我太不好意思了。”这次轮他脸红了。
“一直想感谢你,找不到机会。这次碰巧了,让我了却这个心愿吧!”我心里暗自得意:我要的就是你这份愧疚与不好意思。
他站起身,好像也不会说什么了。他问我:“是不是骑自行车来的。”我说:“不是。是步行。”他说:“那正好,坐我摩托车回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心里窃喜,可转眼一想,我坐摩托车,那学生咋办啊?把他们平安带回家,是我此行的职责。
“不行,我是带六个学生来考试的,要陪他们走啊。”我难为情地说。
“六个学生?”他思虑了一会儿,说,“我们村里还有两个骑摩托赶集的,我让他们每人带上三个学生,咱们就能一块回去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坐摩托车赶集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从此,每逢集日,我们学校坡底响起摩托车鸣笛声时,我就失魂落魄了。那年的夏天与秋天,我的自行车冷落在无人问津的仓库里,我开始坐着扬子江摩托车风光无限地赶集了。
再后来的事情,属于我的隐私,就此省略。可以透露的是扬子江摩托车后来完全变成我的私有财产,“蓝条码”小伙子则变成了我的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