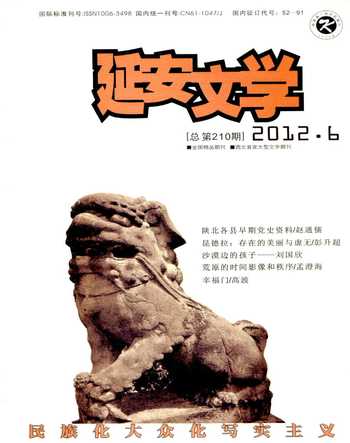寻找红砖墙
孟学祥,1964年生,毛南族,中国作协会员,贵州文学院签约作家。先后在《中国作家》《民族文学》《青年作家》等发表作品100余万字,出版小说集《山路不到头》、散文集《山中那一个家园》,曾获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
张全亮去找一个人,而张全亮又不认识那个人,那个人说他住的地方有红砖墙,张全亮就这样走着在城市中寻找红砖墙。而城市里到处都是钢筋,到处都是水泥,到处都是亮晃晃白森森刺激眼睛的瓷砖墙。张全亮去找红砖墙,张全亮走的是一条泥土路,没有经过水泥装饰的泥土路,这样的路在今天的城市中已所剩不多。脚下的泥土刚经受过雨水的滋润,粘粘糊糊的总想往人的身上沾。行人都远远地绕开这条路,只有几个小孩在路中的水坑边用石头垒了一道长堤。张全亮走近时他们往水中丢了一颗石头,石头在水中跳跃着将水花砸得飞溅起来,张全亮的白衬衣就在那时沾上了黄黄的泥印。水花飞溅起来后孩子们哄笑着跑开了,张全亮无可奈何,只好绕开水坑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一只狗躲在一扇门的背后,“汪汪”地叫着,叫过后又恶狠狠地哼几声。张全亮站在那扇门外,希望看到那只狗冲出来。但是那只狗却深藏不露,待张全亮走远后,狗才从门背后冲出来,“汪汪”地向张全亮示威。
这是一条与众不同的狗,是一条充满狗的个性且敢向人示威的狗,是一条没有被铁链和绳子拴着的自由自在的狗,是一条生活在城市而又没有被城管队员追杀的狗。尽管它没有咬张全亮,但它却用声音警告张全亮,不准张全亮走近那扇门。张全亮远离那扇门后,它虽没有追上来,但是它走出了那扇门,走到了这个除了人之外,不容任何动物乱窜的城市大街。狗站在门边“汪汪”地叫着,惹得几只被困在屋子中的狗也“汪汪”地叫了起来。张全亮看见几台推土机在泥土路的另一头挖掘着,装运泥土的汽车也在来来往往地奔忙着。一位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不无忧伤地告诉张全亮,这条路要改变了,要被人为地弄得面目全非了,这个城市里再也找不到一条属于泥土自己的路了。
城市的生活节奏总是匆匆忙忙,来来往往的人总是忙忙碌碌。大街上不见几个人,而车却是那样的多,车在城市的街道上穿梭来往,让人眼花缭乱。城市的大街是车路,是没有人走的路,车代替了人,车取得了合法的行路权。人不能在大街上乱走,人只能躲在车里,人只能在车上坐着,用心去感受车轮胎同沥青、同水泥路面的磨擦。车在城市的大街上横冲直闯,喇叭震天响,尾气排放得城市的空气中全是油烟味。
张全亮总也找不到红砖墙。张全亮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也不知道那个约他的人是不是也装在车里?张全亮站在城市的十字路口边,一辆车在张全亮的旁边很威武地鸣一声喇叭,浮躁地绝尘而去。没有清静的可去之处,鲜活的生命群体中,那种骚乱和激荡时时在耳边轰鸣。一群飙车的少年骑着车风一般从远处飞来,经过张全亮的身边时,有人“叭”地吐来一块口香糖,沾在了张全亮的衣服上。随后一阵尘土一阵疯笑,从张全亮的眼皮底下一闪而过。
张全亮不知道红砖墙在哪里,这也许就是张全亮的悲剧。但张全亮却没法让自己停下来,张全亮不停地走不停地寻找,就是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寻找到一个新的发现。那个约张全亮的人说,真正的寻找是让一个人孤独地在路上走。张全亮不喜欢孤独,但生活中制造孤独的人,却总是要将孤独强加于人,而自己却无缘去享受孤独。张全亮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在闹市中,这个人或许不孤独。但张全亮很孤独,在闹市中孤独的张全亮又常常在闹市的灯红酒绿中迷失自己。一对父母牵着一个孩子在张全亮的旁边站台上等车,车来了又走了,车门关上的那一刹那,年轻的驾驶员恶狠狠地问张全亮:你走不走?
黄昏夕阳下落后,天边结满了血红的颜色,远处有两个老人走了过来。那才是真正的走,他们一人一支拐杖,空着的两只手互相搀扶着,不知他们这样搀扶着走了多少年?或许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们就一直在互相搀扶着走,走过幸福走过艰难走过曲折,走过坎坷的岁月,走到老态龙钟,他们还在搀扶着走。他们走在浮躁的大街上,走在川流不息的车道边。他们互相搀扶的身影定格在夕阳下,他们将人生长路走得凝重也走得很圆满。生活中的许多浮躁都是人为制造的,要穿、要吃、要买房、买车,要养家糊口、要谋事、谋人、谋金钱、谋地位、谋仕途,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生活概念重叠在人生的肩膀上,才生出了那么多的浮躁。
张全亮去找红砖墙,找不加任何粉饰的,仍散发着泥土香味的红砖墙。张全亮感觉到他已经走过了这条路,但这条路没有终点,张全亮仍然又回到了起点上。张全亮一直都在努力寻找终点,而找到的每一个终点恰又都是另一条路的新起点。路边店的红灯笼发出闪烁的诱惑,几个用化妆品迷失了自己本性的女子,贪婪地用目光召唤每一个从门前走过的男人,躲躲闪闪中,那幽暗的门一闭一合,在外人的目光无法透视的世界里,上演着人生的另一种故事。
红灯笼下的故事很刺激也很悲壮。故事发生时,张全亮还不知道那故事的主角会是在他面前一本正经一身正气的头儿,女人走进张全亮他们的办公大楼,就犹如走进自己的家门,女人旁若无人地推开头办公室的门,就像在推开自己家卧室的门。于是在头儿的办公室门被关上不久,张全亮和同事竖起的耳朵,就听到了争吵声和厮打声。头儿狼狈不堪,气急败坏从办公室冲出来,大声吼叫,冲张全亮和同事发火。太不像话了,公然到办公室来扰乱工作秩序,打110,把她送派出所。张全亮的同事拨了11O。头仍气愤难消,仍在大声斥骂。女人从头的办公室走出来,将身子倚在门边,一脸坏笑一脸阴谋一脸的幸灾乐祸。警察推门进来,警察还没有说话,女人就上去拉头的手,脸上很陶醉很幸福,仿佛是拉着头去赴宴或去幽会。而头的脸却由白变红由红变白。头气急败坏,用力摔开女人的手,大声训斥张全亮和同事:谁叫你们多事,谁叫你们叫警察?
头就这样走了,就这样离开了他心爱的办公室,就这样被一个女人牵着走向了他不愿去的地方。头再回办公室,是纪委的人陪着来的,头无可奈何,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看着头无可奈何。头的夫人领着儿女冲进头的办公室,撬开头的办公桌,拿走了抽屉里的钱,然后又铁面无私同头划清界线,坚决不准头再进家门。头走上了那条充满诱惑,充满欲望而又无法走通,无法理喻的路。张全亮和同事们幸灾乐祸,心情畅快,大家假惺惺去看头,去同头告别。张全亮和同事用语言安慰头,装模做样陪头叹气。离开头张全亮和同事欢呼雀跃,一同冲进路边的酒馆。那天,张全亮和同事们每一个人都喝了个大醉。头被关在囚笼中,如一头野兽,不再有头的威风。头痛哭流涕对去看他的人念叨:女人不可太亲,女人不可相信,女人更不可深交啊。头栽在女人手里,头就恨女人,头咬牙切齿对那些去看他的人说:不要轻易相信女人。
故事的戏剧性往往都是一个沉重的结尾。头在位的时候,张全亮和同事们都讨厌头,张全亮和同事精诚团结,携手共谋对付头。张全亮和同事恨头用公款海吃乱花,恨头私设小金库,恨头独断专行,独霸小车。当面,张全亮和同事唯唯诺诺,背后,大家满腹牢骚大发议论。张全亮和同事常在酒后讲头的闲话,咒头不会有好终。每次看到头,张全亮和同事都点头哈腰,转身后,大家都恨不能在背后给头一刀子才痛快。头走了,张全亮和同事们兴高采烈,心情痛快,有人又瞄着头坐过的位置,开始较着劲展开竞争。竞争中的每一个人暗暗血红着眼盯着对方,所有的人都不再携手,不再做盟友。每一个人都恨不能在竞争中把别人重拳击倒,恨不能把别人踩在脚下,恨不能别人马上犯错误。于是就滋生了新的流言,找到了新的中伤对象,挖出了又一个潜在的敌人。
大家暗暗较劲争得头破血流,争得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大家无心工作,把心思都用在了跑位置上。没有头的那段时间,大家都少了许多约束,大家都不按时上下班,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外出打点,外出找人帮自己活动。唯有五十一岁的老马坚持天天来坐办公室,老马早想退休,老马想回他农村的家去陪伴老伴,共享天伦之乐,去同老伴一起,侍弄那年年都生长着旺盛生命的黑土地。别人白天跑关系,晚上趁天黑提着礼品揣着红包,如鬼子进村般去敲主管领导的门。老马充耳不闻,老马天天有滋有味地喝他的小酒。上级暗访和组织部门找谈话,人人都争着讲别人的缺点,讲别人的坏话,只是没有人讲老马的缺点,讲老马的坏话,都只讲老马的好处。大家都在互相提防,只是谁都没有提防老马。被找去谈话的人出来后,都是一副春风得意样,人人都认为自己稳操胜券,都认为自己就是未来的头。老马是大家都企望的一颗棋子,大家都千方百计讨好老马。老马最后一个被找去谈话,很多人都把目光切切地盯着老马。要不是办公室人多,每一个人都想拉住老马,让老马投自己一票。老马诚惶诚恐走过每一个人的面前,老马就像做错事,老马不敢看每一个人的脸,老马不想得罪身边的这些人,老马只想与大家和平共处,老马只想平平稳稳地享受他的副处,安安全全地把报纸看到退休。谈话出来后,老马脸变异样,老马像做了亏心事。老马不再专心看报,老马在位子上坐立不安。大家都盯着老马,都想向老马打听谈话的结果,但是大家却都没开口。
故事的结局,是不起眼的老马做了张全亮他们的头。老马在张全亮和同事忌妒、愤恨的目光注视下,人模狗样地搬进了那个属于头的办公室。矮矮的组织部长到办公室来宣读任命书的时候,大家的眼睛都死盯着他的脸看,看他是不是喝了早酒,或是熬夜太长,头脑发昏念错了文件,以至于组织部长念完文件,叫大家欢迎老马讲话的时候,大家都无动于衷,大家都没有拍手。尽管没有掌声,但老马讲话时仍春风得意,神采飞扬。平时三天不说两句话,但今天的老马就犹如换了一个人,讲话慢条斯理,抑扬顿挫,充满磁性。坐上了头的位置后,老马吹了头发,刮了胡子,穿了西装,打了领带。老马还重新改装了办公室,买来了高档的新沙发,和坐起来更舒服、款式更新颖更高档的办公桌椅,在办公室里配备了专门装钱的保险柜,装了一部专用电话,卖掉了六成新的小车,换了一辆更高档的新车,撤了原来的秘书,新任命了一名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老马不再喝小酒,老马经常出去吃宴请,老马对酒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马说他只能喝茅台一类档次的酒,而不能喝杂酒。老马挺胸腆肚不再平易近人,也不轻易与同事们说笑。老马当了头后,单位的一切又都恢复了从前的老样子。老马独自享用小车,并经常用公款去洗桑拿,大家上班仍然磨洋工混光阴,聚在一起发牢骚讲怪话。当老马面点头哈腰唯唯诺诺,背后又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大讲老马的坏话,都恨不能老马出车祸遭横祸,都想在背后飞一石头,将老马砸死才痛快。
张全亮走着去找红砖墙。张全亮走在红灯笼故事的后边,融入城市的芸芸众生中,寻找在众多近似聊斋的奇文轶事里。大街边的人行道上有几个人摆开桌子在打麻将,一群背着书包的少年正围在他们身后,聚精会神地观战,象征输赢的人民币,被他们很随意地堆放在麻将桌的一角。不远处那个卖烤牛肉串的摊子上,一个男人光着膀子,两手不停地在烤盘上上下翻弄,一边不停地烤牛肉串,一边又对着大街不停地吆喝,让声音伴随着牛肉串在火上燃烧释放出来的油烟味,传遍城市的大街小巷,一群背着书包的少男少女,吵吵嚷嚷地围在烤牛肉串的摊子边。一个一边喊和牌一边忙着收钱的中年妇女,把钱胡乱地堆到桌子的一角后,对大家说她的女儿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零食,就是不喜欢吃饭。她的话刚说完,另一个正在伸手摸牌的女人,立即抬手指着站在她身后聚精会神观战的一个半大男孩说:我们家小东也是爱吃零食不喜欢吃饭,你看都十四岁了还是瘦筋筋一个,脑子更不见长,都上初二了,写张假条跟老师请假,扯个谎都扯不圆。正说着,远处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女人立即对她身后的孩子说:小东你来帮妈摸一把,我去去就来。
小东帮他妈打麻将,打得聚精会神,打得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几个少男少女站在他的身后,也看得聚精会神看得兴高采烈,他们脸上发着红光为小东鼓劲助威,他们指挥小东出牌摸牌,集中几个人的智慧帮助小东。小东赢了钱,同桌的几个人很不高兴,他们数着桌上的钱,但是却不拿给小东。小东眼巴巴地盯着他们放在桌上的钱,有人一边把桌上的钱大把地搂进口袋一边说:这回和的牌不算,不应该给钱。其余的人也跟着大声地嚷嚷:不算,不算,等他妈来再重新打。站在小东身后的一大群孩子闹了起来:拿钱拿钱,不准耍赖。打牌的其中一人立即沉下脸来吼道:这是大人的事,你们小娃儿家的在这里捣什么乱?小东,你个学生崽来跟我们掺和哪样,去喊你妈来,她赢我们的钱就想躲,没那么便宜的事。小东妈妈来了,小东一脸无奈地从桌子上下来,一副可怜相地站在他妈妈的身后观战。
有人打架了!不知谁喊了一声。街这边刚才还在到处闲逛的人,都纷纷横穿马路朝街的对面跑,张全亮跟在人群的屁股后面,刚跑到街中间,从另一边急驰过来的一辆小轿车差点吻上了他的屁股。驾驶员一边把车刹停,一边从窗子里把头伸出来破口大骂:找死呀你,找死也不看地方,还想拉老子给你垫背不成!张全亮跑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下来回头看时,街上已经不见了停着的车辆和刚才骂人的司机,那辆想吻张全亮的车,又融入了远处的车流中。张全亮正在那里东张西望,寻找打架的地方,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张全亮面前走过,边走边声音颤抖地说:我刚才看见他拿出刀就那么一捅,被捅那个人的眼睛就瞪大了,等刀扯出来好一会,血才涌出来人也才倒在地上。哎唷,你没见倒地的那一分钟哟,那样子实在是太怕人了。有人接着说:不要讲了,那股血的腥臭味呀,搞得现在我都还想吐。哎,我们快走吧,一会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就麻烦了。直到这时张全亮才发现,刚才挤得满街满巷的人,现在都不知跑哪里去了。不远处的大街上,一个人躺在那里大声地呻吟,从他身上流出来的血,把他身边的水泥地都浸成了紫黑色。张全亮刚准备迈脚向那个人躺着的地方走去,一个人从身后拉住了他。张全亮回头一看,是刚才在街那边桌上打麻将的其中一个妇女,张全亮刚想对她说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拉我?张全亮还没有开口,那个妇女就小声对张全亮说:你是闲得慌了是不是?这种事情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要去惹麻烦上身。刚才我看到有人已经打了11O,再不走,公安来你就有麻烦了。她的话刚一说完,张全亮的耳边就传来了“呜哇呜哇”的警报声,张全亮立即转身,同那个不认识的好心妇女一道,融入了人来人往的商场中。
张全亮去找红砖墙,找那个约他的人说的那种充满泥土味的红砖墙。张全亮在大街上不停地走,不停地寻找不停地东游西逛。有人说张全亮这种人是浮躁的一族,说张全亮是那种一天上班无所事事,干领国家发的几个吊命钱混日子不思进取,但却又抱着一副忧国忧民思想,经常牢骚满腹的浮躁一族。张全亮父亲就看不惯张全亮的行为,他说他年轻时工作抢着干,从来就没想过玩,加班加点不计报酬,哪里艰苦就往哪里闯,一心想的都是报效集体和报效国家。哪像现在的人,工作不好好干,却心思一点都没少花,谋利益谋金钱谋地位,生就的完全是一副自私自利的面相,一点上进心和为国为民的思想都没有。张全亮父亲还说把国家弄得诸如腐败、用公款大吃大喝、找小姐玩女人、打着外出考察的旗号游山玩水等,什么乌七八糟的现象,就是张全亮他们这一代人自私自利、贪图享乐的思想造成的。张全亮父亲一副忧国忧民相,一天到晚喝完了他的小酒后,就是满嘴的唠叨满腹的牢骚,对社会不满,对国家的现状不满,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不满。张全亮的父亲说:共产党应该再搞一次整风运动,应该整治社会风气,彻底清除腐败,多枪毙几个腐败分子以顺民心民意,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张全亮不敢苛同父亲的观点。张全亮的工资老是不够用,一天到晚都在想钱,有钱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高档饭店,就可以买高档衣服,就可以买小轿车,就可以尽情享受生活,尝试在妻子之外养个二奶三奶,或者养一至二个小情人。没钱用的时候张全亮就爱胡思乱想,张全亮幻想能在大街上捡到钱,幻想买彩票中大奖,幻想自己也能有机会搞一次腐败,去潇洒一回人生。张全亮父亲说张全亮思想有问题,张全亮的头老马也说张全亮的思想有问题。张全亮不反驳他们,张全亮不想同他们一般见识。张全亮继续往前走,他还得继续去找红砖墙。
张全亮只顾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从身边走过的一个漂亮女孩,只顾盯着她超短裙下白白的大腿,只顾盯着她那欲跑出上身背心挺拔诱人的乳房,一不小心就撞在了迎面走来的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一把揪住张全亮破口大骂:看着路点,不要乱撞,我这里又不是女人的胸部,想吃奶也不看个对象。他的话立即引来了一阵哄笑。张全亮狼狈不堪脸红到耳根,但却不敢有任何怨言,只能在人们的嘲笑声中,急急忙忙地往前走。身后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像吃着了苍蝇一样很响地吐了一口,一身正气地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这大天白日的,就敢当众耍流氓。
张全亮站在一块巨幅广告牌下面,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拿着一把剃须刀的女模特。张全亮正在猜她那十分显眼的乳房,是不是也垫了海绵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一个嘴唇涂得血一样红的女孩,从广告牌下的玻璃门中跑出来,跑到他的面前拉着他,叫他到她那里去洗头去理发。她说她的服务很周到,她可以全方位为张全亮服务,一定让他满意,一定让他全身心都舒服,一定让他去了一次以后,保证下次还会想去,一定让他终生受用永生难忘。张全亮没有去洗头,张全亮没有洗头的钱,张全亮的钱仅仅只够吃饭。尽管张全亮的目光贪婪,心中充满欲望,但还得装着一本正经地往前走。张全亮还在想那把拿在女模特手上的剃须刀,想女模特那十分显眼过分耸立的乳房,想剃须刀与乳房的关系,剃须刀与女人的关系。长了胡子的男人没有资格手握剃须刀站到广告牌上去,没有长胡子的女人却在大街上,帮男人拿着剃须刀亮相,长了胡子的男人不用刮脸,没长胡子的女人专帮男人刮脸。
张全亮无法走出城市的禁锢,就像那些从远处山上被搬到城市里来的树一样,不喜欢城市,但又不得不在城市里扎根生存。城市里年年都在栽树,年年都有人出来大喊大叫要美化和绿化城市。但城市里年年都栽不好树,年年都看到一排排树在被栽上不久后,就一棵棵干枯死去。城市里天天都有人在高喊爱护环境,爱护树木,但城市里的树木却天天都要受到人为的攀折和摇动,有人甚至于还往树根脚下倒脏水,倒油污水,堆放置树于死地的垃圾等废物。张全亮走在春天城市的大街上,一片树叶飘落在张全亮的头上。张全亮问一个把摊子摆在人行道上卖小吃的摊主,为什么要把脏水倒在树根脚下?摊主一脸奇怪,一副居高临下地看着张全亮,用一副很冲的口气说:我不倒在树根脚下,难道要倒在人行道上,倒在大街上,等着城管等着检查卫生的人来罚款?张全亮对她说,倒在树根脚下树就不会成活,树就会死去。摊主说树死不死不关她的事,只要她不被罚款就行。张全亮无言以对,只好向前走去。在人行道上设摊的人,都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盯着张全亮,就像观赏一头途经城市的少有珍稀动物。张全亮走过去好远,都还听到摊主说他是神经病。没有人会去注意在春天落叶的树木,也没有人用时间用心思,来关心那些不会说话的树的死与活,更没有人会用一个与己无关的问题,来困扰自己的思维让自己自寻烦恼。落叶从树上飘落下来,飘落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还来不及品尝水泥的滋味,就立即被清扫掉,然后又被装上垃圾车,连同城市的垃圾一道被运出城市,被运往那些被称作郊区的农村。
张全亮被城市的繁华和热闹包围着,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的脚步。城市把住人的空间和范围扩大了,把人们大脑的思维和想象缩小了。站在门边招揽顾客的服装店老板,看到张全亮走过来,热情地连叫几声“老板”,并把他拉进他的店内。张全亮不想买衣服,老板却对张全亮很热情,他不吝口舌,不厌其烦地向张全亮介绍他的服装,他喋喋不休,殷勤地向张全亮推荐他的每一件衣服。老板说他的所有服装都是名牌都是高档产品,价格也非常便宜,说像张全亮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男人,穿上他的服装会更潇洒更有气质。他的话很入耳,让人听着也很舒服。但张全亮口袋里没有几个钱,张全亮没办法潇洒,也没办法让自己更有气质。趁老板不注意,张全亮立即逃离了他语言的包围,逃离了他的小店。见张全亮不买衣服就离开,老板在他身后骂了一声“穷光蛋”。走出好远张全亮再回头时,老板又热情地站在大街边,招呼起另外一些走过他小店门口的人。
城市的错综复杂让张全亮一直都在走弯路。张全亮寻找在城市的阴影里,在芸芸众生中,不断地把简单的人生走得复杂走得凝重。张全亮在不断地寻找着,许多与张全亮同龄的人也在到处寻找着,寻找快乐的人生路,寻找让人轻松让人愉快,让人无忧无虑的路。那个约张全亮的人说,寻找很累很苦也很折磨人。张全亮没有找到红砖墙,张全亮迷失在现代生活中无力自拔。张全亮的一些网友嘲笑张全亮,说张全亮没有现代意识,说何必折磨自己,何必把自己搞得太累,有时间可以去唱歌跳舞,可以去洗头修脚,可以去玩玩三陪小姐,还可以在网上找个情人玩个心跳。
张全亮在寻找中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修脚屋,又不知不觉地找了三陪小姐,然后又不知不觉地迷失在酒吧,像是刚刚过去不久,也像是在昨天吧,张全亮才从酒吧里面逃出来,从酒吧逃出来的时候,张全亮还三十岁都不到。那时候张全亮还年轻,年轻的张全亮就理直气壮地在城市里面寻找着,寻找青春的梦想,也寻找朦胧的诱惑,和远方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目标。张全亮站在城市的大街上,看见一些人走进了街头随处都可以见到的修脚屋,另一些人在朦胧的灯光下,到路边店去找了三陪小姐。张全亮还看见一大群背着书包的男孩女孩涌进网吧,涌进那个不需要遮掩,而完全可以赤裸裸地向外人袒露心扉的自由世界。正在想心事的张全亮几乎撞上了人行道中央的电杆,电杆上四周都贴满了根治性病和治疗阳萎的广告。根治性病和阳萎的广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稍不注意,这种广告就会贴上你的家门,仿佛你就是性病患者,你就是阳萎患者,你正在需要治疗一样。
张全亮父亲看不惯当今的生活变化,喝酒喝多后就爱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他说社会进步了生活好过了,而日子却变化得让人越来越无法相认了。张全亮父亲是从农村走入城市的,进城五十多年仍依恋农村,他说只有农村那片没有受到污染的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张全亮的父亲还说,他就是农村的儿子,大山的孙子,城市的养子。张全亮父亲身上骨子里那点遗传下来的农村基因,虽然没有改变,但也没有遗传给张全亮。张全亮迷恋城市,但对城市却深爱不起来。张全亮的父亲向往农村,退休后一天无所事事就更加向往农村,要不是张全亮母亲阻拦,他早就丢下家人远离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张全亮母亲骨子里没有农村人的遗传基因,她不喜欢农村,张全亮爷爷奶奶在世时,他母亲去过一次农村,回来后她说她再也不愿踏上那片土地。退休后,张全亮的母亲一天到晚热衷于同一大帮退休的老太太到广场上去跳健身舞。她警告张全亮的父亲:要去农村就你一个人去,我是不会跟去的。母亲还当着全家人的面,数落了一大堆农村的坏处。张全亮的父亲说服不了他母亲,心中很苦闷,就只能呆在城市的家中,天天喝小酒,发牢骚。张全亮想走出城市走到农村去,但爱人也不喜欢农村。张全亮爱人所在的国营厂在红火了十二年后,就被迫停产了,她本人也在这种“国有企业倒闭,私营企业找钱”的怪现象中,成了众多下岗工人中的一员。爱人成了无产阶级,成了除一肚子牢骚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无产阶级。爱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天天出去找工作,经常去应聘经常交报名费,但经常得不到回音。城市里失业的人多,招聘的地方也多,招聘的广告比失业的人更多。张全亮说农村天地广阔,劝爱人到农村去发展,去寻一片大山来重新设计他们的未来。张全亮爱人说她就是在城市饿死,也不会走向农村,就是在城市月月领低保,也不会去那些除了石头,除了泥土,什么都缺的地方搞什么发展。
张全亮走不出城市,很多同张全亮一样的人都走不出城市。张全亮沉迷在城市中,被城市的高楼挡住了向前看的目光,只看到楼房,只看到水泥钢筋的方寸之地,只看到车水马龙的繁华和琳琅满目的长街。而城市却把触角伸向农村,城市吞噬农村的土地,在一片又一片肥沃的农田上,建起了楼房建起了厂房。同时城市也把污染和垃圾推向了农村,城市的延伸让农民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山上的树木在工厂排放的污染空气中干枯死亡。城市把触角触碰到的大山,一个一个地推掉铲平,使山不像山土不像土。城市的脚步走到哪里,哪里就不得安宁。城市的声音传到哪里,那里的山那里的水以及那里的土地,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张全亮寻找着红砖墙,约张全亮的人用诱惑的声音领着张全亮往前走。往前的概念就是那么夸张,夸张到张全亮一走上去,想停都停不下来了。前面路口上那幢修好使用还不到十年的商业大楼,昨天才被炸掉,工人们正在满天的灰尘中清理垃圾。听说除了这幢大楼外,还有好几幢大楼都要被炸掉。那些曾经代表这个城市文明和繁华的建筑物,在走过了一段历史的辉煌后,就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有人说中国的城市规划就是建了拆拆了建,今天刚搞好的规划,说不定明天就要被推翻,今天刚建好的房屋,说不定过了一两天后,就要被拆下重建。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现象,是中国城市发展几十年所形成的一种通病。
有人在远处叫张全亮的名字,张全亮好不容易才在人群中发现叫他的人。那人跟张全亮同一幢办公楼但不在一个办公室,那个人很热情地同张全亮说话,陪张全亮走很长的一段路。在街头分手时,那个人还很热情地说张全亮有事一定要去找他。他说他已经调到了某某局,任副处级干部并主持工作,他特别强调了主持工作这几个字。他走了张全亮还愣在街头,还愣在他那自信的喜悦中。其实张全亮和那个人并不怎么熟悉,平时上下班见面的时候,都很少打招呼,或者最多也只是点点头就过去,并且有时张全亮对他点头他还装看不见。有一段时间,他陪某领导到张全亮的单位进行干部考察,张全亮同他打招呼他都装听不见。今天就不同了,今天那个人升官了,所以就变得很热情了。有人说男人一生有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但是张全亮一件都没有碰到,升官没有张全亮的份,在单位干了二十多年,四十出头了都还只是个科级;发财更不用说,张全亮天天都梦想发财,但张全亮就是发不了财,工资册上的工资,常常都是扣掉比领到手的还要多;张全亮的老婆也还好好地活着,还常常在张全亮领工资回家后,把张全亮衣服的掏空,连一枚硬币都不会给他留下。所以张全亮热情不起来,也高兴不起来。张全亮愣在街头,愣在那个人带给他的热情中,直到那个人融入街上的芸芸众生中,快要从他的眼中消失时,他才冲着他的背影骂出一句最时髦的国骂。机构改革的风吹到张全亮所在的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行政编制人员已经超员了五百多人,于是政府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各单位男五十岁以上、女四十八岁以上年龄段的人,都统统给这些人上一个级别加四档工资,然后动员他们退休。虽然退了一大帮人,但仍然没有缓解人员的压力问题,很多人将面临下岗或者失业,在这种情况下能保住原来的饭碗就不错了。张全亮升官的欲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压制下去的,张全亮报名参加单位的中层干部竞争上岗,在审查资格的时候,组织人事部门的人说张全亮的年龄已经超过,没有资格再参加竞争。张全亮说我不参加竞争,就会被淘汰就要下岗就要失去饭碗,他们说组织会考虑,组织不会让他下岗,更不会让他丢饭碗。然后张全亮他们一大帮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听从组织的安排,眼睁睁看着那些年龄比自己小的人通过竞争走上领导岗位。张全亮失去了竞争资格,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张全亮有年龄优势的时候,组织上没有给他机会,等组织上提供机会的时候,他又失去了年龄的优势。
机构改革把五十岁以上的男人和四十八岁以上的女人都改成了老人,都改成了退休回家无事可做的一个特殊群体。机构改革也把四十岁以上年龄段的人,改成了单位上年龄最大的人,改成了在单位上最受尊重,而又没多少事可做的人。退休回家的人说他们不愿退休,他们还有精力还能够做事情。在单位上班的四十岁以上的人说想退休,说退休以后还可以去找别的事情做。张全亮就在这种情况下走出了单位的大门。张全亮走出单位的时候,单位里还是乱糟糟一团,老马退休了,但老马还锁着他的办公桌,那几个退休的人,也还锁着他们的办公桌不愿腾出来。张全亮走不出这种特殊的现象,无法挣脱那种长期形成的固定脚步,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坐在办公室,坐在单位给他提供的位置上,心却反而忐忑不安。张全亮曾想过辞职,想到社会上去闯荡去干一番事业,但家人和朋友都极力反对,很多人都对张全亮说,四十多岁的人应该成熟了,不应该再冲动,说在单位没有多少事做,但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虽发不了财但也不会饿死。有一个单位就意味着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说什么也比在外到处颠簸强。最终张全亮没有走出单位的大门,张全亮坐在单位提供的位置上,数着四十岁出头的光阴,数着未卜的前程。
张全亮没有找到红砖墙,也无法找到那个约他的人。在街边人行道上打牌的几个老人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红砖墙,也不需要红砖墙了。城市里没有红砖墙,乡村里也没有红砖墙,城市在变化乡村也跟着在发生变化,红砖墙的时代早就消失了。
张全亮愣在街头,愣在一种淡淡的失落中。张全亮决定不再寻找红砖墙,前面的路很长,他还必须得更加努力地朝前走。尽管城市的陷阱很多,但是没有走到终点,张全亮是不能停下来的。人生这种走走停停的寻找方式,凭个人的主观意志是没办法终止的,张全亮还得要开始新的寻找,去力求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责任编辑:侯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