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棠
非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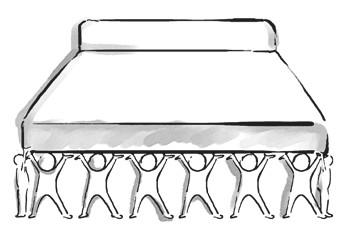
朱广印安静地坐在向阳商店门口,两只蚂蚁在他宽阔的背上漫无边际地驰骋。那株老甘棠树站在不远处的土堆上,像与他作对似的看着他,枝繁叶茂,核桃大小的棠梨在叶间静静地挂着。
没有一丝风,已经是近黄昏了,但依然热得人浑身冒汗。
头顶轰隆隆滚过一个炸雷,让朱广印打了个哆嗦,他往西天看看,赤红的云火焰般在燃烧,染红了远处的房屋和田野。
那年,也是一个这样闷热的夏天,长时间的干旱,让甘棠村的人和牲口都失去了力气,那株甘棠树的叶子打着卷不停地往下掉,树梢已经稀稀拉拉。
从头年冬天就没落过一场雪,春天也没见一滴雨,田里的麦苗干死在地里,黄河只剩下一条气若游丝般的细线,河岸裂开两指宽的缝,干泥像瓦片一样翘起来,踩上去脆响。
队长朱伍愁得满嘴燎泡,嘴唇上暴起一层干皮,他仰起头对着天上的云彩看,把脖子都看酸了,可每天那云彩都躲着不出来,天空蓝得跟染缸里捞出来的布一样,没有一丝儿杂质。朱伍爹说:不行,去娘娘庙那儿求雨吧,咱偷偷去。
朱伍把眼瞪得跟牛眼一样:爹,你疯了?上头知道了,你还活不活?
朱伍爹说:那你倒是想个辙啊,再旱下去,今年绝收不说,人跟牲口都要旱死哩。
第二天,朱伍把甘棠树上挂的那个洋铁车轱辘敲得当当响,把全村人召集起来,说要打井,战天斗地,要从地下找水。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朱广印。那时候的朱广印还是个精壮的汉子,留着络腮胡子,说话跟吵架一样粗声大气。他说:屁,咱村地势这么高,打井得打多深,等井打好了,都渴死个屁了。有人跟着附和:就是,没听说远水解不了近渴,那还有黄河哪,咋不去引?朱伍让朱广印说个解决的办法,他说:我又不是干部,不操那淡闲心。
吆喝来吆喝去,谁都没有说出个子丑寅卯,天依然热得人浑身冒烟。没有更好的办法,朱伍只好带着劳力在村里打井。
朱广印赤肚躺在家里的苇席上摇一把破蒲扇,跷着二郎腿,一只脚打着节拍,听收音机唱《朝阳沟》,心想:妈的,我才没那么傻,这么热的天去打井,朱伍纯粹是脑子有毛病。
吃完他媳妇做的蒜面条,朱广印又躺到炕上呼呼睡到半下午,起来擦擦脸上和身上的汗,到处黏糊糊的,干脆去黄河里涮涮。
从甘棠村一直往西,下了坡,穿过陕州老城就是黄河。河水细了浑了,原本气势磅礴的河水变得有气无力,跟一个患了肺痨的病秧子似的。
朱广印走进河里,让泥汤样的河水洗刷著黏糊糊的自己。有鱼碰着他的腿,他来了兴致,干脆在河里摸起了鱼。
一个下午,朱广印摸到了三条大鱼,他把裤子的两条裤腿打个结,鱼装进去,拎着裤腰回去了。那天晚上,他家炖鱼的香味飘了半个村子。
吃了鱼,又歇了两天,朱广印觉得可以去上工了。见他背着铁锨,朱伍问他这两天咋没出工,干吗去了?他说有事。朱伍说,谁家都有事,有事也不能两天不上工,这两天工分扣了。
扣了?一天十二分,年底可就是三毛七分钱啊!朱伍咋说扣就扣了呢?朱广印不乐意了,他不能让这两天的工分白白损失了啊。
回到家,朱广印越想越气愤,他媳妇还骂他:该!谁让你搁家挺尸,还摸什么鱼,这下好几毛钱没了,吃屁你?不行,他得想办法把两天的工分弄回来,不然亏大发了。
朱广印去找朱伍,他说:你把这两天的工分给我记上。我没上工是真有事,有大事。
朱伍端着碗正在喝汤:你能有屁事,懒事。
朱广印说:我给咱村改村名去了。
朱伍手里的碗差点儿掉下来:广印,可不敢胡来啊!咱这甘棠村叫了多少辈了,好好的,你改啥改,谁让你改的?
朱广印说:你看,是这么回事,旱这么久了,你还鼓捣大家打井,甘棠甘棠,可不就是干塘干塘嘛,咋能打出水来?更何况,我们村要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向阳,社员都是向阳花。
朱伍说:不行,甘棠这名好好的,从召公来的,都是有典的,不能改。
朱广印说:我已经给公社汇报了,公社领导很同意我的意见,谁不同意就是反革命。
朱伍看着朱广印得意的样子,恨不得把手里的碗扣到他脸上,但他不敢,他不想当反革命。
甘棠村改为向阳村这件事,是朱广印向村民宣布的,他激动得手舞足蹈,差点儿从土堆上摔下来:我们要拥护向阳村,坚决反对甘棠村,谁不同意就革谁的命。
没有人敢反对,包括朱广印去公社汇报甘棠村改为向阳村的时候,公社领导也真同意了。从此,甘棠村变成了向阳村,朱广印的两天工分记上了,七毛四分钱年底也分了。
这件事算是朱广印人生里的亮点,一个大手笔。他经常会把圆鼓鼓的肚子拍得嘣嘣响,给他儿子显摆:你爹我大小也是个人物,为七毛四分钱把咱村的村名都给改了,知道吧,这就是我干的,除了我,谁敢?谁?
拍着拍着,朱广印就老了。曾经的风云都变幻成了过往,几十年过去,他不拍了,这件事提也不再提了,但甘棠村的村名却再也改不回来了。
红得火烧似的西天,又滚过一个炸雷,年近八旬的朱广印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摇摇锃亮的光头,好像要把爬上脑袋的蚂蚁晃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