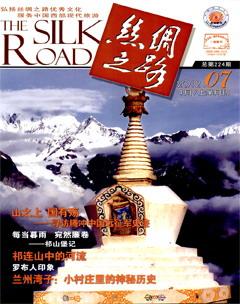甘谷古堡的背影
王琪
亘古的季风,吹过无垠的旷野。夕阳里,连绵的黄土高原上,一座座苍老颓败的古堡,在秋风中瑟瑟发抖,随风而落的土渣,旋即化为灰尘,如一声声沉重的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曾几何时,堡子作为求生路上的避难所、逃难人群的集中营,托付过生命的安危,寄存过颤抖的灵魂。而今,它像一枚在时光风烟中发黄的落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古堡,作为古代一种抵御外来侵略的防御工事,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承载着独特的人文内涵。早在周代,周人为防御外来入侵,就建有连接城墙和城垛的烽火台,这大概是我国最古的城堡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抵御塞外来侵,修筑了万里长城,寄寓了一个帝王千秋万世永保江山的梦想,这是我国最宏大的“古堡”了。到了汉代,西北地区为了防御胡人入侵,朝廷下令修筑“连城堡”。南宋时期为抵御金人入侵,西北一带修筑了大量土堡。但是,无论秦始皇的万里长城,还是老百姓的民间土堡,最终都没能抵挡住呼啸而来的奔腾战马,历史一再被马鞭改写。只有心灵的自信和精神的强大,才能抵御来自外界的任何压力。国如是,人亦然。
甘谷地处“甘陕之关锁,益梁之咽喉”。加之山皆复岭,古时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乱频繁,匪患不断,因而,境内多置堡、寨,操兵练马,以保安宁。甘谷堡子数量多、占地广、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堪称陇上一奇。据说现在甘谷境内遗留的土堡尚有200多处。其中,最古老的是汉朝时在今磐安四十铺所建的四十铺堡,最著名是在今大庄乡城子村修筑的甘谷堡,又名筚篥城。甘谷土堡多系明末清初所建,多居山尖,依势而建,或圆或方,以方居多。其堡墙一般宽6米,高10米,占地10余亩,亦有大者占地数十亩。礼辛下堡子,现内有居民30余户,至今堡墙完好。
堡子于我,既熟悉又陌生,既简单又神秘。在浅淡而平常的生命岁月里,我曾无数次地遥望过古堡,它们居于山巅,远离大路,静穆、淡定、神秘、久远,目睹过凄凄惨惨戚戚的故事,收藏过隐隐约约、扑朔迷离的传说,见证过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变迁。每当我凭窗眺望或注目凝视时,总会无端想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的诗句。古堡,它没有风的走姿,没有鸟的意象,静止是它的姿势,守望是它的宿命。然而,在那些兵荒马乱的峥嵘岁月,在那些匪乱横行的乱世年间,对于手无寸铁、老实本分的庄农人而言,堡子就成了他们安全的保证、生命的寄托。
爬满堡墙的层层青苔,无言地诉说着土堡的久远;随风摇曳的猫儿草,轻轻地讲述着曾经恐怖的传说。甘谷民间,就留传着很多关于堡子的民谣和传说。如:“黄羊堡上拉力人,石峡堡上盛血盆。”这句曾流传于甘谷境内的民谣,让人听后毛骨悚然,心有余悸,也让古堡蒙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和异常诡异的迷雾。黄羊堡位于甘谷觉皇寺村东南的山顶,民国三年(1914),白朗军攻伏羌城不下,遂东移川道区。那天阴风凄凄,大雨滂沱,黄羊堡人万众一心,顶风冒雨,连夜奋战,砌筑堡墙。天亮后,白朗军一眼望去,整齐坚固的堡墙,巍然而立,倒吸一口冷气,一致认为黄羊堡人人心齐,力量大,不能贸然攻打,便转攻石峡堡,杀死无数民众,惨不忍睹,石峡堡人全部遇难。于是便有了那句让人至今胆战心惊的民谣,这也大概就是民间传说中“跑白狼”的故事。类似这样的民谣还有许多,如甘谷大石乡传有民谣:“下堡砦,紫金城;上堡砦,马踏平;付家堡砦一盏灯,王川堡砦盛血盆。”甘谷磐安传有民谣:“三十铺下一盏灯,五十铺下紫金城,石家窑下鸡眼睛,四十铺下盛血盆。” 每一句民谣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都是一段黯淡无光的惨淡日月。历史远去了,只留给我们长长久久的安宁与幸福祥和的日子。
岁月荏苒,时光流逝,在如流的光阴里,一些堡子已经消逝,人们只能在诸如东堡、西堡、李堡、张堡这样的村名里,追忆回想堡子浅淡的意象、模糊的背影;一些堡子正在消逝,它们虽然躲避着人们的视线,远离大路,居于山巅,却苍颜白发,垂垂老矣,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一如夕阳里一枚被秋风扫下的落叶,悄然回归大地,不留恋曾经的坚持,不纠缠有过的悲苦,只把苦难与伤痛丢在荒远的古道,只在身后留下长长久久的幸福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