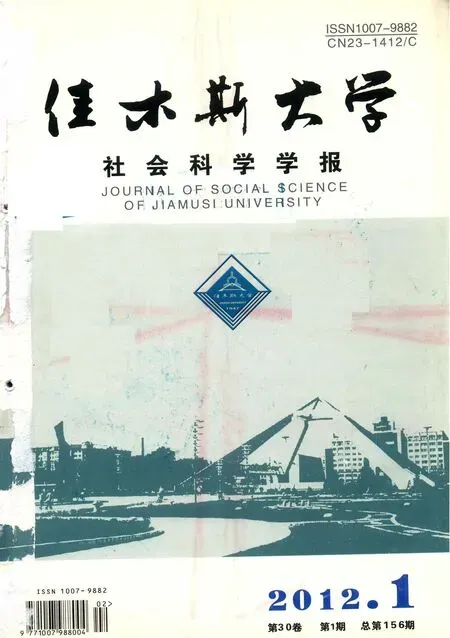试析宇文虚中羁旅金营时期的诗作及其心路历程①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试析宇文虚中羁旅金营时期的诗作及其心路历程①
李秀莲
(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宇文虚中羁旅金营时期的诗作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弥补了虚中滞留金营期间历史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通过诗作研究进一步印证虚中出使金营的原因与目的,客观地再现他在金营的困顿与守节信念的消失,最后,回宋无望,在被迫与无奈中入仕金朝。
宇文虚中;诗作;宋金关系
宇文虚中从出使金营到入仕金朝(1128-1134),有五六年的时间困厄金营,他渴望归宋,但祈请徽、钦二帝的使命不完成,不能回宋。他的心情很复杂,外在环境的变化牵动他的心情,书写这样心情的诗文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本文通过以诗证史,以史释诗,期以更清楚地认识虚中由宋朝使臣转为仕金的心路历程。
一
宇文虚中(1080-1146),字叔通,成都华阳人。登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第,历官州县。入朝为参议官,资政殿大学士,除签书枢密院事。北宋末年曾三使金营。南宋初年,因政敌短毁,又被罪四出金国,羁旅不返,被迫入仕金朝,被迫者内心无法排泄的矛盾通过与女真贵族的冲突而外显,最后被女真贵族构陷而举家罹难皇统朝。
北宋末年,虚中的仕宦经历在宋金的战局中起伏,他一面进言指陈与金和议之危害①,一面为和议而奔走。金兵再困汴京城,虚中往复三使金营。一使是辨姚平仲劫营非朝廷之意;二使是改以肃王枢为质,请康王构归,使回,除签书枢密院事;三使是交涉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对金人索要三镇,虚中泣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州,讵忍割弃”[1](P11528)。金军甫退,台谏言官便以三镇议和之过归罪虚中,虚中上《自辨奉使事疏》[2](卷215,P1)申诉。
尽管割让三镇与虚中无关,但他还是被一贬再贬。罢知青州,寻落职奉祠。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窜韶州。宋廷反省因议和误国的过失,虚中成了徽、钦二帝投降政策的牺牲品,被上议和之罪。《三朝北盟会编》记载:“虚中既奉三镇诏书至金人军中,自以为有和戎之功。识者笑之”[2](卷215,P6)。
建炎二年,康王寻求出使金营者,虚中自被贬途中应诏,复资政殿大学士,祈请使。虚中第四次出使金营,目的是请回二帝,立功复官。徽、钦二帝能否请回取决于宋金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取决于金对宋的态度,女真贵族没有存留赵氏国祚的打算,天会五年(1127)三月,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非赵氏傀儡政权的建立表明了女真贵族的态度,放回二帝是不可能的。祈请二帝的差事能落到被贬的虚中身上,说明南宋官员清楚地认识到请回二帝的难度。虚中把复官的赌注压在请回二帝的身上是必然要输的。
二
初到金营,虚中很茫然,对生对死皆茫然。建炎三年正月(天会七年,1129),与虚中一同出使的副使杨可辅归宋,金遣虚中归,他说,“奉命北来祈请二帝,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1](P11528)。请回二帝对他回宋至关重要,是他回宋唯一的希望,“尝梦挟日以飞”[2](卷215,P5),也确实反映了他内心的期盼。
尽管很茫然,但他对请回二帝抱有一线希望,持节的信念也是坚定的。《己酉岁书怀》[3](卷1,P7)写到:
去国匆匆遂来年,公私无益两茫然。
当时议论不能固,今日穷愁何足怜。
生死已从前世定,是非流与后人传。
孤臣不为沉湘恨,怅望三韩别有天。
茫然不能自持的虚中想到屈原“忠而被谤”,“不为沉湘恨”,以宽慰自己的失意,希望自己留在金营能扭转形势。“三韩”原指古代(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左右)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弁韩、辰韩三个部落,诗中借指东北,二帝当时驻地韩州,“怅望三韩”是对二帝的殷殷关切。
请回二帝越有希望,他持节的信心节越坚定。《从人借琴》[3](卷1,P7)云:
峄阳惯听凤雏鸣,泻出冷然万籁声。
已厌笙簧非雅曲,幸从炊爨脱余生。
昭文不鼓缘何意,靖节无弦且寄情。
乞与南冠囚絷客,为君一奏变春荣。
诗中的“南冠”有典故在其中。《左传·成公九年》记有:“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指楚冠,是楚国的使者,促成秦晋之盟。这里虚中自喻为“南冠”,是有背景的。天会十年(1132)八月,金人让虚中传话宋使王伦、朱弁,“言和议可成”[1](P11551)。《宋史·王伦传》记载:“粘罕(宗翰)忽至馆中与伦议和,纵之归报。是秋,伦至临安,入对,言金人情伪甚悉,帝优奖之”[1](P11523)。宋、金史料都记载了天会十年金遣王伦归宋告议和可成而宋帝大喜。这就是虚中“为君一奏变春荣”的谜底。
金宋议和活动确实给虚中带来请回二帝的希望和自己回宋的希望,“靖节无弦且寄情”道破了虚中持节的前提条件是有希望,有希望者心情也特别好,诗中写“凤雏鸣”、“万籁声”。
三
虚中在金营始终称自己是“客”,天会八年(1130),伪齐政权建立,元帅府密议以张孝纯相刘豫,便以遣归故里诳孝纯,实曲道迫其仕齐。时孝纯、虚中俱在云中,且不知内情,孝纯将行,虚中寄诗与孝纯,其断句曰:“有人若问南冠客 ,为道西山赋蕨薇。”[2](卷149,P11)“客”者的心情与亡国者的心情是不同的,不同的心境导致他们诗作的意境也不尽相同。虚中曾与吴激等集会燕山,宴饮时,出佐酒的侍儿本是宣和殿小宫姬,虚中、吴激等对同一情景各赋长短句。
虚中成《念奴娇》[5](P3):
“竦眉秀目,看来依旧是,宣和妆束,飞步盈盈姿媚巧,举世知非风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劝人满饮,旋旋吹横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行相熟。旧日黄花,如今憔悴,付与杯中酉录。兴亡休问,为伊且尽船玉。”
吴激作《人月圆》: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洲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二者词作造诣高下历史上已有定论②,不必赘言。但造成诗文高下的不同处境与感情因素尚鲜有谈及。对宋朝的灭亡,虚中据事直言:“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兴亡休问”。笔触着意在叙事、在身外。吴激是燕山失陷时被俘者,是亡国的遗民,所言“南朝千古伤心事”,从心底发出的呻吟是切肤的亡国之痛,与因亡国而飘零的小宫姬是同样的命运,是有“同是天涯”之句。“闻者挥涕”[6](卷13,P4),方触动虚中,使之“茫然自失”[3](P539)。虚中虽也有流落天涯的感觉,但他认为自己是“南冠客”,是负有使命者,暂且流落天涯,“客”的身份隔断了他与吴激、小宫姬心与心的相知。
词中的“客”字是很重要的信息源,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背景。此作品当写作于虚中羁留金营时期,而不是皇统二年(1142)。有人根据《容斋随笔》卷十三载:“先公(洪皓,笔者加)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纪之,闻者挥涕,其词云云。”又《容斋五笔》卷三的记载:“至于壬戊,公(洪皓,笔者加)在燕,赴张总侍御家集……”两则资料相综合,虚中等人的集会便发生在皇统二年[7]。根据虚中《念奴娇》的意境,其词不会作于皇统年,皇统年虚中已入仕金朝八年,为金朝做了许多事,也是这年,金移文宋国,理索虚中等人家属,子师瑗携家北来。这样情况下,虚中不会如此矫情地称自己是“客”。
虚中自燕山归来,作《还舍》[3](卷1,P4)一诗,对赴燕山与吴激等人的集会有许多补白:
燕山归来头已白,自笑客中仍作客。
此生悲欢不可料,况复吾年过半百。
故人惊我酒尚狂,为洗缶并 贮春色。
酒阑人散月盈庭,静听清渠流氵郭氵郭。
从诗句“况复吾年过半百”可推知此诗作于天会八年或九年的光景,洪皓建炎三年(天会七年,1129)出使金营,所以,他在燕山也是应该的。虚中到燕山是与吴激等“故人”饮宴,是有“故人惊我酒尚狂”。“自笑客中仍作客”是说他羁旅金营已是“客”,再到张侍御家又为客。“此生悲欢不可料”是感慨自己的宦海经历,竟至“沦落天涯”。诗中写到“贮春色”、“月盈庭”、“静听清渠”等,可见客居金营的虚中这时的心情还不错。
四
宋金“和议”很快搁浅,虚中随之陷于愁苦。金遣王伦归宋,告和议可成,宋马上派潘致尧、韩肖胄、章谊等前往接洽议和事,至天会十二年(1134),宋遣魏良臣、王绘出使,王绘对和议前景已有几分担忧③。
和议搁浅的原因是双向的。宋朝方面,绍兴二年(天会十年,1132),宰相秦桧罢免,主战派渐渐得势,三年,刘光世、韩世宗为宣抚使,岳飞为制置使;金朝方面,伪齐迁都汴京(齐阜昌三年,1131),积极准备侵宋。由于女真贵族始终没有放弃扩张疆土的欲望,而宋方收回失地的呼声随着岳飞等主战派的掌权而高涨,最终,和议搁置在疆界的划定上。和议难成,虚中顿时陷于愁苦,他在《又和九日》[3](卷1,P9)、《中秋觅酒》[3](卷1,P9)③二诗中表达出他的愁苦。
《又和九日》云:
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
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
强忍玄猿泪,聊浮绿蚁杯。
不堪南向望,故国又丛台。
《中秋觅酒》云:
今夜家家月,临筵照绮楼。
那知孤馆客,独抱故乡愁。
感激时难遇,讴吟意未休。
应分千斛酒,来洗百年忧。
诗云“五见菊花开”,一般认为,从天会六年出使算起,此诗当作于天会十年[8]。可是,天会十年八月金遣王伦回宋告议和事,此后的一段日子应该是虚中充满希望的日子,不该忧愁。忧愁应该出现在天会十一年秋,适时宋金和议无望,“愁随秋色来”。在中秋月夜,虚中讴吟孤馆客、故乡愁、千斛酒、百年忧。同年,虚中与妻书也透露出事势的严峻,并云其困苦状,“自离家五年,幽囚困苦非人理所堪……度事势决不得归,纵使得归,亦须在数年以后,兀然旅馆待死而已”[2](卷215,P3)。离家五年整,该是天会十一年,此时虚中已经意识到宋金和议无望,自己归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近于绝望。
至此,虚中“客”的感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燕山集会旧友时,踌躇满志的感觉不见了,因囚禁而思归的心情更加迫切,伤心、无奈、仇恨的情感更加浓重。虚中《在金日作三首》[7](卷上,P13)所反映出来情感的波折与此时的处境相吻合。
诗一: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催秀页空抱朴, 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
诗二: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己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回首两朝具草莽,心驰万里绝农桑,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
诗三: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无辞可奈何。强食小儿犹解事,学妆娇女最怜他。故衾愧见沾秋雨,短褐宁忘拆海波,依杖循环如可待,未愁来日苦无多。
这三首诗除了写作者伤心、愁苦、困顿外,还迸发出憎恨之情,“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有口无辞可奈何”。对于虚中突兀地冒出的充满仇恨的诗句,其寓意的阐释是不同的。
宋人施德操解释说:“所谓‘人生一死浑闲事’云云,岂李陵所谓欲一效范蠡、曹沫之事?……近传明年八月间,果欲行范蠡、曹沫事,欲挟渊圣以归,前五日为人告变,虚中觉有警,急发兵,直至虏主帐下,虏主几不得脱。呜呼痛哉!实绍兴乙丑也”[9](卷上,P13)。
刘克庄在《邓木并木闾宇文枢密诗帖》后又《跋》文,曰:“宇文公上帖(粘)罕(宗翰,笔者加)五诗,造次颠沛,不忘朝廷。其云:‘人生有死浑闲事,不斩奸邪此恨深。’又云:‘横磨大剑人何在,裂背穿胸不汝忘。’岂非追原祸乱之始 ,恨不食京、黼、贯、攸之月(肉)乎 ?”[10](卷105,P11)
施德操对三诗的误解是明显的,第一个误解是把诗的写作时间与空间定为在被害前、金上京,第二个误解是把虚中憎恨的对象说成是女真贵族等。
刘克庄的阐释似优于施德操,诗是呈给宗翰的,是“囚军府”的作品,当时,虚中与宗翰的关系很近,他曾对当年(天会十二年)使金的杨安说,“国相(宗翰)要我入国去”[11](卷78,P1279)。宗翰很赏识虚中,据载,“丞相(指宗翰,笔者加)得宇文相公,直是喜欢。尝说道:‘得汴京时欢喜尤不如得相公时欢喜’”[2](卷163,P4)。刘克庄意识到虚中苦于“频年流落”,应该“追原祸乱之始”。于是,得出虚中所恨者乃蔡京、蔡攸等人的结论。刘浦江先生赞同此结论[12](P25)。
蔡京、童贯固然可恨,但他们在宋钦宗时已被惩处、斩首。虚中的诗(一)中明明写到,“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说明他的仇敌还在。
《上乌林天使三首》[13](P121)之一云:
平生随牒浪推移,只为生民不为私。万里翠舆犹远播,一身幽圄敢终辞,鲁人除馆西河外,汉使驱羊北海湄,不是故人高议切,肯来军府问钟仪。
此诗也应作于军府,其中“除馆西河外”,“驱羊北海湄”与《在金日作三首》之二诗句相似,云“传闻己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可见二诗的背景与作者的心境是一致的,时间当在天会十二年。“筑西河馆”和“除馆西河外”指的就是金朝“议礼制度”,招徕文士之举。
关于乌林天使很难确定,有人推测是与虚中有交往的女真族外交使节[8]。虚中的《上乌林天使三首》之二提到“知君妙有经邦策,存取威怀万世名。”可见乌林是经邦者,威望很高,而且地位稍逊于权臣宗翰(上宗翰五首,上乌林三首),此人可能是乌舍,即完颜希尹。在军府的女真贵族中,唯宗翰与希尹相近,且比较注重文治,希尹又号称“萨满”,可称为“天使”。他们是金朝“议礼制度”的发起者,也是策动虚中入仕金朝的人。
此诗还说来军府是因为“故人高议切”,正是故人的“高议”让他“有口无辞”,让他“不汝忘”。是“故人”的构陷让他贬官,为了逃避贬官,又衔命出使,使命不完成,又难以归宋。困厄金营,虚中最恨的莫过于使其“运交华盖”的言官故人。
五
虚中对政敌的憎恨与走投无路所积郁的情感是复杂,虚中在宋朝“忠而被谤”,怀才难遇,自言:“满腹诗书漫古今,频年流落易伤心”。对宋朝感情的疏离,使其放弃守节,时人夸张地说虚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14](P1795)。贬损的言词是出于缺乏对虚中艰难处境的认识与理解。
在云中元帅府期间,虚中也曾以“持节”自勉。其诗文表现出他没有忘记“使命”,而且还能劝勉他人。天会八年(1130),元帅府遣张孝纯回故里,虚中与张孝纯有诗云:“闾里共惊新素发,儿孙重整旧斑衣。”[2](卷193,P2)张孝纯坚守太原,被俘后拒绝仕金,所以虚中以同道者的身份勉励他“重整旧斑衣”。此后的诗作《从人借琴》云:“靖节无弦且寄情”。天会十年,王伦自金归宋,言:“虚中奉使日久,守节不屈”。虚中与弟书也说:“虚中囚系异域,生理殆尽,困苦濒死自古所无。中遭胁迫幸全素守,惟一节一心待死而已,终期不负社稷”[2](卷215,P3)。与家人书中言其生计困顿,希望家人捎寄银两接济他,足见他没有接受金朝的官禄,虚中效法伯夷、叔齐,誓不食金粟的心迹是明显的。
至天会十一年秋,作《又和九日》有云:“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表明虚中“持节”的信念达到了极限。转年春,“持节”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过居庸关》[3](卷7,P7)一诗云:
“奔峭从天拆,悬流赴壑清。
路回穿石细,崖裂与藤争。
花已从南发,人今又北行。
节旄都落尽,奔走愧平生。”
从峭壁、悬流与“人今又北行”的诗句中可推知此诗当作于去京师(后来的金上京)的途中,即天会十二年。上阕写自然景观,下阕写虚中自己的境遇,“节旄都落尽,奔走愧平生。”暗示他“持节”已经没有耐心,又想到奔走劳碌实在是愧对自己。天会十二年(1134),金朝“议礼制度”,朝廷需要人才,为金所用是虚中唯一的退路。
虚中是一个追求现实的人,在宋朝,当宋金结盟时,他指责当局者失策;当宋金交战时,他又忙碌着一面集结援兵,一面为和议而三使金营;当被人构陷时,为逃避贬官,再衔命出使,不念危厄。虚中被罪出使,祈请二帝,二帝不回,自己也没有归路。和议曾带来一线希望,但很快破灭。虚中在金营不是被扣留,而是委身,委身者的经历与情感是矛盾的,对南宋,虚中是想回而不能回,对金朝,不想去又不得不去。虚中委身于金朝,政治前途是暗淡的,既受金官,又非真心情愿。率真的性格无法掩饰内心的矛盾,既用事于金朝礼仪制度的改定,又屡屡讥讪女真贵族,与女真贵族之间的矛盾注定了悲剧的下场。
[注 释]
①宣和间,虚中为参议官。上书言:“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月之储,安危存亡,系兹一举,岂可轻议?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蕃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藉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持卞庄两斗之计,引兵逾境。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以寡谋安逸之将,角逐于血肉之林。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见[1]卷371《宇文虚中传》第11526-11527页。
②有云:“彦高词集篇数不多,皆精微尽善,虽多用前人诗句,其剪裁点缀若天成,真奇作也,先人尝云,诗不宜用前人语。若夫乐章,则剪截古人语亦无害,但要能使用尔。如彦高《人月圆》,半是古人句,其思致含蓄甚远,不露圭角,不犹胜于宇文自作者哉”。见[15]卷8第84页。
③“绍兴甲寅(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又遣魏良臣、王绘副之以行……绘曰:‘绘辈此行,人或以伪(为)使路通决,无足虑者,绘独忧之,非前日之比’”。见[2]王绘《绍兴甲寅通知录》第4页。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O].光绪四年(1878)铅印本.
[3]元好问.中州集[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59.
[4]吕本中.春秋集解[O].四库本.
[5]唐圭璋.全金元词[Z].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洪迈.容斋随笔(三笔)[M]//四部丛刊续编(五一五二).上海:上海书店,1985.
[7]王庆生.吴激家世生平考述[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8]胡传志.略论仕金宋人的诗歌新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9]施彦辛丸北窗炙车果录[O]//曹溶 ,辑 ,陶樾 ,增订.学海类编(第六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
[10]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Z].四部丛刊本.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6.
[12]刘浦江.金代的一桩文字狱——宇文虚中案发覆[C]//刘浦江.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1999.
[13]阎凤梧,康金声.全辽金诗[Z].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14]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K246.4
A
1007-9882(2012)01-0116-04
2011-12-16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0Y JA770027)
李秀莲(1964-),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北方民族史。
[责任编辑:田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