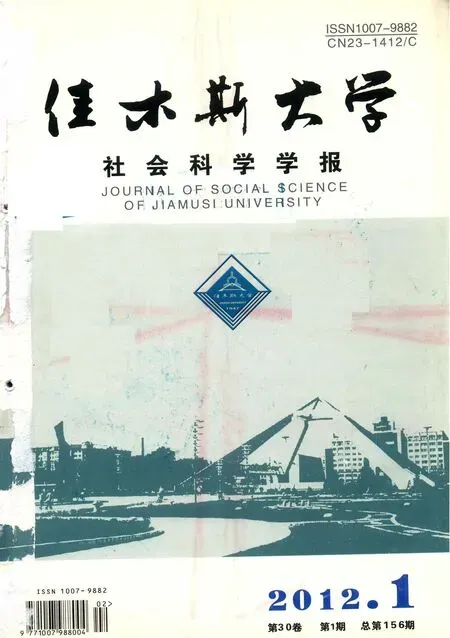中西方政府价值转向的哲学反思①
侯丽岩,吴永忱
(1.佳木斯大学,黑龙江佳木斯154007;2.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中西方政府价值转向的哲学反思①
侯丽岩1,吴永忱2
(1.佳木斯大学,黑龙江佳木斯154007;2.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从主客体关系界定政府的价值,政府是人类权衡、博弈之后理性选择的“公共性”代言人。公共性是政府价值生成的逻辑基础。在公共行政改革中践行的政府价值,偏离了原有的设定而发生了价值的嬗变、迁移。本文从哲学的视角,用比较的方法反思了中西方政府价值转向的异同的深层次原因。
政府价值;价值转向;哲学反思
一、从主客体关系界定政府价值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意义与价值。从“价值是需要的一种效用和思想价值观念的体现”来看,政府价值不能通过政府自身来规定[1]。“行政价值主体的需要是行政价值生成的起点”[2]。政府应社会需要而生。按社会契约论说法,政府是公民以社会契约形式协商让渡个人权利成为“公意”的结果。从功利主义角度分析,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把那些个人无力、不愿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交由公共机构(政府)。政府是人类权衡、博弈之后理性选择的“公共性”代言人。
可见,公共理性是公共性得以发生的主体性条件。行政价值主体对价值客体的“公意”诉求以公共性展现了主客体的价值关系。
(一)公共性规定着政府目标和行为的取向
政府的行政以追求“公共”为最基本的要义,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是有理性的,人创造政府的宗旨是为个人能过上理性的正义的社会生活[3]”。秩序是政府生成和运行的逻辑起点,是公共性应有之义。“理性正义的社会生活”是政府的“善治”目标。政府作为一种理性工具的存在,总是选择能够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策略,保证各种利益公正而充分地实现。政府价值必须改善所有成员的生存境遇,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体现出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追求。这是公共性对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现实中的一种必然选择,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本内核。
(二)以权利为基础,以权利为趋向,以权力为保障,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正如“契约,没有刀剑,就是一纸空文”一样,权力是维护公正、实现公共利益的强有力的保障。权力来源于权利奠定了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既是权力形成的出发点,也是权力行使的最终目标。政府必须公正地行使公共权力,高效地处理公民间的公共事务。改善所有成员的生存境遇,致力于实现社会公正,体现出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政治追求。
从价值主体的期望和政府价值生成的逻辑上分析,公共性价值的预设前提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政府的大公无私、权力的公共性行使、权力对权利的绝对保障、公共利益的表达等,还有对公平、正义、民主、效率等公共性价值内涵的模糊界说,使公共性本身蕴涵着“绝对超越指向”的形而上意念和乌托邦式的虚无情结[4],使之能够成为终极化的价值追求。公共性作为一种文化合理性理想,同时更是一种合主体性、合目的性的价值生存信念。在实践维度上不同的解读与探寻带来政府价值异化与公共性价值的嬗变,就成为一种内在的必然。
二、中西政府价值的转向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前阶段,任何国家的治理,都需要有政府权力的存在和运作,这是人们不能超越的设定。”[5]政府价值的实现,是在公共行政中践行的。公共行政发展的不同阶段,行政价值主体的需求不同,政府价值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定位,价值取向发生着变化。所谓政府价值转向就是价值取向的变化,从一种价值转向另一种价值的过程,是伴随着公共行政改革发生价值的变化、迁移,是对价值的重新解读与定位。
(一)西方政府价值的转变
西方政府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基本上是循着“效率—责任—公平”的价值理路。是伴着着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的变化而发生转变的。在西方,政府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弱政府、强社会(市场和公民)”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的初定位。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弊端开始显现,市场失效。为了减少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巨大浪费,重整效率,社会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把秩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个要求只有政府能办得到。因为政府拥有“产生于社会又超越于社会的公共权力”。于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了充分的理由干预经济,扩张行政领域。事实证明,政府普遍具有潜在扩张的倾向。行政国家的出现,基本逻辑基础是效率。效率成为行政管理的价值尺度中的“头号公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政府在发展壮大,但对经济的干预也仅仅是干预,而不是替代市场,更没有抑制公民社会的生长。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一直是“分庭抗礼”的位置,对政府行为有着很强的影响力的。
“国家(政府)在本质上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行政国家的政府扩张基于效率需求,政府扩张的同时也侵占了原属社会的公共空间。政府与社会对空间控制权的争夺虽然是隐含的,但终究在官僚制模型彰显失效的情况下爆发出来。当官僚制的僵化、低效等弊端彰显,公民对政府能力的质疑,西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政府存在的价值受到挑战。“政府失灵”的结论其实是社会对政府无限扩张的不满。因此,为走出合法性危机,政府价值转向了自身的责任建设,构建服务理念,重塑公共行政精神。
在责任政府建设中,为获得信任,强化了服务理念,对政府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变革了政府治理的方式,把一些公共治理的空间以公共服务外包等形式还给社会,以求“少投入高产出”的效率价值得到较为满意的实现途径。通过广泛对话和扩大参与的的形式,探求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方式路径。民主化价值现实路径的探求,为最终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走向现实奠定了基础。公平的价值取向是一种趋势,一种理想。民主化道路是走向公平、实现政府公共性价值回归的路径选择。实践已经证明,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转向,“体现了民主与效率的反复博弈和双重诉求”[6]。
(二)我国政府价值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的结构模式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价值转向遵循着“效率—公平”的简单路径。建国初期,政府统御着社会所有的领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替代了市场,挤占了公民的社会空间。“一切以长官意志为转移的政府管理模式没有理性的行政价值可言。在改革开放的引领下,我国的行政价值逐渐回归理性本色,并确立了以效率为目标为核心的行政价值”[7]。
当经济实力代替军事实力而成为世界竞争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时,我国政府从“统治”的管辖治理转向“效率”价值。激发活力、提高效率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价值目标。在路径选择上,政府通过政策倾斜与重点扶持,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首先发展起来,“领跑”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成就足以说明,“先富”出效率。“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追求效率的方法问题,而是同时包含着价值选择的成分”[8]。“先富”正是在“效率优先”价值下的路径选择。“效率优先”价值实践的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迅速两极化,富者更富,贫者更贫,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改革让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承担了改革的代价,客观上损害了公平,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是公共权力的不公正行使。因此,政府必须践行“共富”的承诺,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让所有社会成员(阶层)都平等地享受改革的成果。以公平目标引导解决不公正的社会问题,缩小城乡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注民生,成为新时期政府改革的政策目标选择。关注民生、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的政府价值取向,突出了公平价值在公共行政中的地位。
三、中西政府价值转向的逻辑理路
(一)共同的逻辑
中西政府在行政改革中体现出来的政府价值转向理路,有着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效率”成为政府价值基点的定位;2.当前的“服务”理念的定位;3.未来的“公平”价值目标趋向。“效率”和“公平”价值成为中西政府价值的基点和趋向,深层次的原因追溯到政府价值生成的预设逻辑,即政府是人类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人们让渡权利的驱动力是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公平”价值是社会公共价值的终极目标价值,政府作为“公共性”代言人,必须以实现公平为己任,为方向。政府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存在,“效率”价值能很好地证明政府合理合法性存在的价值。效率也是社会产生政府的需要。因此成为中西政府价值选择中殊途同归的理由。
“服务”的治理理念,实质是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方面做出调整的现实努力。在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下,中西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逐渐退出一些公共治理的空间,加强对话和扩大民主参与,是政府实现从“效率”向“公平”转向的民主化路径的探索。最终目标是想寻求效率与公平的融合,最大限度是实现公共利益。
可见,中西方政府在在公共行政的治理中面临着具有共性的问题,在价值转向的路径选择上又表现出惊人相似的殊途同归。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最好地阐释了管理的世界性内容和世界交往日益扩大的现实。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相互影响度越来越高,这是一种时代潮流。一些如效率、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价值,具有了超越国界与种族界限的普适性意义。对各国政府价值选择产生了影响的深远。这是价值主体的“客观意志”成为动力源本质要求,公平价值成为未来价值趋向。
我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正值西方发达国家掀起声势浩大、席卷全球的行政改革浪潮。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我国政府必然做出的时代选择。而入世之后,世界规则对中国政府产生的巨大的外在压力,冲击着中国政府的价值变革。由于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是后发国家,属赶超型发展,因此,与世界接轨,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的改革成果,使我国用33年时间完成了西方100多年才走完的市场化道路,同世界一起迈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新时代。
(二)差异的逻辑
在政府价值转向的整体路径中,在政府价值嬗变的环节上,中西政府是存在差别的:中国没有明显经历责任政府的建设而直接进入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来。“责任”价值环节成为中西政府价值转向差异的关键。为什么中国政府会缺少“责任”价值这一环节呢?这和促进政府价值转向的动力机制紧密相关联。
促进政府改革的驱动力一般在两个维度上产生:来自行政主体的内动力和来自价值主体的外动力。这两种动力或合成,或博弈,在世界意义上形成“效率”、“公平”等具有普适意义的共同价值。而价值主体的“客观意志”成为动力源本质要求,决定着政府未来的价值趋向。中西不同的社会结构中的力量对比,决定了推动政府改革的主导力量的不同。同样是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而陷入困境的中西政府,为了求证自身价值,解决信任危机,做出了相同的路径选择:改革。但考察其促进改革的动力来源却是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公民社会强大的呼吁力量,和对政策的影响力,成为一种压力,促使政府“不得不”、“不能不”加强政府的责任建设,“责任”是对社会压力的回应。社会成为政府价值转向的主导力量。而在我国,政府价值转向的直接动力来源于政府内部领导者的自觉(如朱钅容基总理面对“吃饭政府”现状时强烈的责任意识与变革的激情),而不是来自于社会,因为“在中国的当代境遇中,公民社会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9]社会中还没有生成公民的强烈而强大的声势压力。我国的政府改革是政府的自觉选择,“自己革自己的命”。这种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动力往往表现乏力。这也是我国政府在价值转向环节中缺少“责任”价值环节,准确地说是责任政府建设没能成为一个时期的政府建设的主导的根本原因。因此,培育、发展和壮大我国的公民社会是政府公共性价值回归的现实路径选择。
[1]谢庆魁.政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06.
[2]何颖.政府哲学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1.41.
[3]施雪华.政府智能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张富,赵英男.公共行政价值研究的新动向[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87.
[6]赵蕾,谷松.博弈与融合: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演化[J].学术论坛,2006,(11).
[7]何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30年回顾与反思[J].中国行政管理,2008,(12).
[8]杨俊一.价值择优的“博弈”与理想信念的整合[J].人文杂志,2000,(6).
[9]汪业周.公民社会的意蕴、维度及当代中国语境[J].广西社会科学,2007,(2).
D523
A
1007-9882(2012)01-0072-03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