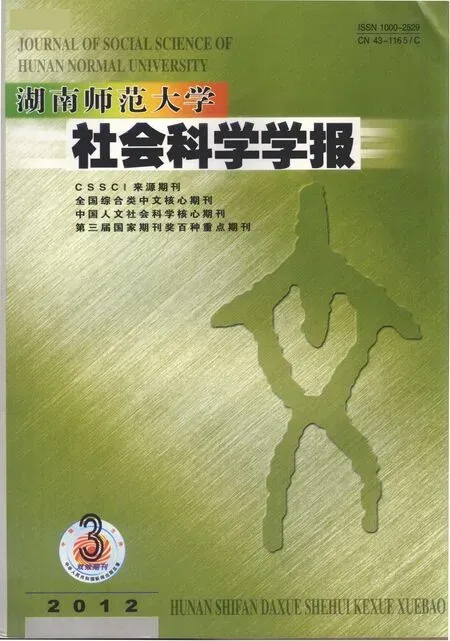利维斯的狄更斯批评回顾及反思
赵炎秋,蔡 熙
利维斯的狄更斯批评回顾及反思
赵炎秋,蔡 熙
剑桥夫妇教授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是20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狄更斯研究专家。他们的狄更斯批评经历了一个由贬而褒的过程:将狄更斯从一个广受欢迎、津津乐道于伤感煽情的“娱乐高手”擢升到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既受大众欢迎又深刻严肃的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们或褒或贬的狄更斯批评皆以道德判断即生活的严肃性为尺度。这种悖谬的批评根源于他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我们只有将它置于批评家所在时代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利维斯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狄更斯;道德批评
一
在剑桥夫妇教授F.R.利维斯和Q.D.利维斯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狄更斯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狄更斯批评经历了一个由贬而褒的过程。Q.D.利维斯的《小说与读者大众》(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1932)蔑视狄更斯小说的大众化传统,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将狄更斯仅仅看作是“娱乐高手”,而在他们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Dickens the Novelist,1970)则彻底修正了以前对狄更斯的负面评价,称狄更斯是既受大众欢迎又深刻严肃的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们对狄更斯或褒或贬的批评皆以道德判断即生活的严肃性为尺度。利维斯夫妇这种悖谬的狄更斯批评与他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根源于他们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我们只有将这种悖谬的狄更斯批评置于批评家所在时代的语境中,才能发现利维斯遗产的价值与意义。
早在1930年代,Q·D.利维斯就开始了对狄更斯的贬抑,将狄更斯深受读者大众喜欢等同于艺术的拙劣而进行恶意揶揄。她的专著《小说与读者大众》不是用心理批评方法去发现小说中的创作个性与心理线索,而是以小说的社会语境为中心肆意对狄更斯进行指责。在她看来,狄更斯深受大众喜欢是因为1830年代读者群的变化,读者群的变化对小说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狄更斯的小说为幼稚的大众和产业工人而生产,他依赖感伤情绪和夸张渲染来博得读者的眼泪,因为这两种手法易于取悦读者。Q·D.利维斯断然说,“无论是谁,只要用批判的眼光看看狄更斯的一两部小说,立即就会发现他的原创性仅仅局限于重温儿童时代对成人世界的看法”。他不仅未“受过教育,而且不成熟”[1](57)。狄更斯满足于以连载形式取得廉价效果,因为通过这种方法让读者期待下一期。她不无讥讽地恭维说,“狄更斯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典型风格,这种世界观和典型风格在别处只是零星地呈现,但在《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却占居支配地位,这样他的小说才足以称之为文学。”[1](158)
F·R.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奠定了英语小说的“伟大传统”,因而被公认为引发了英语小说研究的革命。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小说作为形式的意识是由F.R.利维斯的论述界定的。史诗和诗剧衰落之后,散文小说成了西方文学的主要文类。”[2](230)《伟大的传统》问世两年后有一段逸事,这里不能不提及。1950年BBC广播信息报《广播时代》(Radio Times)宣称杰弗里·格里森(Geoffrey Grigson)将举行系列有关英语小说的专题演讲时,F.R.利维斯认为这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甚至于未及亲临讲座,他就宣布格里森剽窃了他于1948年出版的著作《伟大的传统》。为捍卫其著作权,F·R.利维斯将其告上法庭。
利维斯之所以将格里森告上法庭,因为在他看来,“英语小说”是他的知识产权,是他的发现。在《细察》一文,他自信地说,他建立了——重要的小说——“严肃的艺术所要求的批评方法意识——英语小说传统的新理念。”[3](13)事实的确如此。在《伟大的传统》之前,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小说批评是由小说家本人撰写的,如亨利·詹姆斯,珀西·拉伯克(Percy Lubbock)等。二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小说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发展,是《伟大的传统》把小说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将小说研究提升到如今的学术宝座,是利维斯开创了小说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学科。
但是,这部引发了英语小说研究革命的《伟大的传统》却极尽贬低狄更斯之能事。该著开门见山地指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纳德……都是英国小说里堪称大家之人。”[4](1)《伟大的传统》对文学传统开创者的褒扬是以狄更斯为衬垫的。F.R.利维斯虽然也指出了狄更斯对他们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以谐谑、挖苦的笔调来陈述的,下面试举几例:
(1)“康纳德在某些方面极像狄更斯,以至于我们难以说出狄更斯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康纳德的《特务》所描写的伦敦里无疑就有狄更斯的身影在。”[4](29)康纳德的技巧精湛老道,但是这种影响“来自一个手法远远谈不上精湛考究的作家——狄更斯。”[4](29)在评论康纳德的《胜利》时,利维斯说“他们属于康纳德的艺术中让人想起狄更斯的那一面——一个被一种完全非狄更斯的成熟所限定的狄更斯:他们的存在严格地服从于康纳德那完全非狄更斯式的主题。”[4](347)
(2)F.R.利维斯摘引《罗德里克·赫德森》的三段证明狄更斯对亨利·詹姆斯的影响时说,“狄更斯的影响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不是见于《卡萨玛西玛公主》里写《小杜丽》的那个狄更斯,而是写《马丁·朱述尔维特》的那个狄更斯。当然《罗德里克·赫德森》的这一段不可能是狄更斯所写:作者出手给了狄更斯风格一道令人倍感钦佩的智慧锋芒。”[4](218)“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大家是如何向另一个学习的。詹姆斯在原则标准方面的成熟虽然令狄更斯无法比拟,但狄更斯施惠于他的还不止是个风格。他帮詹姆斯从外面看自己周围的生活并以批判的眼光加以评定。”[4](219)利维斯引用《波士顿人》中的一段后指出,“詹姆斯让我们看到的,乃是《马丁·朱述尔维特》,经过一个大大更富才智也大大更有教养的头脑重写之后而呈现出来的面貌。”[4](222)“詹姆斯对此表现的力度大大超过了狄更斯的笔力(我们还记得《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主题),原因即在詹姆斯的艺术要精湛细腻得多,也在于整个背景所生发出的那种意义。”[4](227-228)
(3)劳伦斯的《迷途的姑娘》明显见出狄更斯的影响,“只不过要无可比拟地更加成熟,构成了一个完整严肃意义的一部分。”[4](33)
“《伟大的传统》出版后几乎引起了公愤。”[5](199)这不仅是因为英国文学传统中的四位开创者中有两个异族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将狄更斯排斥在英国的文学传统之外。瓦尔特·艾伦(Walter Allen)在《英国小说》(English Novel,1954)中迎战了F·R.利维斯对狄更斯的谴责,他将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比肩,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不是漫画人物而是源于孩子般的世界观。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对于《伟大的传统》贬抑菲尔丁、斯特恩、萨克雷、特罗洛普、梅瑞狄思、哈代、艾米莉·勃朗特,把乔伊斯斥为死胡同都不置评价,但对于排斥狄更斯他感到“令人最为惊讶。”[6](375)罗伯特·波默斯(Robert Polhemus)的《滑稽的信仰:从奥斯丁到乔伊斯的伟大传统》(Comic Faith:The great Tradition from Austen to Joyce,1980)在断然反驳利维斯的同时,指出19世纪的滑稽小说履行了宗教功能。他将19世纪的滑稽小说与乔叟、莎士比亚以及18世纪的作家联系起来,提出大众对幽默和传统的大团圆结局的要求并不妨碍小说家狄更斯写出具有严肃道德目的的小说。
二
在狄更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时,利维斯夫妇合著的《小说家狄更斯》对狄更斯的评价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部研究狄更斯的专著修正了以前对狄更斯的负面评价,同时辛辣地驳斥了20世纪扭曲狄更斯天才起源的批评传统,力图消除一种错误的观念:狄更斯的天才仅仅是一位“娱乐高手”。他们在《序言》中明确指出,“狄更斯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艺术家之一,他以其创造性天才全面发展了忠诚于艺术的意识,成了一位既多产,又让大众喜欢,既深刻又严肃,既机敏又训练有素的小说家,他是一位艺术大师。”[7](55)
《小说家狄更斯》共分为七章。F·R.利维斯撰写了论《艰难时世》、《董贝父子》和《小杜丽》三章,而 Q·D.利维斯将《大卫·科波菲尔》、《荒凉山庄》和《远大前程》作为19世纪小说发展的重要环节进行比较研究,另外还撰写了《狄更斯的插图及其功能》。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将《董贝父子》当作狄更斯写作生涯的转折点,认为它再现了重大的主题,是一部精心构思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感伤的情节剧不是影响狄更斯唯一重要的因素。”[7](29)他所发展的艺术不完全是来自斯摩莱特、菲尔丁或本·琼森或者他那个时代的戏剧,狄更斯的天才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在他的创造性思维中有着莎士比亚的气质。第二章《狄更斯与托尔斯泰——以〈大卫·科波菲尔〉为例》驳斥了罗伯特·加里斯(Robert Garis)和罗斯·达布尼(Ross Dabney)对《大卫·科波菲尔》的低评,并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中寻找《大卫·科波菲尔》影响托尔斯泰的证据,详细论析狄更斯对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影响。第三章《〈荒凉山庄〉:大法官法庭世界》驳斥了G·H.刘易斯(G·H.Lewes)和加里斯对狄更斯的讥嘲和贬抑,进而指出狄更斯通过小说来表明自己的观念和复杂的主题,并且“这些观念完全是拟人化的,消融在情节、对话和典型的生活形式的情感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整体。”[7](118)第四章一字不易地重刊了论《艰难时世》一文,以证明狄更斯的公认地位。该论文称道《艰难时世》中的“完善的严肃性”,被公认为开创了狄更斯小说研究的新方法,引起了狄更斯批评的革命。第五章《狄更斯与布莱克:<小杜丽>》认为狄更斯不屈不挠地追求通俗小说畅销书作者的事业,他才成为一流的创造性作家,最优秀的原创艺术家。《小杜丽》是“狄更斯作为大师的主要成就之一,它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将它排除在伟大的欧洲小说名录之外是站不住脚的。”[7](213)狄更斯与布莱克一样,是一位“精神——即生命的守护者。”[7](274)狄更斯与布莱克同为伟大的作家,并且将狄更斯与劳伦斯、布莱克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应有“一条脉络持续进入 20 世纪”[7](275)。由于 Q·D.利维斯认为狄更斯批评家的误导妨碍了读者对狄更斯的接受,从而撰写了第六章《我们如何阅读<远大前程>》,认为这部伟大的小说,以典型化的方式,严肃地讨论了人类经验的基本现实。在学生们与生产自我成才的狄更斯及阅读狄更斯的传统文化失去联系的背景下,以《远大前程》为例,告诉人们阅读狄更斯小说的具体方法。第七章《狄更斯的插图及其功能》研究插图作为艺术的附属部分向读者传达文本意义,它与本书的批评主题有着直接的关系。Q·D.利维斯认为狄更斯自从创作生涯一始,就对小说插图显示了极大的兴趣。她强调了插图以及大众理解插图的传统对于狄更斯的意义,并表明由于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根本变化导致这一传统消失。因此,“狄更斯的逝世标志这一时代的终结。”[7](xii)
三
从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利维斯夫妇的狄更斯批评前后抵牾、自相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同一本书《伟大的传统》中也随处可见。在第一章利维斯说,狄更斯是个大天才,恒居经典文豪之列,小说家的职责是要创造一个世界,大师的标志是外在的丰富性。作家笔下的人物有没有生命,要看在书本之外,他们是否继续存活。“狄更斯的伟大已为时间所证实,而其对手则不然。”[7](34)但他却又将狄更斯排斥在英国的文学传统之外。
如果将《伟大的传统》与《小说家狄更斯》的论断对比一下,则会发现前后抵牾更加明显,简直可以说是自我掌掴。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称狄更斯是个广受欢迎的娱乐高手,津津乐道于“伤感煽情”,他的全部作品中值得称道的只有一部《艰难时世》。而在《小说家狄更斯》他们却极力称道狄更斯的小说的大众传统,“狄更斯作为伟大的通俗艺术家无拘无束的写作自由并没有妨碍他与往昔英国文学艺术的经典建立创造性的联系。”[7](30)论证“狄更斯是娱乐高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指责了布卢姆斯伯里文社(Bloomsbury)的批评家将狄更斯与萨克雷、特罗洛普并列的不妥当,并指出,在最完整的意义上“狄更斯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艺术家。”[7](29)他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最伟大的创造性作家之一,他的艺术是原创的。”[7](ix)《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都是伟大的小说,《小杜丽》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无上伟大”[7](177),可谓“最最伟大的小说之一。”[7](213)利维斯在《小说家狄更斯》指出狄更斯对詹姆斯的影响不仅不再以狄更斯为衬底,而且指出狄更斯远比詹姆斯优秀卓越。“我要挑战詹姆斯对狄更斯的批判态度”,“詹姆斯那自信的批评倾向表明詹姆斯是一位绝对不够伟大的作家。我在此并非贬损詹姆斯,而是要为狄更斯的天才做辩护。”[7](229)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小说家狄更斯》另外提出了一条布莱克——狄更斯——劳伦斯进入20世纪的文学脉络,这无疑等于完全否定了《伟大的传统》中简·奥斯汀奠定的、经乔治·艾略特到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纳德以及D·H.劳伦斯的文学传统。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扬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康纳德、D·H.劳伦斯,贬狄更斯,其理由是什么?由于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求助于具体的实例”的批评方法,大量引用小说文本,再对所引用的文字进行细读品评,往往只做价值判断,而拒绝陈述理由。比如,他认定简·奥斯汀是英国文学传统的奠基人,他不但未辟专章论述,而且不提供任何理由。同样,他将狄更斯排斥在英国文学传统之外,也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他的文学批评基本形式可以概括为:“就是这样的,不是吗?”[8](502)但是细读《伟大的传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利维斯臧否优劣的标准是道德,即“生活的严肃性”。他说“文学批评必须公开讨论情感卫生和道德价值问题——更为概括地说(似乎没有其他适当的措词),是精神健康问题。”[8](525)奥斯汀对于生活抱有独特的道德关怀,“细察一下《爱玛》的完美形式便可以发现,道德关怀正是这个小说家独特生活意趣的特点而我们也只有从道德关怀的角度才能够领会之。”[4](14)反之,要是没有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奥斯汀就不可能成为小说大家。乔治·艾略特正是因为有道德上的严肃性才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康纳德那里,“一个严肃的完整意义才是目的。”[4](30)在利维斯论及的开拓文学传统的经典作家中,亨利·詹姆斯让人抱憾之处明显最多,但他仍在大家之列,因为他有着严肃的道德目的,D·H.劳伦斯的探索动力则是“对生活所抱的严肃而迫切的关怀。”[4](40)同理,在狄更斯的全部作品中利维斯独尊《艰难时世》,因为“这部伟大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其间没有一点童话的成分,以至于完全排除了欢快之气;读者所能获得的满意取决于一种与魅力没有什么关系的道德意蕴。”[4](79)狄更斯是个大天才,恒居经典文豪之列,但却置身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外,是因为“他的那份天才却是一个娱乐高手之资。”[4](30)“成熟的头脑在狄更斯那里,都找不到什么东西要求人去保持一种持久而非同寻常的严肃性。”[4](31)
那么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是什么?反理论的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和《小说家狄更斯》都没有明确界定,在他看来,真正的批评判断标准是直觉的。因此,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是含混、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维斯的道德价值标准与中国语境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语境文学批评的道德标准指的是善,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由于中国文化建基于道德论,往往是善消融了真和美。利维斯秉承了阿诺德的衣钵,阿诺德的“道德”传统将一定的社会价值表现为普遍的人类价值,将文学视为对生活的批评,要求伟大作家的作品具有“高度的严肃性”。通览《伟大的传统》、《小说家狄更斯》以及利维斯在其他地方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维斯那里,道德价值标准的核心就是生活,他摈弃了形式和内容的分立,将道德与真实联系在一起,严肃地批评了生活就是道德的。而生活,也是个含混、模糊的字眼,其含义“从现实、真实转向真诚乃至共同性和同一性。”[6](388)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否定狄更斯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同样,他们夫妇在《小说家狄更斯》盛赞狄更斯也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从而导致很难定位利维斯夫妇前后态度变化的根源。笔者认为,利维斯夫妇盛赞狄更斯还是道德标准,还是含混、模糊的“生活”。其理由有三:(1)《伟大的传统》开篇提出英国文学传统的四位开创者之后,F·R.利维斯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武断和褊狭。“批评家们已经说我褊狭了,而且我敢肯定,如是一番开场白之后,无论我如何阐发,都会被用来加强他们的苛责。”[4](1)《伟大的传统》将狄更斯排除在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外,在当时评论界几乎引起了公愤,此后的利维斯逐步认识到狄更斯在英国小说中的卓异地位,意识到狄更斯是个不容忽略的人物。(2)利维斯在《小说家狄更斯》认为狄更斯胜过詹姆斯,是因为“伟大的狄更斯的艺术有一种莎士比亚式的风范”,“狄更斯不仅是与詹姆斯不同的一位天才作家,而且是比詹姆斯更为伟大的作家。他身上体现出的创作生命力来源更深,流淌更为自由充分。”[7](326)他称《小杜丽》为狄更斯的最佳作品,是因为“它展示了唯有伟大的创造性作家才能驾驭的统一的生活。”[7](213)(3)在很多人看来,托尔斯泰代表 19 世纪经典道德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但是不少托尔斯泰的崇拜者没有认识到的托尔斯泰虽然拒斥莎士比亚,但十分欣赏狄更斯,他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大卫·科波菲尔》无与伦比的崇敬。Q·D.利维斯考辨狄更斯之于托尔斯泰的影响,也是着眼于道德标准。
四
在今天看来,利维斯仅以狄更斯的作品缺乏生活的严肃性,即狄更斯的作品中有着滑稽幽默的成分,就将他排斥在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外,仅以简·奥斯汀的作品有着道德严肃性就把她当作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奠基人,这是极其武断的。利维斯夫妇同样以含混、模糊的“生活”作为终极价值标准而褒扬狄更斯,道德标准所排斥的一切无疑显示出利维斯的文学观念的局限及偏狭。这种局限及偏狭只有置于其历史语境才能得以清晰的观照。因为不仅作家的创作要受到时代的影响,批评家同样要受到其生活和写作的时代的局限。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根源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英国社会在20世纪发生重大转折,传统价值观分崩离析,大众文化汹涌而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有着切身体验的利维斯,惋叹机器文明的进步,眷恋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共同体,主张精英文化,强调社会需要有“受过教育的大众”。因此,他不惜殚精竭虑以确立文学批评的崇高地位来抵制大众文化的冲击,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为此,他苦心孤诣地以文学的严肃性作为唯一的评判尺度,从英国文学史中筛选为数不多的几位大家,甄别优劣高下,以期唤醒一种差别意识,树立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传统观,从而达到以具有强烈道德意识的文学经典来启迪人的心智的目的。
同样,利维斯文学批评的其他局限也只有置于他的文化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中才能得到说明。由于他首先关心的是维护传统,因此,他臧否作品的标准往往以道德,即生活的严肃性为出发点。这种排斥多元论的文学批评将道德判断置于形式之上,有益于生活、激发生命创造的作家作品得到褒扬,而具有幽默搞笑色彩的作家作品遭到贬抑。因此,在利维斯那里,纯粹游戏式、洛可可风格、装饰性、讲究美感、形式主义的艺术成了奚落的对象,唯情论、灵感、辞藻等一向遭到他的贬损。他的文学批评对“审美问题”、“诗篇布局”之美往往视而不见,正如他自己所说,“技巧只能根据它所表达的感受力来加以研究和判断”,否则它“就是一种无益的抽象概念。”[9](113)这样利维斯就成了一位着眼于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则成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虽然利维斯的狄更斯批评有着诸多的局限性,但是其批评遗产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使狄更斯批评、乃至小说批评、文学批评学科化。二战以后,狄更斯研究发生转向,即从业余批评走向职业批评,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利维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细读经典,识别优劣、区别一流与二流,甄别优劣高下,这种将文本细读与19世纪马修·阿诺德所开创的人文主义批评传统结合起来的批评方法,不仅改变了英国大众的阅读习惯,而且使狄更斯批评,乃至小说批评、文学批评提升到学术宝座,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从而成为新批评的源头之一。
(2)奠定了妥当的文学批评态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挑战和批判权威的勇气。利维斯的批评坚定、直白,语言尖刻,咄咄逼人。以《小说家狄更斯》为例,该著对《伟大的传统》出版以来与其观点不一致的批评界权威人士进行了猛烈抨击,如,对美国批评界的权威爱德蒙·威尔逊将狄更斯的全部创作看作是一味沉溺于儿童时代经历的产物这一观点的批判,毫不留情,Q·D.利维斯对沃尔特·雷利和其他牛津大学名流、批评家罗伯特·加里斯和罗斯·达布尼等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们甚至将伦敦的文学艺术权势集团(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英国广播公司、星期日报、左翼周刊)当成了批评的靶子。唯其如此,利维斯才能成为20世纪继“艾略特之后最有影响的英国批评家。”[6](373)一是坚持严格的批评标准,修正错误的勇气。利维斯在喜好的作家中采取苛刻的取舍标准,以生活的严肃性为准绳来评判文学传统的伟大作家,对于不符合他那严格的文学价值评价标准的作家,F.R.利维斯毫不留情地轻蔑以待,并十分苛刻。他严守自己开辟的那方领地,并以之作为“伟大作家”的栖息之地。但是一旦他意识到自己的偏狭以后,他又吝不容情地扭转自己的偏颇,甚至于不怕自我掌掴。这种批评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3)在文学理论泛滥,文学研究中的理论明显脱离文学的当下语境中,利维斯夫妇将人文主义传统、文本细读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的方法,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了范例。利维斯强调文学使命感的道德批评上承阿诺德,下启雷蒙德·威廉斯,已经成为剑桥文学批评传统的象征,推动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利维斯本人也毋容置疑地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利维斯以文学为宗教的虔诚态度,穷毕生精力在文学批评中锻炼心智,砥砺思想的治学精神都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师承的榜样。
[1]Leavis,Q.D.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London:Chattox Windus,1932.
[2]Steiner.“F.R.Leavis”(1962) in his Language and Science:Essays on Language,Literature,and the Inhuman.New York:Atheneum,1967.
[3]F.R.Leavis,“‘Scrutiny’Retrospect”,in Scrutiny XX:‘Retrospect’,Index,Errata(London:Cambridge Univ,Press,1963.
[4]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 伟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Claudia L.Johnson.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 of the English Novel and the Jewish Part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2001,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杨自武译)[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Leavis,F.R.&Q.D.Leavis.Dickens,the Novelist[M].London:Chatto&Windus,1970.
[8]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F.R.Leavis.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1943.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Leavis’s Dickens Criticism
ZHAO Yan-qiu,CAI Xi
F·R.Leavis and Q.D Leavis,the couple professor of Cambridge University,are experts on Dickens with significant impacts in the 20th century.Their criticism of Dickens underwent a process from depreciation to praise:Dickens was promoted by them from a popular and“great entertainer”who was preoccupied with sentimentalism to one of the greatest creative artists who was popular,but yet profound,serious,and bracketed with Shakespeare.Their criticism of Dickens,either praise or depreciation,is based on the yardstick of moral judgments,that is,the seriousness of life.This ambivalent criticism is rooted in their outlook on culture,society and life.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eavis’s heritage can be found only when it is put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era.
F·R.Leavis and Q·D.Leavis;Dickens;moral criticism
赵炎秋,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蔡 熙,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英美中狄更斯学术史研究”(10YJA752040);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英美狄更斯学术史研究”(CX201B182)
(责任编校:文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