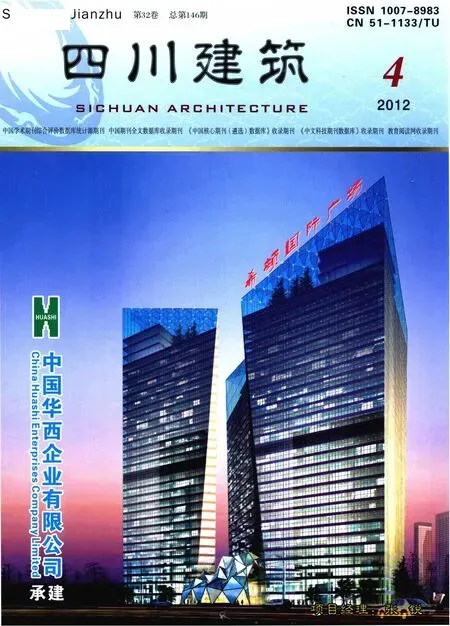传统文化与汉代园林审美思想
崔璐璐
(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学院,重庆 400074)
园林首先是物质生活环境,本质则是精神的居住。这决定了只有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上踞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为满足生活享乐与精神欲求,才有条件建造这种文化上高层次、经济上高消费的园林。而园林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实际也是审美主体思想、心性的必然反映,体现着主体的哲学、美学追求。
张家骥在《中国造园史》中谈到:如果不把造园实践置于社会的发展和运动之中,从造园与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去考察,对一个时代的园林的基本特征,也难形成比较清楚的概念。
要探究汉代园林发展的成因和特定定义,仅局限于园林本身远远不够,而是需要深入到社会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学思想和文学艺术形式发展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应的时代特征等背景文化层面。
1 汉代儒学思想与园林
人对审美的需要是园林艺术发展的动力。中国传统美学以儒、道思想为主体。儒家的艺术精神,常需要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意味的转换;而庄子所开创的艺术精神则相对直接,可视为纯艺术[1]。
中国园林是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自然风景式园林,其中的审美再造刺激物,既有纯自然状态的“山水”,又有人化的自然,还可以是建立在山水自然基础上的“意境”。这一切都离不开“山水——自然”这一审美对象,离不开儒学的贡献。汉代园林尚处于中国古典园林生成期,其审美观方式受儒家影响颇深,而庄子的纯艺术精神似乎不占主导地位,只对东汉后期文人隐逸思想的发展有直接作用。
1.1 汉代儒学思想的发展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具有极强的人文和社会政治倾向,提倡中庸、博学、择善而从。但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其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汉代儒学是在先秦孔孟之道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的新儒学,最主要的特点是杂糅各家学说于儒学中。当其在东汉最终建构完成之后,以宇宙自然法则作为依据,君主制度作为推行力量,循吏为代表的行政系统的教育与灌输,加上便于推广与普及的数字化、简约化的语词系统,实现了思想“标准化”的时代。
在汉人看来,黄老(或老子)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原本是和儒家一致的,汉初众多思想家引用黄老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补充和修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适应性。
1.2 汉代儒学思想的重要理论
1.2.1 阴阳五行体系
以人为中心的阴阳五行体系的完成,是汉儒重要的理论建设,被今天一些学者视为“汉代的思想骨干”。其框架以道、儒二家的追求来设立。一般地说,道家侧重从世界的生成和运行角度去谈阴阳五行,儒家侧重从伦理、道德和意识去谈阴阳五行。两家理论的综合,就是汉代阴阳五行体系的总貌。
阳:天、君、男、夫、德、乐等等;阴:地、臣、女、妻、刑、礼等等。这明显是为了论证儒家的天人感应而人为地构筑的阴阳体系。
五行排列顺序:汉代以前“木”的地位不高;汉代“木”上升至第一位。《尚书·洪范》第一次全面表述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木作为五行之始,代表了生命、生殖、发展、生长之意。《周易》:“生生不息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国语》:“正德、厚生、利用”。汉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第一次确立。
1.2.2 天人之际理论
董仲舒的天人之际理论,把天作为人间秩序和理性的背景,并将这套解释自然与历史的宇宙法则论述得最为充分。“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以天人同类证明的天人合一论;以同类相动证明的天人感应论。
董仲舒之后的诸儒和思想家司马迁、京房、刘向、刘歆、王充、郎回、襄楷、班固、张衡、马融等,更将天与人的关系,发展到天上与地下万事万物的一一对应关系。
《史记·天官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领之。
张衡《灵宪》: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备矣。
可以看出,讨论和阐发得最多的,是天象的意义。
1.2.3 谶纬学说
阴阳五行、天人之际思想得到极致的发挥是汉代的谶纬。《汉书·艺文志》数术略第六部分就是形法:“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
从秦汉之际到东汉之末,纬书之学由兴而盛、由盛而衰,把古代中国关于宇宙的观念、天文地理知识、占星望气之术、神仙传说与故事,与传统道德和政治学说糅和在一起,显示了两汉时期思想的体系化与标准化趋向,也促成了国家神学的诞生。
1.2.4 隐逸思想
知识阶层“为王者师”凭借的是“真理”,但当思想逐渐定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通过教育传播成为普遍知识,知识阶层的地位便下降成为“帝之臣仆”,出、处的矛盾逐渐锐化。于是,文士阶层中一部分在权力压迫下放弃所谓“君子”理想,转入“文吏”;另一部分则高扬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文人园林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文士的隐逸生活之乐。园林作为士大夫遁世的去处,既是自然山水的摹写,也是士大夫内在世界的外化。世道混乱不得志时,士人寄托于优雅的环境增加修养,等待时机出山来改善社会。
2 汉赋与园林
“贵文”思想对园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以载道”和对“文心”的追求,反映着园林与文学、绘画等士人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同步发展。园林的题名用典、园景的意境创造方面都竭力追求士人文化的内涵与神韵。园林已经成为文人阶层特有生活方式的现实反映,园居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流露出浓郁的人文气息。
艺术的本质,是面向感,隆形态的感性思维,而文学的根本规律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即运用形象思维把握世界。文学没有画面限制,自然环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风土百物,琳琅满目。
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
司马相如:“合綦组阻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这里指出赋乃是以美丽的语言形式来描述宏大的世界。
汉代建筑最典型特点是类型空前丰富、体量宏大、铺张,建筑审美成为重要审美内容之一。汉赋人量自然景物的描写带有审美特征,为魏晋南北朝的山水审美打下基础。
3 汉代审美思想与园林艺术特征
3.1 自然审美
深究园林以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原因,还要归功于孔子儒家思想的首倡。源于早期原始思维、集中体现于《诗经》的这一文化传统,经孔子及其后学的重新发掘,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以后园林中的自然审美对象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倡导在历代文人中的影响潜移默化,历久不衰,形成了中国古代重视实学和技艺的优良传统,并由此促进了动植物的培植、豢养与审美,极大地丰富了园林的景观。
园林崇祀对象的变化,从娱神发展到娱人的功能转换,意味着从感官上的快感,导向心性情志即精神的愉悦。儒家强调的正是园林建筑精神、思想而非感官的审美。
3.2 比德与比道
孔子最早提出山水审美的命题,而且认识到山水具有比德与比道两种层次。比德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代表;“子在川上曰”、“登山”、“观水”“鸢飞鱼跃…拳石勺水”“曾皙言志”等则是比道的典型,即透过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和万物运作,直视天地间生生不息、无所不在的“道”——生命的超越精神。
比德说,使山水花卉鸟兽草木鱼虫等摆脱了原始巫术和宗教神话,而作为情感抒发的发端和寄托。在儒学的这种积极倡扬之下,经过理知的中介实现了情感的建构和塑造,导致人们从伦理、功利的角度来认识自然之美、对于大自然山水风景,构建了自觉的审美意识。文学中的比德方法,在屈原、宋玉至两汉的骚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山水比道则是发现了山水具体形态以外的超越性。是面对山水的宇宙和生命本体性的哲学思考。作为儒家美学理论整体框架的一部分,比德审美观点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己不仅是人的伦理道德标准与自然万物的比附,而是将审美主体最终带入了一个超越的天地境界。
3.3 山水审美对汉代园林的影响
山水审美对包括园林在内的艺术的影响,一是在思维方面强化了形象思维,二是在形式上奠定了中国特有的仰观俯察的时空观念和构图方式。班固《西都赋》描述了这种园林创作的审美意象:“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原野萧条。目极四裔。”其观景的载体就是作为苑中苑的长杨榭。另如石阙、封峦二观建于“冈峦纠纷,干霄秀出”的石门山,“崇丘陵之墩酸兮。深沟嵌岩而为谷。离宫般以相烛兮,封峦石关施糜乎延属。”。以建筑结合山川自然而创造园林景观的意象,也是相当明显的。
山水自然的积极意义是使人从中获得精神的愉悦;从负面上讲,山水自然则是作为社会失意后人生幸福的补偿形式出现,成为士人漂泊心态的归宿,使其生活方式上与自然更为接近。同时期隐逸文化的发展加速了山水审美的进程。
4 结束语
汉代文学充分如实地反映了汉代园林的布局、环境和活动,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并且汉赋对造园的指导意向亦十分明显。
汉代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其博大辉煌的文化,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百川汇流式的兼容和重新诠释,堪称“有容乃大”:东汉佛教才开始传入,影响未深,因此汉代文化表现出华夏文化的原生状态。两汉时期这种特有的文化氛围,决定了汉代艺术异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内容,决定了汉代园林的基本格局:以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为背景,以自然山水为主要审美和写仿对象的人工游憩空间。审美客体的确立和想法相对成熟,为后世文论、画论对园林的深远影响直接打下基础。
[1]徐复观.庄子的山水观——中国艺术精神[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2
[2]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5]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