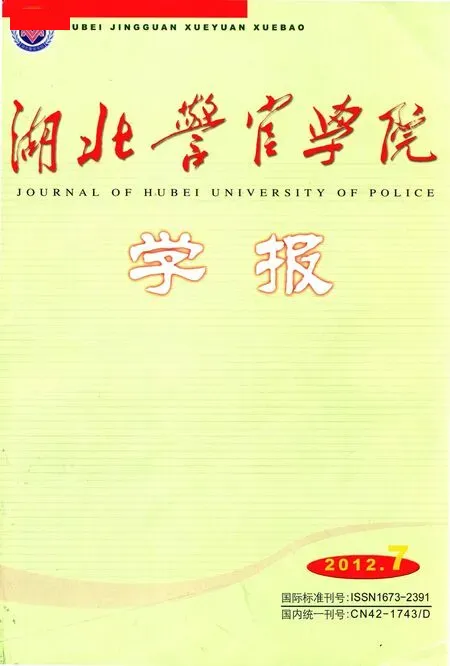传统与超越:构建案例引证制度
管仁亮,潘仲华,付红梅
(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135)
传统与超越:构建案例引证制度
管仁亮1,潘仲华2,付红梅2
(1.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2.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135)
相同或者相似情况同样对待是人类朴素平等观念的体现。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许霆案和何鹏案就是典型例证。相似的案件情节,法官的判决却差之千里。这凸显出法官裁量缺乏一个合理的统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探索一种新的案例制度,赋予其法律效力,才能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走出目前的困境。
案例引证制度;同案不同判;案例指导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总结反思的视角
要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必须建立完善的制度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并丰富相关法学理论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制度研究开始朝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相关的案例编纂活动推动了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人民法院的指导工作,有五百多个案例相继被公布。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案例指导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被明确提出来。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提出构建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以期解决目前的“同案不同判”问题[1]。但是,该制度一经提出,就饱受争议和质疑。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高调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但其实施仍然陷入了以下困境:
一是案例指导制度实际上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界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案例指导制度定位于弥补法律漏洞,这就涉及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的问题。如果承认其具有拘束力,就有违于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立法权独占制;如果不承认,则案例指导制度将仅作为法官判案的参考,不会产生较好的效果,最终会流于形式。二是案例指导制度的制定程序缺少有效制约。确定指导性案例与制定司法解释不同,其没有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意见的过程,也没有相关的备案制度。一旦确立相关的拘束力,司法权极易被滥用。三是指导性案例的推行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具体实践中,关于法官是否有权提出指导性案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何适用指导性案例、法官不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及相关处罚、指导性案例的期间和溯及力等都没有相关规定。[2]四是案例指导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案例指导制度对是否涉及权力监管部门、监管部门是重新设立还是法院内部设立、监督的权限多大、是否要建立专门的违规处罚体系等均无相关规定。五是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对法官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就目前而言,我国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要想在浩瀚如云的判例中找出依据或适用多个指导性案例,有不小的难度。上述分析也暗合相关学者观点,案例指导制度试行的地方性经验在效力载体、适用技术、边界标准、选择机制等方面呈现出上下不统一、平行差异大等问题。这是事关制度成败的重大问题,不能“缓议”,在制度出台之前应当仔细思量。[3]
截至目前,案例指导制度的制度性缺陷难以被克服。然而,其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情境中仍有存在基础和现实意义:一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特别是经济上的差异会影响司法审判的实际效果。因此,要做到“同案同判”,必须建立相关制度,以完成不同地域的司法衔接。二是大众传媒的发展易使“同案不同判”成为社会问题。三是为了适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及遵循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理念,司法系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通过司法能动的方式去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四是“案多人少”是当今司法审判的现实状况。我们急迫需要以一种司法判例的形式为解决类似案件提供统一的法律标准,缓解“爆炸式”的诉讼压力。五是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相关案例引证的需求。诸多大标的案件已经移交到了下级法院。面对新类型的疑难案件,下级法院需要印证相关“先例”。因此,要真正解决“同案不同判”,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我们必须探索一种新的制度,赋予其法律效力,以摆脱目前的困境。
二、发掘与剖析:价值分析的视角
基于案例指导制度的缺陷及现实中的需要,笔者认为可以改良现行案例指导制度为案例引证制度。所谓案例引证制度,是指以裁判文书为载体,将其中的裁判要旨、法律逻辑、裁判规则具体明确化,通过总体的制度构建和运行机制的梳理,在相关案件上征求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的意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后,以公报的形式进行发布,法官在审理同类诉讼时,须以案例的裁判规则为依据,并在裁决理由中加以阐述的制度。案例引证制度源于古代的判例制度和两大法系在判例法上的实践,同时借鉴了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时的经验。其基于固有的性能和功用,具备了诸多法律价值,具体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弥补法律漏洞。法律的稳定性必然导致一定的滞后性,一旦法律无法为法院审理案件提供明确依据,案例引证制度就应当适时出现以弥补其不足。大陆法系的传统就是通过立法来制定完整的程序,不要求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制定法律(法官造法)。但是事实证明,法律无法面面俱到。法律规则具有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根本无法形成尽善尽美、包罗万象的法律体系。[4]法律规则是一种语言。随着社会的多样化发展,这种以法律为载体的语言凸现出种种不足。案例引证制度可在相关规范不确定时统一裁判的适用标准,并发掘成文法在立法时的社会价值标准。同时,法官在审判中引证先例,既保持了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也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即暗含了“同案同判”的诉求。案例引证制度能巧妙地解释法律,不是“立法”,却有效弥补了司法解释的大量出现对成文法的冲击,同时又对成文法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随着国家立法体系的完备,司法解释将最终淡出我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将是以案例引证的方式辅助成文法的实施。
二是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传统的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主要是通过合议庭实现的,但由于具体的司法裁判的尺度不一,在相同事实的案件中,不同的法院或者相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判决。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太大,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到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以现行《刑法》为例,不论是在定罪还是在量刑方面,许多规定都比较抽象、笼统,弹性幅度大。除了法律规定,法官的个人因素也间接地对裁判的效果产生影响。因此,现在的量刑尺度基本上游走于寻求法官裁量权的灵活性与裁判尺度的统一性(限制法官自由裁量)之间。案例引证制度在诸多案件的经验、统计、分析、合法与合理的论证的基础上,脱离了具体案件情形,制定了普遍性规定,在量刑问题上使法官形成普遍性的经验,从而达到量刑公正和量刑均衡。当然,案例引证制度中的法官解释权并不是毫无限制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是在判案过程中,结合引证的案例在判决理由中加以明确的,而不是将司法解释权完全地交给法官。
三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案例引证制度建立的目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通过发挥引证案例的作用,有效解决了审判实践中各法院或法院的各合议庭适用法律时的“同案不同判”问题,保证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使司法审判达到公正性和统一性的要求。[5]案例引证制度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规范司法权的行使,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巩固了司法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6]其要求在相同或者大体相同的案件中实现相同的判决。一旦社会对法律规则或者裁判规则产生预期,人们将自觉地遵守法律。案例引证制度能将尊重“先例”的理念传承下去,将典型案例中的法官智慧和理性体现在之后的裁判规则中,以便法官处理大量的同类诉讼。要想使裁判获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信服,法官必须详尽说明裁判理由,以解决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很难获知具体的事实认定和判决理由的问题,提高判决的信服力。
三、解构与梳理:制度建构的视角
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构建相关制度的探索体现在案例指导制度和判例制度中,如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的案例指导制度、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判例指导制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导制度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示范性案例评审规则等。他们的理念与案例引证制度是一致的,都是为同类诉讼提供具体的裁判规则。但是如何构建案例引证制度的案例选择主体、案例选择标准、案例选择程序和案例发布方式,是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下文将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是案例引证创制主体。这里的创制主体包括案例的上报主体和决定主体。案例引证制度无法打破现有的司法体制,但是可以在现行司法制度框架内,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并负责具体引证案例的选择、制定、公布、汇编、备案和监督。案例的上报主体应当是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而决定主体应当是最高人民法院。部分学者坚持有限主体创制论,认为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创制法律。[7]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例如何约束上级法院。我们必须明确:基层人民法院可以成为判决创制的主体,即将法官的智慧和判案经验写进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是案例引证的创制主体,即由最高人民法院垄断引证案例的创制决定权。当然,高级人民法院也有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对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上报的案例进行初步的筛选,将提炼的裁判规则和法律要旨上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修改并公告。
二是案例引证具体标准。具体的裁判标准可以根据案件类型予以划分:第一类是法律规定相对原则性或者不明确的案件,如许霆案中对ATM机是否属于金融机构的认定。第二类是新类型案件,如知识产权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这类案件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结果往往极具争议性,很多时候会影响社会价值导向,甚至影响未来的立法活动。第三类是易发、多发性案件。此类诉讼即同类诉讼,法官的司法经验相对成熟。我们可以从此类案件中提炼出一般的法律要义,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约束。第四类是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往往比较困难。由于社会舆情、媒体参与、行政权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判决的作出会对整个司法领域产生大的“震荡”,如刘涌案、佘祥林案、聂树彬案、杜培武案、邱兴华案、许霆案、何鹏案、药家鑫案、孙伟铭案等。第五类是疑难复杂案件。这类案件在定性上存在争议,往往是法律未明确规定或者尚未立法的情形,亟需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例引证制度为其提供法律依据。[8]第六类是政策导向性案件。可通过案例的发布对当前的政策进行宣传,以实现法治观念的更新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如美国的米兰达案,就体现了法官对政策的考量。[9]
三是案例选编程序。应在中级及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置专门的案例选编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包括法院政策研究室成员、法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地方大学法学院教授及学者等。对于地方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典型、疑难案例,先由法院的政策研究室进行初步筛选,其间要进行充分讨论,接受法学院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备案。要增强案例的说理性,注意案例选编理由及评析的展开。典型案例的具体内容包括案件事实、控辩双方的观点、判决理由、判决结果以及提炼的判决要旨。遴选后的案件经案例选编委员会上报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再将中级人民法院遴选的案件和本院受理的上诉案件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挑选并确定。
四是案例引证发布方式。案例引证制度要吸取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不足,确保经遴选引证的案例一经向社会公开,当事人及代理律师能方便查询,并成为法庭抗辩的理由。在公开的渠道上,首先要选择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特别是对判决的正当性、合法性争议较大以及在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存在较大分歧的案例,要及时为法官提供法律适用的裁判规则和思路以及相关认定事实和审查证据的典型经验。其次要注重多渠道、多媒体的传播方式。《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等平面媒体具有周期短、发行量大的优势,可供案例引证制度选择。同时,为了方便法官和当事人寻找适用的案例,应建立数据库和案例检索系统,便于分类和查询。最后应重视半官方平台。引证的案例可通过一些出版机构编辑出版,丰富案例引证制度的传播途径。
五是案例引证的采用程序及相关的检察监督。案例引证制度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同类诉讼时,以案例的裁判规则为依据,并在裁决理由中加以阐述;不适用引证案例的应说明理由,理由不当则直接导致案件的重审或改判。人民检察院应对引证的案例实施检察监督,即可提出抗诉。尽管引证的案例已经脱离了审判环节,但是仍然与具体司法实践保持着密切联系。引证案例无法保证正确性和合宪性,理论上就存在被撤销和被提起抗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及下级人民法院在选取案例的过程中要征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意见,邀请其参与讨论,发表意见。
余论
案例引证制度需要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实现应有的效果。在整个司法体制框架内,各个制度之间都存在广泛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案例引证制度和法官遴选与监督制度、文书公开制度以及司法解释制度之间的关系:既要划分各自的适用范围,也要注重制度之间的互相衔接与支持。
[1]黄晓云.案例指导制度的历史沿革[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1(59).
[2]陈灿平.案例指导制度中操作性难点问题探讨[J].法学杂志,2006(3).
[3]杨力.中国案例指导运作研究[J].法律科学,2008(6).
[4]刘作翔,徐景.案例指导制度的理论基础[J].法学研究,2006(2).
[5]龚稼立.关于先例判决和判例指导的思考[J].河南社会科学,2004(2).
[6]陈卫东,李训虎.先例判决·判例制度·司法改革[J].法律适用,2003(1).
[7]冯军.论刑法判例的创制和适用[A].武树臣.判例制度研究(下)[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8]陈灿平.司法改革及相关热点探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9]张艳.案例指导制度的价值探究及理性定位[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D926
A
1673―2391(2012)07―0093―03
2012—03—31
管仁亮,男,山东日照人,西南政法大学;潘仲华,男,上海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付红梅,女,江西新余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责任编校: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