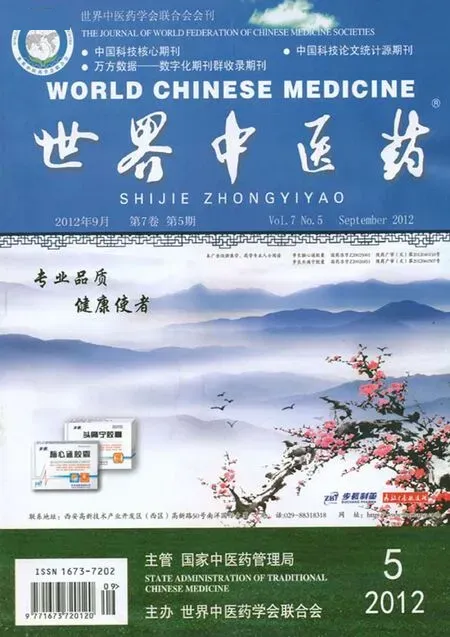鲁兆麟教授谈中医“一”的思维
张家玮
(北京中医药大学各家学说教研室,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1号,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1959年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1965年毕业留校工作。先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教研室、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和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任教。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1]。在长达40多年的中医教学生涯中,鲁教授从未停止过对中医教育教学的思考。他认为,学习中医,不仅要博学强记,更要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否则,不仅对所学的中医知识不能很好地理解和领会,同时,也会影响临床辨证论治的准确性和方药运用的发挥。举例而言,中医里“一”的思维,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思维模式,该模式贯穿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应用的各个环节。鲁教授认为,加强对中医“一”的思维的理解和认识,是学好中医的前提和基础。
1 以气为本的唯物观是中医“一”的思维的核心理念
中医学是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土壤的生命科学,在其发生、发展与演化的进程当中,无时无刻不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与启迪,因之而产生的独特辨治体系与宏观思维方法,使中医学本身孕育了强大的生命力,虽历经数千年而经久不衰[2]。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中医学采纳和引用[3]。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云:“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说明古代的医学家们把气看作是构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物质基础,即不仅人体是由气所构成,包括一切动物、植物以及非生命体也都是由气所构成。正如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所言[4]:“《素问》作者把物质当成是连续的气与不连续的形的统一。”这句话寓意深刻,明确地说明了一点,即气和形是不能割裂开来看待的。所谓形,是指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体,而其本质,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因此,整个自然界,就像一个气包裹着形的有机统一体。当然,这个统一体时刻处于运动和变化当中,而其主角仍然是气的运动变化,故《素问·六微旨大论》云:“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气有胜复,胜复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变”。人体处于自然界当中,其生理病理变化也必然要遵循这个道理。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才有“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的记载。正是在这种以气为本的唯物观的指导下,中医学才将人体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也将人与自然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进而才有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
2 以阴阳学说为基础的辨证观必须以“一”的思维为前提
阴阳学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周易》中“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论点可谓后世阴阳学说的代表。在中医学领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鲁教授认为,中医的阴阳学说,其内容除了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与相互转化之外,还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阴阳的一体观。阴与阳,实际是一体两面,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固有思想。这种阴阳的一体思想,在《内经》中亦早有体现,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也就是说,互为阴阳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或个体,必须存在于一个对立统一体当中,这时二者的阴阳关系才能够存在。以营气与卫气为例,二者均属气的范畴,由于营气行于脉中而将其归属于阴,卫气行于脉外而将其归属于阳。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拿营与血的相互关系来区分阴阳的话,由于营是血中无形之气,故属阳;而血是脉中有形之质,故属阴。同一个“营”,在不同的对立统一体当中,其阴阳属性截然相反。可见,“一”是“二”的前提条件。只有先把“一”确定下来,才能分析“二”的阴阳属性。正如明代医家张介宾于《类经·阴阳类》所言“阴阳者,一分为二”,深刻说明了阴阳的一体观是阴阳学说的理论前提[5]。这一观点,恰恰符合中国哲学关于“一”和“二”问题的认识。其实,“一”和“二”都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之一。虽然在中国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一”和“二”问题的认识各家表述略有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是一致的,那就是“一”为根本,“二”是“一”的化生[6]。正如老子所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医学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哲学一脉相承。
3 学习和理解中医基础理论必须以“一”的思维为指导
鲁教授认为,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数、理、化思维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思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主流地位。这种数、理、化思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注重分解,注重剖析。这种注重分解和剖析的思维模式在现代医学中就有明显的体现,如现代医院的分科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分为呼吸科、消化科、内分泌科、心血管科、免疫科、眼科等。这种看似细化的分科方式不可避免地在医生的脑海里形成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医疗意识。在这样一种大的医疗背景下,中医学所谓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经常在有意无意间被淡化,中医的特色和优势很难得到体现和发挥。鲁教授谈到,“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基础理论的两大特点,“辨证论治”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因此,要想把中医基础理论弄懂学好,就必须牢牢把握住“一”的思维。否则,对中医的学习就只能停留在表面而难以深入。
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在谈及精、气二者的关系时曾言“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明确指出了精、气二者的一体性、统一性及不可分割性。这种精气一体、阴阳一体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中医学的临床认知。比如,临床常用的补血名方——当归补血汤,方中黄芪用量是当归的5倍,其机理正如明代医家吴崑所言“有形之血不能自生,生于无形之气故也”,不离阴阳一体思想。再如,临床著名的补肾名方——六味丸和八味丸,现在普遍认为六味丸是补肾阴,八味丸是补肾阳,这种认识其实有失偏颇,容易让人引起误解。有关六味丸、八味丸的功效及组方机理,明代医家赵献可于其所著《医贯》中有过精准的论述“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这里所谓的“先天水火”,也即肾精、肾气。从这个角度理解,则八味丸属于填精化气,六味丸属于化气填精,亦不离阴阳一体思想。除此而外,鲁教授谈到,在学习中医时,由于受数、理、化思维的影响,很多人喜欢用“拮抗”的思维来看待问题,如看到寒象就会想到用热药,看到热象就会想到用凉药,看到便秘就会想到用泻药,看到便溏就会想到止泻药……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没有把握好中医“一”的思维。正因为如此,金代医家李杲的“甘温除热”理论,明代温补学派的命门学说等,历来都成为学生学习的疑难之点,其关键还是对“一”的思维的理解和运用。
4 学习中药和方剂必须以“一”的思维作依托
鲁教授谈到,现在的学生学习完《中药学》之后,出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把中药当作西药来认识和使用。如杏仁是止咳的,阿胶是补血的,枣仁是安神的,桃仁是活血的,贝母是化痰的,大黄是通便的,山慈菇是抗癌的……可以想象,以这种思维模式和理念来学习中药,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不言而喻。比如,现在一提到“半夏”,很多人都会想到是化痰药[7],而历代含有半夏的许多名方,如麦门冬汤、半夏泻心汤、旋覆代赭汤、小柴胡汤、温经汤、保和丸、藿香正气散、连朴饮等,其中的半夏又都不是在化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同样是在中药的认识问题上没有把握好“一”的思维。中药的药性理论,在于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引经报使,是把中药放在对于人体全身的调节角度上来看待问题[8]。当前这种忽略性味、重视功效的《中药学》学习模式,不仅不利于学生整体观念的培养,同时也扭曲了传统中医药学对于药物作用的认知。《素问·六微旨大论》曾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内经》已将升降出入总结为整个自然界的普遍运动规律,并将其应用于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用药。而中药的作用在于以偏纠偏,调整人体已经失衡的气机状态。因此,对于中药作用的认识,必须从调整人体气机的角度着手,其实质还是“一”的思维问题。
除中药之外,方剂的学习也是如此。现在一提到逍遥散,就将其归入疏肝解郁的方剂。问题在于,既然是疏肝解郁,为何方中要使用酸敛、酸收的白芍?于是就有了逍遥散治疗“肝郁血虚”的说法,即一边养血,一边疏肝,把阴血和肝气分开来看[9]。这种方解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逍遥散的理解还欠深入。鲁教授认为,从肝脏的生理特点来看,肝主疏泄,肝又主藏血,疏泄和藏血是肝脏的一体两用。如果只顾及其中的一面而忽略另一面,临床应用时就难免要出问题。比如,很多人一看见“肝气郁结”的患者,就一味地疏肝理气。实践证明,这种治法往往疗效欠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还是思维方法的问题,缺少“一”的思维的运用和指导。肝脏的“疏泄”和“藏血”,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开”与“合”。因此,要想使肝脏舒畅条达,就必须从功能上保证“开”与“合”、“放”与“收”的协调统一。如果用这样的思路来分析逍遥散的药物组成,则不难理解方中白芍的作用了,以柴胡的疏散,配伍白芍的酸收,一开一合,一放一收,于开合收放之间调整肝脏的气机,顺应肝脏的生理,从而使气机运行达到逍遥自在的境地[10]。这不仅是中医艺术的精髓,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再比如,清代医家杨璿于《伤寒瘟疫条辨》中在继承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创制的升降散,原方由蝉蜕、白僵蚕、片姜黄、大黄四味药物组成。这四个药物组合在一起,用现在的功效学概念去分析则很难理解。原书对该方解析为:“是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为引,蜂蜜为导,六法俱备,而方乃成。”而且,对于其中核心的四味药物——僵蚕、蝉蜕、姜黄、大黄,又有一个特别的说明:“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由此看出,升降散的组方思路,不是单一的君臣佐使,更有升降浮沉的思路在内。杨氏推崇升降散,称之“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如此得意的一首验方,其核心思维便在调节人体气机的升与降[11]。已故著名中医学家赵绍琴教授生前就非常喜欢使用升降散,在其保存下来的大量医案当中,不乏以升降散加减治疗疑难杂病的成功案例,这些都非常值得研究[12]。
除本文上述谈到的几点之外,鲁教授认为,中医“一”的思维渗透到中医药学的方方面面,可以探讨的问题还有很多。在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过程中,不管对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作如何精细复杂的划分,比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气血、津液、诊法、治则等,都时刻不要忘记这些类别的划分都是建立在以“一”为基础的思想之上,即必须从“一”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如果只知阴阳二分,而不知阴阳合二为一,对中医学整体观和辨证观的认知就会大打折扣,中医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也就很难得到发挥。而理解和应用“一”的思维,其关键,在于视人体为一个气化的有机的统一体。无论是对人体生理状态的把握,还是对患者辨证论治的分析,都一定要以气的整体观为基础。人体是由气所构成的,气机的运行失常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而使用中药、方剂治疗疾病的关键,同样在于对人体气机的调整。因此,遣药用方之时,切莫为“君臣佐使”所局限。把握好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引经报使,也就把握好了中医“一”的思维。《孟子·尽心下》曾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学习中医药学的“巧”在何处?“在于把握‘一’的思维”,鲁兆麟教授如是说。
[1]张家玮.鲁兆麟教授谈中医治学之道[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1,29(6):1351-1352.
[2]张家玮.“言不尽意”与中医学思想方法[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9,27(2):269-271.
[3]陈曦.论《黄帝内经》气化理论的思维特点.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2,18(3):236 -237.
[4]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M].1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2.
[5]尚力.理学对张介宾“阴阳一体”思想的影响[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22(5):17 -18.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1 版.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9:41 -45.
[7]周红伟.浅谈半夏之功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4):69-70.
[8]贾德贤,王谦,鲁兆麟.思考“辛味”[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1(2):88-90.
[9]谢鸣.方剂学[M].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97-98.
[10]张家玮,关静,王峰,等.升降理论在五脏阴阳辨证中的应用[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7,14(7):86 -87.
[11]鲁兆麟.中医各家学说专论[M].第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222.
[12]杨连柱,彭建中.从赵绍琴教授临床经验看升降散的双向调节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4):19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