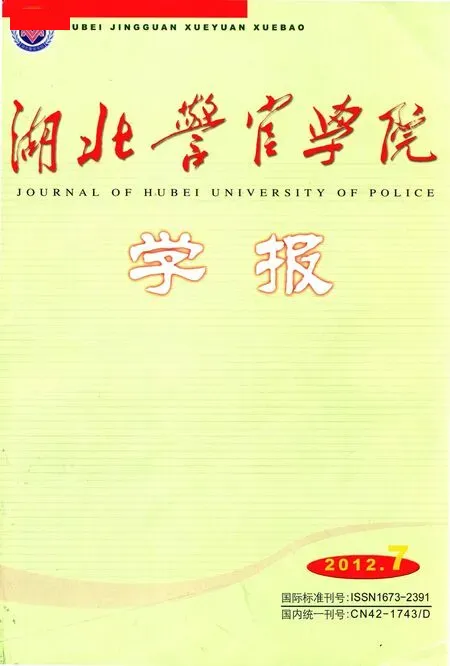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通信权修改之述评
刘 蜜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430034)
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通信权修改之述评
刘 蜜
(湖北警官学院,湖北 武汉430034)
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是对辩护权的重要保障,但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会见设置了诸多门槛,使得这种会见根本无法得到实现。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着力解决了会见难的问题,对辩护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提供了极大便利,并且对于公安司法机关侵犯这种会见权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救济途径。
会见通信;权利保障;诉讼地位;权利救济
辩护制度的确立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它已为各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普遍确认。“辩护原则,是在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基础上,要求刑事诉讼活动体现和保障这一权利的诉讼原则。辩护权是实质意义上的,而不应当是形式的。这就是有效辩护原则的要求。”[1]新《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较充分地吸收了《律师法》的修订成果,使律师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律师法》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不一致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着力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问题,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也保护了律师执业权,体现了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本文拟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通信权的完善方面对新《刑事诉讼法》进行初步解读。
一、“三证”直接会见制度的确立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和实施以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一直没有像辩护人那样独立,很大程度上,我们会把他们称之为“法律帮助人”、“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法律顾问”等,而不是辩护律师。因此,对于会见通信权来说,就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制约。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六部委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有这样一种司法惯例的存在——只要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而需要公安司法机关自由裁量的行为,都会演变成需要申请的权利。律师在侦查机关的会见通信权,这种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自身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也不能“幸免”。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已经成为了“申请会见权”,侦查机关的审批已经成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必经程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在律师被拒绝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后,有何种诉讼程序内的救济途径。因此,这种“被批准才会见”程序的存在,是实践中律师“会见难”的主要的原因,也被称之为律师办案的头号难题,因为不能和犯罪嫌疑人会见,后面的各项诉讼工作都难以展开。“一种本来属于法律明文授予的诉讼权利,竟然在司法实践中变成由办案机关、羁押机关单方面行使的审查批准权力。这种由‘会见权’向‘申请审批会见权’所发生的奇异转化,以及办案机关、看守所普遍漠视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恐怕要比‘会见难’本身更加值得关注”。[2]
基于以上种种弊端,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已经从根源上进行了纠正。第37条第1款规定:“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不仅如此,第37条同时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与辩护律师的会见、通信,也规定可以直接凭“三证”进行会见和通信。这一规定意味着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程序的律师已具有“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只要持有“三证”,无论是在侦查阶段还是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不需要再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基本从根源上解决了律师会见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实践中常常阻挠律师会见的看守所也明确了其“应当及时”安排会见的义务,并且对“及时”进行了时间上的量化,即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可以说,新《刑事诉讼法》的这一条文设计终于将《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统一了起来,杜绝了实践操作中有法却矛盾、无法更无权的现象发生,可谓其在保障律师诉讼权利最重要的进步之一。
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3款还作出了例外的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这个例外规定的一出台,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大家一致认为,基于以前实践的经验,这一系列需要侦查机关自由裁量会见的案件又会重蹈会见难的覆辙。但是我们认为对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在某些特殊犯罪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应当说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可行性。而且对于全世界都着力打击的恐怖活动案件,不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在程序正义方面都是打折扣的,例如美国的《爱国者法》。“从我国现阶段的犯罪形势、侦查条件以及侦查模式来看,如果允许律师在所有案件中随时凭‘三证’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必然难以突破,而且可能引发律师与侦查人员之间的尖锐冲突,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的初期。即使在法治国家,对于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3]基于此,这次新《刑事诉讼法》将这种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的制度作一定的限制,还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否则,过于理想化的会见制度虽然立法初衷是好的,在实践中可能会引发控诉机关大面积的抵制而难以落实,那么法律的规定就会再次成为一纸空文。
二、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规则的明确
如前所述,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已基本无诸多限制,但是如果在会见时,侦查人员在场进行监视,将造成律师会见流于形式。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派员在场。其后的《六部委规定》再次作出了重申,“……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派员在场,”这一系列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中对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构成了极大限制。一方面,侦查机关对律师的会见是否在场监听有着绝对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对于这种权力行使的失范,法律并没有规定律师和犯罪嫌疑人的任何救济措施;另一方面,虽然法律并无明文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与犯罪嫌疑人会见时的交流内容,但作为被侦查人员讯问的对象,侦查人员的在场监听也是对犯罪嫌疑人向律师陈述案情的一种妨碍,一旦犯罪嫌疑人不愿或不敢过多谈论案情,律师将无法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么针对控诉机关的指控,律师也就无法有效进行防御,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因此,法律的这种明文的“在场权”给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所幸的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为我们解决了这一大难题,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同样,辩护律师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也不被监听。这种监听既包括不受电子设备的监听,当然也更不允许侦查人员在场的监视。它既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更有利于保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真正实现有效辩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有效辩护原则是诉讼进步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理念的反映,更是追求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基于此,辩护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交流权也得到了诸多法治国家重视,在英美法系国家,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可以在无监听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还可以要求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接受讯问,如果犯罪嫌疑人想请而又请不起律师的话,政府会免费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此外,联合国的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文件也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会见给予了保障,如《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第18条规定:“被拘留人或被监禁人与其法律顾问的会见可在执法人员视线范围内但听力范围外进行。”[4]《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也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內进行。”[5]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的上述新规定正是体现了这种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越来越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精神。
三、律师执业救济途径之立法明示
在整个刑事司法体系中,辩护律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应该说“刑事司法体系的正当性正式依赖于称职的、具有职业道德的辩护律师们的参与——他们勤勉地帮助当事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6]因此,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应该属于辩护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它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开展辩护活动。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获得辩护律师的帮助应是他们的必需权利,而非奢侈权利,也不是被施舍权利。正是因为律师的法律素养、法律技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羁押后,他们会迫切地希望能与律师进行交流,尽快走出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著名诉讼法学家田口守一先生也曾表示,会见通信权对被羁押后与外界失去联系的犯罪嫌疑人来说,无疑是其保障自身最重要的诉讼权利,“是在押犯罪嫌疑人接受辩护人援助的、刑事程序法上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同时从辩护人来看,会见权也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固有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9条第1款把会见权也规定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7]
会见通信权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开端。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立法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国际法律文件已经将会见权视为是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苦心孤诣地确立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但是却又在不经意中为这种会见增添了诸多阻碍,这种阻碍直接导致在侦查阶段无法真正实现律师的会见通信权,而且当律师执业的过程中,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他们又应该向哪个机构申请救济呢?法律并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经过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会见已经比以前容易得多,但是如果看守所超过48小时不安排会见;又或者侦查机关限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需经侦查机关许可,虽然说这种设置按照国际通行的惯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实践中肯定又会对律师的会见设置门槛,同时这种许可的范围有多大,如何许可,新《刑事诉讼法》均未有明确规定。这都将形成新一轮的会见难,对此,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应如何得到救济呢?新《刑事诉讼法》第47条给了我们明示的答案,“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这条规定虽然明示了律师执业的救济途径,但是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负责受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审查程序,对于人民检察院的这种决定不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否获得进一步的救济程序?而且这条规定的权力设置主要是基于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而非是将被侵权人之申诉和控告交由中立审判者来裁断。如果案件由人民检察院自侦,如何保证这种裁判的公正性呢?就算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为追诉机关,这种“自查自纠”的处理方式将注定难以发挥权利救济的功能。“控辩双方发生争议之后,辩护方必须有机会向中立的裁判者寻求有效的司法救济,否则,对辩护权的保障就会由作为辩护方对立面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所掌控。这经常是导致辩护权无法实施、律师难以获得救济的重要原因。”[8]
按照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一方面,在刑事审前程序活动中,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并不参与对某种程序决断,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无法直接向法院提出救济权利的诉讼请求,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权可以负责对审前所有程序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法律并没有提供具体的程序设计,也就不可能给予有效的权利救济。因为在这种失范行为的裁断中,缺乏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中立的司法机关的介入,显然会破坏审前程序一直强调的三角诉讼结构,使其沦为一种行政程序而丧失了司法诉讼行为的基本性质,从而使人们对其公正性产生质疑,进而威胁到整个司法行为的权威性、信任程度。“无救济即无权利”,确立法院在律师执业困境中的权利救济主体地位才符合控审分离原则,才能真正落实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的庭审过程中,法院既不会主动针对公安司法机关阻碍会见的权力失范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也不会因为辩护人提出这一申请,而判定其“违反法定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这种规定,新《刑事诉讼法》虽然经过了修改,依然未能在最后的特殊程序中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因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给予了明示的救济途径,但是这种救济只能停留在立法的层面上了。
按照中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我们应在审前程序中设立一种类似于西方法治国家“预审法官”的司法审查官员,按照令状主义的原则,对审前程序的合法性进行裁断,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但是仅仅明确这种裁判主体是不够的,还必须为侵权行为设置不利后果,给予一定程度的惩罚。例如,在侦查阶段,对于非法剥夺或者阻碍律师和犯罪嫌疑人会见通信的,犯罪嫌疑人和律师可以向法院起诉,法院一旦确定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检察机关应该根据法院的裁定,不予批准侦查机关要求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申请,除非会见权得到实现;对于侦查机关没有正当理由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或者无故拖延安排律师会见的,法官可以直接裁断侦查过程中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得作为控诉机关证明有罪的证据。当然,我们甚至还可以仿效日本的做法,针对侦查机关不当的指定会见,辩护人可以对这一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请求国家赔偿。但是无论如何采取哪种措施,要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进行有效地救济,必须由法院担负起这种使命,也只有法院行使这种裁断的权力才可能真正摆脱会见难的困境,从而进入一个良性的运行轨道中去。
[1]宋英辉.刑事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52-253.
[3]孙长永.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制度立法的三大疑难问题管见[J].法学,2008(7):8.
[4]韩旭.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规定的进步与不足[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5):39.
[5]韩旭.辩护律师会见通信权规定的进步与不足[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5):39.
[6][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事诉讼法精解[M].吴宏耀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5.
[7][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刘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3.
[8]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60.
D925.2
A
1673―2391(2012)07―0015―03
2012—05—02
刘蜜,女,湖北恩施人,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
湖北省教育厅201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刑事侦查讯问程序研究》(项目负责人:曹诗权,项目编号:2010D064)及湖北省公安厅2011年度公安中心工作理论研究项目《公安机关公正廉洁执法问题研究》(项目负责人:张建良)的研究成果之一。
【责任编校:袁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