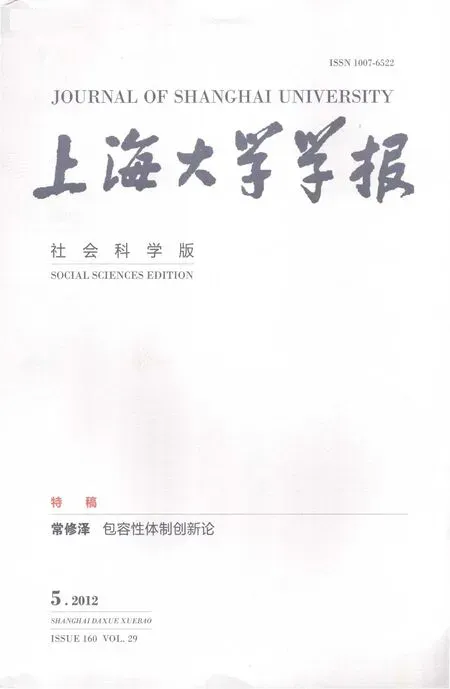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孙 媛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3;2.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363000)
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
——论吴宓的诗歌批评观
孙 媛
(1.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3;2.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363000)
在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中,“情”与“道”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诗歌形式成功与否,不以新旧而论,关键是要具备韵律格调之美。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及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吴宓的诗歌批评观念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在客观上给中国新诗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吴宓;诗歌;情与道;新与旧
文学革命时期,“五四”白话新诗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束缚,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白话诗运动的全面胜利在给现代诗歌带来更大创作空间的同时,也造成了抒情方式的随意化和语言秩序的散文化,使现代诗歌的发展一度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机。所以,从其诞生之日起,现代诗歌的建设问题就一直是诗人及诗评家争论的焦点,对白话新诗合法性的质疑和辩护如影随形,从未停止。作为20世纪20年代颇有造诣的旧体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吴宓敏锐地觉察到了现代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误区,针对新诗倡导者以“作诗如作文”[1]144之说抹杀诗文界限的做法,他一再强调诗与文的差别,从思想情感和艺术审美两方面强调诗之所以为诗的特殊性。他指出论诗的前提是“先确定诗之义,惟诗与文既相对而言,故诗之定义,须示其有别于文之处”,而“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对于诗来说,“(一)属于内质,(二)属于外形。……内质与外形之美,常合一而不可分离是也”。[2]3通过对其诗歌评论文章的详细解读,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吴宓的诗论中,对诗歌“内质”之美的强调,凸显的是诗歌批评的思想情感标准,对诗歌“外形”之美的强调,凸显的是诗歌批评的艺术审美标准,前者主要体现为对“情道合一”这一诗歌理想的激赏和向往,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为对融合新旧诗歌体式的思考。就这一意义而言,吴宓称赞徐志摩的诗句“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①见吴宓诗《挽徐志摩君》:“牛津花园几经巡,檀德雪莱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业,依新依旧共诗神。曾逢琼岛鸳鸯社,忍忆开山火焰尘。万古云霄留片影,欢愉潇洒性灵真。”载1931年12月1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亦是他自己的诗歌理想和诗歌批评观念的真实写照。
一、殉道殉情完世业
在诗歌的“内质”方面,吴宓主张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表现思想感情之美,而这种思想感情之美则主要体现在“殉道殉情完世业”的精神上。“情”与“道”,作为吴宓诗歌批评所关注的核心概念,在他的诗歌理想中缺一不可。譬如,他将好友方玮德对自己诗歌的评价收入1935年印行的《吴宓诗集》之中:“诗往往因情见道,又因道悟情,而以情道合一为教训,寓庄严于缠绵之中。其发也于感,其止也于悟。”[3]15其对方氏总结归纳的“情道合一”这一诗歌理想的激赏和向往由此可见一斑。在他看来,“情”的最高体现是“真情”,而“道”的最高体现则是“至理”。唯有“真情”和“至理”并重,做到“情智双修”,[4]12诗歌才能在表达感情的同时实现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到达“情道合一”的理想境界。在这里,吴宓并不赞成新诗阵营中“诗的本质专在抒情”[5]的说法,而是致力于从“情理兼到”[4]23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来理解与表达诗歌的基本“内质”。
首先,应该看到,无论是在诗歌创作还是在诗歌批评的过程中,吴宓对于情感力量的重视都是显而易见的:“耻效浮夸骋艳辞,但凭真挚写情思。”②见吴宓《南遊杂诗》之九十,全诗为:“耻效浮夸骋艳辞,但凭真挚写情思。传神述事期能信,枯淡平庸我自知。”载《吴宓诗集》卷十,中华书局1935年版。感情是吴宓对于诗歌“内质”的基本要求:“诗中首重真挚之感情。一时一地之生活感想,均应存其真相。”[6]1缺少了真挚情感这一重要“内质”,诗歌就不能成其为真正和纯粹的诗歌,“旧诗之堆积词藻,搬弄典故,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新诗之渺茫晦昧,破碎支离,矫揉作态,矜张弄姿;皆由缺乏真挚之感情,又不肯为明显之表示之故”。[3]2
有了真诚的情感,才谈得上切挚的笔法,吴宓对诗歌“切挚”笔法的倡导即是建立在对情感这一诗歌“内质”进行强调的基础之上:“所谓切挚Intense之笔者,犹言加倍写法,或过甚其词之谓。盖词人感情深强,见解精到,故语重心急,惟恐不达其意,使人末由宣喻者,故用此笔法。”[2]4“切挚”笔法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都是情感之“诚”,情感内质真诚与否是吴宓在诗歌批评实践过程中衡量诗歌价值时所采用的重要标尺,从他对白朗宁夫人和罗色蒂女士的诗作价值所进行的比较和评价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吴宓看来,尽管白朗宁夫人成就卓著,“读其诗者,莫不惊其才之高,服其力之伟”,但是,较之罗色蒂的诗歌中那种“幽婉真情的自然流露”,白郎宁的诗不免有些矫揉作态,言不由衷之处,其“情旨殊不自然”,缺乏真诚之情感与“切挚”之笔法。具体言之,“夫行事宜自然,作诗尤贵真诚。既生为女子,则当以女子天性中最高贵之处,及一己之所亲切感受者,形之歌咏,昭示吾人”。而白朗宁夫人诗中所抒写的情感不符合其身为女子的天性和身份,显然没有做到真诚自然,“其智力之广博,固可惊服,而其矫揉作态,强行追步,言不由衷之处,则未能或免焉”。相形之下,罗色蒂女士的诗作更为真诚自然地表达了身为女子的高贵天性及深挚情感,令“读其诗者,敬其高尚纯洁,喜其幽凄缠绵,而捻其一秉天真,发于至诚”。[7]88-89在吴宓看来,罗色蒂女士诗中所充溢的这种“天真”与“至诚”正是白朗宁夫人所缺乏的,显然更符合自己对于真诚之情感与“切挚”之笔法的要求,故而两相比较,罗色蒂女士的诗歌价值远远超过了白朗宁夫人。撇开这个结论的主观色彩不论(吴宓多情善感的气质和作为新人文主义信徒的身份决定了他会更加喜爱和推崇罗色蒂女士诗中那种既缠绵悱恻又隐忍节制的情感表达方式),单就其对真挚情感的重视和强调而言,吴宓作为“殉情”者的论诗姿态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尽管吴宓十分重视情感的力量,但是,真挚的情感并不是他对诗歌“内质”唯一和最终的要求,除了“浓厚之感情”,“明显之哲理”亦为优秀的文学艺术所必需。①吴宓在1928年5月14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英国大诗人兼画家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中谈到“罗色蒂之画与诗之特点,其中不具明显之哲理,亦无浓厚之感情”,故而称不上上品。因为,在他看来,“由情入道”才是“哲学之进步与方向”。[4]176“情”包括被各种现实人生境遇所激发出来的林林总总的感性经验,而“道”则代表着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永恒的真理。前者属于“多”的层面,代表着“人的世界”:“看来是混乱,无秩序,迷惘,与必然(一句话,浑沌);不可理解,不可控制。我们被捕捉在生存之网中,被卷入行动的潮流中,没有、也不顾我们个人的意志、理解和愿望。”[4]187而后者则属于“一”的层面,代表着“上帝的世界”:“作为一种秩序、系统、计划、协作、目的、理解、美、完美……它是完整的,永恒的,不可摧毁的——然而它也并不需要或依赖人的努力去保护或修补它——这样它就支持了我们的终极信念。”[4]187-188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如同“多”的最后归属是“一”,“情”的最后归属也应该是“道”,文学创作不应该停留在宣泄感情的层面,伟大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应该是“作家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不是他对具体的人和事的判断”。[4]19这种对宇宙至理和对人类理想存在方式的终极关怀即是吴宓所推崇的“殉道”者所应具备的论诗精神,②吴宓在《余生随笔》中说:“韩昌黎谓文以载道,此道非仅儒家之道,孔孟之道,实即万事之本原,人生之真理。如上所说者是也。余谓诗亦以载道。盖诗乃晓示普遍根本之原理也。”由此可见,吴宓心目中诗歌所应承载的“道”指的即是对宇宙至理和人类理想存在方式。(见《吴宓诗集·卷末》附录三《余生随笔》节录之三十三,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40页。)如此,吴宓对诗歌“内质”的关注重心就自然而然地从“情”转向了“道”,而后者就成了他对于诗歌的最终要求。
如前所述,“情”所代表的是“人的世界”,即“人界”,而“道”所代表的是“上帝的世界”,即“天界”。要想实现“因情入道”,从“人界”上升到“天界”,就必须借助自由意志进行自我超越,而诗歌借助“高妙之笔”所进行的“幻境”营造即是这种自由意志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只有经由“高妙之笔”“提高一层写法。……以想象力Imagination造成一种幻境”,[2]5-6诗歌才有可能实现由情向道的升华,挖掘和发现现实经验和真挚情感背后的本质精神和永恒真理,做到“由情悟道”,[4]186从对“真情”的体验自然而然地转向对“至理”①“真情”、“至理”之说见吴宓著,王岷源译:《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的探寻。
从吴宓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由情悟道=从生活的痛苦的经历(由于政治、爱情或战争等来的)到逐渐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宗教)”。[4]188很显然,吴宓并没有将“道”等同于柏拉图式的高高在上的客观存在的形而上理念,而是将其理解为宗教意义上的能够使人性获得完善、使人生获得救赎的真理。诗歌在吴宓的文学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完善人性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对此,他屡次借用安诺德(Mattew Arno1d)(1822—1888)《论诗教》(The Study of Poety)中“谓诗为今世之宗教”[3]5的言论加以说明:“诗之前途极伟大。因宗教既衰,诗将起而承其乏。宗教隶于制度,囿于传说,当今世变俗易,宗教势难更存。若诗则主于情感,不系于事实。事实虽殊,人之性情不变,故诗可永存。且将替代宗教,为人类所托命。”[7]188在这里,诗歌被提升到宗教的高度,而吴宓心目中的“宗教乃融合(一)深彻之理智(二)真挚之感情,信所可信,行所当行,而使实际之人生成为极乐”。[7]214也就是说,随着宗教力量的式微,诗的最大作用就是继承和代替宗教的功能去实现“深彻之理智”与“真挚之感情”之间的融合,通过“情智双修”,[4]12使人性不断趋于完善并最终具备神性的光辉。
对“情智双修”人生境界的向往决定了吴宓所理解的“情”“道”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圆融会通的,他理想中的“道”并不在“情”之外,而就在“情”之中,只有在这样情、道和谐的关系中,“由情悟道”的过程才会发展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从吴宓对《牛津尖塔》一诗所进行的分析与批评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这一观点。
《牛津尖塔》一诗写于1915年,②《牛津尖塔》(“The Spires of Oxford”)是英国女诗人莱兹(Winifred M.Letts)1915年所做,吴宓对此诗大加推崇。曾先后用文言与白话两次翻译过该诗。1922年发表于《学衡》第9期的译诗:牛津古尖塔/我行认崔嵬/黝黝古尖塔/矗立青天隈/忽念行役人/忠骨异国埋//岁月去何疾/韶华不少待/广场恣跳掷/人间绝忧痗/一旦胡笳鸣/从征无留怠//浅草供蹴鞠/清流容艇擢/舍此安乐窝/趋彼血泥淖/事急不顾身/为国为神效//神兮能福汝/就义何慨慷/戎衣荷戈去/不用儒冠裳/永生极乐国/勿念牛津乡。是英国诗人莱兹女士为追念在一战中阵亡的牛津学生所做的,吴宓曾在1922年和1936年分别以文言和白话翻译该诗,足见其对该诗的重视和推崇。而他之所以会对《牛津尖塔》如此重视和推崇,除考虑到该诗具有“格律韵调极佳,而字义明晰,毫不费解”[8]5的优点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此诗做到了情中有道——即于真挚之情中体现出了一种超越“一时一地之感情,一国一党之是非”的“普遍及永久之性”。[8]4-5在他看来,这种真挚之情和“普遍及永久之性”源自诗人莱兹女士的“温柔敦厚之心、悱恻缠绵之意”:[8]5牛津尖塔依旧,可曾经在塔下嬉戏的学生却已经战死在异国的荒郊野外,目睹着此情此景,感慨着物是人非,作者心中充满了“悱恻缠绵之意”,“感情深挚,悱恻低徊有余而不尽”;[8]6如果说“悱恻缠绵之意”使该诗充满了真挚动人之情,那么“温柔敦厚之心”则在这种情中注入了道,使情本身就包容了对于生命真义的体验和理解,从而远远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情感,流露出了对生命本身的关爱和敬仰,“通篇不及狭小国家之见,一党一族之争,超空立论,起于学术,终于明神,足见其命意之高妙”。[8]6可以说,正是这种与道合一的真挚之情使《牛津尖塔》超越了一般专以“写一己之壮怀”、“激国人之敌忾”为要务的“欧战文学”,后者中的“情”诚则诚矣,却缺乏“道”的约束和升华,只能停留在一时一地的狭隘民族感情上:“气虽壮,情虽切,志虽雄,然而人各爱其国而互相仇杀……在我则为忠君报国,在人则为灭天背义,故其弊也,不免狭隘之讥,专凭狠戾之气……虽受国人之欢迎,而为他族所垢弃,则以其乏普遍性也……方战之酣,人读之无不感动,然战后事过境迁,人心厌乱,恶谈兵革,则视之味同嚼蜡……则以其乏永久性也。”[8]4-5相形之下,在真挚之情中体现出“普遍及永久之性”的《牛津尖塔》实为吴宓情中有道,情道和谐的诗歌理想的最佳体现,故而他才会将该诗定位为“欧战中最著名之篇章”,认为其完全可“列上等而有传后之望”。[8]4
但是,在吴宓的具体诗歌批评实践中,他亦常常会为“真情”与“至理”、“体验”与“思维”之间的矛盾所牵绊,无法恰到好处地处理“情”与“道”之间的关系,每到此时,他便会自觉地将“道”置于最高的位置。在吴宓对诗歌所做的分析和评价中,“真情”永远也不能逾越“至理”,感情最终必然会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所左右。从他对但丁和雪莱所做的比较性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丁亦富热情,其性则较雪莱为严正深刻,但丁亦言爱,然非如雪莱之止于人间,失望悲丧,而更融合天人,归纳宇宙,使爱化为至善至美之理想,救己救人之福音,则其爱更为伟大更为高尚,此但丁为雪莱所莫及之处……”[9]1而他之所以会对女诗人罗色蒂的诗作倍加推崇,固然是因为欣赏其诗中所体现的深挚之情,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看到了这种“深挚之情”的背后是“移其人间之爱而为天帝之爱。笃信宗教,企向至美至真至善”[3]5的殉道者精神。在他的眼中,尽管“殉情”和“殉道”都是诗人“世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殉道”的重要性却必须而且只能排在“殉情”的前面。
二、依新依旧共诗神
如前所述,在诗歌的“内质”方面,吴宓主张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表现情道合一的“思想感情之美”,但要使这种内质真正落到实处,则需要以新旧兼容之法创造出“具有音律之文”作为其“外形”依托,“切挚高妙之笔”与“具有音律之文”共同组成了诗之所以为诗的本质属性,两者缺一不可。这一观点使吴宓对诗歌“外形”的分析和批评与当时新诗运动所关注的“诗体大解放”①胡适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谈到:“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这一焦点问题相隔甚远。
新诗运动是“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口,而新诗运动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则是通过实现诗体形式的大解放创建新体诗。在新诗运动的先驱者看来,古典诗歌的韵律形式作为束缚诗歌发展的枷锁,已经成了新诗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桎梏,必须通过“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来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10]81以完成新体诗对旧体诗的全面替代。如此,胡适等一代新诗创建者对以“白话”语言和“自然音节”为特征的新体诗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倡导,就推动着中国新诗从此走上了一条通过全面否定旧体诗的存在合法性来发展自身现代性的道路,一时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其理论宗旨“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11]新诗创建者和倡导者沉浸在诗体解放的狂欢之中,他们充满自信地认为,只要彻底摧毁旧体诗在现代中国的生存空间,使形式自由解放的新体诗拥有绝对的权威,新诗的现代性发展便会一帆风顺。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在新体诗迅速崛起并成为现代诗坛的正统和主流之后,中国新诗仍然面临着源自其内部的发展危机,需要进行新的突破和结构性的调整。在使新诗面临危机的诸多因素中,对旧体诗的笼统否定给诗歌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因为,“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12]264从共时的角度看,诗歌现代性的发展有赖于跨区域的文学交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诗歌现代性的滋生则有赖于跨时代的文学传承。只有在吸收传统文学积极因子的前提下,“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才能“因了外来影响而日益美化”,[12]264新诗对外来文学思想的借鉴和吸收才有可能避免“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12]264的弊端。胡适等人对白话新体诗的倡导虽然在回应思想革命和促进诗歌现代转化方面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其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价值的全面否定却直接导致新体诗的现代性建设因强行切断与本土文学根基的传承关系而陷入了忽视“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的误区,从而使其对西方诗歌理论资源的借鉴脱离了中国诗歌的自然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停留在机械搬运的层面上,这势必会为新诗理论和创作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可见,新诗的成功必须以旧体诗的消亡为代价的看法并不符合文学的实际发展规律,而新体诗的“弑父”行为也无法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走向真正的完善。对此,当时就有论诗者愤激地指出,“新诗底发动和当时底理论或口号,——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是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13]与胡适等新诗倡导者对新体诗和旧体诗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所进行的设定与强调不同,尽管吴宓并不否认诗歌形态会随着时势变迁发生变化,①吴宓在清华读书时,就在《余生随笔》中对赵云崧诗中“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之语赞赏有加,称之为“是实先获我心之语”,认为“凡文学皆循进化变迁之轨辙”。(见《吴宓诗集·卷末》附录三《余生随笔》之二,第18页)且进一步提出“文章既随时势为变迁,故其升降消长之机,亦皆循一定之公例。与政治风教,相比相成,如影之逐形,莫能独行。又如镜之鉴物,妍珪明暗,莫能丝毫改异”。(见《吴宓诗集·卷末》附录三《余生随笔》节录之三十,第36页)但是,在他看来,“诗之根本精神及艺术原理,当无有二”,[9]1“若论诗之本旨、诗之妙用、美恶工拙如何分辨、作诗必讲韵律等事,则中西各国之诗皆同”。[7]49正是在这种诗歌理念的基础上,吴宓对旧体诗的现代价值才充满了自信。应该说,吴宓的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特别之处,但是与“五四”新文学阵营对旧体诗除之务尽的决绝态度相比,他的见解显然更为宽容,也更有道理,并不能作为他反对新诗的凭证。在他看来,新诗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新诗的具体衡量标准,应该对新诗提出更高的要求。
吴宓所强调的对新诗的更高的要求,即是对诗歌固有规律的强调和追求。在他看来,“凡艺术必有规律,必须宗传(Tradition)。从事此道者,久久沿袭,人人遵守。然后作者有所依据,不至茫无津埃;然后评者可得标准(标准有精神、形式二种之不同,但皆关系重要),可为公平之裁判与比较”。[14]1而“文学中之规律尤不可不遵守,规律乃所以助成天才,不可比于枷锁”。[15]1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针对诗体盲目解放所带来的弊端,吴宓坚决反对剥离或抛弃诗歌的固有规律,认为那很容易使诗的本质性规约完全丧失,产生诗不是诗的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无论时势如何变迁,诗体如何变化,“切挚高妙之笔”和“具有音律之文”作为诗歌在“内质”和“外形”方面的审美特质,都是诗歌固有规律和本质规定性的体现。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他才将“韵律格调”上升到诗的本体地位,认为“诗之所述,无非喜怒哀乐之情而已。此情为人所同具,而诗之妙处正在其形式,即韵律格调之工。若去韵律格调而不讲,则所余之糟粕,人人心目中有之,何必于诗中求之。韵律格调属于文字之本体,不能以他国文字表出”。[7]49由此出发,他坚决反对时下废除韵律格调的新诗主张:“若举韵律格调而歼除之,是直破坏诗之本体,使之不存。”[2]4强调即使是在革新诗歌形式建立新诗体的时侯,也必须将“具有音律之文”作为诗歌不可或缺的美学内核加以坚持。
在《诗学总论》一文中,吴宓从三个层面步步深入地对中国诗歌音律的基本含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其一,音律由节奏而来:“音律乃节奏之一种”,“故凡有节奏者,皆可成音律”。所谓“节奏者,重叠Repetition错综Alternation之排列也”。即“某形式某声相重而叠见,而与他形式他声相间而错出,合此二者而成节奏”。在吴宓看来,“本乎异中有同,寓整于散之原理”的节奏是使文学作品产生“动人之美感”的关键,故而应为“诗与文之所同具”。[2]12-13其二,音律虽然具有节奏的基本特征,但是却不是一般的节奏,而是“节奏之整饬而有规则者也”。具体言之,若是如“甲甲乙甲乙甲甲乙乙乙乙乙甲甲乙乙甲乙乙乙甲乙甲甲”般只是“相间相重”,则为节奏;若是如“甲甲乙乙甲甲乙乙甲甲乙乙甲甲乙乙甲甲乙乙甲甲乙乙”或“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甲甲乙”般“相间相重之处之间隔有定”,“则名之曰音律Metre。”与诗文同具的节奏不同,“音律者,乃诗之所独有。故可以音律别诗与文。……无音律者,不能谓之诗”。[2]12-13其三,诗歌音律的具体形式是由文字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就是说,尽管各国之诗皆有音律,但是,各国语言文字发音方式的不同在使人产生不同听觉美感的同时也决定了各国诗歌音律的不同类型和特征,“希腊拉丁诗之音律,以长音及短音之部分,相重相间而成”。“英国诗之音律,以重读及轻读之部分,相重相间而成”,“吾国诗之音律以仄(高)声及平(低)声字,相重相间而成”。[2]13-18尽管吴宓的这种分类与归纳方式尚有粗率和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其对中西方诗歌音律的不同表现方式和汉语诗歌音律的特征所进行的分析和强调在当时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经过对中西方文字发音方式的分析与考察,吴宓断言,以汉语平仄高低的字音特点为基础形成的韵律之美是中国诗歌音律的重要体现方式——“吾国文字之本性”决定了中国诗歌更“适于用韵,行之数千年而已,然经验可以证明,故今仍当存之,决不可强学希腊拉丁古诗或借口英诗之Bank Verse而径倡废韵也”。[2]20如此,平仄之韵就成了中国诗歌在形式方面的固有规律和美感来源,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一旦受到破坏,必然会对中国诗歌创作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今世之无韵自由诗,但求破坏规律,脱除束缚”。[15]1虽“以改良中国之诗自命”,实际上却昧于诗之原理,[2]4“直与作诗之正法背道而驰,所得者不能谓之诗也”。[15]1在吴宓看来,无论诗歌演进到了何种时代,只要作为其构成媒质的文字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固有的诗韵规律就不会被全盘抛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才会强调,“诗韵不特有其演进之历史,且有其当保存之价值”。[14]1中国古典诗歌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和流传,已经将中国文字平仄起伏的诗韵潜质发挥到了极致,其韵律格调闪现着无法磨灭的形式美,充分凸显出汉语的特性及其魅力,粗暴地对其冠以“旧体诗”之名加以贬斥,借牺牲旧体诗的诗韵来凸显新体诗的价值,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荒谬的。而且,尽管西方各国诗歌都有诗韵规律,但是其所用媒质与我国文字发音方式的不同使其与我国诗歌所固有的诗韵规律有很大差异。如果在新诗创作中全面否定我国诗歌传统,转而盲目崇信和照搬外来诗歌的创作方法,就很容易导致新诗的文体形式发生负性蜕变,从而削弱甚至失去中国诗歌特有的美感魅力与艺术表现力。由此可见,吴宓对中国古典诗歌韵律的推崇并不只是出于自己的个人偏好,而是经过了审慎的考察研究和严密的学术逻辑推理,有其具体的理论支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吴宓对中国诗歌音律特征的强调,既是对新诗开创者有意忽略甚至破坏中国诗歌审美形式的偏激行为的一种纠正,又是对当时全盘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学倾向的一种反拨,就中国现代诗体的建设而言,他的观点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在当时,吴宓的诗韵观点却因为新文学阵营的冷落和排拒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新诗现代性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损失。
新文学阵营之所以会冷落和排拒吴宓的诗韵观点,主要是因为它牵涉到了以文言写诗还是以白话写诗这一在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①时至今日,古代的诗歌辉煌和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都已经尘埃落定,反观历史,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给予我们的启示更多的应该是现代诗歌可以用白话来写,而不是像当时的新诗倡导者所激烈主张的那样:现代诗歌不能用文言来写。新文学阵营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所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用“白话征服这个诗国”,[1]155即“坚持要用白话作诗,以抢夺下白话文学这场战争中的最大壁垒……因为诗毕竟是文字最精纯的结晶,是文学艺术的极致表现。诗这个用以言志的战场可以攻下,白话文的成功才可以得到终极的保障”。[16]为了彻底攻下诗歌这个“战场”,新文学阵营将旧体诗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坚决反对以文言写诗,主张“把从前一切束缚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0]81在新文学阵营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大环境中,吴宓反对废除文言诗的主张明显不合时宜且别有深意。尽管他后来已经不再反对以白话写诗,①从1920年的《英文诗话》、1922年的《诗学总论》、1923年的《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1932年的《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等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白话新诗从拒绝到接受的态度转变。而且,白话新诗创作者徐志摩罹难之后,吴宓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开辟专版,发表叶公超的《志摩的风趣》、胡适的短诗《狮子》和自己写的诗歌《挽徐志摩君》对其进行悼念,并在《宇宙风》上发表文章《徐志摩与雪莱》,对徐的诗歌大加赞赏,甚至将其和自己一向崇拜的英国大诗人雪莱相提并论。但是却一直积极倡导且身体力行地进行着文言诗歌的创作,因为,在他看来,除了可以发挥保存汉文文字特质、光大民族文化的作用,文言诗歌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诗词特有的韵律之美,具有白话诗歌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在新文学阵营如火如荼地开展无韵的、口语化的白话诗歌创作的历史大环境中,吴宓对文言诗歌的重视和强调,纵然与他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但从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来看都已经具备了一种与白话诗运动对垒的姿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文学阵营会将吴宓视作捍卫旧诗反对新诗的守旧派代表——在一片高涨的革命热潮中,倾听对垒者的声音,原本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在今天看来,新文学阵营对吴宓诗论和诗作的指责显然不够公正,因为他在批评“新派以破除格律恣意乱写而油滑轻率”的同时,也指出了“旧派以但知步武格律剿袭摹仿而亦油滑轻率”,认为两者“其失相等”。[17]而他以推崇中国古典诗歌韵律和进行古体诗写作的本意亦不是为了固守旧格律和文言文,而是为了捍卫诗美。况且,早期新体白话诗的创作在诗美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不足:“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所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18]对此,有论者指出,“我们且慢为白话文运动的成功觉得欣喜。假如白话文只有实用的价值,假如白话文只为便于普及教育之用,白话文的成就非但是很有限的,而且将有日趋粗陋的可能。假如白话文不能成为‘文学的文字’,我们对于白话文,始终不会尊重。……我们现在写诗是白话文能不能‘担负重大的责任’,白话文能不能成为‘美’的文字。假如不能,白话文将证明是一种劣等的文字;白话文既是大家写作的工具,那么中国文化的前途也就大可忧虑的了”。[19]72-73而后期新月派所要做的,就是要反拨主张早期白话诗缺乏诗美的倾向,将诗歌创作的重心从白话转向诗,而从新诗创作中汲取旧诗的形式美,则是他们完成这一任务所要采取的重要手段。就这一意义而言,吴宓对于新诗诗美的要求和新月派的努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其主张的合理性也在新月派的具体创作实践中得到了证实与回应。他之所以会对新诗诗人徐志摩赞赏有加,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诗韵格律对徐志摩诗歌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带来的诗美:“杨丙辰君讥徐志摩君过重格律,而方玮德则以此为徐君对于新诗之首功。……然而天才及修养既在个人,则对于一般人,极力提倡格律,使作者对于表现技术咸极努力而不苟且,此在任何时地任何派别,均属正道,均是美事。是则方君推重徐君之说,诚确乎不可易矣。”[6]1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白话诗人的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中已经不可能再固守旧体诗的精严格律,而吴宓仍然对其在诗歌格律方面的贡献加以肯定,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吴宓探讨徐诗形式的立论重心显然并不在其是否坚守旧格律,而是在其是否具有和谐的音律之美。易言之,吴宓此时所强调的格律已经走出了传统诗学范畴的语用空间,而更接近于现代理论视角下的音律概念,其中暗含着他对新月派诗人深入探求现代汉语音乐性的肯定之意与激赏之情:“作新诗者,如何用韵,尽可自由试验,创造适用之新韵。”[14]1由此可以推断,吴宓强调学习古典诗歌字音平仄和押韵法则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拘泥于已有的规范,而是为了从加强诗歌语言审美功能这一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现代诗体形式的建设问题。
可见,在现代诗体形式的建设问题上,吴宓和早期新诗倡导者有着巨大的分歧:前者注重的是诗体形式的审美价值,后者强调的是诗体形式的工具效用,造成这种分歧的深层动因是双方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方式。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社会之维和审美之维应该共同构成其相生相克的双重维度。但是,在中国诗歌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追求启蒙理想的渴望和焦虑却使早期新诗倡导者策略性地选择和认同了文学现代性中的社会之维,有意回避和忽略了其中的审美之维。显而易见,早期新诗倡导者更多地是将诗歌作为改良政治和启蒙思想的武器,其立论重心显然并不在诗体形式的审美价值本身。在他们看来,新诗主要是作为建构和宣扬社会现代性理念的工具而受到重视,新诗形式的根本价值在于其传播新思想的实用性,“明白清楚”是第一要务,①1924年胡适在为他侄儿的遗诗作序的时候,对胡适之体的新诗特点作出了总结:“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胡思永的遗诗〉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所以,作为对社会现代性追求缺乏工具效用的诗体形式,中国古典诗词严格的韵律格调就成了诗歌创作和传播过程中亟须清除的障碍。相形之下,吴宓更多地是从审美之维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现代性和诗歌现代性的,诗美是其评判诗歌价值的重要标准,他对新诗运动质疑的主要理由也是该运动破坏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审美特征。在他看来,无论新诗旧诗,只要创作出“具有音律之文”,符合诗美要求的就有可能成为好诗。
显然,对诗歌形式艺术性和审美功能的强调有助于吴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新诗旧诗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路,打破偏激的新诗革命埋下的诗体定型的窠臼,使其获得了不同诗体形式可以并存的视野和思路——“在现今新诗(语体诗)可作,旧诗亦可作”。[14]1与早期新诗倡导者对旧诗形式一概否定的偏激态度不同,吴宓并不主张在新诗旧诗之间划分截然的界限,更没有把旧体诗和新体诗这两类诗体在形式上的区别看作衡量诗歌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尺。他对于现代诗体的理想是“依新依旧共诗神”:既欢迎新的,也发扬旧的;既反对一味模仿传统诗词形式、不思创新的因循守旧倾向,又反对全盘抛弃旧诗创作、简单割裂新诗创作与传统诗词关系的激进武断做法。吴宓对于现代诗体的这种理想,体现出了对新旧文学的兼有态度和包容态度。可以说,他以“依新依旧”、新旧兼容的方式推动现代诗体形式建构的观点在客观上已经给中国新诗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给我们留下了假想的空间:吴宓如果在进行旧体诗写作的同时,也能够用“新式(语体诗)”的实际创作成就来作为其“依新依旧”的诗体形式理想的注脚,情况又会怎样呢?令人遗憾的是,历史不可能假设,撇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偏见不谈,也许实际创作成就的匮乏才是限制吴宓“依新依旧”的诗体理论在新诗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的关键原因。
在今天看来,吴宓从“内质”和“外形”两个方面入手来进行诗歌定义和诗歌批评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突破或创新之处,但是在主张恣肆奔放地宣泄情感和展示个性的白话新诗运动和“诗体大解放”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中国现代诗发展过程中,吴宓进行诗歌批评时所坚持的理论主张却无疑是以特立独行和不合时宜的面貌出现的。而其诗歌理论与批评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诗坛在白话诗理论主流之外的另一诗论倾向,所以,对吴宓诗歌批评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吴宓诗学思想,对于重新挖掘整理看似已经成为定论的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胡适.胡适文集: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吴宓.诗学总论[J].学衡,1922,(9):1-20.
[3]吴宓.吴宓诗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吴宓.文学与人生[M].王岷源,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5]郭沫若.论诗三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215.
[6]吴宓.论诗之创作——答方玮德君[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01-18(8).
[7]吴宓.吴宓诗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吴宓.英诗浅释[J].学衡,1922,(9):1-8.
[9]吴宓.挽徐志摩君[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12-14(7).
[10]胡适.胡适文集: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C]//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8.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8.
[12]周作人.扬鞭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3]梁宗岱.梁宗岱文集:2[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156.
[14]吴宓.诗韵问题之我见[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01-18(8).
[15]吴宓.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J].学衡,1928,(63):1-8.
[16]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87.
[17]吴宓.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06-03(13).
[18]梁实秋.梁实秋文集:6[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178.
[19]夏济安.夏济安选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72-73.
Abstract:This essay elaborates Wu Mi's poetic criticism.According to Wu Mi's poetry ideals,firstly ,the relation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isn't contradictory,but supplement each other;secondly,the standard of the external form of poetry's characteristics isn't“new”or“old”,but the beauty of poetic rhythm.In the Chinese modern poetry development course during which the feelings and individuality were overemphasized,Wu Mi's poetic thought showed another tendency of literary criticism besides the free verse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Objectively,Wu Mi's poetic thought provided the Chinese new poetry development with another selection.
Key words:WU Mi;Poetry;The sense and sensibility;The new and the old
(责任编辑:魏 琼)
Finishing the Undertak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Construsting the poetic soul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ew and the Old——The study of Wu Mi's thought about poetic criticism
SUN Yu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Jilin University,Jilin 130023,China;Chinese department of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Zhangzhou 363000,China)
I206.6
A
1007-6522(2012)05-0108-12
2010-10-2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11JHQ048)
孙 媛(1975- ),女,河北省张家口市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基础文艺理论和现代文论史。
10.3969/j.issn 1007-6522.2012.05.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