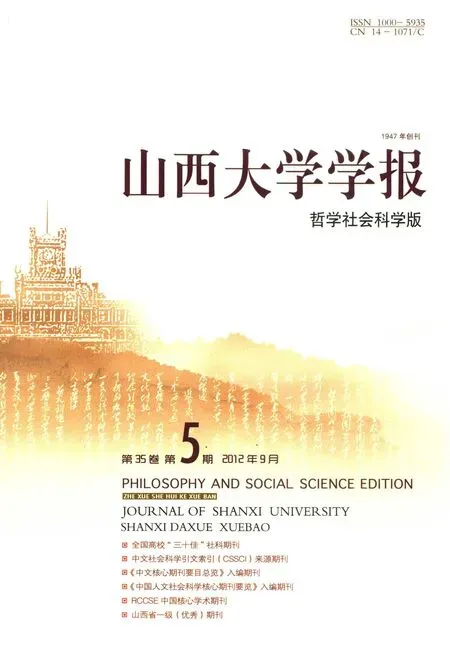韩柳文道关系论的三个层次
罗书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韩柳文道关系论的三个层次
罗书华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文道关系是韩柳古文理论的核心。在这方面,人们多看到韩柳“文以明道”的论述,其实,韩柳的文道关系论包含了三个层次,一是文以明道,一是文本于道,一是道归于文。正因为后两个层次的存在,韩柳得以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他们的道论才成为文论而不是纯粹的思想论。缺少任何一个层次,对于韩柳文道关系的理解都不全面。
韩柳;古文理论;文道关系
韩柳古文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文,一是道,文与道的关系则是其古文理论的核心。提起韩柳文道关系,人们很快就会想到“文以明道”来。“文以明道”固然是韩柳文道关系的重要一维,然而,这并非韩柳文道关系的全部。要正确理解韩柳古文与古文运动,就应注意到韩柳文道关系的其他维度。
一 文以明道
韩柳的志向在道而不在文,只是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自己的宏道,以及道与文无法分离的原因,他们这才回到文学之中。而即使回到文学中,他们仍然不能忘怀自己的大道。在他们心里,道永远是第一位目的,文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途径。韩愈说得清楚:“修其辞以明其道”,[1]“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2]后面的“理”也就是“道”,前句与后句互文。也许在明道的过程当中,他不知不觉地被文章所吸引,也许他人不太理解他的真义,韩愈还曾多次表白与辩解。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3]在《答尉迟生书》中他也说:“愈又敢有爱于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4]在《题哀辞后》中他也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5]这些言论,是表白,也是一种自我提醒。
柳宗元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以明道为目的,不过,没过多久就回归到道的轨道上。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6]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他也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7]以为不管从写作的角度看,还是从接受的角度(读书)看,都应该以道为准的。道虽然离不开言辞,要依靠言辞来传播,但接受者却不应忘记自己的目的是什么。接受既是这样,写作当然更不在话下。
韩柳的写作都是这种理论的忠实实践,韩愈在《答窦秀才书》中反思自己少年时虽然“发愤笃专于文学”,但是因为“不通时事”,“学不得其术”,因此作品“皆符于空言而不适于实用。”[8]就清晰地折射出他成熟时期为道而文,而不是为文而文的创作风貌。与此相应,他们对古代作品的接受、分析、批评,也是以有道无道、道醇道疵作为标准。柳宗元作《非国语》,对《国语》进行清理与批判,就是因为“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9]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也说:“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10]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又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11]在他看来,文章的目的在于道,如果书著文章偏离道的轨辙,那就无异于文锦覆井,文章写得越漂亮越有文采,就越让人沉迷在文采中不能自拔,越让人掉进陷阱当中,而与道的距离当然也就越远,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益。
站在现在的立场看,韩柳这样强调文章中的道,多少有些重道轻文的倾向。不过,考虑到韩柳本来是天才的文章之士,他们这样说,其实不无自警的意味。另外,六朝以来,文笔两分,文章与道日趋分离,所谓“文章道弊五百年矣”。[12]入唐以来,由于科举考试中帖经、特别是诗赋比重的增大,士子们越来越不重经学,文与道的分离状态并没有得到弥合。广德元年(763)杨绾上《条奏贡举疏》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孟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13]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贾至不仅对杨绾的说法表示赞同,甚至还认为帖经、诗赋的考试,直接导致了“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最后“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14]虽然陈子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也一直在呼唤道的归来,但是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将韩柳“文以明道”放到这个背景上来考察,就可以发现,他们对“道”的强调,不仅不是偏颇,相反,恰恰是形势的急需。正是因为有了道,他们的文章这才有了充实的内容和强劲的发展动力,而古文也得以在道的带动下全面复兴。
二 文本于道
将道作为文的目的,而将文作为实现道的途径,固然促进了道的回归及文道的结合。不过,严格说来,目的途径的说法还是把道与文看作两件不同的事物。好在这并不是他们对文道关系的唯一认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还是从本源与呈现的角度来认识道与文的关系。
韩愈在著名的《答李翊书》中,一下笔就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以为文是道德的外表,言下之意,道德是文的内里,有道德,也就自然有文章。接下来他又进一步阐述说,要学习古文,“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15]以为文章是枝叶和果实,道德则是根本;文章如光,道德就像是这发光的膏油。文章的关键不在文章自身,而在于道德修养。根深才能叶茂,根深自然叶茂;膏厚才能光晔,膏厚自然光晔。也就是说,它们其实是属于同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而不是分离的两个事物。在《答尉迟生书》中,他也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4]而《进学解》中也有“闳其中而肆其外”[16]这样的名言。这几句话中的“中”、“实”、“本”、“形”、“行”、“心”,合起来也就是“道”;“发”、“末”、“声”、“言”、“气”也可以说是“文”,或者说与文相对应。都是从本体的角度来认识文道关系。
柳宗元虽然没有像韩愈那样明确地说道文是一体本末,但是许多相关论述也包含了相近的意思。他说:“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7]“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17]他称赞叔父“植于内而文于外”,[18]称赏杜周士“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积为义府,溢为高文”,[19]都隐含了道为内,文为外;道为本,文为末;道为源,文为流的意思。以为有内就有外,有本方有末,有源才有流,先道后有文。
客观地说,道本文末的观念并不是韩柳的独创,前人对于这点也多有论说,这个观念与他们自己的目的途径说也不尽相合。不过,前人往往只有理论上的论述,而缺乏创作实绩的支撑。只是到了韩柳,这才真正在写作上践行这样的理论,将它们发展成深入人心、深入散文的重大命题。
三 道归于文
韩柳既以道为文的目的,以道为文的根本,确实有一些重道轻文的意味。不过,在另一方面,韩柳对于文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也有清楚的认识。
韩愈在谈到文道关系的时候,有时会将文看作道的附庸,但也有不少论述很难分清文道的先后轻重,比如他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3]“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0]文道就算有些先后轻重,差别也是微乎其微了,似乎它们是互为起点和终点,头衔尾,尾连头,循环传动的关系。对于庄子、屈原、扬雄、司马相如等人,韩愈多有微辞,可是,《送孟东野序》与《答崔立之》中却又分别称他们为“善鸣者”和“古之豪杰之士”。文道之间略有矛盾,而大体统一。
相对说来,柳宗元对于文的独立价值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加强调。他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穽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栝羽之道,圣人以为重。”[21]“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22]将无内与无外相提并论,其实也就是将有内与有外、道与文等量齐观。就算是将文当作达道的工具,它也是非同一般的、具有独立价值的工具。正因为这样,他一方面对于《庄子》、《列子》、《国语》的思想内容或者“道”的缺陷提出非议,另一方面对它们的文的成就却持赞赏口吻。如说《列子》“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23]《国语》“深闳杰异”。[24]
韩柳对于道的强调,本来就有中和天性中喜好文学的因素,既然如此,就算他们极力想用道来平衡或掩盖,也未必能够真正将文忘怀。柳宗元自己就坦承:“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7]他们虽然强调从道出发,以道为目的,却常常给人以沉浸在文中的印象。对于这点,后人多有评说。吴孝宗说:“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韩退之学文而及道。”[25]程颐也说韩愈:“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26]朱熹更说他:“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27]“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28]“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29]王守仁更是语带不屑地说:“退之文人之雄耳。”[30]清人钱大昕也说:“魏征、陆贽之论事,刘蕡之对策,皆经国名言,所宜备录。至韩愈《进学解》、《平淮西碑》,柳宗元《贞符》、《与许孟容书》之类,文虽工而无裨于政治。”[31]这些说法固然多带道学味,但是指出韩柳主要以文胜而不是以道胜,却与事实大体吻合。
韩柳以道作为文的目的,又以道为文的根本,但结果却是道归于文,文道合一。对于文的相对压制没有成就他们的道,对于道的强调却成就了他们的文。虽说他们的儒道在思想史上也可以占据一定的篇章,但它们还不足以形成“古道运动”,更不要说与文学史中的“古文运动”相比。这在政治史、思想史上也许是损失,但在散文学史上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柳宗元在《答严厚舆论师道书》说:“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32]明确表示自己不做章句师,明确表示自己以“言道讲古穷文辞”为己任,“言道”与“讲古”与“文辞”三者并提,最为准确地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文道关系。
[1]韩 愈.争臣论[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170.
[2]韩 愈.送陈秀才彤序[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668.
[3]韩 愈.答李秀才书[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527.
[4]韩 愈.答尉迟生书[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462.
[5]韩 愈.题哀辞后[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500.
[6]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M]//柳宗元集:卷 34.北京:中华书局,1979:873.
[7]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M]//柳宗元集: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9:886.
[8]韩 愈.答窦秀才书[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639.
[9]柳宗元.非国语序[M]//柳宗元集:卷43.北京:中华书局,1979:1265.
[10]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M]//柳宗元集: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9:825.
[11]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M]//柳宗元集: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9:822.
[12]陈子昂.修竹篇并序[M]//陈子昂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1960:15.
[13]杨 绾.条奏贡举疏[M]//全唐文:第四册(卷331).北京:中华书局,1983:3356-3357.
[14]贾 至.议杨绾条奏贡举疏[M]//全唐文:第四册(卷368).北京:中华书局,1983:3735.
[15]韩 愈.答李翊书[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454.
[16]韩 愈.进学解[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910.
[17]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M]//柳宗元集: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9:880 -881.
[18]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M]//柳宗元集: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79:294.
[19]柳宗元.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M]//柳宗元集:卷 22.北京:中华书局,1979:594.
[20]韩 愈.答陈生书[M]//屈守元,常思春.韩昌黎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1529.
[21]柳宗元.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M]//柳宗元集: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79:607.
[22]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M]//柳宗元集:卷21.北京:中华书局,1979:578-579.
[23]柳宗元.辩列子[M]//柳宗元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9:108.
[24]柳宗元.非国语序[M]//柳宗元集: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79:1265.
[25]吴 曾.韩退之学文而及道[M]//能改斋漫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60:234.
[26]程 颐,程 颢.河南程氏遗书:卷18[M]//刘元承手编.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32.
[2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7.战国汉唐诸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73.
[2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22.吕伯恭[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52.
[29]朱 熹.沧州精舍论学者[M]//朱熹集:第七册(卷74).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3901.
[30]王守仁.传习录上[M]//王阳明全集: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7.
[31]钱大昕.续通志列传总叙[M]//潜研堂集:卷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95.
[32]柳宗元.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M]//柳宗元集:卷34.北京:中华书局,1979:878.
(责任编辑 魏晓虹)
Three Levels of HAN Yu and LIU Zhong-yuan’s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LUO Shu-hua
(Centre for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Studi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Theorie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is the core of HAN Yu and LIU Zhong-yuan’s ancient literature theories.In this respect,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HAN Yu and LIU Zhong - yuan’s theories of expressing opinions by literature.However,HAN Yu and LIU Zhong - yuan's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include three levels:literature expresses doctrine;the foundation of literature is doctrine;doctrine is attributed to literature.It i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latter two levels that HAN Yu and LIU Zhong - yuan’s theories can maintain a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become literary theories rather than theories on thoughts.Each one of the three levels 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HAN Yu and LIU Zhong - yuan's theori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HAN Yu and LIU Zhong-yuan;ancient literature theory;the relation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doctrine
I207.62
A
1000-5935(2012)05-0001-04
2012-06-10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散文学史”(01JAZJD750.11-4404)
罗书华(1965-),男,江西泰和人,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