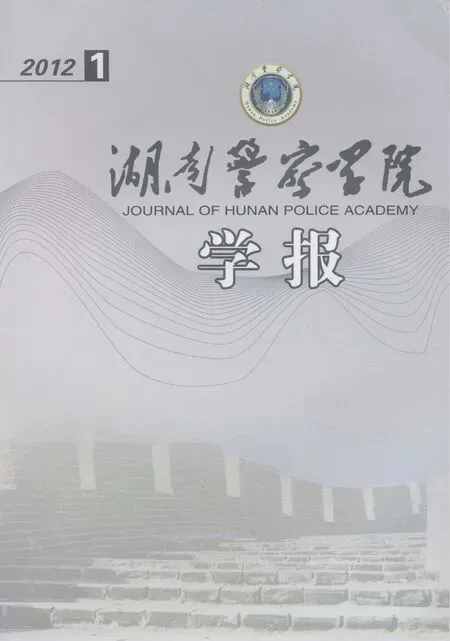携带凶器抢夺行为之研究
石艳芳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河南 郑州 450000)
携带凶器抢夺行为之研究
石艳芳
(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河南 郑州 450000)
自1997年中国刑法中规定“携带凶器抢夺”以来,因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进而发展为一个研究热点。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对“凶器”、“携带”的概念界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法理反思以及对2000年司法解释的理解和反思等。鉴于此,通过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相关理论分析,希望能得出一些有用的理论。
携带;凶器;携带凶器抢夺
一、现行刑法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
刑法第267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刑法规范具有普遍性,它是从各种各样的行为中抽象出来的犯罪行为,对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仅仅抽象其一般的共性,而不可能具体详细描述每种具体的犯罪行为,否则刑法的规定和具体的命令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刑法条文必须以较少的文字表达更多复杂的犯罪,以期刑法简短明了。简明的后果是,刑法不可能解释所有规范性概念,或许由于种种原因而“故意”不作具体解释性规定。因此,刑法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规定不免有些笼统、模糊,产生诸多争议。例如刑法对“凶器”与“携带”的含义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导致此类案件的定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司法人员在认定犯罪行为时显得不知所措,甚至望法条而兴叹。在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之间都存在不同的理解,以至于使此规定不能正确适用。
二、对凶器的界定
常见凶器有匕首、三棱刀等,如何给“凶器”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对此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凶器顾名思义即行凶时所使用的器具;[1](P11)另一种观点认为,凶器是指专门用于作案的器具;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凶器,是指在性质上或者用法上,足以杀伤他人的器具。性质上的凶器,如枪炮、刀剑等有直接杀伤力,通常情况下一般人都能够感受到其威胁性;用法上的凶器,即该器具本身不是为了满足杀伤他人的目的而制造或者存在的,[2](P167)例如木棒、菜刀、钳子、起子等一些金属用品,只有这些东西被利用于杀伤目的时,应认定为凶器。
凶器与犯罪工具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凶器必须是用来杀伤他人的;而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阐释“犯罪工具”,一般是根据其字面意思并结合司法实践和立法本意,“犯罪工具”可以理解为“供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使用的财物或器具”。由此可见,凶器和犯罪工具都属于器具,二者有一部分交集,存在相同的地方,但又不完全相同。凶器侧重于其本身自然属性,具有危险性和杀伤力,而犯罪工具侧重于强调该器具在实施犯罪时使用,可能这些器具仅仅具有毁坏物品的特性而不具有杀伤他人的机能,甚至很多犯罪工具本身也并不具有毁坏性,也没有危险性。譬如小偷实施盗窃时所使用的万能钥匙,虽然可谓是犯罪工具,但它不是杀伤他人的器具,故不属于凶器。从范围上来说,一部分犯罪工具是凶器,但犯罪工具并不等于凶器。
某一器物是否可以在法律上评价为凶器,通常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1.根据一般的社会观念,正常人在面对该器具时,是否会感觉害怕、恐惧,即该器具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是否让人感到害怕;如果某种器具在外观上不会使人产生危险感,例如看到菜刀就像看到吃饭用的筷子一样,就是一个厨房用具而已,难以认被定为凶器。2.该器具本身是否具有杀伤力,杀伤技能较低或者是不具有杀伤力的器具,不能认定为凶器。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如塑料制成的仿真刀剑、步枪、匕首模型等,虽然在外观上看起来与真实的凶器一样,但由于其本身不具有杀伤力或者是其杀伤他人的物理性能较低,不能认定为凶器。3.在司法认定上,该器具用于杀伤目的可能性程度。有些器具不可能杀伤他人,当然就不能认定为凶器,如果机械理解无形之中就加大了打击范围。4.器具被携带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大小,即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是否异常,要注意将凶器与随身携带的其他物品相区别,如水果刀用于日常生活时,客观上并没有以此为行凶武器进行抢夺,不能认定为“凶器”。一般人外出时,不会经常随身携带菜刀,携带该器具抢夺的,可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携带一些器具的原因、动机和目的很多,应着重考虑这些携带凶器的动机和目的,通常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有目的性的携带,有目的性的携带是指行为人携带器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借助器具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完成特定犯罪。此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明确要使用该器具来实施预谋的行凶行为。现实的犯罪行为发生后,行为人所携带的器具无非就两种情况:在犯罪中得以使用或没被使用。2.不确定的目的性携带,不确定的目的性携带是指行为人不是故意为了犯罪而携带器具,可能是基于日常生活或职业的需要带有器具,主观上不是为了犯罪而带,后来他用不用该器具也不一定。3.无目的性的携带,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恶性通常不深,因为行为人携带器具的目的不明确,不一定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器具是否认定为凶器还在于该凶器是否用于犯罪。因为“凶器”本身也是器具,有法律禁止携带的器具,也有法律允许个人携带的器具,有些人在特定条件下为了防身而携带法律允许携带的器具。而“器具只有被行为人用来实施犯罪活动进入法律评价时才有可能成为‘凶器’,日常生活中没有被用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就不能认定为‘凶器’,另外,即使用于犯罪的器具因其自然属性和法律属性成了凶器,未被使用的器具则没有进入法律评价的范围,依然是器具”,[3](P21)不能认定为凶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因为行为人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就将其所带的器具一律认定为凶器。总之,行为人携带某种器具,可说明行为人有意图使用该器具,但实际上未使用的,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影响,显然不应该对行为的性质的认定产生影响。
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也提及有关凶器方面的概念,但基本上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对凶器的含义没有具体详细的解释。例如日本刑法第208条之二规定:“在二人以上共同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为目的而集合时,准备凶器或者知道有此准备而集合的,处二年以下惩役或者30万元以下罚金”。“在前项情况下,准备凶器或者知道有此准备而聚集他人的,处三年以下惩役”。但日本刑法原则上并没有对凶器作具体的规定或进一步解释,可操作性也不强,司法实践中很难适用。德国刑法分则有很多条文规定了携带“武器”,而不是明确为“凶器”,[4](P91)但对“武器”一词作了相对较为细致的规定,其中把武器区分为分射击武器与其他武器,但并没有对武器的含义与范围做出具体规定。瑞士刑法有些条文规定了携带武器,其中分射击武器与其他危险武器,其刑法也没有对武器作任何解释。例如,英国《1977年刑事法》第8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携带犯罪凶器侵入任何房屋而无任何法律根据或充分理由的,构成犯罪;该条第2款规定,“犯罪凶器,是指为了用来伤害某人或使其残废而制造或者使用的任何物品,或为了这种用途而故意携带的任何物品”。不难看出,这一解释性规定并不明确,故英国刑法理论常常花较大篇幅讨论凶器的含义;不难明白,即使刑法对凶器做出解释性规定,也并不意味着凶器的概念自然明确。[5](P91)
三、对携带的界定
“所谓携带,就是指在从日常生活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的场所,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携带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携带与持有二者具有相同之处。持有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行为人与所持有的物之间具有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2](P168)携带与持有都不要求对所携带或持有之物具有所有权;二者都可以通过介入第三者进行携带或持有,都是一种持续行为。“但携带与持有不是等同的概念,携带只是持有的一种表现形式。持有具体表现为占有、携带、藏有或者以其他方法支配某种物品;持有不要求物理上的握有,不要求行为人时刻将物品握在手中、放在身上或装在口袋里,只要认识到它的存在能够对之进行管理或者支配,就是持有。而携带则只要求行为人将物品握在手中、放在身上、装在口袋里或置于随身的容器中”。[5](P31)由此可见,携带与持有的关键区别在:“持有只要求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而不要求行为人可以时刻地予以支配;携带则是一种现实上的支配,行为人随时可以使用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或器具。手中持有凶器、怀中藏有凶器、将凶器置于衣服口袋、将凶器放入随身的手提包等容器中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属于携带凶器的行为”。[5](P32)
“携带行为在本质上是一个控制物品的行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含义。只有当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其所携带的器具才具有法律评价的意义。当然,依据自然属性,行为人携带了杀伤力很强的器具”,[3](P21)如菜刀、利剑等,可以通过行为人携带的器具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同样是抢夺,行为人有时带上刀具,有时仅带一根绳子,带有刀具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情况下要比带一根绳子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为人携带的器具也能够反映出犯罪手段的强弱及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大小,行为人携带一把小刀与带有匕首或手枪所造成的危害结果通常也不同。
如何界定“携带”?目前,刑法学界和司法实践活动中也有分歧。要准确把握或界定“携带凶器抢夺”,还必须考察行为人在“携带”凶器行为的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例如,一个成年男子腰间别着一把菜刀在大街上行走,仅仅凭此我们很难判断该成年男子的行为是否属于“携带”凶器的行为,只有全面考察该男子行为的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主观上是否有行凶的目的,客观上有没有利用腰间的菜刀实施抢夺),才能进行准确判断。
在主观上,行为人必须对自己带有的凶器有明确的认识,如果行为人对带在身上的凶器并不知情,还照搬刑法规定来评价行为人“携带”凶器就失去了意义。例如,甲事前在乙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入乙口袋中一个匕首,而乙恰巧在大街上抢夺钱包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就不能认定乙“携带凶器抢夺”定罪处罚。否则就违反了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从客观方面来看,“携带”是指随身携带,携带要求行为人将器具握在手中,放在身上、装在衣服口袋里等。[6](P33)携带是现实上对器具的支配,行为人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自己所带的器具或物品。如果行为人不能随时使用或者当场使用,就很难理解为对器具的现实上的支配,难以认定为携带。
“携带”行为应该具有如下特点:1.“携带”行为发生的时间应该在实施抢夺行为之前或者是实施抢夺时带有凶器。行为人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之前事先准备或者“携带”以备利用,为了犯罪预先准备好犯罪凶器,然后带着凶器伺机实施抢夺行为。2.携带方式不影响定性。明露式携带凶器能够让被害人直接感知行为人携带凶器所带来的危险性,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威胁更大、更直观。暗藏式携带凶器虽然被害人看不到凶器,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威胁相对小些,胁迫性弱一些,但是,行为人可能因凭借所携带的凶器强化其犯罪心理,因带有凶器而更加有恃无恐;也可能不因带有凶器而强化其犯罪心理。3.携带应随时可以使用或当场能及时使用,即行为人能够随时使用携带的器具。[7](P7-8)
四、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界定
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进行界定,要以以下几点为标准:1.携带凶器实施抢夺必须具备抢夺罪的犯罪构成条件,以构成抢夺罪为基础。携带凶器抢夺的定罪所以不同于普通的抢夺罪,只是因为行为人在实施抢夺的过程中携带了凶器。2.要把握行为人在实施抢夺过程中如何处理凶器(使用凶器)。[8](P52)行为人在抢夺过程中因带有凶器,使使用凶器的可能性变大,从而会导致这种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危害性与普通的抢劫罪的危害性接近。3.通过造成这种危害的可能性程度也可以用来界定是否属于携带凶器抢夺行为。
携带凶器抢夺必须是以行为人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他人不备并不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基本的犯罪构成仍是抢夺罪,如果行为人突破了这种非暴力方式,性质就改变了,构成抢劫罪。
把握行为人如何利用凶器是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界定的重要因素。行为人在抢夺被害人财物时,故意显示其带有凶器,这里的“显示”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凶器的威力对被害人造成心理强制,这种抢夺行为也经常发生在被害人有所提防的情况下。例如,行为人以购买商品为理由,让营业员从柜台里拿出钻石戒指或项链,当营业员拿着商品进行推销或介绍时,行为人故意向其显示所带凶器,在营业员惊恐之时,行为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营业员手中夺走钻石戒指或项链。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趁“火”打劫。这种情况行为人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所带的器械进行威胁,但是其显示凶器的行为本身就是利用器械使被害人因为凶器而受到精神上强制,它与夺取财物的目的行为相结合,使行为人能够抓住机会,强行夺取财物。从这种行为状态中也可以看出,行为人是故意让被害人看见自己所带的器械,实际上利用了其所携带的器械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达到其犯罪目的,实际上属于以胁迫方式进行抢劫,[8](P52)这种行为造成的危害性和抢劫罪的危害性相差无几,应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暗藏式携带凶器抢夺,没有向被害人直接显示其所携带的凶器而公然夺取被害人的财物的行为。对这种情况要区别对待,第一种情况:行为人随身携带器械实施抢夺行为,但并没有向被害人显示其所带器械,即没有利用凶器对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等精神强制。如行为人在实施抢夺行为的过程之中,将凶器藏在身上某些地方引而不露,也不会为被害人所感知,(虽然携带凶器但并没有利用凶器),当然也不会对被害人产生恐惧等精神强制,如果行为人没有因携带凶器而有恃无恐,即使遇到被害人反抗也不使用其所携带的凶器,也不以暴力作为后盾,此时携带凶器跟没有携带凶器实施抢夺行为没什么实质的区别,行为人仅仅是携带了凶器而已,至于为什么携带凶器暂时在所不问。此时,携带凶器抢夺行为就不能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9]抢劫罪与携带凶器抢夺行为在实施各自的行为方法、强力指向,行为所带来的影响以及侵犯的客体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第二种情况:如果行为人随身携带器械实施抢夺行为,虽没有向被害人显示其所带器械即没有利用凶器对被害人产生心理的恐惧等精神强制,即行为人在实施抢夺行为的过程之中,将凶器藏在身上某些地方藏而不露,也不会为被害人所感知,这种行为显然不属于胁迫行为。但是,如果利用凶器对行为人自己产生了影响,行为人会因其带有凶器而更加猖狂,一旦遇到被害人的反抗便会使用其藏而不露的凶器,这便是以暴力为后盾,其人身危险性要比普通的抢夺罪所要求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得多,凶器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产生了影响,实质上还是利用了凶器。藏而不露的情况下,凶器在实施抢夺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凶器的作用的话就不能转化为抢劫行为,不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是,如果凶器在实施抢夺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的话就是携带凶器抢夺,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此外,在界定携带凶器抢夺时也应该注意以下两种例外情况:
1.有佩刀习惯的少数民族的居民携刀抢夺的情况
在新疆、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基于当地民族风俗习惯或生活需要,经常在身上带有刀具、佩剑等器具,如果对他人实施抢夺,就不能简单地以“携带凶器抢夺”为理由依据抢劫罪定罪处罚,法律必须对此做出特殊规定,如果以“携带凶器抢夺”一概而论就会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但是,如果被害人也是本民族同胞的话就应另当别论,本民族被害人明知佩带刀剑是生活习惯或本民族习俗,其可以抗拒行为人因佩带刀剑带来的威胁,[1](P13)不会像非本族被害人那样对刀剑产生心理上的恐惧,因为本民族被害人本身也可能带有刀剑,基于此不能加重因佩带刀剑习惯的少数民族实施抢夺的处罚;另外,携带民族佩刀针对他人(不包括本民族同胞)实施抢夺,或者不在该民族居住点而是去别的地方实施抢夺行为,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将刀剑抽出刀鞘为准,如果抽出刀鞘当场威胁被害人,应该以抢劫罪定罪处罚。[6](P34)针对有佩刀习惯的少数民族实施抢夺,要按照具体情况区别看待,不可一概而论,否则,势必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
2.特殊职业携带凶器抢夺的情形
一些特殊职业人员因职业需要随身携带凶器而实施抢夺行为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以其所携带凶器作为暴力后盾,被害人因为看到行为人佩带刀具而产生心理上的恐惧等强制性心理,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7](P22)此时,应该直接适用《刑法》第263条的规定直接定性为抢劫罪定罪处罚。另外,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以其所携带凶器作为暴力后盾,但并没有显示其所带凶器或者是虽然露在外面(行为人并没有故意显露),对被害人也没有造成心理上的恐惧等精神强制,则应依照刑法第267条款第2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即转化型抢劫罪。再次,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抢夺行为时既无以所带凶器作为暴力后盾的意图,也没有对被害人产生心理上的恐惧等精神强制,不能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而是以抢夺罪定罪处罚。
五、界定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的建议
(一)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怎样准确认定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呢?第一种观点仍然延续了我国重口供轻实物证据的传统,认为如果被告人在供述中承认了其抢夺时携带凶器,则是携带凶器抢夺,否则不能认定。第二种观点则主张根据犯罪现场查获的物证来认定,如果查获了凶器则认定为刑法第267条的抢劫罪,如果没有就只能按照抢夺罪定罪处罚。第三种观点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折中,认为要综合考虑被告人的供述和现场查获的证据认定被告人是否属于携带凶器抢夺。第一种观点显然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与刑事司法的大趋势相悖。第二种观点重现现场物证,有其积极的一面,但难以排除被告人合理携带凶器的可能,因而容易导致客观归罪。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精神,物证和口供都是刑诉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如果查证属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笔者认为:1.如果被告人的供述与现场查获的证据可以相印证,则应该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2.如果被告人对携带凶器的事实不予供认,但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携带了凶器,且被告人对此不能做出合理的说明,则可以认定“携带凶器抢夺”;3.如果被告人对携带凶器的事实不予供认,但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携带了凶器,但被告人可以给出合理的理由则不能认定“携带凶器抢夺”。
(二)司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第267第2款专门以法律拟制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予以规定,但是,该规定看似通俗易懂,实则含混不清,因为该规定对凶器和携带凶器的含义都没有明确界定,司法实务中难以统一适用。笔者建议在此后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再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具体、明确,对携带凶器抢夺行为给出明确界定标准,然后,依据这些标准进行定性;也可以将携带凶器抢夺行为规定为加重抢夺罪的情形,这样可全面贯彻罪刑法定和罪行相适应原则的法律精神。
[1]汪海燕.认定“携带凶器抢夺”要注意的几个问题[J].法学论坛,1999,(2).
[2]鲍雷等.侵犯财产犯罪疑难案例精析[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冯英菊.“凶器”问题初探[J].人民检察,2003,(7).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5]康明已等.“携带凶器抢夺”以抢劫罪论罪探析[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3).
[6]彭泽君.“携带凶器抢夺”认定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3).
[7]赵梅.携带凶器抢夺研究[D].湘潭大学,2006.
[8]莫曲波.携带凶器抢夺定性问题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5,(2).
[9]章国安.论“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及立法完善[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4,(2):16.
Study on the behavior of snatching w ith lethal weapon
SHI Yan-fang
(He Nan Ke Jin LawOffice,Zhengzhou,Henan,450000)
The provision of snatching with lethal weapons of Chinese Criminal Law has been provided since1997.Due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it ca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legal circle and developed into a hotspot.This study is to define the word"lethal weapons"and"carrying",reflect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carrying with lethal weapons",and hoping to draw some useful theor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theory concerning carrying lethal weapons behavior.
carry;lethal weapon;snatching with lethal weapons
D914.1
A
2095-1140(2012)01-0080-05
2011-11-23
石艳芳(1985- ),女,河南许昌人,西南政法大学2008级法律硕士,河南克谨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