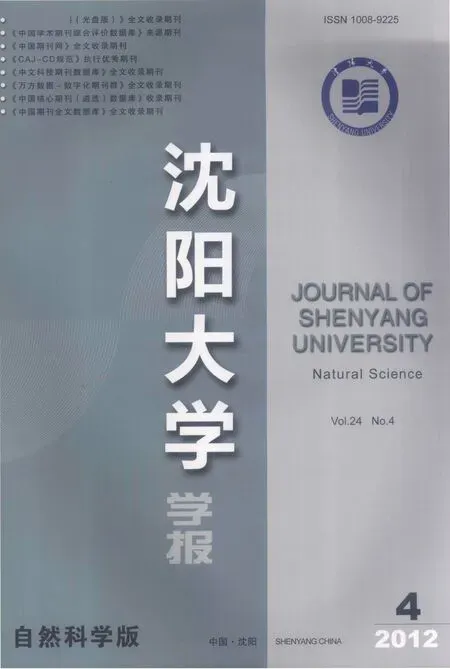合作化文本中的分家行为分析
——以《三里湾》为中心
张 思,田英宣,2
(1.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中心研究室,天津 300192;2.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天津 300204)
合作化文本中的分家行为分析
——以《三里湾》为中心
张 思1,田英宣1,2
(1.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中心研究室,天津 300192;2.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天津 300204)
以当代文学中第一部描述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中心,通过深入解读文本中有关分家的描述,探讨推行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基层政权对民间习俗的巧妙借用,以及政治力量推行下的分家习俗对农村传统大家庭和家庭伦理、家庭秩序的影响。
合作化文本;分家行为;《三里湾》;民间习俗;政治运作
作为合作化的典型文本,《创业史》用农村格言“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1]来概括合作化运动对农村、农民们的影响;而1959年发表的《山乡巨变》则明确表明:“合作化运动是农村的一次深刻的革命,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这些剧烈尖锐的矛盾,必然波及每一个家庭,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底。”[2]深入解读此时期合作化文本就会发现:合作化运动对家庭的冲击和影响体现在父权的衰落、家长制的瓦解上;传统聚族而居的大家庭迅速为一个个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所代替;《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这几部合作化的典型文本,每一部都存在着因互助合作而带来的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传统的分家析产、异爨而居的民间习俗在文本中具有了政治运作的色彩和意味,成为解决父子矛盾、推动家庭中统一合作化运动意见的强有力的手段;日渐普遍的分家习俗、逐渐提前的分家要求迅速导致了中国农村中大家庭的解体。本文以当代文学中第一部描述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为中心,通过深入解读文本中有关分家的描述,探讨合作化运动推行过程中基层政权对民间习俗的巧妙借用,以及政治力量推行下的分家习俗对农村传统大家庭和家庭伦理、家庭秩序的影响。
一、马家分家三部曲
马家是三里湾村有名的封建家长制大家庭:这个家庭由封建家长马多寿、封建婆婆“常有理”掌权;四个儿子:马有余、马有福、马有喜、马有翼;老二为县干部,老三为军人;在家的是长子和最小的儿子;未婚的是马有翼;妯娌间的摩擦时常发生在长媳“惹不起”和三儿媳菊英之间。“闭门锁户”的生活习惯象征着这个家庭的封闭、守旧;在家庭事宜上,马家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权至上、妇女靠边站的封建家庭组织原则;无论是马多寿常年的装糊涂,巧于算计、聚敛家财;还是马多寿老婆“常有理”对媳妇们色厉内荏的管教、指派;马家都遵循着家长说了算,“父母老,长子继”的封建家庭秩序运行着。导致这一大家庭走向解体的是互助合作运动。
《三里湾》文本由三个主体事件构成:秋收、扩社、开渠。秋收涉及到互助合作的分配问题;扩社是进一步扩大村子里成立刚一年的农业合作社,解散农民间的互助组,吸收更多的农民加入合作社;开渠则要占用一些农民的土地,修筑公共的灌溉水渠,是扩大的农业合作社提高生产力的必要建设项目。
和马家这个封建家庭密切相关的事件首先是合作社的开渠工作。按照合作社的工作计划,修筑水渠需要经过马家最为看重的一块肥沃、浇灌便利的好地—— “刀把地”。而依马家的封建、落后、悭吝,马家既不会放弃和几个弱户组成的互助组,更不会主动入社—— 一旦入社,土地由合作社集体管理,“刀把地”便会无偿地被合作社使用,新建筑的水渠从“刀把地”上经过,而马家不会有更多的收益。
文本的矛盾展开集中在涉及集体利益的开渠和争取“刀把地”上,扩社则是作为一个背景和铺垫。分析文本的事件发展可以看到,合作社争取到“刀把地”之后,扩社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而这个关键点的击破在进行了劝说、教育、交换各方面努力均不得成功的情况下最后由三里湾的基层政权借助马家分家这一民间习俗顺利实现了。
马家分家遵循的是一次完成,而不是渐次分家;在文本的叙述构成中由相续的三个主要事件构成,而每一个事件对导致这个封建家庭的分裂,促动马家归顺合作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三儿媳菊英的分家要求:解决家庭矛盾的杀手锏
马家的家庭矛盾一方面由婆媳相互攻摠形成;另一方面是妯娌间的利益纷争。文本由借房打扫卫生、孩子们的游戏吵闹引出菊英和长嫂“惹不起”的矛盾;再由套驴磨面,婆婆“常有理”、嫂子“惹不起”不给菊英中午饭吃使得婆媳、妯娌间的矛盾纠结、升级;由菊英到村调解委员会寻求调解、帮助,使得马家积累多年的家庭矛盾得以解决。而解决的方式“分家”先是由没有名姓的群众“军属”们气愤不过,为菊英谋划出主意;随后经过调解委员会委员、优抚委员会主任、军干属之一的“秦小凤”强有力地坚持、执行得以实现。
而封建家长马多寿最害怕的就是“分家”:因为只要一分家就要分走他的一部分家产和土地,这对悭吝的马多寿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但在村调解委员会的坚持下,马多寿的家还是被“分”了。
马多寿和老婆“常有理”以及长子马有余都想多占有一些财产,并坚决反对入社。因此分家的焦点之一便是想方设法拿住“刀把地”—— 阻挠开渠、扩社。马家请来了“常有理”的娘家老舅主持分家。他们主要考虑了四个问题:第一,按什么标准分地。第二,刀把上的那块地。第三,调解委员会会不会推翻这些分单,主张重新分配。第四,万一丢了刀把上那块地,大年、满喜两个人入了社,互助组也散了,菊英也分出去了,自己也入社是不是比单干合算?
马多寿拿出了十多年前为对抗“减租减息”而制造的假分家的旧分单。马多寿看到在已经捏造好的旧分单中,重点关注的不愿意被合作社拿走的“刀把地”分在老二马有福名下,而不是积极进步的老三、老四名下,他才放了心。至于是入社合适还是单干合适,经过长子、外号“铁算盘”马有余的精心计算,单干还是比入社收获多。所以,马多寿和长子马有余达成的共识是,尽力保住“刀把地”,反对开渠,坚持单干;把老三家分出去,把分家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而为菊英主持公道的调解委员会的意见是:“分单合理,假的也赞成;如果分单不合理,真的也反对”[3]113-114。在支持菊英坚决分家的基础上,调解委员会的意见是希望菊英能争取到“刀把地”。如果菊英能争取到“刀把地”,作为青年团员的她肯定会配合合作社的开渠工作,主动把“刀把地”入社,从而为开渠、扩社铺平道路。因此,调解委员会还特意嘱咐参加马家分家会议的村干部、调解委员会主任范登高要帮忙菊英争取到“刀把地”:
(社主任)永清接着说:“昨天夜里我们支部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最好让菊英把这块地争取到手,免得到开工的时候再和有翼他爹打麻烦。菊英先想一想你自己愿不愿这么做!你只要把这块地争取到手,明年要是入社,社里按产量给你计算土地分红,要不入社,社里给你换好地!”菊英打断他的话说:“能分了家我怎么还肯不入社?”[3]98
在调解委员会布置的这次分家“调解”中,从大方向的制定到具体的交涉,调解委员会都一一进行了详细策划。从中可以看出,调解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已经不再是如何“调解”马家的家庭矛盾,而是转变为借由马家“分家”顺利争取到“刀把地”。
文本借助有错误思想的“自发”干部范登高之口质疑调解委员会的做法:“作为一个党员,我要向支委会提意见:第一、党不应该替人家分家。第二、提出这个问题,马多寿一定会说是共产党为了谋他的一块地才挑唆菊英和他分家。这对党的影响多么坏!”[3]99-100
在文本中,范登高是一个教育对象。文本要表达的意思是:对基层政权调解马家分家这件事虽然存在不同意见,但也仅仅是有错误思想的“发家”干部范登高一人的怀疑。何况范登高还属于“教育”对象。他的质疑不仅引不起大家的共鸣,反而同他的“发家致富”“反对开渠、扩社”一样都是属于应该批评、否定的思想。但范登高的质疑不仅代表了一般村民的看法,而且不无道理:“分家”是家庭问题,是村民自己家的事,党、政府都不应该“干涉”。但三里湾的合作化运动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障碍,三里湾基层政权不得不冒着“谋算老百姓土地”的嫌疑强行推进。文本中事件发展的结果表明,三里湾的基层政权正是借用了马家分家的机会,“合理”地争取到了“刀把地”,为开渠、扩社工作铺平了道路。
因此,当调解委员会看到分给菊英的土地还算不错,就同意了马家按照旧分单分家的决定。并且从这张分单中,调解委员会找到了实现“开渠”“扩社”两件核心任务的契机:马家难以撼动的“刀把地”分在老二马有福名下,而马有福是县干部,是“县委会互助合作办公室主任”,没有不支持村子推行合作化运动的理由。于是,合作社就采取了动员马有福捐地的计策。这样,合作社利用马家这次分家的机会,把原本不可动摇的马家“刀把地”顺利地扩充成为集体的土地。
从文本的构成来看,王金生、秦小凤所代表的三里湾村基层党组织在推行互助合作的政策过程中,巧妙地借用了民间的“分家”习俗:借助“分家”这一民间家庭调解手段顺利地化解了马家的家庭积怨;更重要地是成功地使马家的“刀把地”名正言顺地归公到了合作社的名下,搬走了阻碍开渠工作的绊脚石,为扩社的顺利进展挺进了一步。
这次分家给马家这个封建家庭致命一击,使这个封闭、顽固的封建家庭出现了决裂的突破口。而传统的分家析产,在《三里湾》的情节构成中也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味。
2.马有翼的独立要求:不入社就分家
长期生活在封建、迂腐、守旧的父母亲羽翼的庇护下,马有翼形成了胆小怕事、懦弱游移的性格。马有翼中学没读完就被父亲强迫辍学回家务农。在婚姻大事上,马有翼的“常有理”母亲事先没有争取他的任何意见,就和他的“能不够”姨妈暗自撺掇,把离了婚的表妹小俊“包办”给了他。马有翼在大吵大闹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被母亲“常有理”借口有病“软禁”在了家里。马有翼除了流泪,想不出任何更有效的办法。
恰在此时,和马有翼青梅竹马的范灵芝,嫌弃他政治、思想上不进步,嫌弃他有个封建大家庭的拖累,深思熟虑之后坚决断绝了和他的模糊恋爱关系而选择了村子里的“小能人”王玉生订了婚。马有翼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先是痛哭,继而“勇敢”地逃出了“关押”他的小南屋。马有翼逃到地里,找到正在干活的王玉梅,追问对他有好感的王玉梅是否同意嫁给他。王玉梅给他的答复是:赞成和他一起学文化,但不赞成在他那个封建老妈手里做儿媳妇,如果要结婚,除非马有翼先和家里一刀两断。
马有翼听了王玉梅的话,非常沮丧:
(他)一边走一边想:不愿意受我妈管制,不愿意和惹不起吵架,不愿意从社里退出,除了分家还有什么办法呢?好!回去分家去![3]145
马有翼边走边想如何提出分家的具体办法。在婚姻与封建大家庭面前,马有翼抛弃了传统的“父母命,媒妁言”;回家向父母、兄长宣布:“把分单给了我,我自己过日子去!”[3]146这个封建大家庭培养出来的被父母认为最乖顺、听话的孩子,最终在自主婚姻、入社合作这一时代潮流中背弃了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教养,选择了“分家—单过—入社”。
在《治病竞赛》一节里,范灵芝曾给马有翼出主意说,如果不能带动他的封建大家庭进步,争取他的封建老爹马多寿入社,那就摆脱掉封建家庭的拖累—— “为了不被他拖住自己,也只好和他分家!”[3]40范灵芝给马有翼的建议,王玉梅的婚姻誓言都昭示了这样一种逻辑:不入社便分家!甚至范灵芝自己,因为反感发家致富的父亲范登高不觉悟,痛恨父亲不放弃赶牲口拉脚、做小买卖的私利,不主动投入到合作社这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作为独生女、青年团支委的范灵芝也曾经向自己的父母宣告:如果身为干部的父亲再不觉悟,她也要“飞”:灵芝看到人家这一家子的生活趣味,想到自己的父亲在家里摆个零货摊子,和赶骡的小聚吵个架,钻头觅缝弄个钱,摆个有权力的架子……觉着实在比不得。她恨她自己不生在这个家里[3]107。
追求进步、青春激昂的农村青年们在互助合作的时代大潮中,担负带动家庭、建设新农村的使命;一旦家庭成员不能尽快转变,响应互助合作的要求,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就会发出“不入社,就分家”的誓言。《三里湾》中范灵芝、马有翼、王玉梅的这种青春誓言成为一种叙事范式,在后继的合作化文本中一再被书写:例如《山乡巨变》中盛学文对父亲“亭面糊”入社犹豫不决的苛责、瞧不起;陈大春兄妹对父亲陈先晋的家庭围攻;直至《艳阳天》中韩家父子的爱恨交织:为了一袋私藏的粮食,在“破坏社会主义”的心理压力下,做父亲的韩百安屈膝跪倒在儿子韩道满面前,请求儿子原谅他的一时糊涂;而在富农家庭马斋的家中,虽然经过土改、入社,富农马斋已不再是“富农”,但追求进步,不甘心被集体抛弃的儿子马立本还是在院子中筑起了一道篱笆,表示和“富农”爸爸要一刀两断,划清界限;地主马小辫的儿子马志德从不敢在人前喊自己的父亲一声“爸爸”;背后没人的时候,在自家的院落里,也不敢高声,唯恐被人听了去,说他立场不坚定。
王跃生在考察了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的家庭关系之后,认为:“连续的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家庭中最为重要的父子关系,导致了父权的衰落。”[4]328合作化文本中有关不入社就分家的书写模式正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典型概括。
3.未婚媳妇王玉梅的分家要求:合不来就分家
王玉梅要求马有翼和封建家庭决裂,追求进步,分家后才能结婚的想法被大家知道了之后,王玉梅遭到了一番“责难”:作为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的兄长王金生责问王玉梅:马家已经入社了,她为什么还要坚持马有翼和父母分家之后再结婚的条件?王玉梅的回答是:“入社是一回事,家里又是一回事!我斗不了常有理和惹不起!”[3]163王玉梅认为在常有理和惹不起这对有名的泼妇变好以前,最好是和她们分开过。玉梅的理由是:分开了,各家都在社里劳动,自然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分开,让年轻人到了社里走社会主义道路,回到家里受封建管制,是不合理的。王玉梅更说出了结婚、过日子和互助合作类比的话:“我觉着弟兄们、妯娌们在一块过日子也跟互助组一样,应该是自愿的—— 有人不自愿了就该分开。”[3]164-165
虽然分家、异爨而居的习俗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社会里,分家并不是光彩的事情。在家长制森严、孝悌伦理稳固的时期,分家行为往往发生在父亲去世后的兄弟之间;父亲在世时,一旦儿子向父亲提出分家的要求,父亲多数情况下会加以阻止,不得已时才作出让步[4]227-279。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基本还遵循结婚生子之后方分家的习俗[5]。《三里湾》文本中王玉梅未婚就提出分家的要求,在50年代初期的农村还不能被大家认可和接受。文本的这种叙事意味着:合作社的建立加强了农村中年轻一代的独立生活能力,工分制的劳动-分配关系对于促成年轻一代脱离大家庭,组成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起到了促动作用。
玉梅的分家要求促使马家这个封建家庭彻底走向了分裂。文本最后一节通过老两口花费心机主动寻求和小儿子马有翼住在一起,马有翼向合作社报户口,登记土地、牲畜为结局,昭示了父权趋向衰落,互助合作改造了这个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依附关系这一历史现实。
二、支部书记的“拆”字策略
文本的第二节写支部书记王金生在扩社运动中计划施行“高、大、好、剥、拆”的政策。“拆”就是对村子里顽固不想入社的大家庭的一种分化劝说入社的方式:“四种户中的‘大’户,要因为入社问题闹分家,最好是打打气让他们分,不要让落后的拖住进步的不得进步。”[3]11
文本的第31节在写王玉梅的分家要求时,又呼应王金生的这个“拆字”政策写到:
金生对玉梅的回答很满意。像马家这种家庭,在他们没有入社以前,金生本来是主张“拆”的,可是人家现在报名入社了,他还没有顾上详细考虑这问题,所以当秦小凤一提出来,他觉着是不分对,可是和玉梅辩论了一番之后,又觉着是分开对了[3]165。
主张青年们顺应时代潮流,追求进步,投入到合作化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是文本宣传的一个目的。但鼓励青年们大胆脱离落后家庭的束缚,采取分家的方式在基层政权的执行者看来还有一些顾虑:因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建设毕竟不再是“五四”时期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五四”时期的“民主、人权”倡导青年们大胆背叛自己的封建家庭,获取做人的权利和自由(例如:巴金《家》《春》《秋》中觉慧和觉民的觉悟和抗争);而在合作化运动中,农村封建大家庭的儿女所采取的妥善做法则是分家—— 脱离家庭但并不背叛家庭的温和斗争。
支部书记王金生面对村子里复杂难缠的入社情况,制定了采用“分家”民俗各个击破的策略,但对于自己这个大家庭的分家却是无能为力的:
作为马家的对立面,王家是三里湾文本中塑造的理想家庭:父母慈善、兄弟友爱和睦,全家人从长到幼都积极响应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互助合作的实施。老父亲王宝全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他不仅积极支持儿子们参与互助合作的工作,而且自身还积极搞“工具改造”,为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兄长王金生是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主任;兄弟王玉生是村子里有名的“小能人”,合作社的技术骨干;妹妹王玉梅是青年团员,同样既能干又追求进步。但这个既讲究“孝悌”传统伦理又追求政治进步、充满时代活力的复合大家庭却也不能保持它的稳定、和睦发展,同样因为分家而走向了瓦解。
王家分家主要起因于刁蛮的二儿媳小俊受了“能不够”母亲的挑唆。“能不够”挑唆女儿分家的主要原因是王家的人都忙于集体事业,对自己居家过日子不用心;再是希望女儿尽快在婚后当家作主。在最初分家时,小俊的丈夫王玉生不同意;小俊以不分家就离婚为逼迫闹了一年多,最后还是作为支部书记兼合作社主任的兄长王金生说:如果因为不分家而导致离婚,影响更不好,与其这样还不如同意了小俊的要求好。于是王家就把小俊和王玉生夫妇两个分了出去,但只是分爨,劳动生产还在一起。最后还是因为“能不够”的挑唆,小俊的自私、落后,导致了小俊和王玉生的离婚。
文本最后,通达、进步、开朗的范灵芝和王玉生结合了,但两人的做法是:
“你作的工还记在你家,我作的工还记我家,只是晚上住在一块儿;这办法要行不通的话,后天食堂就开门了,咱们就立上个户口,到食堂吃饭去!”“穿衣服呢?”“靠临河镇的裁缝铺!”[3]180
范灵芝和王玉生的结合并没有使作为时代家庭典范的王家恢复原有的规模和和谐。无论是封建、自闭、落后的马家还是充满温情、人伦孝悌、时代政治激情的王家最终都随着子女的分家解体了。
互助、合作,土地、牲畜、农具折价入社;家长对家产的控制权被剥夺了;子女们却可以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获得生存的条件。文本中生动的分家事件的实质是集体经济对传统自给自足个体农业经济的冲击和摧毁;是对传统家庭结构、家庭伦理的改造;是基层政权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过程中,对民间习俗的巧妙借用。
[1]柳青.创业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扉页.
[2]周立波.山乡巨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114.
[3]赵树理.三里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4]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61-168.
【责任编辑:田懋秀】
Behavior Analysis of Family Division in Cooperative Text——Focus onSanLi Wan
ZHANG Si1,TIAN Yingxuan1,2
(1.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of China,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192,China;2.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Tianjin 300204,China)
The description of family division inSanli Wanis interpreted,which is the first novel that describing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The clever borrow of folk customs by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s discussed,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division,which is implemented by political forces,on the rural traditional extended family,the family ethics,and family order.
cooperative text;family division;Sanli Wan;folk custom;political operation
I 207.425
A
1008-3862(2012)04-0101-05
2012-03-04
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BZS054)。
张 思(1957-),男,重庆人,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