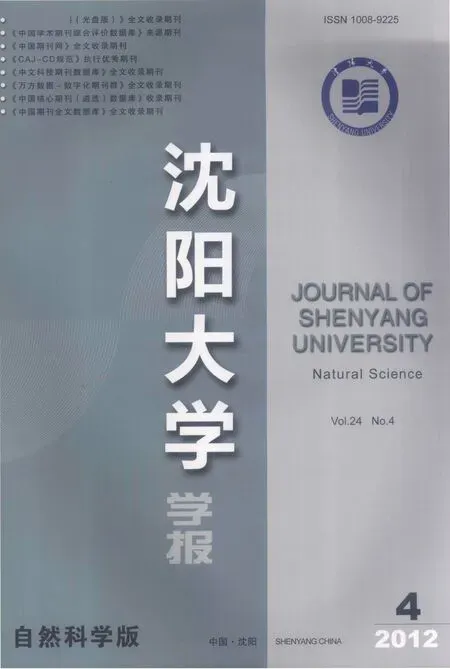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莫 静,刘 宇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莫 静,刘 宇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从社会保险法所确立的权利保障体系的制度理性基础出发,结合社会保险的基本特点,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探究社会保险的法律制度设置中存在的问题,并从中发现,诸如社会保险账户的建立、社会保险费及其征缴比例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等都还存在着许多尚需改良的地方。而以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为标准来度量政府干预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将是社会保险实效的最佳评判机制。
社会保险法;制度经济学;社会再分配;代际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为建构民生保障和民生改善工程、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进夯定了制度保障的基石;它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这种传统的从制度内部探索其优异性的方式,并不能带动制度的外部适用性与协调性,这种缺失制度保障性与经济效益性之间如何衔接的分析方法将会大大影响法律制度的实效和公信力。笔者试图用法经济学的视角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即从社会保险法所确立的权利保障体系出发,来度量该法律制度中政府干预涉及面的广度与深度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的制度理性基础
社会保险的特性决定了社会保险的法律地位和相应的机能。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被誉为社会公平的“调节器”“润滑剂”,同时也是体现政府职能、树立政府良好公众形象的主要政策手段。
1.人权的宪法保障
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45条第1款还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有的学者从作为宪法规范的人权保障原则的五个层面和作为规范存在的四个意义出发[1],对于这一条款进行了详细的解读,这为人权内容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和基本法依据。而社会保障权作为人权的重要构成内容,其基本上是一项经济权利,同时又是一项社会权利,另外还具有人身权利的性质。体现在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上,亦能显现出这三种权利属性: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这五项保险项目不仅体现在相应状况下的基于劳动者身份、工资待遇与工作年限等而享受的一种经济上的补助与赔偿,还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劳动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关注与保护。
2.国家义务
“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历史发展及趋势表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主轴”[2]。根据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孙世彦教授认为,国家承担了承认、尊重、保障和促进以及保护人权四个方面的国际义务[3]。进而言之,在国内的民生保障层面,龚向和教授认为,义务层次理论仍然可以作为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基本体系,但其义务内容则应按照履行难易程度分为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尊重、保护和给付[4]。社会保险作为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不仅体现为国家对劳动者社会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还体现为因劳动付出而本应享有的福利和遭受的伤害的补偿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及积极给付义务。诚然,以国家义务的形式来对公民社会保障权进行规范,是最为彻底、最为稳固的,也更易“使得社会保障权变得可实用、可获取、可接受和可调适”[5]。
3.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
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是指其主观权利权利属性和客观价值秩序属性:前者是基于“个人的主张”,即个人可据自己的意志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国家必须按此要求作为或不作为,并包括防御权功能和受益权功能两个方面;后者是指基本法所确立的“价值秩序”,这一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其主要包括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和保护义务三个方面[6]。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在“客观法”层面为公民的社会保障权提供了价值秩序,而且亦是对主观权利,尤其是“受益权功能”的确认与落实。
二、社会保险法的经济理性分析
通过上述制度基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险法背后深层的制度需求,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对于上层建筑背后的经济基础的探究更能找到问题的根源。笔者将进一步分析该制度设计的本质需求层面的理论与预期的效用。
1.经济理性基础的分析
社会保险,“是基于社会公平原则而对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再分配”[7],因而,其经济理性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人假设。人类行为的双重动机,即一方面追求财富最大化,一方面追求非财富最大化的成立基础来自于“经济人”这一假设。而这使他的活动往往以利己开始,以利他和利社会结束。而这一结果通过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和法律制度框架这一“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更加彰显[8]267。社会保险法运用了“保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特性,将人类行为的利己与利他、利社会统筹兼顾,充分运用了“经济人”这一人类经济理性的假设。
(2)资源的稀缺性。所谓资源稀缺,“是指任何可用资源针对人的需求来说,都是不足的,因此,必须有针对人需求的分配。”[9]205在社会制度的框架之下,“国家为保障民生的给付义务履行,不仅取决于国家在民生保障方面积极与否的态度,而且取决于国家可利用的资源数量。”[10]正是基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社会保险所涵涉的对象仅仅只能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的“保障性”待遇,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3)社会再分配。虽然对于资源分配的最优方式是市场分配,但是在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分配对于弱者而言是无力的,且必然会造成贫富悬殊、市场竞争失败者无所保护的境况。而且,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许多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本人往往会选择忽视对于将来市场失灵时自己境遇的恶化来避免当前所需付出的成本或者资源。因而,在承认资源稀缺和市场失灵的前提下,需要由国家和社会运用各种调节杠杆对于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第二次分配,来消除以第一次市场分配所产生的不良后果。社会保障是国家对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进行积极干预的大有作为的领域[9]205。而社会保险的“强制性”正是对于一般商业保险所体现的市场失灵的一种矫正。
2.具体制度的经济理性分析
(1)关于社会保险账户的建立。从危险转移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险,其实社会保险也是一种危险转嫁机制,个人或者团体可借此以支付一定的社会保险费为代价,将特定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进而,从契约理论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险费是来自于个人财产所有权的让渡和集合:个人一旦将其财产放入基金就丧失了个人所有权。因而社会保险基金的产权问题成了影响“经济人”抉择的关键。
我国的社会保险账户以社会统筹为原则,目前只在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中设立了个人账户制度,且仅将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缴纳的和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缴纳以及用人单位所缴纳小部分才划入个人账户,其他的全部归入社会统筹范围。而且,一般情况下,危险的转移总是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参加保险的人之间,但是社会保险却可能使危险实现代际转移[11]。虽然具有这种特定功能,但目前,我国仅在《社会保险法》第14条和《社会保险法实施细则》第6条第2款中规定了个人账户余额的可继承性。
所以,个人账户设置的覆盖面比较的窄,其账户基金的数额比较的少而且可继承性不够明确。这种所有权的相对“丧失”,产权大部分归属于国家或者暂时性由国家保管的制度,虽然可以降低基金管理方面的风险,但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的参保积极性。且为了弥补该制度设计过渡段中历史空户,“这个资金缺口无论是由国家和企业补足,都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从而影响了国家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12]。
(2)关于社会保险费及其征缴比例。现代的社会保险费制度是从“基特尔”逐步演化而来的[9]191。所谓“基尔特”,即手工业者互助基金会,出现于中世纪的德国,它通过向会员收取会费筹集基金,以帮助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又没有土地作为生活依托的手工业会员,自愿性、互助性是“基特尔”的显著特征。
然而,社会保险费因其牵涉利益的“社会性”特征使其不得不具有“强制性”,其在社会保险基金来源方面的主要体现是资金通常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三者来负担。用人单位与个人负担的比例大致如下:①基本养老保险中,用人单位20%而个人8%;②基本医疗保险中,用人单位8%而个人2%;③失业保险中,用人单位2%而个人1%;④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中,个人无需缴费,由用人单位按照相应的水平在相应比率范围内缴纳。
从上述的比率我们可以看到,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研究称,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2009年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如此重大缴费压力,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的话,这并非是一种基于全体自愿的帕累托最优的选择,而更多的是一种“赢利者可以对损失者进行补偿”的卡尔多-希克斯方式[13]。对于基本养老保险、生育保险而言,这两者都是比较确定且可预期的风险,因而在缴费上需要考量的是不会因缴费率设置的额度而影响到用人单位对选聘劳动者时的年龄、婚姻状况等过度地“变向”挑剔。而在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保险方面,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具体比例时,国家时应考虑两个方面的机制:
其一,是用人单位风险畏惧程度。比如某一用人单位改善相应的劳动条件提供职工福利待遇的成本花费是100万元而发生相应的职工赔偿风险概率是10%,因而,若规定向国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总额若大于10万元,则用人单位的风险畏惧度则显然不高,缴费的合法性与自主性亦不强。
其二,是劳动者的道德危机和逆向选择问题。首先,“如果有可能通过保险而防止贫困,那么任何一个购买保险的人的工作和节俭的积极性就会降低而拥有孩子和从事极具风险的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就会上升。这就是道德危机。”[14]国家将收益的取得以领受人竭力寻找工作、接受培训及其他为条件,提高放弃工作所得福利的成本等机制来化解道德危机。其次,随着财富的积累贫富差距的增大,那些可能贫困化的人就可能大量购买贫困保险,从而使保险费率上升而对不太可能贫困化的人不具吸引力,这又将使保险费率上升,而且很有可能最需要这种保险的人无力支付费率。因而导致了“逆向选择”。所以社会保险应尽量使被保险人的总人数下降到了只包括那些在近期非常有可能贫困化的人,并确保其不可能因为支付不起保险费而退保。
(3)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运营。社会保险基金的产权来自于个人所有权的让渡与集合,且只是为了其当初所设立的目的服务,而不能被个人所操纵和挪用,也不能被第三方操纵和挪用。所以,必须用“专款专用”这一强制性规定来保障基金能够始终用于设立它的目的。
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的另一个显著的强制性规定是“保值增值”。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就是一种“优胜劣汰”,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的最佳资源配置。然而,要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市场操作的零风险,显然不能像其他资金一样正常的在市场上流通,而且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也主要只是依靠银行存款储蓄来进行市场操作,这种资金利用的低效率显然不能充分发挥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社会管理功能[15]。
(4)关于社会保险的效果评判标准。劳动者为了获取维持生存的收入,必须靠出售劳动力来实现。而社会保险的设置减少了这种劳动力的非商品化,为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瑞典的社会政策专家埃斯平安德森认为,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是衡量政府对满足公民社会需要的干预程度的重要标志[16]。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律对经济活动具有着巨大的作用。总的来说,它能规范经济活动使之有序化,从而减少交易活动的成本、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8]275。社会保险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降低了社会保险关系建立的交易成本、提供了劳动者积极工作的激励机制、防止和化解了社会经济发展中对社会弱势保护不足的矛盾语冲突。
因而,笔者亦认为,社会保险作为一种公共政策作用于市场的产物,其最终的效果评判也应以劳动力的非商品化程度为标准:劳动者在因年老、患病、生育、伤残、死亡等原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而中断劳动而使本人和家属失去生活来源时,能够从国家获得基本上能维持原本生活水准需求的物质帮助。
四、结 语
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我国政府在兼顾社会公平和成果共享的政策目标的同时,应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 劳动者的社会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义务,和其因劳动付出而本应享有的福利和遭受的伤害的补偿权利的保护义务以及积极给付义务,利用国家权力和市场经济规律来充分实现对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和民生的改善。
[1]林来梵,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J].法商研究,2005(4):64-68.
[2]龚向和.国家义务是公民权利的根本保障:国家与公民关系新视角[J].法律科学,2010(4):5.
[3]孙世彦.论国际人权法下国家的义务[J].法学评论,2001(2):93-96.
[4]龚向和,邓炜辉.国家保障民生义务的宪政分析[J].河北法学,2009(6):60.
[5]钟会兵.论社会保障权实现中的国家义务[J].学术论坛,2009(10):163.
[6]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J].法学研究,2005(3):24-29.
[7]马新.社会保障的制度约束及其矫正[J].重庆社会科学,2011(9):18.
[8]何勤华,严存生.西方法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9]郭捷.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M].3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10]刘耀辉.国家义务的可诉性[J].法学论坛,2010(9):93.
[11]董保华.社会保障的法学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8.
[12]张楠.考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问题[J].中国商界,2009(7):279.
[13]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35.
[14]王昌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252.
[15]中国保监会武汉保监办课题组.对保险功能的再认识[J].保险研究,2003(1):121.
[16]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01(3):114.
【责任编辑:田懋秀】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China’s Social Insurance Law
MO Jing,LIU Yu
(Law School,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1189,China)
From the institutional rational basis of the rights protec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Social Insurance Law,combined with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insurance,the problems in the setting of the legal system of social insurance are explored by economic rational analysis method.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need to be improved,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accounts,social insurance and its collection ratio,the social insurance fund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etc.It is proposed that,if the non-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s considered as a standard to measure the tension between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the best judg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insurance mechanism.
social insurance law;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ocial redistribution;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ring
G 979
A
1008-3862(2012)04-0059-04
2012-03-15
东南大学2011年SRTP基金项目(T11251004)。
莫 静(1988-),女,湖南益阳人,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