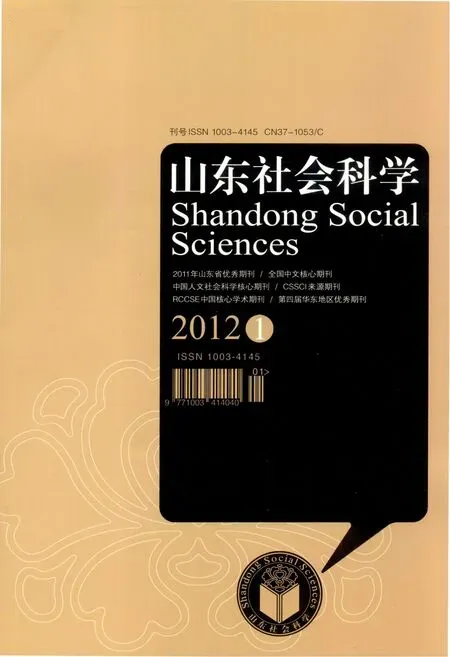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
徐文芝
(山东体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浅论萧红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探究
徐文芝
(山东体育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萧红通过其作品描述了女性人生的自然悲剧和社会悲剧,不仅拷问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而且深入女性精神肌理,挖掘女性自身的精神病弱,即充当了男权社会的同谋。全面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
男权压制;悲剧命运;女性意识
萧红,作为中国20世纪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以《生死场》、《王阿嫂的死》、《呼兰河传》等里程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在面对个人及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觉醒和不断的抗争。其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不幸女性。在同时代的女性作家中,在刻划女性人物的深刻性和真实性上,称得上独树一帜。她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深切地关注和思考所处时代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探究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萧红的童年生活缺乏温暖和爱护。成年之后,把希望寄托于爱情,却又屡遭挫折,几次离异。一生追求爱和温暖,最后落得客死异乡。所以她的作品大多关照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直面女性的困境,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1]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从社会层面观照下层女性的生存形态和生存困境,从自然层面表现女性的生育苦难,从文化层面揭示了性别关系中男性对于女性人格和尊严的践踏,批判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对女性的束缚,这一切都使她的作品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
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扩大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它能把他们的心灵所熔铸的形象原原本本地描摹出来,而且还具有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力量,独特的敏锐。”萧红也正是这样有个性的作家,她不是政治理论或文学思潮的复写者,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书写着女人自身的生命体验,以女性为主体将人生的荒凉感与女性的悲剧融为一体。所以,萧红的小说有一份格外打动人心的美丽和引人深思的力量。
从女性意识的形成来看,萧红的女性意识主要源自不幸的童年经历和成年后的情感悲剧,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构成了萧红女性意识的起点。她曾说过“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2]
萧红小说中对女性生活的描写首先表现为女性求生的艰难和悲惨命运。《王阿嫂的死》中王阿嫂的形象集中反映了阶级压迫下劳动妇女的生存处境。她成年累月地为地主干活,吃的却是“地主用以喂猪的烂土豆”,在丈夫被张地主活活烧死之后,她把丈夫的骨头包在衣襟下,拖着临产的身子继续劳作。当她因为再也带不动自己的肚子而在地头喘口气时,又被张地主踢了致命的一脚而母子双亡。
正如聂绀弩先生在《蛇与塔》中的隐喻:蛇与塔分别代表白娘子和雷峰塔,寓示着无论女性走到哪里,对妇女的压迫和虐待便到哪里,男权社会之塔都如影随形。这一点,萧红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的《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无情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赞扬了东北农民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鲁迅给她的《生死场》作序:“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美国学者刘禾却认为,鲁迅用的是一套民族国家话语,他说:“鲁迅根本未曾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生死场》表现的也许还是女性的身体体验,特别是与农村妇女生活密切相关的两种体验——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正如他所说,萧红将自己的寂寞与痛苦融入了她笔下的女性人物中,冷静叙述中参透的凄凉与悲哀让人不忍。《生死场》中“刑法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幅惨痛的画面,“赤身的女人,她一点都不能爬动,她不能为尘死再挣扎最后一刻……”在这里,生育对于女人来说,失去了为人母亲的喜悦和幸福,而是沉痛人生的又一大悲剧。时代和社会的灾难已经漆黑了女性的天空,男权的狭隘和残忍更加蚕食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处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氛围中,如金枝、月英等女性的生命就这样凋谢了,而那些充当了刽子手的男人们,却显出理所应当的冷漠。在《生死场》中女人们“蚊子似的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劳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角的暴君下面。”(胡风语)。[3]
一群蚁民,按其固有的、无需教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某种潜在信念在“生”“死”之间顽愚地挣扎,这正是萧红这一系列作品所描述的一种愚昧、麻木,可怜可悲的生存状态。像《小城三月》中的翠姨一样,在悄悄地等待死亡的到来,生命对于她们不是太短暂,而是太漫长了。在这片土地上,只有人对自然的盲从,而没有人对自然的抗争,甚至没有因生命短促而及时行乐的欲望,她们不思索生存的意义,一切只是顺从天意,他们生活中无所谓幸福和痛苦,因为一切都还没有萌芽。这样,人还如何称之为人?
现代文学大师鲁迅先生在《离婚》中也对女性的这种悲剧命运进行了反思。她对地位的屈从,对权力的恐惧,对七大人权威的盲目崇拜,使她最终被男性社会所吞没。鲁迅先生说的好,历史不过是两种时代的交替循环,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的妇女们无非是在这两种地位间沉浮,男权社会的伦理纲常已经深深地烙进了她们身心,使她们心甘情愿做奴隶。
萧红继承了鲁迅先生清醒深刻的现实主义,她说:“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而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男权社会的压制固然是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更为不幸的是,女性又将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内化成为她们共有的集体无意识。
在小说《小城三月》中,萧红怀着沉痛的心情塑造了翠姨这个温婉内在的女性,在与“我”的堂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气息和年轻生命的冲动。可是她的寡母却把她许配给了一个矮小的男人。虽然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馈赠,但是世俗的偏见仍左右了她的行为举止。她的沉默与内向更是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结果。她不敢有七情六欲,心甘情愿地受命运摆布,自甘成为男权意识的奴隶。
可以看出,萧红透过文本真诚地呐喊,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自我人格和自由,就必须摈弃精神的死角中残存的奴性,清涤渗透于她们内心的传统桎梏和浓厚的男权意识,这样才会有丰满的羽翼。
“女人啊,你的名字叫脆弱!”但在萧红看来,女人也是可以成为欺压和残害别人的主体,尽管她们在变异的过程中也遭受过别人的残害,深知被人吃的痛苦——女性主体的危机,不在于对男权压制自己的默然,而是在于同性之间的毁灭。女性同类之间的残杀远远超出了“吃人”本身的快感,“乐”在其中,拿起男权社会的屠刀复制更多的悲剧,在同性的痛苦呻吟中玩味着畸形变态的愉悦!
萧红作为三四十年代文坛上最具个性的女作家,以最真挚和焦虑的灵魂书写着女性的悲剧命运,并执着于这悲剧人生的探究。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苦难坎坷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她一方面鞭挞了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冷静的嘲讽了女性甘愿被奴役的特点,并进一步揭示女性深层精神肌理的痼疾。
[1]徐珊、娜拉:《何处是归程》,《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第23页。
[2]聂绀弩:《在西安》,新华日报出版社1946年版。
[3]《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I207.65
A
1003-4145[2012]专辑-0029-02
2012-06-05
徐文芝(1968—),女,山东体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文升)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