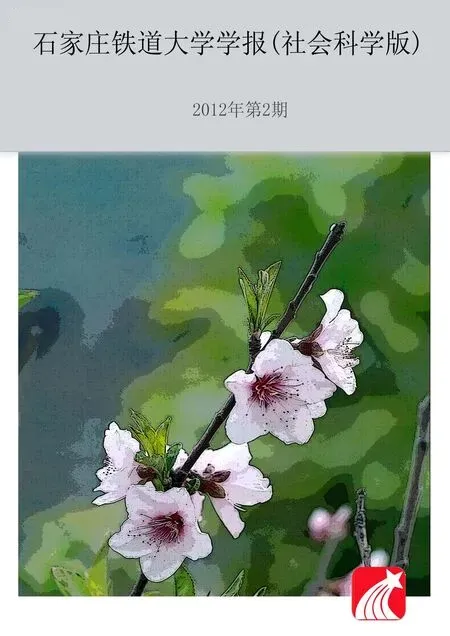曹尔堪与清初三次重要唱和
李 文 胜
(云南临沧师专中文系,云南 临沧 677000)
曹尔堪(1617—1679),字子颍,号顾庵,浙江嘉善人。顺治九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清初著名词人,是清初柳洲词派的重要代表。“曹尔堪多次倡导和参与大唱和活动,对词的创作和繁荣促进,对清初词风演变的推进,起着不应低估的作用。”[1]45他在清初就以词著名,与山东曹贞吉并称“南北二曹”,与“宋琬、施润章、沈荃、王士禄、王士祯、汪琬、程可则齐名称海内八大家”。明末清初,云间词派异军突起,开启了清词中兴的大幕。在云间词派为清词赢得契机的同时,曹尔堪以清逸疏旷的风格在清初词坛独树一帜,为婉丽的词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清词复兴和词风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他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很多文学史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很多词选不选他的作品,对这样一位著名词人失之公允。
一、三次唱和的起因和经过
清初三次重要唱和指“江村唱和”、“红桥唱和”和“秋水轩唱和”。
(一)江村唱和
江村唱和发生在康熙四年(1665),地点在杭州,此次唱和又称“湖上唱和词”,参与者有曹尔堪、王士禄、宋琬,后来各地很多词人纷纷应和,此次唱和影响很大,有“同门纸贵”之誉。他们借题发挥,一吐为快。唱和的原因是他们三人都经历了沉重的打击,人生遭际坎坷,死里逃生,相同的遭遇使得他们相遇于西湖,无限感慨,借词抒发胸中郁闷情怀,正值天崩地裂的明清易代,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与身世际遇交织在一起,互相唱和以泄愤。“顺治十八年(1661),江南苏、松、常、镇四府发生了奏销案,”[2]曹尔堪受奏销案牵连,差点被谪戍关外,经亲朋好友努力相救才幸免于难,这一经历给曹尔堪以沉重的打击,影响并改变着他的词风。宋琬、王士禄也因事刚刚出狱,相同的遭遇触动了他们内心痛苦的心弦,一经拨动便强烈地共鸣起来。正如严迪昌所说:“江村唱和是当时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迁谪之客感受的一次大抒发,有着时代的印记,绝非出于闲情逸致[1]53。此次唱和对清词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词人徐士俊在《三子唱和词序》中说:“盖三先生胸中各抱怀思,互相感叹,不托诸诗,而一一寄之于词,岂非以诗之谨严,反多豪放,词之妍秀。足耐幽寻者乎?”指明了唱和的起因,此次唱和对清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次唱和中三人各填《满江红》词八首,曹尔堪首唱《满江红·江村》,王士禄、宋琬唱和次韵,集成了《三子唱和词》。三人在相似的坎坷境遇后互相酬唱,各赋“状”字韵《满江红》八首,风格却各不相同。王士禄之作的旷达乐观,闲适恬淡,不露怨怒,是由其性格、自身经历及当时社会现实三方面原因所造就。江村唱和作为词坛一时之盛事,后引来南北词人数十位争相和之,影响深远,必须承认的事实是“江村唱和”确实是由曹尔堪发起,他是这次唱和的重要组织者,表达自己在明清易代之际的遭遇,他曾被逮下狱,及国破代易、仕途宦海艰险的感慨。词风深沉悲慨。这三次倡和使“词场一时之盛”,词创作在清初快速繁荣起来,引发了清词的中兴。
《满江红·同荔裳观察、西樵考功湖楼小坐,因忆阮亭祠部》:
漂泊东南,空回首,凤池春涨。家已破,逢人羞语,菊松无恙。余齿偕归江海畔,浮生培土,幸脱刀砧上。君还有、请室断葱来,高堂饷。 天怒解,精魂漾。且笑傲,且赓唱。为周郎而醉,不须倾酿。从此休焉蜗作舍,吾其哀矣为杖。见卯君备说老夫穷,无佳状。(予与荔裳、西樵皆被奇祸得免)
这首词回忆了自己劫后余生的幸运,描写了家破漂泊的痛苦心情,传达出遭祸之后的愤懑忧伤,看破尘世,决定隐居,借山水寄托心志,寄情山水颐养余生。直抒胸臆,反映了自己不幸遭遇,凄凉心态,是江村唱和词整体风貌。
(二)红桥唱和
时间是康熙七年(1668),地点是扬州,又称“广陵唱和”,曹尔堪是此次唱和的重要参与者,王士祯于顺治十七年三月起任扬州通判,在扬州为官五年,以他为核心发起了“红桥唱和”,最早起因是曹尔堪、宋琬、王士禄再次在扬州相聚,与北来的王士祯会合,共同发起了此次唱和,参与者有17人,分别是:曹尔堪、宋琬、王士禄、陈世祥、邓汉仪、范国禄、沈泌、季公琦、谈允谦、程邃、孙枝蔚、冒襄、李以笃、陈维崧、孙金砺、宗元鼎、汪楫等。各填《念奴娇》十二首,结为《广陵唱和词》一卷,写词204首,附于康熙刊本《国朝名家诗余》之后,每位词人词作后面,都有名家评语,是了解当时词坛面貌的重要史料。此次唱和是在“江村唱和”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从根本上讲两次唱和均源于曹尔堪的组织参与,他是两次唱和的诱因,其贡献极大。
《念奴娇﹒舟中携酒同西樵送荔裳入都》:
临江洒酒,叹萍踪聚散。惊鸥骇鹭,湖上牙墙客舆处,正是樱桃初熟。恰又成三,扬州重见,醉看今宵菊。短歌酬酢,依然身在迈轴。 匆遽送别宦河,雁行先起,万种离情簇。弹铗且无鱼可饱,安向渠渠夏屋。小雨昏鸦,发船鼓,赛唱何年续。明朝相忆,板桥茆店人独。
这是曹尔堪、宋琬、王士禄三人再次相聚扬州时曹尔堪写的一首词,在经历了相同不幸遭遇之后,劫后余生的感慨,三年后再次相聚,他们感慨万千,无限伤感,语语动人,借景抒情,标志着曹词词风的转变。
(三)秋水轩唱和
时间是康熙十年(1671),地点在北京孙承泽别墅——秋水轩,曹尔堪是此次唱和的主角和开题首唱者。曹尔堪在《纪略》中讲明了此次唱和的原因:“周子雪客至京师,侨居于孙少宰之秋水轩。轩在正阳门之西,背城临河,葭秀其荫。当夏雨暴涨,水痕啮岸,卷帘凭几而观之,不帝秋水一壑,心骨具清。此亦都市中之濠濮也。雨后晚凉,停鞭小坐,见壁间酬唱之诗,云蒸霞蔚,偶赋《贺新凉》一阙,厕名其旁。大宗伯公携尊饯客,见而称之,即席和韵。既而露垂泉涌,叠奏新篇,可谓濯绮笔于锦江,吐秀肠于沙籀者矣,蘖子,方虎,同授餐于宗伯,亦示钵而庚焉,均工组练,并擅赋心,秋来雁字分行,重以河梁赠之,忝附阳春,一以志愧,亦以志幸。仍以秋水轩系之,存所自也。”
1671年,曹尔堪为了结案情,到京城孙承泽秋水轩,从此告别官场,准备回家乡居,选择了“剪”字韵酬唱抒怀,寄托情感,这是曹尔堪词创作的最后辉煌活动。秋水轩唱和韵皆以“卷、遣、泫、茧、浅、展、显、扁、犬、免、典、剪”十二字为限,大多险僻。他是这次唱和的首唱者,有26人参加唱和,存词176首,26位唱和词人来自大江南北,涉及地域辽阔,有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安徽等。曹尔堪7首,梁清标2首、龚鼎孳22首、纪映钟17首、徐倬22首、王豸耒12首、陈维岳12首、沈光裕2首、宋琬1首、 王士禄6首、龚士稹8首、陈祚明3首、张每句3首、曹贞吉4首、吴之振1首、 汪懋麟2首、杜首昌4首、周在浚15首、王蓍4首、宗元鼎4首、蒋文焕6首、冯肇杞5首、吴宗信 1首、黄虞稷6首、张芳2首。主题多元化,以抒发内心惆怅悲凉为主,此次唱和不在同一时间,也不在同一地点,跨地域唱和,整体上形成了“心骨具清”的风貌,秋水轩唱和在清初词风嬗变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规模较前两次大得多,在清词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曹尔堪词风在此次唱和中变得更为雄健,这对词风在大江南北的整体传播和转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秋水轩唱和”全以“剪”韵写成《贺新郎》一百余首。曹尔堪自己写了7首,而参与倡和的范围更遍及全国,词人词作无数,表达自己在明清易代、江山换主严峻现实下的遭遇,仕途艰险、屡遭宦海风波的悲叹,词风深沉悲慨。彻底转变了自己前期词风,题材由写田园词转变为写政治现实,仕途坎坷,词风由前期的清雅俊逸转变为清雄劲健,经过“秋水轩唱和”,曹尔堪自己的词风彻底完成转变,改变了自己前期模仿学习明末云间词派的“香奁体”,彻底转向辛弃疾的豪放词风,“稼轩风”在秋水轩唱和后迅速盛行起来,改变了此前云间派香软词风,举一例:
金缕曲 康熙帝(八步秋水轩韵):
大帐秋风卷。甫登基、英明独断,三藩须遣。童子数人制骄悍,坐令西南血泫。平台海、易如抽茧。一战雅萨震异域,又划疆勘界恨波浅。登狼居,八旗展。
兼容气度时时显。启洋吏、重修历法,细量天扁。博学鸿科剃心发,从此木兰围犬。文字狱、微词难免。手不释书知大义,有字音韵谱后人典。吐蕃乱,教儿剪。
这首词用词反映当时的时事政治,词风刚健豪放,气势磅礴,词中提到清初的“文字狱”、“雅克萨之战”、“吐蕃之乱”,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怒且怨的悲壮之音代替了前期的云间香软词风,可见“秋水轩唱和”对清初词风的扭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三次唱和的影响及意义
(一)三次唱和对曹尔堪词风及清初词风的影响
三次唱和对曹尔堪词风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三次唱和的主要倡导者和参与者,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他是“江村唱和”、“秋水轩唱和”的重要发起人,“江村唱和”直接诱发了“红桥唱和”,曹尔堪在三次唱和中完成了自身词风的转变,以唱和为契机带动了清初词风的转变,为云间派笼罩下的词坛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云间派和浙西派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三次唱和中,曹尔堪词风一次雄健于一次,对清初“稼轩风”的盛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曹尔堪早期的词风以清雅为主,以花间为宗,风格轻巧雅逸。词多以小令为主,清初邹祗谟《远志斋词衷》云:“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列徒作壮语有别。近惟顾庵学士情景相生,纵笔便合,酷似渭南老人。言远、方伯,洮洮清迥,与葛理间震文喻亮。更如岸初、文夏、耕坞、昆仑诸公,俱以闲淡秀脱为宗,不作浓情致语。”
早期词《如梦令﹒荻溪农家》:
“朝来晴,晚来晴。罩屋桑阴分外清,短檐鳩妇女声。云须耕,雨须耕,新织蓑衣掩骭轻,竹枝歌太平。”
该首小令描写了农家生活,乡土气息厚重,写景生动活泼,语言朴实生动,具有文人的意趣,淡中有味。经过奏销案之后,人生坎坷失意之后,曹尔堪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和迁客骚人失意落魄情怀、易代之思寄托于唱和中,通过寄愤于“三次唱和”中,使曹尔堪词风发生了重大转变,词风由清雅渐趋清雄,人生巨变,使其词风前后风格迥异。曹尔在为尤侗堪写的《百末词序》中对自己后期词风转变原因有过解释:“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追随三十年以来,世事沧桑,功名荣落,不可胜记。独笔墨之缘,少年积习,老而不辍……翻读平日所作小词,疑是古人,疑是前身,不复记忆。”[3]遭际坎坷,世事沧桑巨变,宦海沉浮,险些被谪戍关外荒寒之地,这些都深深刺激了他的心灵,直接发起了“江村唱和”,间接诱发了“红桥唱和”,带动了清初词风转变。曹尔堪在唱和中表现出的清雄之气,改变了以往婉丽词风,正如自己所说,连自己都认不出前期的作品了,疑是古人之作。他在告诉人们,人生经历不同是造成词风差异的重要原因。后期三次唱和中没有小令作品,中长调明显增多,唱和中将自己凄凉心境、贬官、谪戍、迁客心态寄托在词中,形成雄健刚劲的词风,例如:
《贺新凉﹒南归留别》:
鱼直蘧蓬偏卷。但传闻、锋车绣斧,重臣分遣。杼轴空时民力尽,寡妇秋原泪泫。何处贡、八蚕成茧。薄薄酒,香聊送日,福难消,莫怪杯中浅。山远近,翠屏展。 诸公台阁文章显。自归来、悬壶村巷,牛医非扁。检点行囊存犊鼻,游倦相如字犬。谅渴病、今生可免。白木柄边书簏敝。授生徒,饭罢翻经典。畦畔韭、雨中剪。
上阙关心民生疾苦,对人民苦难给予同情。下阙表明要与官场诀别,告官归田,词风悲凉雄健,自然率真。这是曹尔堪在“秋水轩唱和”中的作品,押的是“剪”字韵,“卷”、“遣”、“泫”、“茧”“浅”“展”、“扁”、“犬”、“典”,更好地表达了词人苍凉愤懑的情绪,颇具稼轩风。
通过“三次唱和”使得曹尔堪词抒情色彩进一步加强,题材更加广泛多样,将人生坎坷遭际直接寄情于唱和中,完成了自身词风的转变,并对整个清初稼轩词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清词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如严迪昌所说:“秋水轩唱和,真正把‘稼轩风’从京师吹向南北词坛。”[1]125由曹尔堪组织倡导的“三次唱和”在清初产生了重要影响,参与人数之多,影响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词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在“江村唱和”中有11人用曹尔堪韵,“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反复使用达到百次。陈维崧当时评价“江村唱和”时说:“《西湖唱和词》,脍炙海内。”[4]红桥唱和中,曹尔堪十一次自用韵,应和者17人,通过三次唱和引发了清词的革新,为清初词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纳兰性德、陈维崧、尤侗、王士祯、王士录、宋琬、陈维岳、宋婉、曹贞吉等都曾经参与过由曹尔堪组织和参与的“清初三次重要唱和”,这些词人都曾经与曹尔堪交游,朱彝尊曾言:“今之工于词者,大都昔曾与曹学士游。”可以说没有这三次唱和,很难有清初词坛的复兴与辉煌。“三次唱和”对扭转清初香软词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宋琬为例,宋琬前期词多小令,严昌迪老先生说:“宋婉词前期词以绵丽见长,后期则多凄怨声”。[1]52宋琬的前期词《破阵子 关山道中》:
投地千盘深黑,插天一线青冥。行旅远从鱼贯入,樵牧深穿虎穴行,高高秋月明。半紫半红山树,如歌如哭泉声。六月阴崖残雪在,千骑宵征画角清,丹青似李成。
专注于写景,风格淡雅,属于婉约风格。
后期词《满江红 燕台怀古》:
易水东流,与西去、荆卿长别。祖帐处、三千宾客,衣冠如雪。督亢图中雷电作,咸阳殿上襟裾绝。恨夫人、匕首竟何为,同顽铁。渐离筑,笙歌咽。博浪铁,车轮折。纵奇功未就,祖龙褫魄。一死翻令燕国蹙,九原悔与田光诀。叹千年、寒水尚萧萧,虹霓灭。
词风豪放悲凉,刚健有力,有“稼轩风骨”,明显不同于前期,多喜运用典故。从这首词中能感受到词人那种怨且怒的激昂心情,人生的坎坷遭遇,康熙二年宋琬做过监狱,出狱后与曹尔堪相遇,曹尔堪差点被贬谪到塞外,境遇相同,引起深深共鸣。“江村唱和”成了宋琬词风转变的契机,宋琬还参加了“红桥唱和”,经过三次唱和,宋婉词走上了慷慨悲壮的豪放道路,这是清初三次唱和扭转清初词风的一个例子。
(二)对浙西、阳羡派的影响
三次唱和对浙西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朱彝尊在《振雅堂词序》中说:“崇祯之际,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顾雄视其间。守其学派,无异于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4]对阳羡派也产生了影响,陈维崧是红桥唱和的重要参与者,词风不能不受到影响,各方面与唱和者保持一致,是一次交流的机会。曹尔堪倡导的“三次重要唱和”之后数十年,“浙西派”、“阳羡派”诞生,阳羡派盟主陈维崧参加过“江村唱和”和“红桥唱和”,在江村唱和中他追步宋琬词,写下了《满江红·岁暮渡江》,标志着陈维崧词开始向豪放派转变,“红桥唱和”中进一步显示出陈维崧词慷慨劲健的豪放词风。曹尔堪提倡的“清雅”与浙西派提倡的“醇雅”相通,曹尔堪领导的柳洲词派最终融入到浙西词派中去了,这说明两派词风有相通之处。
三、结语
总之,曹尔堪组织领导的“三次唱和”对自身词风转变以及清初词风转变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曹尔堪成为清词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词人。清康熙十年的“秋水轩唱和”是一场社集性质的群体酬唱活动,当时确实由词人曹尔堪首唱开题,响应者众多,词人遍及大江南北,写词三百多首,龚鼎孳一人独填23首词,自此后清初词风转向豪放一派,改变了云间词风,对于扭转清初词风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次唱和影响之深、之广,不言而喻。对明末清初词风演变起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影响。曹尔堪功不可没,应该给予合理的评价。曹尔堪与清初三次唱和在文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对清初词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