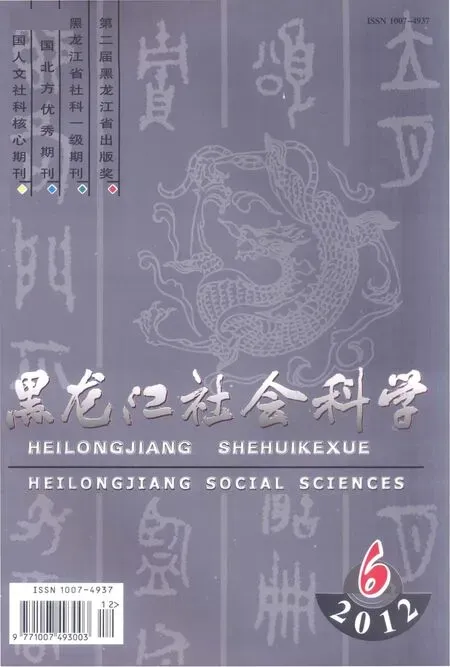从政党政治角度看1972年德中建交事件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1972年,联邦德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一事件对于德中两国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外交与内政总是密切联系的。按照联邦德国批判社会史学派代表汉斯—乌尔里希·韦勒的观点,内政甚至处于优先地位[1]。韦勒虽然主要是针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外交决策提出“内政优先论”的,但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意义,为考察外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的“政党政治角度”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选定的。笔者认为,政党政治,作为众多的国内因素之一,对1972年的德中建交有重要影响。在勃兰特政府时期,执政党和反对党都赞成同中国建交,认为建交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可是作为政府代表的执政党,主要出于对苏联的顾虑,一再推迟与中国建交的时间,而在野的反对党则积极要求和推动同中国建交,这不仅加速了建交的进程,而且起到了在国际上试探和为政府“分担风险”的作用。
一、联邦德国的政党政治
所谓政党政治,它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各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围绕竞选、组阁、执政方针等重大问题而进行的斗争”[2],其运行方式及其特点因政党体制而异。联邦德国的政党体制主要表现为两党为主的三党制(或称“两个半党制”)。具体来说,就是在认同联邦德国政治体制的大前提下,国内两个最大的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它们之间相互竞争,轮流执政,而作为小党的自民党则与联盟党或社民党联合执政。所以联邦德国政党体制的特点在于,各政党在联合组阁的情况下实行政权交替,在意识形态上“妥协、靠近、寻求共识”[3]。
联邦德国的这种政党体制中存在多个政党,故比起两党制,它拥有更多的沟通途径和信息渠道,更具民主性;而且政党的宪法化和法制化对政党的数目进行了限制,可以避免多个政党纷争造成危机的局面。在这种政党体制下,联邦德国的政党政治呈现为政党之间的良性竞争,因为各个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不存在对立,反对党虽然主要是以重新执政为目的,在内政外交问题上监督和反对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但二者的分歧只局限在联邦德国政体的内部,即二者是在维护联邦德国政体的前提下展开争论和进行角逐的。反对党的存在虽然会大大增加执政党的执政难度,甚至可能造成执政党执政效率的下降,但它同时也意味着政党间权力制约体制的形成。反对党作为议会政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和执政党一起承担政治风险的局面。为了避免被执政党的政治“失误”所牵连,反而在其中脱颖而出,彰显自己的高明之处,反对党往往会对执政党实行“高效监督”,不断提出它认为可以接受的不同于政府的另一种政策,从而牵制或者协助执政党,在国家的政治生活起到平衡作用。正是这套体制,使得联邦德国中出现的任何腐败甚至动乱现象都只是导致执政党的下台,而不足以引起整个政治体制的崩溃,这其实正是联邦德国政党政治的基本功用所在。
在对外关系方面,执政党和反对党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有的时候,两者的意见和倾向也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导致它们在对外关系中经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执政党代表政府,其行为直接体现国家的意图,而任何不小心的失误都有可能给国家在国际上带来外交纠纷,所以执政党在制定对外政策的时候一般都非常谨慎。当遇到外部压力的时候,它甚至会把某些早已准备采取的政策或者行动暂时放缓。与之相反,在野党或者说反对党则是非政府的,一方面它具有接管政府的权力意识,另一方面它没有执政党的诸多顾虑,所以当面对它认为正确而执政党却不以为然或者心有畏忌而踌躇于行动的时候,反对党可以比较自由地发表主张和见解,批评执政党的行为,或者为执政党的政策推行营造舆论基础,以敦促政府采取行动。而一旦政府的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时,反对党又会被政府推到前台,替政府承担一定程度的政治责任,减少或避免外交风险。这一点在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德中建交计划的出台
1949年,联邦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两国长期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虽然联邦德国的历届政府一直奉行比较“克制的”对华政策,但在联邦德国内部却从不缺乏要求开展积极对华政策的声音。不过由于考虑到中美矛盾,以及担心在大陆和台湾中承认一方会对联邦德国在德国的地位产生不利影响,联邦德国在同中国建交的问题上一直举足不前。
1969年10月,由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邦政府成立了,战后执政了20年的联盟党第一次成为了议会反对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虽然在打破外交僵局和扩大外交范围的目标上具有一致性[4]124,但在具体的策略、步骤和重点等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执政党希望通过和苏东国家缓和,即“新东方政策”来达到这个目标;而反对党虽然赞同与苏东国家缓和关系,也赞同把民主德国当成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但是它主张以美、苏、中“大三角”和“多中心”世界为基础,在加强德美关系,维护大西洋联盟,优先推进西欧一体化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压苏联作出更大的让步[5],所以它不赞同政府的“新东方政策”。
具体到对华政策,执政党虽然不反对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中苏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其“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所以执政党的对华态度和行为一直表现得十分消极。勃兰特总理在其1969年10月28日的政府声明中表示,愿意同一切有同样愿望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虽然这些国家中不排除中国,但是勃兰特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之后在其他的声明和讲话中,勃兰特也都有意避开提及联邦德国同中国的关系。这种消极的态度,引起了反对党的批评。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可以通过中国达到打破联邦德国外交僵局和扩大外交范围的目标。他们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顺从地按苏联的意图行事,忽视了中国,并指出“新东方政策”应该包括中国。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执政党的赞同。勃兰特虽然重视中国,愿意和中国改善关系,但他暂时仍把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关系一事置于首位。
随着1971年7月中美关系缓和的公开化,要求同中国发展外交关系的声音得到增强。反对党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打“中国牌”的现实意义,认为“言语和气”但事实上不退让的苏联是欧洲各国的主要威胁[4]124。反对党领导人开始大胆地公开表示同中国建交的意愿。基民盟主席赖纳·巴泽尔(Rainer Barzel)在1971年7月19日联邦议院的会议中提出,联邦德国应该和中国关系正常化[6]。
但在此时,勃兰特政府仍然担心苏联的态度,坚持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态度,反对在双边贸易的基础上同中国进行官方接触[7]。然而,面对中美关系已经缓和的现实,也为了平息反对党的大肆攻击,本身并无反华倾向的勃兰特也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松动。为了试探苏联,在1971年9月同勃列日涅夫会晤时,勃兰特主动提出了中国问题,说明了联邦政府以及国内反对派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意见,并保证“如果在将来和中国建交的问题被提出,联邦政府会及时告知苏联”[8]314。虽然勃列日涅夫没有对德中建交表现出强硬的反对,但他依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成为了常任理事国之一。对于联合国的决定,联邦德国立即表示了积极支持,它期望中国也可以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的愿望。这一事件虽然大大提升了联邦德国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但勃兰特只表示愿意在恰当的时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一再声称,在采取具体行动之前,一定会告知美国、苏联及日本[8]452。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缓和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态度。对于苏联的担心,依然是联邦德国推行积极的对华政策的主要障碍。
三、德中建交的最终实现
勃兰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消极态度遭到了当时身处在野地位的联盟党的坚决反对。其实,联盟党并非在成为反对党后,才要求实行积极的对华政策的。在艾哈德政府时期,处于执政地位的联盟党内部就有人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中美关系缓和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联盟党要求与中国建交的呼声更加高涨了起来。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施特劳斯和施罗德了。
施特劳斯自1961年以来出任基社盟主席,曾主张承认台湾。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恶化,施特劳斯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施特劳斯放弃了原先的主张,转而积极支持发展对华关系,在1971年还曾两次提出访华意愿,最早一次甚至提出可以自费访华。与此同时,施特劳斯毫不隐晦地在议会、媒体等多种场合强调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利用中苏冲突可以为联邦德国带来政治利益,德中两国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在1972年2月讨论批准“东方条约”的会议上,施特劳斯积极地参与了反对党和执政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争论,再次强调了“在中国的帮助下德国可以获利更多”[9]的观点。施特劳斯的这种把中国放在更重要位置的战略眼光在德中建交后依然未变。
施罗德对德中建交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施罗德于1961—1966年间任外交部长,1967—1973年间担任基民盟副主席和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施罗德就主张积极的对华政策,认为加强同中国的接触有助于德国的重新统一。所以自勃兰特政府成立以来,施罗德就反对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冷淡态度。他不仅在联邦议院的会议中支持加强对华政策的意见,而且还在1971年两次向记者表示了愿意到中国来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的要求[9]。1972年7月,施罗德以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问中国,成为了联邦德国第一位访华的政治家。在访问期间,施罗德同中国方面签署了一个书面声明,即双方一致认为,德中两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行的,不存在任何困难。回国后,施罗德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时机已经成熟,联邦德国应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0]984。
虽然联邦政府和施罗德本人都强调此次访华的“超党派性”,但与反对党人的高度赞扬相比,政府对待施罗德中国之行的反应则是相当消极的。这一方面源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政治利益之争;另一方面是因为施罗德访华事件遭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强烈批评,联邦政府认为“给予施罗德特殊的保护帮助以抵抗来自东欧的攻击是不符合联邦德国的利益的,在完全说明对华政策的下一步之前,应该继续对施罗德访华采取克制的态度”[10]961。所以谢尔表示,施罗德访华未对政府产生“任何新的观点”,“谈判的请求必须由北京发起”[11]18。社民党的发言人也作了一些友好而基本无意义的评论。但是几天之后,政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国务秘书康拉德·阿勒斯(Konrad Ahlers)宣布,如果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选举之前完成,那么将是可能的和令人希望的。政府在这一系列问题面前不再犹豫,将努力尽快开始建交进程[11]19。
勃兰特政府态度的最终转变,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反对党的压力,同时也是顺应民意的必要选择。反对党对执政党在对华政策上消极态度的大肆攻击,不仅使执政党看到了国内民众的倾向和意愿,认识到了改善德中关系的重要性,而且为执政党松动对华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创造了政治环境,使联邦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了被迫同中国进行接触的形象。本来由反对党帮助执政党在国际上开展困难的接触,打开外交的僵局,不是不同寻常的事,但施罗德带回来的书面声明大大地提升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政治价值,迫使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和检测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意义[11]15,而反对党也在此方面进行推波助澜。施罗德回国后不久,巴泽尔就对他表示感谢:“作为反对党只有很少的可能性,在外交上直接获得鲜明的特点。您伟大地利用了这个机会。”[12]162一个基社盟的竞选广告词也展示了施罗德中国之行的画面,施罗德在画面上自信地说:“如果没有我的访华,现在就不会有当今外长的访华。”[12]165时值1972年大选在即,执政党担心对华政策问题成为选举议题,为了不把发展对华关系的政治资本让给反对党,排除对华政策问题进入选举议题的可能性,执政党加快了与中国建交的进程。
至此联邦德国执政党同反对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达成了一致,于是德中两国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开始了实质性会谈。由于两国间无根本利害冲突,而且联邦德国也从未承认过台湾,所以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1972年10月11日,谢尔外长和姬鹏飞外长在北京正式签署了联合公报,由此拉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四、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政党政治在德中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反对党对建交事件的不断倡议和大力推动。反对党的政治前途在于重新获得执政地位,这一点对于在勃兰特政府时期首次沦为反对党的联盟党人士来说尤为迫切和明显。所以尽管党内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为了重新夺回政权,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联盟党和政府据理力争,对执政党施加压力,要求把中国纳入“新东方政策”的框架内,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它还积极地寻求同中国进行接触,以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这除了源于联盟党内长期存在的反苏思想,以及反对党的在野地位赋予其的指责和批评它所认为的执政党的不足之处的权利以外,还因为反对党具有帮助和代替执政党完成其难以亲自出面完成的任务的义务,即为政府“分担风险”的义务。而作为执政党的社民党和自民党,则是在德中建交成为大势所趋,而且有可能成为反对党的政治资本时,才不得不采取主动,同意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 [德]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M].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163-164.
[2] 陈志斌.德国政体教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37.
[3] 王长江.政党政治原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212.
[4] Tim Trampedach.Bonn und Peking:Die wechselseitige Einbindung in auβenpolitische Strategien 1949-1990[M].Hamburg:Institut für Asienkunde,1997.
[5]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机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15.
[6] Uwe G.Fabritzek,Gelber Drache,Schwarzer Adler,München/Gütersloh u.a.:C.Bertelsmann Verlag,1973,S.313.
[7] Bonn plant keine Handelkontakte zu Peking,Sü ddeutsche Zeitung 1.9.1971.
[8] Hans-Peter Schwarz(Hrsg.).Akten zur ausw?rtigen Politik der Bun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71[M].München:R.Oldenbourg Verlag,2002.
[9] 王殊.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侧记[J].德国研究,2002,(1):8.
[10] Hans-Peter Schwarz(Hrsg.).Akten zur ausw?rtigen Politik der Bun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72,München:R.Oldenbourg,2002.
[11] Erik von Groeling.Die Kontaktaufnahme Bonn-Peking im internationalen Kr?ftespiel,in: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39,K?ln:Bundesinstitut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1972.
[12] Carsten Penzlin.Wahlkampf und Auβenpolitik-Eine vergleichende Studie zu den Bundestagswahlen von 1957 und 1972,Rostock:Baltic Sea Press,200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