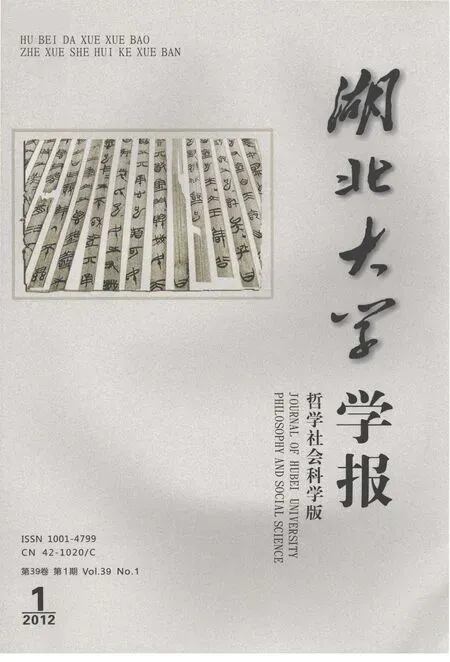信义义务的概念
范世乾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信义义务的概念
范世乾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信义义务是一项在英美法系国家广泛使用的规则,该规则适用的范围在近百年来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它要求受信人为了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行事,是一种利他性的义务。为了说明信义义务的本质,学者们形成了财产理论、信赖理论、不平等理论、合同理论、不当得利理论、脆弱性理论、权力和自由裁量理论、重要资源理论等诸多的观点。单一的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信义义务的涵义,应该注意其本质要求是为他人最大利益使用权力或者行为。信义义务的扩张应该有界限,它只能适用于一些极端情形,不能毫无原则地滥用。
信义义务;受信人;信赖
在信托法、公司法、代理法研究成果中,随处可见信义义务的字眼,但令人惊奇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使用频繁的表述,国内学者却几乎没有深入研究和分析过其含义。笔者认为,对信义义务概念的理解是分析一系列受信人——董事、高管、控制股东、合伙人、代理人、信托受托人、监护人、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义务的出发点。实际上,信义义务概念并非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性概念,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信义法(fiduciary law)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专门的理论范式。笔者在本文中尝试从比较法的角度,跳出公司法研究视角,从更广泛的信义法角度对信义义务概念的本质内涵进行分析。
一、信义义务概念的迷雾
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也被有的学者翻译成诚信义务[1]、受信义务,它是源自信义法(fiduciary law)的概念,通常指受益人对受信人施加信任和信赖,使其怀有最大真诚、正直、公正和忠诚的态度,为了前者最大利益行事。同时,受信人有义务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无私地行为,并不得不公平地利用对受益人的优势损害后者的利益[2]837~839。这是一种最大忠诚的义务[3]824。信义义务被描述为一种无私义务[4]或者类似于受信人履行了一项关心他人偏好(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功能的义务[5]。
信义义务从出现到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英国法中可以回溯至250年前的著名的Keech v.Sandford案①(1726),25E.R.223(Ch.).。在此之前,它是罗马法中早已确立的一部分规则②在罗马社会中的特定关系——诸如丈夫和妻子、医师和病人、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等——他们之间的关系受信义类型的规则的约束。其他类似信义关系也受到规制。。传统的“受信人”(fiduciary)术语的定义主要关注受信人(fiduciary)和受托人(trustee)的相似性,以及信义关系和信托关系的相似性。确实,“受信人”这一表述源自拉丁文“fiducia”和“fiduciarius”。前者的意思就是信任(trust)或信赖(confidence),后者的意思可以解释为被委托和信任的某事。而且,后两者源自动词“fido”,意思是“信任”(to trust)。在法律背景下,信义关系的概念最初源自衡平法最伟大的创造——信托,随后由衡平法用于与受托人有关的事项,再后来扩展到包括拥有信任地位或被其他人为特定目的授权的任何人的行为。而受托人—受益人关系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信义关系的最终范式[6]23~25。但对于信义义务含义的精确界定却一直是困扰法律界的一大难题,法律上存在的相当多的模糊性仍然没有被消除[1]285。这导致信义义务成为一个难以琢磨的概念。信义法持续和经常地适用于广泛的关系,这一现象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信义义务概念是法律概念中理解最清楚的概念之一的印象[7]。但实际上,对信义义务概念的界定主要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将其界定为信义关系(fiduciary relationship)中的义务,一种是将其描述为受信人(fiduciary)的义务。前者首先分析某种关系是否是信义关系,认为只要存在信义关系就存在信义义务;后者则着重于辨别受信人,只要认定某人为受信人,则认定其应该负有信义义务。这两种思路本质上都是一种同义循环,因此意义不大[8]。而且,从信义关系和信义义务的关系来看,只要能够认定某种法律关系为信义关系,则必定存在信义义务。当关系中的大量义务是受信人义务的时候,该关系可能被称作正式的信义关系或者本质上的信义关系。然而,具体的信义义务可能源自并非正式信义关系中的特别情形,本质上属于信义关系的法律关系通常是那些早已确定的信义关系,如信托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律师-客户关系、医师-病人关系等[9]76。
二、关于信义义务概念的各种理论
在过去数十年间,普通法系国家讨论了高级管理者/董事和公司之间[10]、监护人父母和非监护人父母之间、律师和客户、联邦政府和印第安部落、医生和病人、父亲和女儿、金融顾问和客户等信义关系的存在。然而,通过仔细地研究,法院经常适用的信义原则仅仅是虚弱的外表,内部隐藏着折磨信义理论的不确定性。为了说明信义义务的本质,学者们形成了财产理论、信赖理论、不平等理论、合同理论、不当得利理论、脆弱性理论、权力和自由裁量理论、重要资源理论等诸多的观点。
1.财产理论(property theory)。财产理论建议信义关系仅存在于某人对属于他人的财产拥有事实上的或法律上的控制的情形之下。据此,如果不存在财产利益(在传统的普通法意义上),就不存在信义关系。财产理论是大多数信义原则经济分析的开端。例如,Cooter和Freedman描述信义关系为存在于“受益人授予受信人控制和管理财产”的情形下。
这一信义原则理论可以被视为源自信托法,在信托法中信托财产或客体是信托关系存在的前提。然而,虽然可以认定信托关系导致存在信义义务,但二者并不等同。一个受托人是一种受信人,但一个受信人并不必然是受托人,即信义义务的概念大于信托义务的概念。实际上,很多信义关系不存在财产因素,或者至少不是传统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利益。正如La Forest法官在Canson Enterprises Ltd v.Boughton&Co.案中指出的:“在法院看来,一方当事人控制了属于他方财产的情形和一方当事人负有信义义务来真诚地履行承诺之间存在一种显著的区别。”例如,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宗教领袖和教徒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信义关系,但不具有财产因素。虽然病人的健康和教徒的精神愉悦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财产”,但他们并不是普通法一般性意义上的财产[2]。由此可见,通过财产理论来界定信义关系并不全面。
2.信赖理论(reliance theory)。该理论是所有理论之中最为直接的,同时也是最经常使用的一种。信赖理论认为,如果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给予信任和信赖,则该项关系是信义关系。
但并不是所有的信赖都会产生信义关系。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施加的信任存在不同的种类。信义关系中所需的信任种类与其他关系如合同中的信任、信赖或期待是不同的。案例法中有关产生信义关系的信任程度是不明确的,主观的信任或信赖既不是必需的也不是信义关系存在的结论性因素。
实际上,单纯的信赖并不能将信义关系与合同关系区分开来,而且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没有本质区别,如Gautreau认为信义义务和合同或侵权责任在本质上没有区别[8]。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信任的种类而不是信任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合同的履行中,产生的关系完全是内部的。信义关系中的信任是不同的,它不单纯涉及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而是还扩展至第三人。它超越能力问题而将受信人纳入受益人的财富创造之中,即关系的目的是促进受益人的财富最大化[6]。
虽然不确定性是强烈地反对将信任作为一项区分信义关系和非信义关系标准的理由,但存在更为普遍地对使用信任来确定信义关系的批评。根据美国近期的学界观点,信任概念是不确定的。虽然对信任的定义是不同的,但该术语通常意味着缺乏针对损害的法律或其他保护在某种程度上是脆弱的。例如,现在广泛接受的观点认为信任在商事关系中是普遍而深入的,它扮演着重要的填补不完全合同缝隙的角色。如果信任在所有关系合同中都存在,那么它就不能区分纯粹的合同关系和信义关系。
更为根本的是,在当事人依赖法律规制从而获得保护的意义上,他们根本没有信任其他方当事人,相反依赖的是信义义务法。此种对法律的信赖取代了对他方当事人的信任[9]。这一现象正是Oliver Williamson所指的“计算”[10]。由此可见,信赖理论也不能合理地界定信义关系。
3.不平等理论(inequality theory)。该理论基于受益人通常在权力上劣于受信人的事实,强调信义法的功能是通过对受信人施加严格的为受益人最佳利益行为的义务来调和此种不平等。一个通常的对信义关系的不平等理论的例证是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利义务。
虽然不平等理论强调信义关系范围之内的受信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但它被不适当地扩展到这些限定之外。对这种不纯粹的、不平等理论形式的坚持使得很多人相信所有的信义关系仅存在于支配主体和附属主体之间,但这一前提完全是不真实的。信义关系既存在于平等主体之间——诸如企业中的合伙人、配偶、公司董事以及专业服务事务所中的合伙人,也存在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诸如雇主和雇员。虽然很多信义关系中受信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力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信义关系都必然存在不平等性。
受信人和受益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源自权力从受益人处转移至受信人处,这一地位的不平等可以由受益人和受信人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最初二者都拥有完全和平等的权力——Q。在权力(p)从受益人处转移至受信人处后,信义关系出现。然而,在该信义关系范围之内,受信人的权力现在等于Q+p,而受益人的权力等于Q-p,由此导致在信义关系存在之前不存在的权力的不平等。虽然受益人的利益受信义法的保护,但这一保护仅仅作为对受信人滥用受益人授予权力的能力的制衡[2]。由上述分析可知,不平等是多数信义关系的特征,但由于现在信义法已经拓展到平等主体(如合伙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不平等也无法全面说明信义义务。
4.合同理论(contract theory)或承诺理论(undertaking test)。该理论认为信义关系是准合同性的,因为一方当事人承诺为另一方的最大利益而行事[11]。在该交易中受益人将特定的权力转移至受信人处,而后者忠诚地承诺是为了前者的最大利益行事[12]。根据该理论,有人主张信义关系仅仅是一种履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非常高的合同关系:“信义关系用忠诚义务替代详尽的合同条款,而法院通过描述在谈判成本低且所有承诺都完全履行的情形下,则当事人自己本应该选择的行为,来充实忠实义务。”
使用合同法类比来理解信义义务可能是将信义法所暗含的模糊的原则与更为具体的合同法联系在一起的尝试。然而,该类比有一些明显的瑕疵。虽然一个合同必然存在要约和承诺,但信义关系可能完全源自没有此种形式的情形。例如,信义关系可能源自受信人的单方行为,或者作为当事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源自主动和共同的协议,或者源自法院的判决。而且,虽然一个无偿的承诺在合同法中是不可执行的,但依信义法却是可以执行的;而且,信义关系可以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意图创设该关系的情形下出现。
除了这些问题,当事人所受的合同约束在根本上与受信人对受益人负有的义务也不一致。在前者,合同是决定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核心;而后者,信义法更为关注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各自的承诺以及受益人对受信人的信赖程度;最后,也许是最为重要的是,合同法规制所有合同当事人的行为,而信义法通过排他性地关注受信人的行为来规制信义关系。
合同法和信义法理论上还存在其他重要的不同。合同法的思想基础与市场经济的道德紧密联系。在历史上,自由和合同神圣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而不受约束的合同自由不再拥有其曾经的地位,合理期待和市场压力的商事标准在决定合同当事人之间可接受的标准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信义法一直不受参与者行为的限制或者表述的原则约束。而且,信义法所立基的是高于市场道德标准的更高道德标准。信义标准的基础是对当事人自我利益的合同信赖的镜像假设,即信义标准要求受信人像维护自己利益一样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由此可知,合同理论存在混淆合同与信义关系本质区别的危险,因此不应作为描述信义义务的工具。
5.不当得利理论(unjust enrichment)。该理论指出,信义关系存在于当受信人为自己而不是受益人利益使用权力,受益人从受信人处获得救济性帮助的情形。当受信人从受益人处接受权力而为了受益人的最大利益行事时,如果受信人使用这些权力从而为自己获得个人利益的,则存在不当得利。在此种情形下,受信人违反其对受益人的义务,应当对他们自己获得的不当得利或者被他们不当地赋予了利益的第三人获得的不当得利负有赔偿责任。
但不当得利理论存在循环证明的缺陷[2]。而且,即使在更狭窄意义上,用不当得利概念涵盖信义义务的本质也过于宽泛。两者的区别在于受信人的义务源自受信人会利用针对受益人的优势的关心,并不是对疏忽的损害的关心,而是对自利行为的关心。这一细微差别最好通过区分“错误的得利”(“wrongful enrichment”)和“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来观察[13]1777。虽然“每一个错误的得利”可以通过“不当得利”的语言来掩盖[13]1783。区别的关键是决定原告是否被要求依赖被告的错误行为来支撑该诉讼请求。依此观点,有过失与不当得利的请求没有关系[13]1788,这主要限于涉及错误的案件。虽然所有的评论者似乎同意违反信义义务处于恢复原状法的范围之内,但确定违反信义义务作为错误而不是不当得利案件强调了信义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其对机会主义的关注。因此,不当得利理论对决定某种关系是否是信义关系没有任何意义[2]。
6.脆弱性理论(vulnerability theory)。该理论认为,当一项法律关系中存在脆弱性时,则应该适用信义义务。从法院在Hodgkinson v.Simms等案的判决中可以看到受益人的脆弱性似乎完全源自他们对受信人在限定的信义关系中为前者最大利益最大诚信或者最大真诚行为的依赖[14]。脆弱性理论实际上是不平等理论的拓展,并且如何界定脆弱性却也是该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脆弱性理论实际上是用一个模糊的概念来界定另一个模糊的概念,其理论的解释力并不强。
7.权力和自由裁量理论(power and discretion theory)[15]。Frankel主张,信义关系有以下两个特征,(1)受信人“作为委托人的替代者服务”;(2)“仅为了能够使得受信人有效地行为的目的”,受信人“从委托人或第三人处获得权力”。“权力”是指“一种影响委托人变化的能力”[16]。这就是信义义务的权力与自由裁量理论。
信义关系在每一种受信人可以滥用其权力损害委托人的意义上不同。滥用风险的程度依赖:(1)当事人建立关系的目的,以及因此必须被委任以便实现当事人目的的权力的本质;(2)被委任给受信人的权力的程度;(3)降低滥用可能的保护机制的可获得性。
在决定滥用风险时这些因素的角色可以由比较不同种类的信义关系来说明。例如,确立公共公司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集中的管理。结果,公司的董事应该拥有作出及时决策的自由,而不用寻求股东的批准。另一方面,雇员通常被期待仅依雇主的控制来行为。因此,委托人/股东在与公司董事的信义关系中比委托人/雇主与雇员的信义关系中更容易遭受权力滥用的侵害。
即使在同一种类的信义关系中,权力滥用的风险也可能不同。例如,代理人可能在委托人不直接控制的情形下比在直接控制情形下需要更多的自由[16]。实际上,根据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法律理念,拥有权力和自由裁量权意味着应该承担一定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并不一定是信义义务,信义义务仅仅针对权力和自由裁量权过大而委托人无法完全控制受托人行为的情形,因此权力和自由裁量权理论的解释力也是有限的。
8.重要资源理论(critical resource theory)。重要资源理论认为,信义关系在一方当事人(受信人)代表另一方当事人(受益人)行为,并行使属于受益人的主要资源的自由裁量时形成。
“代表”(on behalf of)要求描述了某人主要为他人利益行为的关系。“自由裁量”(discretion)要求暗示受信人作出如何履行义务的选择。“重要资源”(critical resource)要求是该理论最为创新的特征,强调受信人掌握的是重要的财产或权力。
三、信义义务概念的本质内涵
上述只是学者们提出的有关信义义务的多种理论,这些理论可能会存在交叉和重合。实际上,由于信义义务语言的模糊性,我们很难用一种单一的理论来界定信义义务的概念,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信义义务的发展历史中把握信义义务的本质要求。信义义务最初源自财产法中的信托义务和罗马法中的善良家父义务(bonus paterfamilias)。用英美法系学者的观点来说,信托法中受托人(trustee)的义务是一种为了受益人最大利益行为的义务,因此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而大陆法系中的善良家父义务是指家父对家子的监护义务,也是一种利他性质的义务。随着近代社会对家父权的废除,善良家父义务也发展成为善良管理人义务。所谓的善良管理人义务是指像对待自己事务一样处理他人事务。这是一种最谨慎的注意义务,未尽善良家父义务与违反抽象轻过失相对应[17]。而由于人的自利本质,该表述与信托法中的为了他人最大利益行事的含义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将信托关系中受托人的义务表述为,受托人(trustee)“在管理所有信托事务时,有义务真诚地行为,并使用普通谨慎之人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具有的警惕、睿智、勤勉和谨慎,以及他们在处理自己相似事务上的智慧”[18]。因此,正如J.C.Shepherd所述:“信义关系存在于任何人接受任何一种权力,如果他还接受了一项为了其他人最大利益使用权力的义务,而权力的接受者使用了该权力。”[19]所以,我们在分析某种关系是否是信义关系时,需要掌握的核心内容是信义义务是一种为他人最大利益使用权力或者行为的义务。
四、余论
20世纪目睹了信义法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发展。例如,医师和精神病医生在近期成为受信人的一员,也有学者建议将信托法作为规制国家、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模型。而且,在20世纪40-80年代,信义义务逐渐从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政策领域。
到如今,信义关系从最初的信托关系发展到涵盖代理关系、高级管理者/董事和公司之间、监护人父母和非监护人父母之间的关系、律师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联邦政府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关系、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金融顾问和客户之间的关系等。正是信义法在各项领域中的蓬勃发展,使得法官将其作为一项良药。但我们需要时刻警醒,信义义务是一种为他人最大利益使用权力或者行为的义务,它仅仅出现在一些极端的情形下,不能毫无原则地滥用。
[1]卡塔琳娜·皮斯托.转型的大陆法法律体系中的诚信义务:从不完备法律理论得到的经验[M].黄少卿,译.吴敬琏.比较:第11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2]Lennar I.Rotman,Fiduciary Doctrine:A Concept in Need of Understanding[J].Alberta Law Review,vol.xxxiv,1996,(4):837-839.
[3]John C.Carter.The Fiduciary Rights of Shareholder[J].29Wm.&Mary L.Rev.824,1987-1988,at 824.
[4]Larry E.Ribstein,Fiduciary Duty Contracts in Unincorporated Firms[J].54 Wash.&Lee L.Rev.537,542(1997).
[5]Margaret M.Blair&Lynn A.Stout,Trust,Trustworthiness,and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Law[J].149 U.Pa.L.Rev.1735,1783(2001).
[6]Gerard M.D.Bean,Fiduciary Obligations and Joint Ventures[M].Clarendon Press.Oxford,1995.
[7]Robert Flannigan,The Fiduciary Obligation[J].9 Oxford J.Legal Stud.285,1989,at 285.
[8]Gautreau J,‘Demystifying the Fiduciary Mystique’[J].(1989)68 Can.Bar Rev.1,15-17.
[9]Larry E.Ribstein,Law V.Trust[J].81 B.U.L.Rev.553,568-71(2001).
[10]Oliver E.Williamson,Calculativeness,Trust,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36 J.L.&Econ.453,463(1993).
[11]Hospital Products Ltd v.United States Surgical Corp.[Z].(1984)156 CLR 41(HC of Aust).
[12]Austin W.Scott,The Fiduciary Principle[J].37 Cal.L.Rev.539(1949),at 540.
[13]Peter Birks,Unjust Enrichment and Wrongful Enrichment[J].79 Tex.L.Rev.1767,1779(2001),at 1777.
[14]Leonard I.Rotman,The Vulneralbe Position of Fiduciray Doctrine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J].24Man.L.J.90,1996-1997.
[15]LAC Minerals Ltd v.International Corana Resources Ltd[J].(1989)61 DLR(4th)14(SC of Canada).
[16]Tamar Frankel,Fiduciary Law[J].71 Cal.L.Rev.795,825 n.100(1983),at 809 n.47.
[17]陈志红.罗马法“善良家父的勤谨注意”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5,(8).
[18]Brawn v.Cleveland Trust Co.[Z].135N.E.829,831(N.Y.1922).
[19]J.C.Shepherd,Towards a Unified Concept of Fiduciary Relationships[J].97 L.Q.Rev.51,75(1981).
D923.99
A
1001-4799(2012)01-0062-05
2009-05-10
范世乾(1979-),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经济法研究。
朱建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