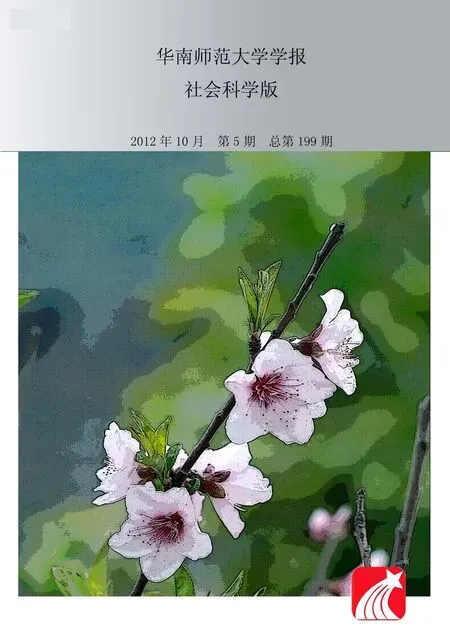屈宋作品的山水审美取向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侯文学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一
屈宋作品的山水审美取向对汉赋产生了重要影响,与《诗经》山水观照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虽然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题材在《诗经》中并不存在,但这并不等于时人对于山水缺乏审美观照。《诗经》中多有描写山水的词语,虽然简括,并且多用为兴喻,却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山水的观照角度及审美态度。检索相关诗篇不难发现,凡是以山水为兴喻的诗,都侧重关注山体的高大与水域的盛满。这其中又有情感体验的积极与消极之分。
就表达积极情感体验的诗篇来看,按照其所兴喻的本体又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以山水喻硕人。《陈风·泽陂》中“委委佗佗”的丰硕美人,诗人出之以“如山如河”的象喻,《卫风·硕人》则以“洋洋”的“河水”兴喻健硕的士女,所谓“庶姜孽孽,庶士有朅”也。其二,以山水喻盛物。《小雅·天保》祈颂君王的命禄则云:“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于山阜冈陵取其高广,于川源取其不竭,表达对于命禄无穷的祈愿。《大雅·江汉》颂美王师勇武而众盛:“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浮浮、汤汤,皆水流强盛之貌。其三,以山水喻身份功绩。《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唯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高大摩天的四岳,既是神灵的栖息之所,又是人才的渊薮。对山岳的赞美与对人才的歌颂融合在一起。《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龟蒙指龟山和蒙山,在鲁国境内。诗人在赞美鲁侯的文治武功时,一再言及鲁境的高山,显然认为二者具有同构关系,高山是功绩赫赫的鲁侯的物化象征。他如《齐风·南山》之“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小雅·节南山》之“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维何”,均以高峻的山体、深不可测的水域反衬贵族徒居高位。本体作为否定的对象出现,反映社会政治失序时人们的反常心态,然其以山为正面兴喻的思路仍然是传统的。
《诗经》中另有一部分涉及山水的诗篇,山水只是令人欢愉的事件发生的临近场所,或者也有兴喻之意。这类诗篇往往直接交代山水之貌,用以刻绘山水的词语,仍不离盛大之意:“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郑风·溱洧》)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韩‘涣’作‘洹’,云:盛貌也,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至盛也。”“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周颂·潜》)猗,又见于《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毛传》:“猗猗,美盛貌。”则以猗状漆沮二水之盛。
由上面诸例我们看到,不论对山水所兴喻的本体态度如何,诗人们面对高山的审美态度均是积极、肯定的,高山盛水又引发人们的崇敬与欢悦。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诗篇中诗人的审美视角均是外围的,人与山水保持一定的距离。由此而来,当一切审美活动还依附于生存需要的《诗经》时期的人们一旦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进入山间水域,态度就会发生变化。事实也确乎如此。《诗经》中的若干篇章便将征人的况瘁与山川的阻隔相并,后者成为前者的原因,所谓“陟彼崔嵬,我马虺”(《周南·卷耳》)、“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小雅·渐渐之石》),莫不如是。由此实际生活经验而来,诗人以山水喻恶境或悲愁,或用为反衬生活中的丑陋事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小雅·谷风》)、“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蓼莪》)、“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尽瘁以仕,宁莫我有”(《四月》),险山深水作为危害生存的对象的象喻出现,给人带来压抑、艰险之感。但是就数量来看,此类作品在《诗经》中并不占据主要位置。
综合言之,《诗经》时期人们对于山水的观照大都侧重于山之高、水之盛。其审美体验则分为两种:积极肯定与消极否定,而尤以积极肯定为主。先民在审美观照中对于高山广川的关注与认可,原因可以追溯至早期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生殖崇拜。自然与生殖崇拜均是基于生存需要而生的功利性崇拜。早期先民对于山川的祭祀,即是为实现对山川的索取。周文化的态度也是如此。《国语·鲁语》中展禽谈到祭祀对象的入选条件,即以功利为原则:“祀天之三辰,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十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在先民的观念里,山水与人类一样,是有生之属。山岳生长草木,兴云作雨,水中孕育鳞虫,是生命所自出之处。山水为人类生活提供各种资源。这种认识,绵延久远。《荀子·劝学》犹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汉代的《尚书大传》借孔子之口所作的解说尤为详尽:“夫山者,嵬嵬然草木生焉,禽兽蕃焉,材用殖焉,四方皆无私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顺便指出,与水相较,周人尤为重山,原因已有学者指出:“周代的天神崇拜实际上就是嵩岳崇拜。周人把自己所崇拜的处于中土的嵩山称作崇、岳、天室或太室,也单称为天,认为天神都居住在这些高山峻岭之中。”①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68页,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人重山是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合一所致。但是这种崇拜并不意味着周人喜欢山野生活;相反,人神道殊与隔绝的认识加重了周人对于崇山的敬畏与疏远。
就直观经验而言,生命体的硕大与生殖力的旺盛构成正比,所谓“水广者鱼大,山高者木修”(《淮南子·说山训》)。高山广川因生养万物而被先民关注,身居高位的君子使人伦攸叙、民生安定而被先民认可,二者均体现宇宙的好生之德。正是在化育生灵这一点上,自然界的山水(尤其是高山)与人间的君子呈现出相似性,所以《诗经》在赞美君子时,以高山广川起兴作比,将二者加以沟通。基于早期先民的生命一体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高山广川与岂弟的君子同时出现,即是对君子形象化的赞美与期待。这种对于山水的审美取向被后世儒家加以发挥并提炼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汉代经学家对于《诗经》山水的阐释,大体都是根据上述言说而来的。但是,周代传统、先秦儒家学者、汉代经学家的上述山水审美情态并未在战国文学与汉代文学中发生太大影响。
二
屈原是楚国宗室贵族,对于宗族与国家的使命感,使他一生未能忘情于政治。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孔子的入世态度更为坚执。孔子虽然并不主张避世,但也曾“欲居九夷”,考虑过“乘桴浮于海”的生活,并有过周游列国的实际经历;而屈原在心理上却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招魂章句》)的《招魂》②关于《招魂》的作者,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是宋玉作,司马迁以为是屈原作:“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我们采用司马迁的说法。而即便为宋玉所作,也不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就是对这种心理最直接的抒写。在《招魂》中,虽然也有被视为赏心悦目之景的高山与川谷的零星描写,但它们只是作为“层台累榭”、“穾厦”等华美人工建筑的点缀。这是身在政治与文明中心的屈原对待山水的基本态度。但事实却不由人愿。屈原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时间是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山水之域度过的,身在山野而心存魏阙是他离开郢都以后的生存境遇。他大部分涉及山水的作品就创作在政治失意以后。对于政治挥之不去的热情,与政治挫折感、伤痛感交织,构成屈原创作的直接心理背景。郢都是当时楚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与其相距遥远的流放地的山林臯壤则被挡在楚国政治与文明的大门之外,充满荒凉与恐怖的气息,这是屈原创作的地理文化背景。
正是受上述心理与地理文化观念的支配,处于流放地的屈原在对山水的观照态度上必然与《诗经》有所不同。就山而言,屈原只是片面继承了《诗经》对于险山的观照,将其作为自然暴力来看待。这种态度集中表现于《九章》:“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涉江》)山野之中,密林杳杳,猿狖出没,山高蔽日,阴雨绵绵。这一切对诗人而言,构成生存的困境。先秦多以日喻君,险山又似乎是象征造成屈原与楚王君臣乖隔的罪魁。“轸石崴嵬,蹇吾愿兮。超回志度,行隐进兮。”(《抽思》)超回、隐进,并状山之高迥纡曲之貌。诗人本欲南行娱心,却被轸石遍布的险山阻遏行程,举步维艰。《九章》是抒情诗,表达诗人因不被信任遭到流放而产生的抑郁伤感之情,流放地生存环境的恶劣为他宣情寄志提供现实依据。在屈原笔下,虽然山野远离浊世,但同时也是令人恐怖的生活场所,是欢乐的消解之地。所以,《涉江》下文又说:“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志在入世,山野作为出世之所,是现实政治失意者的被动归宿,为诗人主观所不取。在屈原这里,山野既构成对世俗的对抗,又非理想的存身之处。屈原对于山的观照角度与态度,与流放地的僻陋、远离权力中心的现实及其挥之不去的政治热情直接相关。
相较于山而言,屈原对于水的态度显得复杂。一方面,水与忧思愁怀相伴出现:“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九章·哀郢》)“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乎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九章·怀沙》)另一方面,水也是现实失意的诗人主动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长濑湍流,泝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九章·抽思》)江汉之水,沟通流放地与郢都,诗人顺水南行,冀以抒忧。“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礚礚兮,听波声之汹汹。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潏潏其前后兮,伴张弛之信期。”(《九章·悲回风》①《悲回风》的作者为屈原,宋代以前并无异议。自宋代魏了翁怀疑其非屈作以后,便不断有人引申、发挥这种看法(如清末吴汝纶、闻一多等人),但仍嫌证据不足。)面对茫茫江水,主人公思忖伯夷、叔齐等人隐处的行迹:“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盛大而极富动感的水域,是现实政治失意后的主人公主动选择的避世之所。丰赡的笔墨,承载着诗人对水的亲切情感。
屈原对于水的亲切态度,原因可以追溯到楚族的水崇拜。②关于楚族的水崇拜,可以参阅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第159-179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楚族出自高阳帝颛顼氏,对此,《离骚》曾以自豪的笔调出之:“帝高阳之苗裔兮。”在神话中,颛顼氏以鱼的形态完成生命的转化:“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死即复苏的过程中,“大水泉”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楚人认为,本族人的生命和鱼、水有不解之缘:鱼是本族人死后转生之物,水则是鱼维持生命的必须之物,水是快乐之乡。故与楚文化密切关联的《老子》多以水喻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其无以易之。”(第七十八章)可以说,水是楚族的灵魂家园,所以屈原早年在其《九歌·湘夫人》中热衷于湘君为湘夫人所筑的水下宫殿的描绘:“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也因之,在政治失意之际,诗人便每每“思彭咸之水游”。
但是就总体而言,自然山水的清新与朴野并不能抚慰诗人在现实社会中所受到的挫折,不能化解诗人对政治的热情和焦灼。即便是水,也只能是生命终结后的灵魂归宿,而非现实政治失意后给伤痛的诗人以安慰的有效疗养之域。从诗人对于山水的总体态度来看,屈作向上片面承接《诗经》的余绪而有所发展,向下则直接影响汉代楚辞体作品,是汉代楚辞体作品的重要文化基因。
在汉代《楚辞》作品中,山作为自然暴力出现,是生命的对抗因素;水主要作为现实苦痛的避难所出现,抒情主人公以水消忧,但水景最终并未达成对主人公心灵的安慰。我们先看写山之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山气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坱兮轧,山曲,心淹留兮恫慌忽。”“嵚岑碕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骩。”作者运用诸多表现山之曲险的词语如、嵯峨、坱圠、曲、嵚岑、碕礒、碅磳、磈硊等渲染山中的幽峻惨厉之状,以为世人生存的困境,劝诱隐于其中的王孙回归世俗:“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东方朔《七谏》:“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岭峨而嵯。”(《怨世》)“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哀命》)或用形容山体险峻的词语来表现世俗的险恶,或把山势的崎岖与心灵的偃蹇并提,注意到两者之间存在异质同构之处。刘向《九叹》:“山峻高以无垠兮,遂曾闳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云霏霏而陨集。阜隘狭而幽险兮,石嵯以翳日。悲故乡而发愤兮,去余邦之弥久。”(《远逝》)“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遗泣。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思古》)山野生活与愁苦的情绪相伴生,似乎险山就是产生不幸的根源。
再看写水之例。王褒《九怀·尊嘉》:“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子兮浮江,屈子兮沉湘。运余兮念兹,心内兮怀伤。望淮兮沛沛,滨流兮则逝。”主人公回顾以往,想到伍子胥、屈原沉江之事,黯然伤怀。见到眼前的沛沛淮水欲顺流而去,远离尘世的困扰。虽然水中有诸般快乐:“蛟龙兮导引,文鱼兮上濑。抽蒲兮陈坐,援芙蕖兮为盖……河伯兮开门,迎余兮欢欣。”但是主人公最终也未能融入,仍是“顾念兮旧都,怀恨兮艰难”。刘向《九叹·离世》:“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遵江曲之逶移兮,触石碕而衡游。波澧澧而扬浇兮,顺长濑之浊流。”“河水淫淫,情所愿兮。顾瞻郢路,终不返兮。”主人公选择水中作为避世的场所,饱含无奈的情绪。又《九叹·惜贤》:“江湘油油,长流汩兮。挑揄扬汰,荡迅疾兮。忧心展转,愁怫郁兮。冤结未舒,长隐忿兮。”主人公借水消忧,然事与愿违。
上述楚辞体作品多为悼屈、代屈立言之作,情志、语言等方面于屈辞多所模拟,对于山水的观照角度与态度自然也作了因袭。当然,因为缺乏内在的真实而深切的感受,汉人的模拟只是流于形式上的相似。这固然属于艺术上的失败,但于此模拟中,我们也还要看到屈作对于有汉一代文学发生深刻影响的一面。
三
带着对《诗经》及屈原作品中的相关山水描写的认识,我们看宋玉作品中的同类文字,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印象。就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宋玉关于山水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完整的篇帙只有《高唐赋》。关于此篇的性质,现代学者已有定论,即以铺写巫山景观为主,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①参阅褚斌杰:《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及艺术探微》,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吴广平:《宋玉研究》,第251-258页,岳麓书社2004年版。这里需要申说的是,该赋所刻意展现的山水之美的范型及其地域、时代文化背景没有受到充分注意,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该赋用四段文字描写巫山的形势,均围绕山体的险要着墨,尤以第三段最为精彩:“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盘岸岏,裖陈硙硙。磐石险峻,倾倚崕。岩岖参差,纵横相追。陬互横牾,背穴偃跖。交加累积,重叠增益。壮若砥柱,在巫山下。仰视山颠,肃何千千,炫耀虹蜺。俯视崝嵘,窐寥窈冥。不见其底,虚闻松声。倾岸洋洋,立而熊经。久而不去,足尽汗出。悠悠忽忽,怊怅自失。使人心动,无故自恐。贲育之断,不能为勇。纵纵莘莘,若生于鬼,若出于神。状似走兽,或象飞禽。谲诡奇伟,不可究陈。”登高远望,令人心惊而神疲。崖岸险曲,高高耸立。险峻的磐石,像要倾倒,像要崩塌。山岩崎岖,参差纵横。山脚横石逆立,背穴高耸,如有所踏。山石层叠,高如砥柱,立在巫山脚下。向上仰望山顶,山色苍苍,虹霓炫耀;向下张望,深谷冥冥,不可测度,只听见松涛阵阵。崖岸险峻,似乎就要崩倒,人站在旁边,就像攀挂在树上的熊,若长久不去,就会战栗恐惧,脚下虚汗淋漓,进而精神恍惚,不知所措。这一切都让人心惊胆战,恐惧害怕。即使如贲育那样勇于决断的勇士,面临此境,也无法展现他的勇敢。又如忽然遇到怪异之物,不知从何而来。怪石林立,形状各异,如鬼斧神工。诸般瑰奇怪异之象,不能一一道尽。作者选取大量表现山之险峻陡峭的词语加以铺排,并通过对登山者感受的叙述将山势的陡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产生“使人心瘁”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就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虽然伴随痛感,但又很有吸引力。对比前面的《诗经》及屈原作品中的相关文字,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至宋玉《高唐赋》,山的险峻危绝才首次以独立形态作为正面的审美观照对象走入文学作品。
宋玉的赋作对江河之水的观照同样呈现出与《诗经》及屈作的差异。《高唐赋》有如下一段文字:“登巉岩而下望兮,临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霁兮,观百谷之俱集。濞汹汹其无声兮,溃淡淡而并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弗止。长风至而波起兮,若丽山之孤亩。势薄岸而相击兮,隘交引而却会。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砾磥磥而相摩兮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厉。水澹澹而盘纡兮,洪波淫淫之溶。奔扬踊而相击兮,云兴声之霈霈。”较之前人,这段文字对水的描写既有承袭,又有别开生面之处。在观望视角上,与《悲回风》同,是登高而望(“登巉岩而下望”)。但作者对水的审视不是瞬间的,而是有一个时间的进程,从天雨新霁至长风吹起时水的景象都尽收眼底,对水的动静之态、水的声响以及引起这一切的原因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和交代:起初,因天雨新霁,没有一丝风,虽然百谷汇集,水势盛大,但见水涌,不闻水声。及至长风吹起,水体发生变化——洪波涌起,整个水体如骊山上一道狭长的田亩,以上是总观稸水。水浪击打岸边,遇到阻碍,回波逆折,与涌过来的后浪荟萃相击。水中间有怪石高耸,给人以海中碣石之感。风吹浪涌,汹涌的水浪击打怪石,大大小小的浪花四散飞扬,遮蔽天空,并发出震天的声响。以上对部分稸水作出绘写。接下来又对稸水进行总观:在地理平面上,水体蜿蜒曲折;在立体空间上,波起云涌,并伴有巨响。这种种描写,给人以惊险恐怖之感。下文即明言这种感受:“猛兽惊而跳骇兮,妄奔走而驰迈。虎豹豺兕,失气恐喙。雕鹗鹰鹞,飞扬伏窜。股战胁息,安敢妄挚。”飞禽走兽在盛大的水势面前,表现出恐惧之态。作者在此是用禽兽的恐惧之态来反衬水的惊险。关注水势的惊险,屈原《悲回风》已然;然《高唐赋》作者的心情却并非屈原式的忧怨不平,而是平静的、审美的。他并非因为内心有所郁结才关注到水势的湍急恐怖,并以再现水势的特点来消解心中的块垒。在作者眼里,这湍急浩大的水势是纯粹的审美对象,对于它带给生灵的恐惧,作者也持欣赏态度,予以审美观照。
由此,山的险峻危绝、水的湍急汹涌成为宋玉赋描写铺排的重点,并受到作者的赏爱。宋玉对于山水的这种审美取向,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战国楚地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虽然对于宋玉的身世问题学界多有争论,但他长期生活在楚国,受楚文化的影响却无可争议。战国楚文化的特点,相对于周文化而言,表现出以悲伤为美的倾向。在音乐方面,战国楚声即以清急哀伤著称。在战国两汉时期涉及楚地音乐表演的文献中,“激楚”一词经常出现。然关于“激楚”之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或以为楚乐曲名,或以为对楚风清急哀伤特点的描述。其实二说并非截然对立。东汉王逸注《楚辞·招魂》“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句即调停二说:“激,清声也。言吹竽击鼓,众乐并会,宫廷之内,莫不震动惊骇,复作《激楚》之清声,以发其音也。”王逸的解说在汉代有语言学的依据。扬雄《方言》卷十二即云:“激,清也。”是激、清同义,“激楚”即清楚。在战国两汉时代,清、悲作为音乐审美范畴,义亦同。战国文献称悲哀之乐为“清商”、“清徵”、“清角”,说明时人对二者关系的普遍认知。《韩非子·十过》载,卫灵公朝见晋平公路上,于濮水岸边偶得一曲。至晋,令乐师奏与平公,遂有如下情节:“(晋)平公问师旷曰:‘此所谓何声也?’师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平公)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对于所有的悲曲,均冠以“清”字,是清音等同于悲曲。另外,对于楚歌,汉人多用“噭咷”①《汉书·韩延寿传》:“噭咷楚歌。”扬雄《方言》卷二:“平原谓啼极无声谓之唴哴,楚谓之噭咷。”来形容,这表明即便在普遍以悲为美的汉风中,楚声的悲哀还是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这种赏乐求悲的倾向作为艺术理论的表达方式,也较早见于楚地文献。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中期文献《性自命出》即肯定悲哀是人情的极至,即至情。简文第二十三:“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播人之心也厚。”声,即声乐。简文作者认为,发自真情的音乐,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简文第二十九、三十则进一步指出:“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濬深舀,其则流如也以悲,条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意谓最美的音乐必是悲曲,因悲情与哭泣相同,是人至情的表现。悲情受到推崇。
较早将这种以悲伤为美的观念落实于文学作品的,自然非楚地作家莫属。《楚辞》中的屈宋作品、宋玉的《高唐赋》对山水的上述描写正是这种地域文化氛围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屈原政治的失意遮蔽了我们对于这种赏乐求悲的审美风尚的注意的话,宋玉《高唐赋》无疑更具有揭橥此风气的意义。《高唐赋》对巫山各类景观的铺写莫不以凸显欣赏者的恐惧、哀伤为旨归——登巉岩而下望,临大阺之稸水,但见波涛奔腾,水势汹涌,中流巨石出没,响声震天,这景象让虎豹豺兕等凶猛的野兽丧失勇气,雕鹗鹰鹞一类猛禽不敢呼吸和动作;中阪遥望,所闻则是“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清浊相和,五变四会。感心动耳,回肠荡气。孤子寡妇,寒心酸鼻。长吏隳官,贤士失志。愁思无已,叹息垂泪”;登高远望,则“使人心瘁”,登上高唐观之后,所闻为“雌雄相失,哀鸣相号”。
这些令人产生悲伤恐惧的心理感受的事物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西方学者对悲剧于人心灵的净化作用的探讨固然可以用为理论的解释,其实此类表述已经见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汉代枚乘的《七发》则以文学的形式给予了回答,其“曲江观涛”一段文字即是:“临朱汜而远逝兮,中虚烦而益怠。莫离散而发曙兮,内存心而自持。于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揄弃恬怠,输写淟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当是之时,虽有淹病滞疾,犹将伸伛起躄,发瞽披聋而观望之也。况直眇小烦懑,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发蒙解惑,不足以言也。”作者认为其笔下的浩大迅疾的水势具有极大的观赏价值,是水景中最美的一面,其所以让人感觉美,在于其令人惊怖。对此,《七发》反复陈说:“直使人踣焉,洄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这奇异诡怪的景象简直吓得人跌倒,使人情绪凄黯,但同时也得到提升,并最终获得疗救。枚乘是淮阴人,淮阴战国以来颇受楚文化沾溉。由此可以说,由楚人开启的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在理论上也必然由楚人总结和完成;楚人浪漫的情思决定这种理论的总结与深化表现为文学的方式。
如果将宋玉的《高唐赋》放到山水文学的纵向链条上,我们不难看到宋玉的贡献——他最先将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落实于山水题材作品,并由此开启了古代文学山水审美的一个主要倾向。汉代散体赋中的山水类文字,就审美取向来看,直接而且主要受到宋玉的影响。枚乘《梁王菟园赋》在展现梁园景观时,将山水作为重要事项。且看其对梁园西山的表现:“西山隑隑焉。崣,岩,巍焉。”或写山路的曲折漫长,或写山势高耸险峻。稍后的司马相如在其《上林赋》中也有大段文字描绘山峦:“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嵳。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岩阤甗錡,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阜陵别坞。崴磈嵔廆,丘虚堀礨。隐辚郁,登降施靡。”作者把十余个表示险峭的形容词(主要是双音词)四字一句排列,完成对险山的描绘。虽然这种堆砌同义词的手法在今天看来并非成功的文学表现手段,但作者极力展示山之险峻的意图至为明显。此赋是夸饰天子苑囿广大巨丽的作品,险山是正面表现对象。西汉末年,扬雄作《蜀都赋》,讴歌家乡蜀地。自然风物之美,受到最高礼赞。险山作为蜀地重要景观获得表现:“尔乃仓山隐天,岔崟回丛,增崭重崒……湔山岩岩,观上岑嵓,龙阳累峗。漼粲交倚……集胁施,形精出偈,堪垱隐倚。”岔崟回丛、增崭重崒诸语,均为险峭之义,扬雄以此总写蜀山之险;次列湔、观上、龙阳等诸山名,每山之后,复缀一表示险要的词语;再罗列数个表示险要之词,概写诸山,手法回环往复,则蜀地群山之难攀、难于上青天之感登时托出。东汉张衡是南阳人,亦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创作《南都赋》,开篇之“于乐显都,既丽且康”是此赋的基调。其中有关于南阳境内山峦的描写:“或嶙而连,或豁尔而中绝。鞠巍巍其隐天,俯而观乎云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旷荡,下蒙笼而崎岖;坂坻嶻而成甗,溪壑错缪而盘纡。”前面与扬雄《蜀都赋》手法略近,尾处以下窄上宽之甑喻山形,颇显别致。险山峻岭依然是令人心仪的对象。
枚乘《梁王菟园赋》写菟园之水:“溪谷沙石,涸波沸日。湲浸疾东,流连焉辚辚。”流水回旋,水浪激扬,迅疾东行,绵绵不断,发出巨响。其《七发》列举七事以启发太子,曲江观涛是其中重要一项,其写江涛的旁作而奔起之状则云:“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骆驿。颙颙卬卬,椐椐强强,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礚,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傍,则滂渤怫郁,暗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骨母之场。淩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亏陂池,决胜乃罢。汨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作者主要运用各种比喻表现江涛的迅疾:像素车白马,像三军之腾装,像轻车之勒兵,像壁垒军行,像突怒而无畏的勇壮之卒,像巨雷之行,像奔腾的骏马;声响巨大,如雷鼓之鸣。这里的潮水,既有庞大的体积,又有令人惊骇的速度和声响,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在对潮水的表现上,既写其色彩,又绘其动态,所用的动态性词语更多。司马相如在对江河之水的观照上,仍然是欣赏其浩大迅疾的极具动感的美。其《上林赋》在夸述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时,有这样一段文字:“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鹜往来……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弗宓汩,偪侧泌。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穷隆云桡,宛胶盭,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漂疾。”与枚乘相比,司马相如对江河之水的绘写不再用各种比喻,而是直接罗列各种表示强烈动作的动词及表示动态的形容词,为我们呈示一幅浩荡、迅疾、曲折的川流画面,此手法得益于司马相如对词语的丰富把握。《汉书·艺文志》载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虽然类似字书,在语言学史上没有特殊贡献,但足以说明相如在词语方面的深厚积累。扬雄的《蜀都赋》亦有描写江水之句:“旋溺冤,绥颓惭。博岸敌呷,濑磴岩,樘汾汾,忽溶沛,逾窘出限。连混陁隧。铚钉钟涌,声欢薄泙龙,历丰隆,潜延延,雷抶电击。鸿康濭,速远乎长喻,驰山下卒,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旋、绥、呷、磴、逾、抶、击、驰等动感强烈的词语,分置于三、四言短句中,增强水的迅疾之感。同样是铺张扬厉的风格,因作家素养不同,其具体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略去表现手法的差异,背后一以贯之的是以险怪、迅疾为美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自然不同于魏晋以后受玄学与佛道影响的山水诗“以清朗澄澈、明净空灵为最高境界”①葛晓音:《东晋玄学自然观向山水审美观的转化——兼探支遁注〈逍遥游〉新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的审美理想。而追溯其本始,自然要归功于宋玉。
四
汉代是经学“昌明”与“极盛”的时代,《诗经》是汉代经学家进言立说的重要文本依据。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作为汉代文学重要构成的汉赋所呈现的山水审美取向,汉代《诗经》学的影迹几乎看不到。汉代《诗经》学承周代传统与先秦儒学而来,以山水比德,这种思路化为辞章,现存汉代文学作品则只有董仲舒的《山川颂》。在汉代关于山水的文学中,董文属于一支别调。由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汉代经学对于汉代文学的山水审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
相反,我们于汉赋中却可以清晰看到屈原与宋玉的笔墨所发生的普遍影响。至于屈宋何以对汉代文学发生如此影响,则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根植于楚文化的屈宋作品对于山水的观照角度与态度为先秦文学带来的新变以及这种新变对于汉代文学的深刻影响。也顺便纠正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认识,即以为汉代以前包括汉代的人们对于山水缺乏审美意识。钱钟书就曾针对汉代文学说:“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②钱钟书:《管锥编》,第10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钱先生以为,班张等人的赋作虽然涉及山水,但也只是叙述了山水的形势及物产而已,至若《山川颂》,只用山水来比喻品德,均非出于对山川之美的欣赏。其实,无论陈列其形势产品还是喻心性德性,只要细考其造语,详究其时代文化背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对于山水审美的基本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