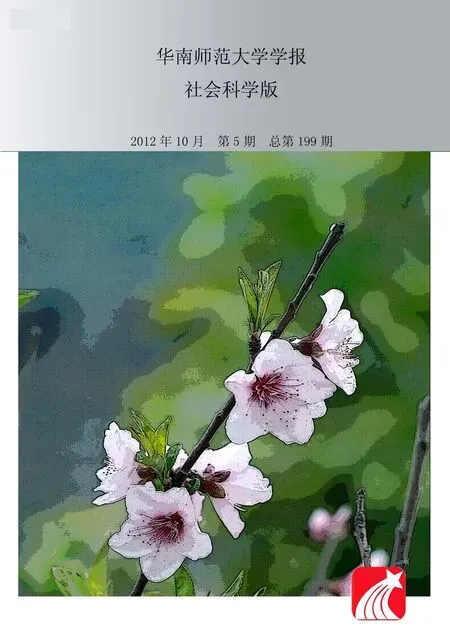幸福广东建设的道德理路
罗明星
(广州大学政治与公民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幸福广东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有经济理路、政治理路等不同选择,但道德理路可以提供不同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实践价值。因此,充分考量道德与幸福的内在关联,并籍此找寻民众幸福感建构的道德理路,是幸福广东建设的当然选择。
一、通过道德的幸福价值发现达成“德福一致”的社会共识
德福一致,是具有通约性的道德认知。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幸福的人拥有我们所要求的稳定性,并且在一生中幸福。因为,他总是或至少经常在做着和思考着合德性的事情。”①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第28-29页,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张载亦有言:“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②《张载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两位思想家都深刻说明了德福之间的依存关系。历史上,康德曾经试图将道德与幸福进行切割,甚至认为“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律令,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行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合乎我们所谓的至善”。③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16-117页,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但事实证明,康德的理论努力在生活事实面前归于徒劳,真实的情形是,德福之间不仅有静态的依存,而且有动态的辩证,道德与幸福的效应关系一直存在于人类现实生活,尤其是在现代契约社会,德福的一体同构,已经成为幸福实现的根本性文化依据。因此,幸福广东的建设,必须有“德福一致”的社会共识,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应该学会发现道德的幸福价值,唯有道德的幸福认知,才会有道德的行动,进而有伴随行动的幸福。
“德福一致”社会共识的形成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社会道德心理。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幸福感“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④邢占军:《解读幸福指数 求证幸福方程——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实地获得幸福之“感”时,这“感”已经不是转瞬即逝的情绪体验,而是具有强大生活经验支撑的稳定的心理定势。幸福生活“既是‘值得欲望的生活’,又是‘值得赞赏的生活’”⑤江畅:《幸福: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载《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幸福生活之所以“值得赞赏”,乃是因为幸福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是生活的德性为德性的生活塑造了道德上的高贵。2004年,美国人的幸福感没有明显变化,但却表现出幸福难以维系的心理忧郁,作为应对策略,他们在总统选举中,将“道德价值观”列为美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压倒了经济增长、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教育、卫生保健。①[美]阿瑟角·布鲁克斯:《美国人的幸福观》,载《精神文明导刊》2010年第11期。很显然,美国人希望通过道德的稳定来维系幸福的稳定,这从侧面证明了道德之于幸福的绝对性价值。当下,包括广东人在内的中国民众,我们正在感受道德沦丧对幸福生活的威胁,理论界甚至有人发出了道德危机的警示。不管是基于经验直观还是基于理性审视,国民的道德忧郁已经成为普遍化的社会心理,它实质上是一份珍贵的道德资源,说明我们的民众还有道德的知觉,我们的社会还有道德的人活着,而这正是道德的希望所在,也是幸福的希望所在。因此,何以利用社会的道德忧郁激发民众的道德责任,是幸福广东建设应该关注的道德主题。
建构“德福一致”的社会共识,关键是帮助人们在观念上矫正道德与幸福的排斥性关系,进而确认道德对幸福的增值效应。作为一种思维习惯,人们通常将道德理解为利益的排斥性存在,认为讲道德必然要以牺牲利益甚至以牺牲幸福为前提。其实,这是对道德的严重误解。事实上,道德不是幸福的对立物,道德可以通过激发主体的内在潜能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从而通过社会利益总量的绝对增加实现社会幸福的增值。即使在社会利益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道德也可以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规范,让利益获得的社会成本普遍降低,从而变相放大社会的幸福总量。比如,在公共场合乘坐电梯时,如果每位乘客都按秩序排队,那么,电梯就不会因为拥挤或超载而延误时间,可以在同一时间运送最大量的客人,电梯的效用价值就会得到最充分利用,更多人就可以享受到乘坐电梯的幸福。不止如此,道德还可以实现幸福传递,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幸福最大化。有心理学家做过统计,如果一个人早上起来面带微笑,他的幸福感在一天时间里至少可以传递给70个人。幸福感呈几何级数的放大效应,正是道德的人们之间主动传递善意的结果。而且,即使是道德倡导的利益牺牲,也可以实现幸福增值。利他性的利益牺牲其实并不是真正“牺牲”,而是利益向他主体的让渡,通常,这种让渡使得利益转移到最有需要的人,利益的效用价值反而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正如一位行善者,如果将自己的面包让渡给濒临饿死的人,面包可能拯救一条生命,濒临死亡者可能获得死后余生的极度幸福感受,道德就此实现了幸福的无限增值。所以,幸福广东的建设,有必要通过教育、媒体等一切社会资源,广泛传播道德的幸福价值,让每一位民众都发现,道德不是幸福的对立物,而是幸福的文化之源。
二、通过恪守道德底线为民众幸福提供最基本的伦理保证
道德底线是维持民众幸福感最基本的伦理前提。道德底线通常被理解为道德上的最低要求,但是,何处是道德底线之“底”?在伦理学界本身是仁者见仁的问题。曾经有人将道德按照“损人利己、自私自利、先私后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进行分层,将“不损人利己”视为道德底线,但“小悦悦”事件之后,人们发现见死不救的“自私自利”,不仅跨越了道德底线,而且也逾越了普通人能够承受的道德心理极限。那么,维持民众幸福感的道德底线到底应该如何界定?笔者认为,可以借助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进行解读。根据马氏理论,人的需要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可以分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荣誉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因此,触及人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的道德之“底”,便是道德的底线所在。在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民众连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就意味着幸福基础的绝对丧失,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就广东而言,我们已经具备让民众享有幸福的物质条件,但尚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安全基础,特别是心理安全基础,充斥于生活中的欺诈与冷漠等恶性道德现象,直接危及民众基本的社会信任,消解着民众的幸福感受,因此,恪守道德底线,对民众幸福感实施最大限度的道德保护,已然是幸福广东建设的应有之义。
恪守道德底线,必须动用社会法权力量强力遏制违法犯罪行为。违法犯罪行为是对道德底线的突破,这种行为不仅为以公共福利为价值指向的集体主义道德所不齿,即便是以自我价值为目标指向的利己主义道德,也对此表示谴责。费尔巴哈曾经从自然本性肯定了利己主义的天然合理性,但即便作为利己主义者,他也对损害他人幸福权利的极端利己行为给予了严厉痛斥,认为这是“为自己发明出天堂,为别人发明出地狱;……为自己发明出自由,为别人发明出奴役;为自己发明出享受,为别人发明出制欲”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册),第806页,荣震华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利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为了自己幸福而损害他人幸福,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果幸福追求失去道德规戒,就会让每个人的幸福权利遭受威胁。对违法犯罪者而言,道德的规戒功能已然失效,唯有动用法权的强制力,才能对其恶性实施有效威慑,法权力量的参与可以有效放大道德的作用能量,让道德在善与恶的博弈中取得胜利,最终为幸福的实现提供道德支撑。就当下而言,有两类性质的违法犯罪尤其应该重点打击。其一是遍及日常生活世界的商业欺诈,不仅让许多民众蒙受直接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破坏了社会的相互信任,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怀疑,甚至让熟人也成为熟悉的陌生人。欺诈导致的社会信任缺乏,极大地加重了社会交往成本,对民众的精神幸福构成极大威胁。其二是隐藏在阳光世界的黑恶势力,以隐蔽但强势的违法方式践踏社会公义,极大地打击民众的道德信心,制造民众的无助感和恐惧感,毁灭民众的幸福愿景。因此,通过社会法权力量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既是社会正义的伸张,亦是对底线道德和民众幸福希望的有效保护。
恪守道德底线,必须防止金钱力量的非法伸张。金钱是人们获得幸福的必要物质前提,对金钱的适度追求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但是,金钱力量必须得到有效遏制,否则,金钱逻辑将僭越生活逻辑,金钱会成为民众幸福生活的异己力量。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金钱力量泛滥的社会通常也是道德沦丧的社会,是民众幸福感被严重剥夺的社会。莎士比亚曾经提醒我们,金子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使黑变成白,使丑变成美,使错变成对,使懦夫变成英雄,让老朽变得朝气蓬勃”,所以,幸福广东的建设,既要追求以金钱为表征的社会财富最大化,同时,也必须对金钱力量的非法伸张保持高度警惕,力求让金钱的作用领域最小化,尤其在生命尊严与法律权威面前,要让金钱的购买力归于无效。我们的社会要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性生活景观:豪车车主由于环卫工人让路不及时而对其无理殴打,警察处理纠纷时让车主给环卫工人赔偿,车主扔下金钱之后扬长而去。表面上看,事情似乎得到了圆满解决,但其给社会传递的却是恶劣的道德信息,即只要有钱就可以随便打人,本质上怂恿了金钱力量对人格尊严的贬损。
恪守道德底线,还必须建构灵敏的道德赏罚机制。道德赏罚是抑制社会恶行、促成道德善举持续化和普遍化不可缺少的利益机制。亚当·斯密指出:“任何表现为合宜的感激对象的行为,显然应该得到报答;同样,任何表现为合宜的愤恨对象的行为,显然应该受到惩罚。”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82页,蒋白强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道德赏罚机制,只是由于社会性质不同而呈现出了不同的道德样态。幸福广东建设,既要通过道德惩戒为道德底线设防,更需要有效的道德回报对底线道德加以提升。正如,社会倡导“勤劳”美德,就应该通过制度设置尽可能让勤劳的人获得利益回报并在劳动中感受人生幸福。但是,道德回报可能遭遇“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指称的是道德与幸福的背反情形,讲道德的人可能因为道德反而失却了应得的幸福。尽管“囚徒困境”一直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于社会道德生活,但是,“囚徒困境”只是也只能是道德上的偶然情形,否则道德就会在与幸福的对立中遭人遗弃。
三、通过政府道德示范营造民众幸福希望
政府的道德示范是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道德角色示范。孔子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③论语·颜渊。政府如果能够在道德上率先垂范,民众就会从善如流,并在积极的道德氛围中营造幸福希望。政府的道德示范主要应该从制度和行为两方面展开。
在制度层面,政府应该致力于建构道德的制度。道德的制度是以民众福利为终极价值所指,直接服务于民众个人幸福的制度。制度的品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品性,一个政府在制度设计中是优先考虑政府利益还是优先考虑民众利益,直接反映着政府的德性,也直接关涉着民众的幸福感。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民众利益,如加工资时将教师摆在公务员之先,财政投入时让学校的危房改造优先于政府办公楼修建,等等,政府无需自我标榜,通过制度设计本身即可以让自己站在道德的至高点,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国外学者Ramakrishna和Chan的研究发现:“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生活满意程度可以根据情感体验判断;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人的生活满意与外部规范却紧密联系在一起。”①苗元江、余嘉元:《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我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民众对作为制度的外部规范反应敏感,可能将个人幸福与制度做更紧密的价值关联,因此,政府应该特别重视制度设计的道德性质。在世界范围内,举凡有德性的政府,都是通过制度设计来实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最终达到提升民众幸福感的政策目标。
在行为层面,政府应该致力于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严格来说,政府公职人员既不是人民的公仆,也不是人民的主人,其本身是人民的一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拥有平等人格,因此,遵守社会法律与道德秩序,也是公职人员的基本义务。由于政府公职人员具有职业的特殊性,其手中握有的公权力客观上放大了行为的道德影响力,于是,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往往成为社会的道德风向标。通常的情况是,假如政府公职人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社会道德氛围就会呈现良性态势,民众的幸福希望就会提升;反之,假如政府公职人员违法乱纪,腐败盛行,社会的道德氛围就会呈现颓废态势,民众的幸福希望就会沦落。所以,对民众幸福承担责任的政府,总是要求公职人员有更积极的道德担当,并注重培养公职人员在社会共同体中的“共存意识”②刘悦笛:《今日政治和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载《哲学动态》2009年第11期。,因为他们知道,公职人员的道德面貌不仅是政府的道德脸面问题,同时也是直接关涉民众幸福的切身利益问题。
四、通过欲望的道德控制实现幸福感的可持续
欲望可以成就幸福,亦可以毁灭幸福。卢梭曾经崇尚自然状态下的幸福,因为自然人的欲望只限于本能,没有超越本能的复杂欲望对人的幸福造成干扰,而文明社会,“由于我们力图增加我们的幸福,才使我们的幸福变成了痛苦”③卢梭:《爱弥尔》(上卷),第76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叔本华甚至直接将欲望与幸福相对立,将欲望看成是幸福的排斥性存在,是幸福的敌人。原因是,人的欲望永远没有尽头,欲望满足之后马上会生出一个更难满足的欲望,由于人总是处在欲望的绝对不满足状态,人生因此充满痛苦。卢梭与叔本华的欲望观虽然极端,有一点却成为人类共识,即欲望应该合理节制。那么,幸福广东的建设,如何对欲望进行有效的道德控制以实现幸福感的可持续?
在改革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政府的发展欲望控制是实现民众幸福可持续的关键所在。我们的政府一直有一个美好愿望,就是通过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尽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民众的幸福指数,甚至在幸福指标上力图向欧美发达国家看齐。但是,政府的发展欲望却潜隐着不言而喻的伦理危险,即政府关于幸福指标的美好构想可能已经逾越了现实环境与人口的承载能力,违背了发展伦理的可持续原则。如果让无节制的发展欲望自由伸张,将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透支,最终对民众的未来幸福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应该冷静下来,慎重思考我们发展的极限在哪里。政府应该追求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y),而不是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尤其要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发展水平下通过社会整体优化以实现民众幸福的最大化。历史上已经有此成功范例,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④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充分说明有限的发展亦可实现非有限的幸福。
当然,幸福感的可持续,仅仅靠政府发展欲望的节制还不够,民众消费欲望的控制也至关重要。任何幸福,只有当其与主体的现实欲求相匹配并且与主体能力相适应时,幸福才成为真实的幸福。相反,如果主体的幸福欲求得不到有效控制,膨胀的欲求就会夺走人的现实幸福,因为,“在各种动物中,惟有人享有一种可悲的特权:在他身上自我保存的本能可以变为狂傲的利己主义,对事物的需求可以变为贪食无度”⑤[俄]弗兰克:《实在与人》,第217-218页,李昭时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丹尼尔·贝尔在论及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时指出,曾经建构了美国人幸福理想的美国资本主义,其传统合法性正是“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教观念上,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化的报偿体系”,但现在,传统的“行善道德观(goodness morality)”演变为“娱乐道德观(fun morality)”,享乐主义让人“失掉了与他人同甘共苦和自我牺牲的能力”①丹尼尔·贝尔:《资本仁义文化矛盾》,第131-132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没有道德节制的享乐不仅没有带来美国人的幸福反而让他们失却了曾经拥有的幸福。所以,幸福广东的建设,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民众消费欲望进行适度遏制,避免享乐需求蜕变为享乐主义需求,尤其是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下的炫耀性消费应该被有效制止。尽管社会没有权利对民众的合法消费妄加干涉,但可以通过现代媒体等传播手段为民众的精神世界注入消费理性,倡导“节制”美德,让民众懂得“节制可以让享乐加深和幸福长久”②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第3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同时,政府亦可以通过高额税收等经济手段和纪律条例等行政手段对炫耀性消费进行抑制,让放纵欲望者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和荣誉代价,从而根本上抑制消费欲望的非理性张扬。
五、通过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实现幸福感的精神升华
虽然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证明,总体而论,“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③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但是,这只能说明经济因素是决定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并不代表经济因素是决定幸福感的唯一因素甚至是根本因素。早在1974年,美国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Masterliness)就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幸福悖论”,其基本观点是,收入与幸福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联,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持续地提高人们的幸福度。国外的研究数据也表明,“当人均国民年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民收入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就消失了”④郭永玉:《从社会和个人层面认识幸福》,载《精神文明导刊》2010年11期。。这就意味着,幸福感的提升不可能仅仅依凭物质生活发展来实现。也许有鉴于此,弗洛姆将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占有”与“存在”(To Have or To Be)的区分,认为重占有者将生活理解为无止境追求功利价值的过程,而重存在者则将生活理解为生命生长和人性潜能的实现过程,前者会陷入幸福的烦恼进而失却幸福的所在,后者则会得到恒久幸福。可见,幸福感不能仅仅拘泥于物性感觉,因为纯粹的物性感觉并非像伊壁鸠鲁所言的那样是“真理的报道者”,很多时候,它只是“脱离定在的幸福,而不是定在的幸福”。人只有将幸福从物性感觉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幸福感的本质性提升。
所以,幸福广东的建设,必须促成民众幸福感从重物质到重精神的转向,让民众通过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实现幸福感的精神升华。何以至此?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有效的制度设置和社会动员,让所有民众都有机会服务于他人,并在服务于他人的过程中走进他人的心灵世界,感受心灵交融的幸福体验。具体策略就是,建立遍及社区的志愿服务网络,将志愿服务作为义务赋予生活中的每一位民众,让民众通过志愿服务获得生活的幸福体验。
志愿服务是道德高尚性的行动诠释,是毋庸置疑的道德善行。志愿服务让服务对象获得来自他人的热心帮助,感受他人带来的人间温情,接受服务者会获得愉悦体验。亚当·斯密曾经说:“同情通过提供另一种使人满足的源泉来增加快乐,同时通过暗示当时几乎是唯一可接受的合意情感来减轻痛苦。”⑤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12页。斯密指称的同情还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情感付出,如果同情同时伴随对他人的利益付出,善行主体将会获得更强烈的愉悦体验。我们可以绝对相信,自觉性的志愿服务既是对他人的奉献,也是对自己的心灵洗礼,它让人与自己的同类融为一体,并充分体验相互的存在价值,人可以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发现,并为自己的幸福感提供永不枯竭的幸福源泉。在社会信任度偏下的当代中国,志愿服务还有一个重大的伦理意义,即促成陌生人的“真实性”接触,促进彼此之间的心灵和解,实现人际信任的渐进性复苏,为幸福感的普遍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
志愿服务不仅可以促进民众的幸福体验,亦可以让民众通过幸福体验获得道德提升,从而实现道德与幸福的良性循环。幸福的人一般处于心理的放松和开放状态,幸福的愉悦让其更容易对生活进行善意解读,并将善良、宽容等美德同构于自己的精神生活。虽然没有实证数据证明多少人因为幸福接受了道德,但至少,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幸福的人的确更愿意接受道德,而且,不只是更愿意接受道德,其行为表现也更有道德。“在美国,有幸福感的人,捐赠者比不捐赠者多出43%”①阿瑟角·布鲁克斯:《美国人的幸福观》。,即是最好的明证。因此,志愿服务既是幸福的社会化过程同时也是道德的社会化过程,幸福的人不可能是孤独的幸福享有者,其与他人分享幸福的过程客观上就是道德善意的表达过程,也是社会美德的传播过程。正如我们所见,志愿者将物质温暖送给贫困山区的儿童,儿童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幸福,同时也收获着仁爱、奉献等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