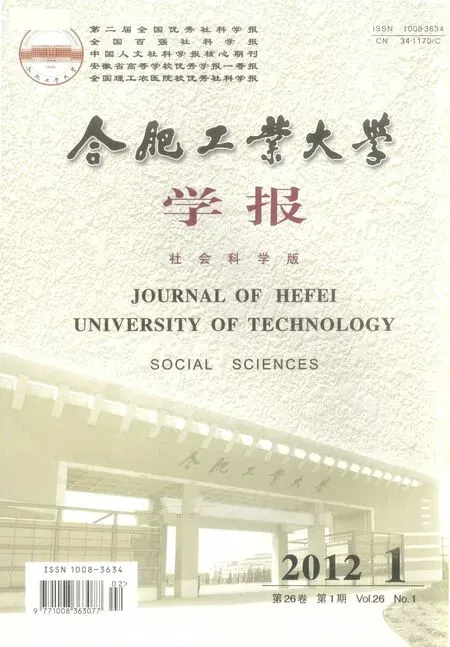论恐怖小说翻译中的叙述和描写问题——评《来自墓穴里的种子》的两篇汉译
夏 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南京 210044)
论恐怖小说翻译中的叙述和描写问题
——评《来自墓穴里的种子》的两篇汉译
夏 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南京 210044)
恐怖文学常用叙述和描写来造成紧张和恐怖的气氛,短篇小说《来自墓穴里的种子》的氛围之所以让人觉得既恐怖又妖艳,就是作者以精益求精的叙述和描写营造而成的。鉴于恐怖小说创作中叙述性和描写性文字重要的气氛烘托作用,文章关注恐怖小说翻译中叙述性和描写性文字的翻译,通过分析该小说的两个汉译版本,主要在叙述的线索和视角、细节描写和气氛营造等方面探讨英文恐怖小说汉译问题。
恐怖小说翻译;叙述线索;叙述视角;细节描写;气氛营造
一、引 言
恐怖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概念来自于西方,源于“黑暗时代”关于鬼魂、幽冥世界的文学传统,在基本叙事模式上和18世纪中叶哥特式小说颇有渊源,但恐怖小说更重超自然事件和惊悚效果[1]。它往往通过营造神秘阴森的气氛、渲染血腥暴力的场景,给明知自己身处安全境地的读者构造出虚幻的危险,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引起特殊的阅读快感。除了惊悚、神秘、悬念等元素的运用,恐怖小说甚至还可以通过营造某种恐怖的“美感”引起读者的兴趣。The Seed from the Sepulchre(《来自墓穴里的种子》)就是具有这种妖艳而恐怖魅力的小说,吸引读者走完一段奇异的梦幻之旅,是“具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风格的作品”[2]67。这篇小说译文的两个版本,一为仵从巨译的(以下简称仵译)《来自墓穴里的种子》[2]38-68,一为姚锦熔译的(以下简称姚译)《墓坑里出来的种子》[3],年份不同,译者不同,译本风格也有不同。
这篇小说的梗概是:索恩和法尔莫是两个以找寻兰花为业的人,在委内瑞拉寻兰花时得知当地一个传说,说有个墓葬坑里有许多陪葬的金银财宝。于是他们带着两个印第安向导深入热带雨林寻宝。索恩因为路上生病发烧,法尔莫只好自己带着一个向导去了。但这个向导似乎知道那里有某种可怕的东西,不愿陪他,法尔莫就让他留在河边,自己下了墓穴坑。回来后法尔莫性格大变,似乎突然染上某种热带怪病。索恩给他打了奎宁针。法尔莫趁着神志恢复清醒时讲述了自己的恐怖遭遇。(原来,墓穴中有种吸人膏血的寄生植物。法尔莫不知道自己已沾上它的种子。)随着病情的恶化,一株令人恶心的植物从法尔莫头上破壳而出,不断生长,吸食他的机体。索恩恐惧却又无力逃离。这植物吸食完法尔莫,开出一朵妖艳的恶魔般的人面花,“散发出致人死命的柔情”寻找下一个进食目标,索恩无法抗拒其诱惑和魅力,“只能听命于它而自甘毁灭”,最后“在堕落的兴奋和痛苦的快感中被它同化”[2]68。于是,又一朵妖艳的花儿绽放了。
流畅的叙事和恐怖的氛围是恐怖小说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译者在翻译恐怖小说时,需要留心译文的叙事是否流畅、易于阅读,细节描写是否在译文中处理得很好,原文的气氛是否在译文中得到再现。笔者认为,这应成为恐怖小说翻译研究中重要的内容。本文选取该小说的两种汉译材料,从上述角度来对恐怖小说翻译作一些探讨。
二、叙述线索和叙述视角
恐怖小说基本上属于通俗小说,情节发展主要依靠叙事,为了保证阅读流畅,叙述性文字的翻译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黄国文认为,叙事的特点在于叙述中事件发生的时序就是事件实际发生的时序,并以叙事句、非叙事句结合事件实际发生时序和叙事次序讨论过叙事结构的问题[4]。实际语料中的叙述性文字可能比较复杂:一是“在许多语篇中我们都会发现描写、叙述和论说功能相混合的现象”[5],小说中的文字当然也不例外,可能既是叙述又是描写(甚至还夹杂说明或议论);二是叙事线索除了时间的推移,还有地点的变换、事件的发展、人物的活动、事物的象征意义,既可以顺叙、倒叙,还可以插叙的形式进行追叙、补叙或分叙[6]5。但是不管具体情况怎样,译者需注意把握的是,对以叙述功能为主的文字,应当在译文中以适当的形式体现出原文的叙述线索和叙述视角。这样译文才会清晰有序,达到通俗小说译文阅读流畅的目的。
原文:Thone,still weak and dizzy from the fever that had incapacitated him for continuing their journey to its end,was curiously puzzled.Falmer,he thought,had undergone an inexplicable changeduring the three days of his absence;a change that was too elusive in some of its phases to be fully defined or delimited.
仵译:索恩由于发烧,身体仍然虚弱,时时感到眩晕。发烧使他无法在他和法尔莫一起进行的这次旅行中坚持到底。他觉得困惑不解,认为法尔莫在离他而去的那三天里发生了令人费解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某些方面甚为微妙,难以捉摸,若要弄个明白、说说清楚,几乎不大可能。
姚译:三天前,索恩由于高烧,身体虚弱,头昏目眩,不能和法尔默一起把这次行程坚持到底。此刻,他心里直纳闷,实在想不通,法尔默走后那三天里,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在某些方面可以说莫名其妙,说不清,也道不明。
这是小说的第三段内容。作者为了造成悬念,第一、二段以倒叙的手法讲述法尔莫寻宝归来后的言行举止,在第三段进行补叙,通过索恩的眼睛告诉读者法尔莫某些令人费解的反常变化。对原文中的“Thone…Falmer…”仵译和姚译都把“索恩”(Thone)作为叙述主体,在选择叙述视角上比较一致。但在叙述线索的把握上,姚译似乎更好一些。这段文字是对前面的内容进行补叙,译者有必要把时间线索交代清楚。姚译通观全段落,把隐含的时间意义“三天前”译出,和下文的during the three days of his ab-sence(法尔默走后那三天里)形成对照,将补叙的内容翻译得更清楚一些。
上例不仅涉及叙述线索,还涉及叙述的视角。所谓叙述视角,即文学作品中叙说和交待人物、事件、场景时所选取的观察角度和叙述的立足点,包括作家的叙述视角(即叙事人称)和作品中的具体的叙事视角,通俗地讲,就是“谁”站在什么“位置”讲故事的问题。叙述角度不同,叙述效果也会不同。英汉语言叙述习惯不一样,原文叙述角度有时须视具体情况加以变通,使译文清晰通顺[6]3。但是,译者创作的自由是在原著基础上展开的,是有限度而非无限度的自由[7]。即使是为了通顺的目的,译者也不可以随意变换叙述视角,原文和原作者还是应当受到尊重的。例如小说的第33段和第56段的翻译:
原文:As if the effort of coherent narration had been too heavy a strain,Falmer lapsed into disconnected mumblings.The mysterious malady,whatever it was,returned upon him,and his delirious ramblings were mixed with groans of torture.But at moments he regained a flash of coherence….Falmer's features had shrunken till the outlines of every bone were visible as if beneath tightened paper.He was a mere death's head in a mask of human skin;and…
仵译:为了想把那件可怕的怪事的前前后后一一交待清楚,法尔莫似乎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对他是一桩过于沉重的负担。所以,当他讲完了这些话,法尔莫立即又陷人语无伦次的咕咕哝哝之中。他那不可思议的疾病又复发了。他时而狂言呓语,时而痛苦呻吟,时而又有一阵短暂的清醒……法尔莫的面貌已经萎缩得每一块骨头的轮廓都清晰可见了,就象在绷紧的纸下面。他的生命已结束,只留下一副人皮面罩……
姚译:法尔默原想竭尽全力要把自己的经历连贯地一一交代清楚,这对他来说似乎已力不从心。说到这里,他的话已是前言不搭后语,说出来的只是些嘟囔声了。那不可名状的怪病又发作了。你听他又在胡言呓语,又是痛苦呻吟,不过其间也有一阵短暂的时刻,说起话来还是有条有理的……法尔默的脸面已完全干瘪,只剩下几块骨头,毕露无遗,而紧紧包着骨头的皮肤薄如纸。你看他的头颅全无生命的气息,留下的只是包在外面的人皮而已……
采用第一、第三人称,甚至包括从作品中某个人物的视角出发进行叙述,一般都属于比较传统的叙述方式。第二人称叙述则比较特殊,较少使用,通常出现在文章局部,在不同的语境中所指对象也不同,有时用来代指读者,有时用来代称人或事。小说第33、56段中,作者直接使用Falmer,he,the mysterious malady,the atrocious plant等词语,以全知全能的视角,对法尔莫再次发病的症状和被这株植物吸食后干瘪的体貌分别进行了客观的叙述和描写。仵译在人称的使用、译文的口吻上都较为忠实地保留了原文的叙述视角。而姚译使用了“你听”、“你看”这样直接称呼的词语,这样的口吻使作者直接介入作品中与读者进行对话,然后充满个人感情地告诉读者这是一株“行凶作恶”的植物,改变了原文的叙述视角和情感色彩。此译虽然很有特点,但是值得商榷。因为该小说并不存在比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那样通过作者直接介入作品中拉近读者、人物和叙述者的距离,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8]。这平添了原作中没有的写作意图和叙事口吻。
三、细节描写和气氛营造
我们知道,恐怖小说之所以为恐怖小说,就是因为通过塑造恐怖意象、营造恐怖场景、设置恐怖情节等技法营造了恐怖感[9]。塑造恐怖意象、营造恐怖场景固然离不开细节描写,情节的设置和发展其实也需要细节描写的支撑。这篇小说先是以法尔莫寻宝归来的反常表现造成了悬念,随着他病情的恶化,气氛变得更加紧张,等到索恩得知法尔莫的遭遇并目睹他骇人的变化,心中更加恐惧,但当他从昏迷中醒来面对着那株已经长大开花的植物,却无法逃脱那邪恶之“美”的诱惑,最终投向死亡的怀抱。整个过程,作者都在竭力渲染恐怖的气氛,如仵从巨所言,这篇小说在叙述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细节描写上作者几乎是用工笔绘出一幅又一幅恐怖的“图画”[10],甚至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以恐怖的细节堆砌而成的。
原作的情节设置和展开是小说结构的总体安排,一般说来,译者对此不会做大的改动,除非是改译或节译,只要在翻译过程中沿着作者的思路往下走,就会造成相应的紧张气氛。然而,支撑情节发展的一幅幅“图画”是必须要落实到细节描写上的。描写一般有景物描写、人物描写,景物描写包括场面、环境、情景等描写,人物描写包括肖像、心理、行为、语言等方面的描写[6]7-11。这些细节对于小说的气氛营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必须引起译者足够的重视,才能使译文中的细节描写再现出原文的气氛。
原文:Falmer did not speak again,but satglaringbefore him as if he saw something invisible to othersbeyond the labyrinth of fire-touched boughs and lianas in which the whispering,stealthy darkness crouched.Somehow,there wasa shadowy fear in his aspect….
仵译:法尔莫没有再讲话。他坐在索恩面前,目光灼灼地望着远处。他的视线越过了火光映照下的藤萝和树枝组成的迷宫,好像看到了一些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窃窃私语着的和悄悄隐匿着的黑暗就在那儿潜伏不动。不知怎么的,法尔莫的神情看上去流露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恐惧……
姚译:法尔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着,凝神望着前方,视线似乎穿过火光映照下的迷宫似纠缠着的藤蔓和树的枝干,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某些东西。而藤蔓和树木构成的迷宫里潜伏着一片黑暗,里面传出阵阵悄声絮语。不知什么原因,法尔默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恐慌的神情……
这段文字人物描写和情景描写相结合,讲的是法尔莫从墓穴归来后令人费解的外在表现。对第一句,两种译文在空间顺序上都作了调整,使法尔莫视线由近及远。但就the labyrinth of fire-touched boughs and lianas in which the whispering,stealthy darkness crouched这一句而言,姚译“火光映照下的迷宫似纠缠着的藤蔓和树的枝干”和“潜伏着一片黑暗,里面传出阵阵悄声絮语”,较仵译“火光映照下的藤萝和树枝组成的迷宫”和“窃窃私语着的和悄悄隐匿着的黑暗就在那儿潜伏不动”,要符合中文习惯一些,效果也似乎好一点。并且,由于法尔莫得了病,不像往常那样“神采飞扬”,而是“郁郁不乐”、“忧心忡忡”,甚至“流露出一种朦朦胧胧的恐惧”,根据这种氛围,把glaring一词译为“目光灼灼地望着远处”让人觉得法尔莫身体非常健康,精力旺盛,这不大符合该人物的身心变化,值得商榷。
上个例子谈的是根据小说气氛把握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状态的翻译。由于恐怖文学重视情节,人物塑造则退居二线[11],恐怖小说中的场景描写往往比人物描写更加重要。李运兴指出,语篇的描写功能是传达外表和态貌等静态形象信息[12]。但笔者以为情况不应只限于此。描写的对象有静有动,描写的场景自然也分静态场景和动态场景。下面举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原文:…and the swaying of the great plant assumed an indescribably seductive tempo.It was like the allurement of voluptuous sirens,the deadly languor of dancing cobras…Inch by inch,with terror and fascination contending in his brain,he crept forward…till his head was against the withered hands of Falmer,from which hung and floated the questing roots…He felt the rootletsas they movedlike delving fingersthrough his hair and over his face and neck,andstarted to strike in with agonizing,needle-sharp tips.He could not stir,he could not even close his lids.In a frozen stare,he saw the gold and carmine flash of a hovering butterflyas the roots began to pierce his pupils.
仵译:……那株摇晃着的巨大植物也采取了难以言传的美妙的节奏。它好像是正在施展诱人魔法的一个个妖娆迷人的娇娃,又像是散发出致人死命的柔情的一条条扭动着舞蹈的眼镜蛇……伴随着正在心里斗争不已的恐怖和迷恋,索恩一寸一寸地向前爬去……直到他的头撞上了法尔莫的枯萎的双手,那上面悬挂着寻求新的牺牲品的根须……当那些根须像一个个抠挖着的手指穿过了他的头发,越过了他的脸和脖颈,用它那尖尖的末梢开始扎人他的体内慢慢运动起来的时候,他痛苦地感到了针尖般锐利的刺扎。他不能动弹,甚至连眼睑也闭合不上。当那些根须开始刺破他的瞳仁的时候,在凝固了的瞠目凝视中,他看到了一只盘旋着鼓翼飞翔的金色蝴蝶洋红色的闪光。
姚译:……那株硕大的植物摇晃的节奏也随之变得具有难以言传的巨大蛊惑力。它像是迷人的女妖在施展魔力,又像是起舞的眼镜蛇催人昏迷,致人死命……他的内心充满着恐怖和迷恋,在矛盾和斗争中,他向前一寸一寸爬去……他的头终于碰到法尔默干枯的手,那手上悬挂着的根须正在寻找新的牺牲品……那些根须像是手指,抠着、挖着他的头发,然后越过面部和颈项,那尖尖的末梢开始扎入他体内,折磨得他痛不欲生,就在这时候他才有所感觉。但是他动弹不得,连眼睛也无法闭上。根须已开始刺入他的瞳仁,他呆呆地望着,这时候他见到一只金黄的蝴蝶盘旋着,发出洋红色的闪光。
该例原文是在讲这植物把法尔莫吸食完之后开了一朵花,准备把索恩作为下一个进食目标,对他进行诱惑和催眠,而索恩则是既害怕又迷恋,最终还是无力逃脱厄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的动词、形容词、动名词来进行细节描写。这些词语中,动词自不待言,形容词和动名词如swaying,dancing,questing,delving等等其实也是由动词变过来的,甚至连名词allurement也是由动词allure派生来的,所以在整体上极具动感。这样的动态场景,只有使用动态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再现出恐怖而妖艳的气氛。
经过分析可知,在词语的处理上,仵译使用的偏正词组较多,如the questing roots译为“寻求新的牺牲品的根须”,delving fingers译为“抠挖着的手指”;在句式的表达上,仵译使用的静态结构较多,如“伴随着……”、“当……的时候”、“在……中”。而姚译在词语上则多用主谓结构,如“女妖在施展魔力”、“眼镜蛇催人昏迷”,句子的转换上也较为灵活。因此,综合起来看,仵译在整体上动感相对不如姚译强烈,这可能和仵从巨认为该小说是在用细节描写绘出一幅又一幅恐怖的“图画”有关。(当然,不同的人在翻译中认知有所不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姚译由于译文整体上具有更加动感的效果,使得气氛塑造得更加妖艳而恐怖,很好地达到了恐怖小说需要的阅读效果。
四、结束语
欧美恐怖小说在中国有不小的读者群。目前,关于恐怖小说已有不少文学研究,但是翻译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取材于The Seed from the Sepulchre的两篇汉译,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对恐怖小说翻译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恐怖小说是通俗小说,为了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倚重于紧张的情节、恐怖的气氛,这就离不开叙述和描写。叙述性和描写性文字翻译的成功与否,对于恐怖小说的翻译至关重要。《来自墓穴里的种子》这篇恐怖小说具有独特的《恶之花》的妖艳之美,令人恐怖却又充满诱惑。笔者对比该小说的两篇汉译文,关注其中的叙述性文字和描写性文字,分别从叙述的线索和视角、细节描写和气氛营造等方面探讨了英语恐怖小说汉译问题,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再现原文的叙述线索,使译文清晰流畅,便于阅读;尽量尊重原作,不要随意变动叙述视角;要根据小说的气氛,把握景物描写和人物心理状态描写;深入研究原文的细节描写,分清静态场景和动态场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服务于整体气氛的营造。
[1]张家恕.论恐怖小说的渊源——演化及基本叙事语法[J].中国文学研究,2007,(3):25-27;41.
[2]朱乃长.欧美恐怖故事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3]高 兴.外国名家惊恐小说36篇[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3-11.
[4]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要[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142-147.
[5]Beaugrande,Robert de,Dressler W.Introduction to Text,Linguistics[M].London:Longman,1981:184.
[6]冯国华,吴 群.英译汉别裁[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7]冯庆华.文体翻译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42.
[8]叶立刚.试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的介入[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6,(10):30.
[9]秦绍峰.恐怖小说“恐怖感”营造技法举隅[J].写作,2006,(9):40-42.
[10]仵从巨.“恐怖”中的“快感”——谈恐怖小说与《来自墓穴里的种子》[J].名作欣赏,2004,(2):63-67.
[11]张家恕.恐怖文学类型特征论[J].江苏社会科学,2004,(4):165-168.
[12]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72.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in Horrific Fiction Translation-On Two Chinese Versions ofThe Seed from the Sepulchre
XIA Yang
(Schoo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often employed by horrific fiction to create tense and grisly atmosphere,are brought into full and detailed play inThe Seed from the Sepulchre,a novella which contains many bewitching and horrific scenes.With the awareness of their importance in horrific fiction and its translation,this paper,after analyzing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tory,probes into narrative clue,narrative perspective,detail description and atmosphere creation in horrific fiction translation.
horrific fiction translation;narrative clue;narrative perspective;detail description;atmosphere creation
H315.9
A
1008-3634(2012)01-0118-05
2010-12-13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0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部省级预研项目(SK20090178)
夏 杨(1976-),男,安徽繁昌人,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郭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