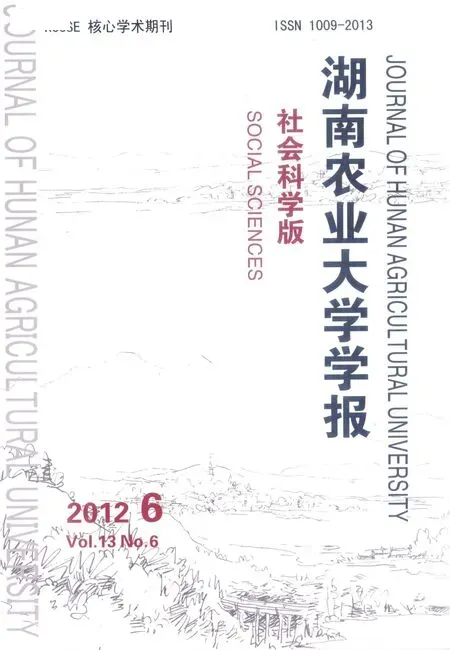兰亭之会及其对唐宋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基于东晋名士与唐宋浙东联唱诗人的比较
俞林波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传统士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受儒家礼教的熏染,一般都有着文化人的儒雅,追求一种高雅的格调。同时,他们并不以奢侈华丽、繁华热闹为审美取向,而是追求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那样平淡的闲适。另外,由于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意的文化,诗情画意无疑也成为了传统士人的审美追求。因而高雅脱俗、平淡闲适、诗情画意构成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东晋名士的参与,而江南山水的感发至关重要。江南山水之中功劳尤著者乃山阴会稽之兰亭。
会稽(今浙江绍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六江南道二越州载:“会稽县,山阴,越之前故灵文园也。秦立以为会稽山阴。汉初为都尉。隋平陈,改山阴为会稽县,皇朝因之。”[1]会稽山水秀美,由于人的加入,山水就拥有了文化底蕴。越中会稽以其非常之境吸引了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在非常之境的浸润、感发下融入其中,达到了一种人与山水相得于一时的妙境。会稽山水正是有了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的开发与游处,在东晋时才开始成为一个文化圣境和象征,深深地烙在了一代代士子文人的心中。唐王师乾《王右军祠堂碑》载王羲之除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穷游名山,遍历沧海,捐龟组,褫龙章,练金膏,屑琼蕊,浚曲水,茂兰亭,开礼贤之馆,引贞肥之客。于是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许迈辈,若非俯首谢时,即是文章冠代,何尝不攀胜慕德,夕处朝游,公自为之序,以申其志也。”[2]231
会稽山水孕育了中国士人的审美情趣,又感发他们产生了辉煌的吟咏会稽山水的诗文。会稽山水是构建吟咏会稽山水诗文的显形材料,审美情趣是构建吟咏会稽山水诗文的隐形材料,吟咏会稽山水的诗文又反过来表现着会稽山水和审美情趣。《会稽掇英总集》二十卷,北宋孔延之(1014—1074)熙宁五年(1072)编就,正是收录吟咏会稽山水诗文的诗文总集。笔者拟在研究考察《会稽掇英总集》的基础上,分析东晋名士兰亭之会与会稽山水的融合及其对唐宋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并对东晋名士和唐宋浙东联唱诗人的审美情趣进行比较。
一、东晋名士兰亭之会与山水的融合
永嘉南渡,东晋政权偏安于江南一隅,王羲之等名士畅游于会稽的秀美山水之间。所谓“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自然环境深深影响着人的气质和文化心理。江南山水逐渐改变了这群来自北方的士人,对他们审美情趣的形成有不可磨灭之功,而其中功劳尤著者乃是会稽之兰亭。兰亭的名气与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的“兰亭之会”紧密联系。王羲之《兰亭集·序》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2]43-44永和九年(353)暮春时节,东晋名贤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四十几人集于会稽兰亭,游赏山水,流觞赋诗,雅称“兰亭之会”。兰亭之会是一次文士的盛会,其唱和诗结集为《兰亭集》。此次高雅、闲适、情韵无穷的集会,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及其《兰亭集序贴》广为人知而流传久远,成为后世文人的向往和追求。
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3]物我情契、物之所表即我之衷怀,则物我融会一体。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正可以说实现了名士与山水的融合。王羲之《兰亭集·序》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王羲之指出虽然现实之中人生遭际各有不同,出处取舍亦有“万殊”,不快之事在所难免,但置身于会稽兰亭秀美山水之中确是实现了“欣于所遇”、“快然自足”的人与山水的融合。
东晋玄言诗虽不可说完全依托山水,但山水在其中有重要作用。参加兰亭之会的士人中就有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孙绰,其《兰亭诗》[2]46(《会稽掇英总集》卷三)云:
流风拂枉渚,亭云荫九皋。莺羽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
此诗由山水而玄言,将兰亭的自然山水与玄理结合在一起。《兰亭集》,王羲之有前序,孙绰有后序。孙绰《兰亭集·后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渟之则清,淆之则浊耶!故振辔于朝市,则克诎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寥落之意兴。仰瞻羲唐,邈然远矣;近咏台阁,顾探增怀。聊于暧昧之中,期乎莹拂之道。”[2]51-52诗人陶醉在兰亭的幽美山水之中,在与兰亭山水的亲昵暧昧之中,不经意间即与“道”不期而遇。这也是只有在人与山水融合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境界。兰亭山水景观的“兴意”作用,孙绰于此已交待得相当明了。此又如王序所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从王、孙二序及《兰亭诗》不难体会兰亭山水对玄言诗、谈玄意趣及审美情趣的作用。
二、东晋兰亭之会对唐宋文人的影响
唐代会稽山水也时常成为士子文人关注的对象,这些山水名胜通常作为东晋名士审美情趣的象征而被咏及。初唐王勃有一篇《修禊于云门王献之山亭序》[2]293云:“观夫天下四海,以宇宙为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为窟宅;虽朝野殊致,出处异途,莫不拥冠盖于烟霞,披薜萝于山水。况乎山阴旧地,王逸少之池亭;永兴新郊,许玄度之风月。”王勃认为,朝野出处看似殊致异途,其实归于一处:拥冠盖于烟霞,披薜萝于山水。在山阴旧地、右军池亭更容易产生这种倾向。又云:“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祓禊于献之山亭也。迟迟风景出没,媚于郊原;片片仙云远近,生于林薄。杂花争发,非止桃蹊;迟鸟乱飞,有余莺谷。王孙春草,处处皆青;仲统芳园,家家并翠。于是携旨酒,列芳筵,先祓禊于长洲,却申文于促席。良谈吐玉,长江与斜汉争流;清歌绕梁,白云将红尘并落。他乡易感,自凄恨于兹晨;羁客何情,更欢娱于此日。加以今之视昔,已非昔日之欢;后之视今,岂复今时之会?人之情也,能不悲乎?”不仅如此,王勃此序仿效兰亭之会,先写景致之幽美,再写文酒之风流,后写感慨之悲凉,亦似有与王羲之序争胜之意。
盛唐,天宝三年(744)贺知章还乡,唐玄宗倡导的送行诗一时使会稽再次成为焦点。唐玄宗作有《送贺秘监归会稽诗并序》,命预宴者皆属和。《会稽掇英总集》卷二收录其《送贺秘监归会稽应制》诗36 首。应制诗中,会稽的名胜如会稽山、四明山、镜湖多被咏及。又卢象作有《送贺秘监归会稽歌并序》以赠别,诗有云:“山阴旧宅作仙坛,湖上闲田种芝草。镜湖之水含杳冥,会稽仙洞多精灵。须乘赤鲤游沧海,当以群鹅写道经。”[2]35在此,会稽山水在承担固有审美情趣象征意义的同时,又被加入了一点神仙味道。
肃代诗坛,浙东联唱诗人对东晋名士风流的向往之情尤为强烈。天宝十四年(755)底,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大批诗人逃至江东。浙东联唱即发生在安史之乱后的大历年间。[4]《会稽掇英总集》收录浙东联唱诗人十二首唱和诗[2]197-202,其《经兰亭故池联句》、《征镜湖故事》云:
曲水邀欢处,遗芳尚宛然。名从右军出,山在古人前。芜没成尘迹,规模得大贤。湖心舟已并,村步骑仍连。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茂林无旧径,修竹起新烟。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边。院开新胜地,门占旧畬田。荒阪披兰筑,枯池带墨穿。序成应唱道,杯得每推先。空见云生岫,时闻鹤唳天。滑苔封石磴,密条碍飞泉。事感人寰变,归惭府服牵。寓时仍睹叶,叹逝更临川。野兴攀藤坐,幽情枕石眠。玩奇聊寄策,寻异稍移船。草露犹沾服,松风尚入弦。山游颇同调,今古有多篇。
将寻炼药井,更逐卖樵风。刻石秦山上,探书禹穴中。溪边寻五老,桥上觅双童。梅市西陵近,兰亭上道通。雷门惊鹤去,射的验年丰。古寺思王令,孤潭忆谢公。帆开岩上石,剑出浦间铜。兴里还寻戴,东山更向东。
浙东联唱诗人的联句诗《经兰亭故池联句》,正表达了对王羲之等人“兰亭之会”的仰慕之情。浙东联唱诗人很自然地与当年的兰亭盛会相比:“曲水邀欢处,遗芳尚宛然”,“赏是文辞会,欢同癸丑年”,“宛是崇山下,仍依古道边”,“山游颇同调,今古有多篇。”浙东联唱诗人将其“文辞会”与王羲之等人的“癸丑年”之会等同,以其“遗芳”自比。浙东联唱诗人追慕东晋名士的“文酒风流”,向往他们那种闲适儒雅而又充满情韵的生活状态。
赵宋时期对王羲之等人“兰亭之会”仍有积极追慕者。蒋堂治会稽期间,修葺兰亭旧地,并赋诗唱和。宋唐询《题曲水阁诗并序》记其事,序有曰:“即渠之南,夹植文栋,引梁横度,隐若虹起,命之曰:‘曲水阁。’缘山北向,聚流为池,至于正俗亭。又从而西,奠渠之北,考室其上,曰:‘流觞亭。’压城之隅,治茀而基,中可以望,曰:‘茂林亭。’既已事,我公帅官属集而落之。弦匏相和,曲奏未阕,举酒环视,四阿无蔽,灌木回映,鸣禽互变,层岩在石,流水相续。方其乐甚愉愉,自得缅然,盖游于世俗之外,而百虑不得奸焉。”[2]22景祐四年(1037)三月,兰亭旧地修葺完毕,蒋堂与其僚属宴于此,追想永和盛集,于是作诗美之,也是模仿东晋名士文酒风流的一场盛事。和诗二十一篇,今有佚,《会稽掇英总集》卷二收其和诗五首。诸官诗成,蒋堂又有总结,其《诸官诗成,因书二韵于后》云:“一派西园曲水声,水边终日会冠缨。几多诗笔无停缀,不似当年有罚觥。”蒋堂依然在拿自己的此次集会与东晋名士的兰亭之会相比照。
三、东晋名士与浙东联唱诗人“兰亭之会”的同中之异
唐宋文人对东晋名士风流的体会可以说深浅不一。其中对名士风流体会最深刻、最向往的当是浙东联唱诗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时代原因。东晋政权是一个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政权。经由几次北伐的失败,东晋士人渐渐接受了偏安的现实,随之也产生了与这种偏安心理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由于外部世界的不可作为,东晋士人转向了江南清秀的自然山水,追求一种宁静、闲适、高雅的生活。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当然不是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政权,而浙东联唱诗人及当时很大一批避难江东的文人却实际上成了偏安于江南一隅的一个群体。浙东联唱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这些联唱诗人为躲避战火偏安于江南一隅(越中会稽)。时代原因造成的偏安心态,与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能够相通,进而与他们产生共鸣,所以体会比较深刻。其二,地域文化的影响。浙东联唱就发生在东晋名士最活跃的会稽兰亭。浙东联唱诗人远离战火,不愿意关注战乱的社会而是沉溺于会稽兰亭明净的自然山水之中,在面对王羲之等人曾玩赏过的“兰亭”时,他们的偏安心态与兰亭的自然山水自然一拍即合。浙东联唱诗人游览的胜迹无不闪烁着东晋名士的文化印记,身临其境,物是人非,感触自油然而生。其他像初唐王勃、北宋蒋堂等对会稽山水的感悟,因不具备战乱的时代背景,即使是身临其境,体会也终隔一层。
虽然浙东联唱诗人对东晋名士风流体会最深刻、最向往,但二者又颇有区别。东晋名士的风流源于其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5]东晋人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使他们诗句中自然流淌出一种对人生、宇宙彻悟后的真性情。王羲之《兰亭序》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是一种悟透喜与悲、生与死、有限与无限等人生、宇宙哲理后达到的境界。东晋名士的体认自然、儒雅风流正是以这一彻悟作根基,因而他们对自然山水的体味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赏,“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5]
浙东联唱诗人重游兰亭旧地,触物思人,向往的正是这样一种彻悟后的充满活泼泼生机而又富含情韵的真性情。然而,浙东联唱诗人却称不上真正的风流,甚至相反。在战乱之中,他们寄人篱下,以自己微薄的诗才投地方官“爱才”的所好才换得暂时的衣食无忧,因而很难产生真正宽广的胸襟和真正自由、洒脱的行为,也就不会有真正的风流。
[1]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邹志方.会稽掇英总集点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钱钟书.谈艺录:补订重排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1:165.
[4]俞林波.大历年浙东联唱集考论[J].东南大学学报,2008(2):82-86.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7.
———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