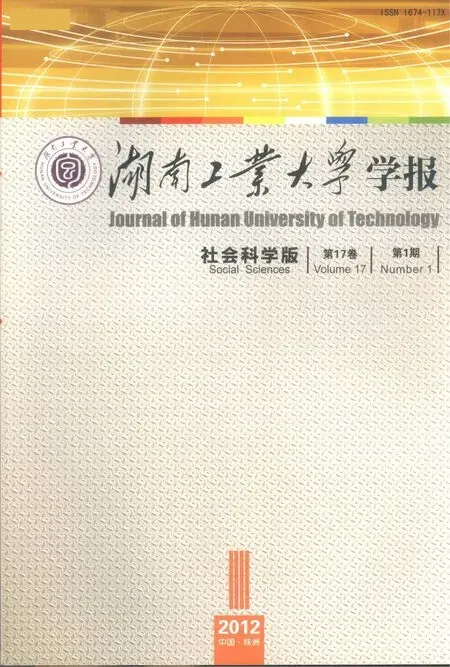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412007)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湘报》;晚清;外交观念
在古代相对封闭的东亚区域环境中,中国拥有无可匹敌的物质力量和强势的儒家文化,自视为文明中心,极重夷夏之防。历代推衍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对异邦的宗藩观念,使中国与其周边国家建立起宗藩关系,这种宗藩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封贡制度,成为中国处理对外交往的基本制度。至晚清以前,中央朝廷一直没有设外交衙门,因为中国从来就不在外交的级别上承认其他国家,而只是在藩务和商务的基础上对待他国。藩务由礼部执掌,因为它们本质上反映一种礼仪关系,体现出天朝上国“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外交观念。这种缺少世界意识的自我中心论外交观及由此而来的外交制度,到了近代强权外交时期,现代外交登场,就显得自我蔽锢,反应迟缓,远不能应付时代的挑战。
思想总是伴随着问题而产生的,它的活力在于能否应对现实的挑战。面对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挑战,“故夫通商传教,觅地殖民,以神其争之术;覃精格致,迸力船械,以券其争之具;沟通君民,机宜和战,固结党会,磨砺任侠,以策其争之群。争一也,而争之途万,争之学万。万其途,一其心;万其学,一其旨。故能以争权者争种,争种者争国,争国者争天。”[1]时人基于现实的国际形势,已领悟到时局的嬗变,而设法寻求新的外交方略。“在此酝酿过程中,一部分就固有学说中找根据,进一步加上现代的诠释和命义,一部分则纯由西方外交规制中采摭新的理论,直接向国人介绍。”[2]至晚清时期,中国的外交观念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晚清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湘报》,来透视、梳理其中的变化轨迹。
一 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在华传教活动往往与其殖民主义战争密切相关,国人对传教士在境内传教极为反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法、俄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传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虽明文载入条约,受到中国政府保护,但因对西方文化的隔膜与殖民压迫的愤恨,屡造教案,列强往往以此为由,发动侵略战争,令中国政府陷入外交困局。1897年,德国借口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而湖南亦在地方士绅周汉的带领下,到处散发揭帖、传单,号召人们反教、抗教,“而于外国之人,素不习见,故常有聚观喧嚷,甚至有肆口骂詈,抛掷瓦石之事”,引发外交纠纷。[3]认为列强“见中国一意讲和,无词可执,意在挑衅,藉为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4]给中国带来割地赔款,乃至亡国灭种之危险。湘报意识到,中国惟有遵守条约,求得和平,才能赢来生机。“今日时局而论,莫如保护外教,免生衅端,昌明己教,以保族类,波兰之灭,令人寒心,其所以首在保护外教,欲延中国岁月,四万万众庶几日开其智,或者免其分割,亦未可知。”[5]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政府,一方面对周汉等人进行劝诫、训斥乃至关押;另一方面,借助《湘报》等大众传媒,传播新的对外观念。这样,中国采取何种外交观念以应对西方,成为《湘报》反复讨论、辨析的基本主题。
1.西方通商、传教于我有益无害。就通商言,《湘报》认为“相与通商,固天理之自然,古今之公义”,极言与西方通商之利:“天假手于西国,以通商而成,此万国交通之盛,是不啻为四万万人增广其生业也。”[6]自传教言,谭嗣同认为时人动辄诋毁西人无伦常的观点是错误的:“夫无伦常,安得有国使无伦常,而犹能至今日之治平强盛,则治国者又何必要伦常乎?”[7]易鼐认为,耶稣之道,“遇事有以自主,随时有以自兴”,故欧美皆成强国。中国之孔教,当“改革其差缪,弥补其缺憾”,如此孔教方能大行于天下,此为“通教以绵教”的强国之法。[8]皮锡瑞总此二端,言传教与通商对中国有益无害:“今与西人交涉,为通商传教两事,我能讲求商务,开通利源,彼即通商,不能夺我中国之利;我能讲明义理,尊信孔教,彼即传教,不能惑我中国之人。”[4]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蕞尔岛国,于甲午一战而成亚洲强国,极为中国士绅所欣羡,其开放外交政策亦成为学习的对象。“日本自伊藤侯明于公法,愿与西人通商传教之利权,列入公法之国,故如英美诸国都认为友邦,于是日本骎骎列为头等之国。”[9]
2.与西人交涉,当守公法。通商、传教既与我有益无害,中国则当放弃自我中心观念,持开放的外交政策,打开国门,与西方交涉。交涉之中,难免有纷争,当谨守国际法则与惯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公理绳之。两人相争,不得谓己是,人尽不是;两国相争,不得谓中国是,外国尽不是。中国人憾中国为外夷欺侮,外夷憾中国人无信义,反谓中国欺侮。”[4]因此,惟有遵守国际法,方能维持和平。“公法者,世界上人数相维相系之大经大法,亦即前后古人心中相亲相爱之公性情。”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西人将此家规、国法充而大之,成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基本框架:“由此国推及彼国,由一方推及全球。孔之所谓大同,耶之所谓天国,皆赖此为之起点也。”[9]
遵守国际法,以积极的态度去了解对手,并自觉运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和准则,才能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易鼐认为,中国若加入万国公会,谨遵国际公法,“各国之要求我而无厌者,可据公法以拒之;我之要求各国而不允者,可据公法以争之;向之受欺于各国,损我利权者,并可据公法以易之。”[8]公法成为维护中国权益的有力工具。
唐才常从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人讲求国际公法,遵守和约,“将以收自主之权,振尸居之气,上体素王改制、悲悯救世之苦衷,下规日本锐意更约、顶踵不辞之热力,则生死肉骨,未必不基于此。”国际公法遂成为“由小康至大同之法界”、“由有争至无争之公理”、“平万国权力者之根原”,是中国抗衡列强,保国保种保教之至法。[1]
3.守信、和戎是中国文化之传统。“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和’哲学对封建王朝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以‘崇和’为基本理念的外交思想,体现了儒家‘和’哲学在其中的核心价值地位。”[10]当此观念鼎革之际,《湘报》同人为使新的观念便于传播与接受,对传统进行深度挖掘,为新的外交观念寻找历史依据,指出孔子之《春秋》,即体现了现在国际公法的基本原则。“吾谓春秋为公法之时也,自汉以来,诸儒略讲明春秋大义,而未阐及微言,故未能尽服泰西各国之心。今太平之事业已萌芽,将来环球钦佩我春秋之公法,事在意中。”故“春秋公法律例高明于泰西公法律例”。[11]唐才常亦认为公法出于《春秋》,“要其微言宏旨,如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以礼义判夷夏,以天统君,以元统天,与远近大小若一诸大端,则所以纳万世于大同之准的,与天地相终始。彼西国布衣有能不戾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公理,而世界日进文明之朕兆。”[1]国人遵守约法不但没有向帝国主义投降,损害天朝权威,反而是继承、发扬了儒家文化之真精神。皮锡瑞说:“‘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又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是圣人待夷狄蛮貊亦必用恭敬忠信,若少见多怪,忽睹见异言异服,即加侮辱,甚至殴詈,与圣人之言恭敬忠信大背,岂义理文明之国所为。”[4]国人如果不守信遵约,违反了孔教传统,就会被西方列强视为半开化之国、野蛮之国,受到侮辱和欺凌。
4.遵约和夷的前提是要了解外情,熟悉公法,培养人才。外交人才专门化是近代外交的重要内容,对此,《湘报》撰文对传统科举体制进行了激烈批评,呼吁改革教育内容和考试制度,培养熟悉公法,了解西方情况的外交人才,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当时主管湖南教育的徐仁铸极力推动改革,“值此时事多艰,交涉日棘,亟需通权达变、折冲御武之才,”[12]地方士绅亦热心参与,《湘报》则发布政府公文,刊载学校章程,极力呼吁。如刊载的《沅州府知府连培基扩修沅水校经堂禀稿》中指出,以国际公法入掌故之学,虽以本国律例为主,但宜兼知各国条约,方能在外交中折冲樽俎,维护本国利益;学习西方地理、语言尤为急务,“大地九万里,环球五大洲,疆域沿革,山川险要,物产土宜”,非专门学习无以成其才。语言则如译学,“既关交涉,尤为通知四国之故所造端。”[12]皮锡瑞指出:“今时事日棘,学者宜考求中外形势、风俗、政事,通晓各国文字语言与公法交涉之学,此在圣门为言语科,不得以为西学而斥之也”。[13]毕永年、唐才常等,为改变时人“以万国公法为机钤诡谲、设阱陷兽、张网罗鸿之秘策”的成见,召集同道,建立公法学会,专讲公法之学,研究约章公法、关税和外交掌故,“期于古今中外政法之蕃变,和战之机宜,条例约章之殽列,与中国所以不齿公法之故,一一讲明而切究之”,以期改变人们的外交观念,培养外交人才。[1]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4]“守约和夷”与传统“和戎”外交观的最大区别,一是放弃了“天下中心观”,树立了平等观念,意识到中外关系不再是宗藩模式下的尊卑关系,中国必须按照以近代主权国家为中心的近代外交体制来处理对外关系。守约也不再是传统的羁縻怀柔政策,而是国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二是否认了传统的剿抚兼用、恩威并施的手法,确认外交以和平为目的。[15]平等被视之为对外交往之公理,“天之义,从公;地之质,从通;人之性,从同。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州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16]皮锡瑞为使人们明白此理,特编《醒世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道:“若把地图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西洋英俄德法美,欧洲各国争雄强。纵然种族有不同,何必骂他是鬼子。况且东洋日本人,同居亚东势更亲。相貌与我无异处,若说为鬼犹不伦。佛法书中说平等,人人不必分流品。又有墨子说兼爱,利人竟不妨摩顶。圣贤一视本同仁,不论秦楚吴越人。”[17]只有把自己视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才会切实地履行条约责任,得到真正的和平。
二 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民族危机日深。“图绘瓜分,瀛寰大震”,面临此种形势,《湘报》同人认为,中国国力弱小,在确认守法和夷的睦邻外交政策的同时,必须在了解中外大势的基础上,与外国结盟,以抗衡列强之侵略,避免如波斯、波兰等亡国之覆辙。因此,中国之外交,当慎择友邦,以维持国际均势。
《湘报》从当时国际形势出发,认为沙俄与中国有广袤的边界线,在中国之势力日益扩张,构成严重的威胁,是中国最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沙俄对波兰的三次领土瓜分,更是令国人持高度戒备之心理。“夫俄之为国,非他国比也,其灭波兰也,极残酷,或问其何以如是,俄人曰,惟杀得多则服得久,可见俄之历代政策如此,若以此道施之中国,中国其无噍类矣。”故“今日之势,日可以忍,德又可以忍,惟俄不可忍。”[18]而英国之侵略中国,主要是为了求得商业利益,没有领土野心,故“商战之祸,孰如兵战之祸”,“印度之惨,孰如波兰之惨”;[19]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其时已成为中国维新运动的效法典范,且甲午之后,日本为了抗衡沙俄在东北之影响,主张与中国修好,对维新派亦较为友善,希望维新成功后能建立一个亲日政府。因此,联英日以抗沙俄成为《湘报》同人一致的对外政策。“联英日为今日延国之上策,明知联英不无流弊,而择祸莫如轻,与其为波兰之屠割,不如为印度之钳制也。”[20]唐才常特撰文《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力主与英日联盟以抗俄,“今日人既愿联盟我,且愿密联中英相犄角,且愿性命死生相扶持,千载一遇,何幸如之,何快如之!”[19]在《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中,唐才常再申此义:“夫两利相形取其重,两害相形取其轻。联俄则眉睫火燃,即见危亡于旦夕;联日以联英,则皮肤癣害,犹可疗救于将来。孰重孰轻,孰生孰死,不待烦言决矣。”[21]要求朝廷制订联英日以抗俄的方针以指导中国的外交事务,以免除各国引发战争,避免中国被瓜分的趋势。
中国作为弱国,试图忘却与英日之间的民族仇恨与传统上的天朝上国之虚荣,希望借助与强国的结盟来维持国际均势,以缓和紧张局面,避免惨遭瓜分的厄运。前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具有很大随意性,而《湘报》所提出的“联夷抗夷”的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慎择邦交,具有了很强的指向性与明确性,显示了中国对外交往中主权观念的觉醒。但均势主义为国际强权政治的产物,在维持此均势中,弱小国家势必受到更多的限制和牺牲。纵然列强之间有矛盾的一面,但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更多的是利益相关与相互勾结。均势平衡的和平局面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缺少实力支撑的“联夷抗夷”策略,面对列强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与军事侵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实无多少有力的手段与斡旋的余地,最终的结果不但不能“抗夷”、“制夷”,而是被“夷”所“制”。
三 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
《湘报》强调要“守法和夷”、“联夷制夷”,但这种和平外交并非消极妥协。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自古中国之于外国,不讳言和,惟不可专于求和,不求自强”,[4]西方列强的炮舰外交使国人完全服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丛林法则,封闭保守的“天朝”观念不能抵挡殖民者的蜂拥而入。在《湘报》对国际局势的讨论分析中,土耳其、印度、暹罗、安南、缅甸等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历史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警醒中国应努力向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睦仁天皇学习,变法自强,增强国力,唯此中国方能在世界“丛林”中体面地生存下去,而不至成为强者的“猎物”。“南洋之矮奴,非美洲之红黑番,其种甚贱,沦为奴隶,固无论矣。曰波斯,曰印度,曰埃及,悉亚当之裔族,恳辟与中国等,国不可谓不旧,种不可谓不贵,而受役无异黑奴着,诚可为之寒心也。是国无论旧新,强则旧而新;种无论贵贱,强则贱而贵。”[8]中国的和戎外交是与变法自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衣裳局变,而兵战起焉;兵车局变,而舌战起焉。今中外联属之局一变矣,海族勃兴,学群战起。大势五千年,大地九万里,群与群战,人与天战,公私交战,人物交战。”[22]497实力成为国家生存与对外交往的基础。中国通过变法自强可以取得强大的国力,而强大国力则是外交的坚实后盾。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湘报》的“守法和夷”也获得了新的意义:中国只有采取“守法和夷”的外交政策,方能为中国的自强变法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皮锡瑞将之视为“字小事大”的外交政策。“惟仁者能以大字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所谓字小事大,并非一意求和,其中作用,先求自固,再求自强”。皮氏检点历史,春秋时的息国,逆天而行,不自量力地挑战强国,最终导致亡国。反之,“汤事葛而后卒伐葛,文王事昆夷,而后駾昆夷,勾践事吴而终灭吴,太王事獯鬻其后文王亦服獯鬻,是孟子所说仁者智者,非但仁智而已,皆有大勇在内”;“今德国威廉第三,亦得此意。”在遭法国灭国之后,能忍辱负重,在毕士麻克(即俾斯麦)和毛奇的辅佐下,终成欧洲强国。[4]这些历史案例为湘报同人的守法和夷外交策略提供了强大的合理性论证,中国当以此为效法典范,改革图强,增强国力,赢得最终胜利。简言之,通过维新变法以增强国力是《湘报》的基本主题。
1.国家硬实力——“商战”。中国当效法西方,振兴实业,广泛采纳现代科学技术,开办铁路、轮船、采矿等现代工业,建立现代国防。“商者,国家之元气,课税所从出,百姓之筦库,日用所取资”,故“西人以通商为富强之本务”,“商战足以兴邦,今泰西以商立国,越重洋数万里,冒风涛不测之险,争利蛟龙之窟,国势蒸蒸,纵横海上。”中国富强之道,要多开通商口岸,广辟利源,与西方进行商贸活动:“虽然有缓急二办法,在急办则广公司也,兴制造也,人之所共知也;缓办则设商务学堂也,开商务会也,讲均利均势之法,求赴机应变之方。”[23]因此,通商是中国自强的重要内容:通商“在我能自强,无为人弱而已。自强则通商利,不通商反不利;不自强则不通商害,通商亦害。”[6]这种增强国家实力以在对外交往中谋求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观念,反映《湘报》同人“逐步抛弃‘华尊夷卑’的传统观念,开始向西方学习,力图通过兴办洋务、发展本国经济同西方展开国力层面上的竞争,”[24]意识到了国家实力才是外交的真正基础。
2.国家软实力——“学战”。在增强国家实力以与西方进行竞争的过程中,《湘报》认为“大凡有学问之人必能制伏无学问之人,而无学问之人自然不能不受制于有学问之人,此世界之公理也。”[7]意识到了文化是国家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必须提高本国文化的竞争力,以与西方进行“学战”,以“昌明吾种教,固结吾民心,而成真豪杰之国”。“至夫学,至夫战,至夫会,不予以戈矛,不授以甲胄,不务壮士之所行,不聒舞蹈之所习,津津欣欣,张口鼓舌;坚坚冰冰,致敬尽礼。曰志在新学、强学焉尔;曰善战于不战,善不战于战焉尔;曰其所恃,惟在博通西学者,往往揭出兵战商战不如学战之旨,而所为勤勤恳恳,尸我种教之自存于群与群战、人与天战、公私交战、人物交战焉尔。”[22]国家实力的竞争,归结到最后是文化的竞争,只有文化昌明之国家与民族,才能立足于世界,与列强一争短长。而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湘报》所主张的自强之道,是固守中国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自开辟以来,地球之上,惟孔子之教至为广大中正,此外各国皆有偏驳不纯之处”;[25]孔教不亡,中国当有以弱变强之机。在此基础上,“通教以绵教”,借鉴、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以造成新的文化形态,树立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才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经过与西方列强50余年的战争,国人领略了西方炮舰的威力,也深刻意识到了中国为了在未来世界中体面而有尊严地生存下去,必须改变既往的外交观念,寻求一条与各国和平竞争的道路。这虽然艰难,但毕竟已经起步。“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的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26]简言之,弭兵主义才是外交的正确宗旨,而“和戎”则是中国历史传之久远的外交原则。《湘报》所坚持的“守约和夷”、“联夷抗夷”与“自强制夷”的外交观念,既有西方外交思想的灌入,更有古老传统思想的继承。现代外交思想被纳入到传统儒学的框架中进行表达,是传统外交观念向现代外交观念转变的有机环节。他们看到了大众传媒的作用,借助《湘报》这个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试图以此来影响政府和社会。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现代邦交思想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唐才常.公法学会叙[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43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2]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9.
[3]补抚院告示[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0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36.
[4]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五次讲义[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5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5]南学会问答[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9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308.
[6]彭名寿.中外通商利害论[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44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7]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五次讲义[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20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8]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20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9]南学会问答[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22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邹丽娟.从儒家“和”哲学看晚清的“和戎”外交策略[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5).
[11]南学会问答[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4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69.
[12]沅州知府连培基扩修沅水校经堂禀稿[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14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皮鹿门学长南学会第七次讲义[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7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91.
[14]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郑天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87.
[15]刘馨.试论晚清时期外交思潮的演变[J].外交学院学报,2004(3).
[16]樊锥.发锢[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8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98.
[17]皮锡瑞.醒世歌[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27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11-212.
[18]南学会问答[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2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53.
[19]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23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20]南学会问答[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3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60.
[21]唐才常.恭拟密筹大计吁恳代奏折[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1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41.
[22]黄蕚.学战会叙[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58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涂儒翯.商务平论[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13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97.
[24]李慧芹.浅析晚清主流外交思想的演变》[J].宜宾学院学报,2006(7).
[25]陈中丞南学会第七次讲义[G]//《湘报》馆.湘报:上卷第31号.北京:中华书局,2006:242.
[26]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M].杨立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3.
Analysis on Changing the Diplomacy Conception in Late Qing Period from the“Hunan Daily”
YANG Hai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412007,China)
In view of weak circumstances of modern Chinese an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self-improvement”,“military harmony”,Xiangbao Daily absorbed the western modern diplomatic concept.It proposed the equal diplomatic thoughts of“abiding by contracts in order to keep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barbarians”,the balanced diplomatic thoughts of“allying barbarians to beating back barbarians”,the powerful diplomatic thoughts of“improving ourselves to control barbarians”.Tak Xiangbao Daily for the communication platform,these thoughts were spreaded to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These diplomatic thoughts have played an enlightening and promoting role for inspiring the public wisdom and eventually forming Chinese modern diplomatic concept.
Xiangbao Daily;late Qing;diplomatic conception
K252;D829.1
A
1674-117X(2012)01-0141-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26
2011-09-11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湘报》研究”(09C343);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湘报》与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早期进展”(09YBB12)
阳海洪(1969-),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新闻史论与媒介批评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