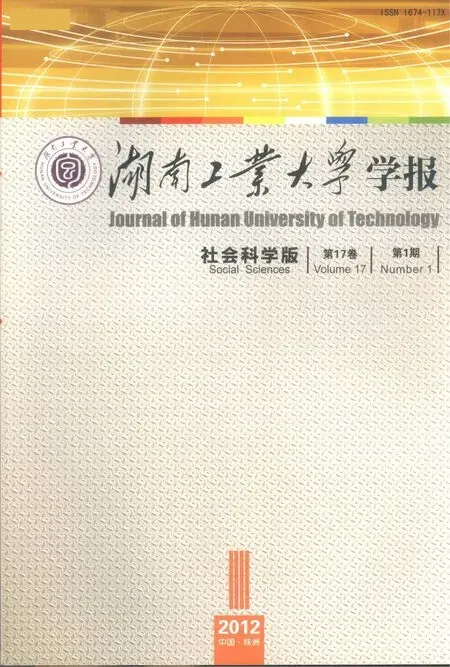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龙其林
(广州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006)
转型期文化的探索与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和特质*
龙其林
(广州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006)
吴定宇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他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以及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百年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吴定宇倡导文化整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对文学现象中的独立、自由精神进行追溯,为当代学术研究注入了思想活力和自由意识。
吴定宇;学术研究;文化整合;学人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状态逐渐地被打破,绵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一次新的冲击和整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料,并进而进行扬弃、整合是中国文化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这就规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整合的性质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任务是通过中外文化的整合,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1]这是中国文化所面临的际遇和挑战,亦是中国学人必须承载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毫无疑问,在当代中国社会走入新时期之后,这种使命和责任首先是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三代学者来肩负的,吴定宇先生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吴定宇先生的研究涉及现代文学与文化的诸多领域,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建树则集中体现在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探索、郭沫若研究、陈寅恪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的梳理等方面。吴定宇先生对中国转型期文化与文学的宏观把握和独特判断及对于文化整合方式的梳理,奠定了他在该领域的学术重镇地位;与此相关,他提出的“转型期中国文学”的概念弥补了“现代文学”、“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诸多概念存在的缺陷,为百余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切入点;而吴定宇先生在巴金研究、郭沫若研究等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视野的开阔、文化整合的观念,促进了这些研究的进步和发展。除此之外,吴定宇先生还以陈寅恪研究闻名学界,其对史学大师的研究不仅很好地体现了他关于文化整合与转型的设想,而且通过他对独立、自由的学人精神的追述,为当代学人的学术研究注入思想的活力和自由的意识。同时,他对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日渐模糊的史实的爬梳和发掘,厘清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盲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定宇,1944年3月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1963年至1967年就读于重庆四川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垫江县从事教学工作。1979年至1982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其导师为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著名学者吴宏聪教授。1982年,吴定宇先生获中山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历任中文系副主任、教务处副处长、《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山大学编辑学与出版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的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理事、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会长等。
吴定宇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正好是中国拨乱反正之后的最初几年,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重点在于清理极左路线造成的认识偏差。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文学历史真相的探究,努力还原现代文学史的真实面目,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张闻天的文学活动散论》《<狂人日记>是浪漫主义作品吗?》《论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论鲁迅和胡适》《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重读巴金<憩园>》等十余篇论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引起较大反响。留校任教之后,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他积极汲取此时文化知识界涌动的思想养料,探究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吴定宇先生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现代文学史料的勾稽和补充,一是对于现代著名作家的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
在现代文学史料的勾稽方面,他相继撰写了《抗战期间香港关于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言——读<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等文章,对于抗战期间一些散佚的文学史料进行了挖掘。《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宣言——读<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从1941年7月7日香港《华商报》文艺副刊《灯塔》中发掘出郭沫若、许地山、巴金、胡风、茅盾、夏衍、许广平等7位中国作家联名给肖伯纳、罗曼·罗兰、海明威、U·辛克莱等30多位欧美文化界人士写了一封信的史实。虽然这封信曾在当时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各个报刊上发表过,但只有香港《华商报》的编者把这封信的英文稿译成中文,所以熟悉这一文稿的人并不太多。加之战争影响和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界的控制,《华商报》在国内少有人见到,此信遂鲜为人知。吴定宇先生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这份抗战文艺运动期间的珍贵文献,这不仅对于研究7位作家在抗战中的思想与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完善人们对于香港文化界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一份颇具分量的史料。
在现代作家的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方面吴定宇先生亦用力颇勤,《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巴金的家庭题材小说探胜》《论胡适何时投向敌对营垒》等影响颇大的论文即发表于这一时期。在《巴金与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中,吴定宇先生系统地考察了巴金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渊源、影响以及他如何扬弃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复杂历程,勾勒出巴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抉择和思想脉络。在分析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对于巴金思想的影响时,吴先生这样论述:“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无疑滋长了巴金反专制的精神。但是巴金分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封建专制在本质上的区别,他说,这二者‘名称虽不同,实质却无差别’。巴金援引柏克曼《俄罗斯的悲剧》中的材料,抨击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布党专政下的俄罗斯已成了屠杀革命党的刑场,执政的共产党便是行刑的刽子手。’在另一篇文章中,巴金进而指出,无产阶级占人类的大多数,‘要用大多数人专政来压制少数人是做不到的’,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做不到的’。他天真地认为,有产阶级利用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利用政权来压迫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原来的有产阶级一变而为无产阶级,……这样反复循环下去,阶级斗争定会没有停止的时候’。由此推断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压制无产阶级的工具’、‘不能消灭阶级’、‘不能消灭国家’的错误结论。”[2]这段分析鞭辟入里,如今读来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效果。这篇文章旁征博引,细致分析,将巴金“由一个否定一切国家、政府、政党、军队、法律和专政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成为了共产党的战友和新中国的热情歌手”的历程生动地揭示出来,[2]从而再现了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为寻找社会解放的真理所历经的艰苦、曲折的思想道路及其浓郁的悲壮精神。此外,《论胡适何时投向敌对营垒》《先驱与跋涉者——论鲁迅与巴金》等文章中吴先生分别对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进行了分析,探究了他们的人生道路、思想嬗变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深化了学术界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
如果说这一时期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对于现代文学史的重新认识与资料的发掘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之后,他的研究则由微观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料的勾稽转向于转型时期中国文化与文学整合的宏大领域,并以其作为第三代学人所具有的敏锐眼光、严谨理性,做出了许多令人激赏的研究。1989年,吴定宇先生发表了《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从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比较性地研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对源自中西文化语境的忏悔意识和内省意识进行了对照分析,既指出了两者在文化背景和表现方式上的差异,又对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式忏悔意识进行了深入分析。吴定宇先生分析了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内省意识之间的文化落差,指出西方忏悔意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一种宗教观念,而中国的内省意识则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念,这种文化落差在中西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吴定宇先生看来,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突破了中国传统内省意识固有的框架,但并未机械地硬套西方忏悔意识的模式,而是吸取二者的长处,显示出中国式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作家显然是把忏悔意识当作人类的美德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热力而移植过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带有功利性,却几乎没有西方忏悔意识那种基督教文化的宗教色彩”;同时由于中国现代作家生活在充满优患的时代,“他们在进行反省时,忧患意识也往往掺兑在忏悔意识之中,所以,他们的忏悔录也带着浓厚的优患色彩。这种忧患色彩在西方文学家的《忏悔录》中,是不多见的。”[3]不仅如此,吴定宇先生还对现代文学史上的中国式忏悔意识的类型进行了概括,从而揭示出其中与西方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鲁迅和郁达夫的忏悔小说,代表了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两种忏悔模式。鲁迅通过对艺木形象的精心镂刻,从艺术形象身上体现出作者的忏悔意识。郁达夫却是直抒胸臆,通篇展现出作者的忏悔过程,流溢着率真的忏悔情感。这两种忏悔模式经过后来的巴金、倪贻德等现代作家的继承和发展,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叙事文学的忏悔特色。”[3]不难看出,经过对于现代作家的全面认识以及文学史料的勾稽,吴定宇先生关于转型时期文化与文学整合的思想逐渐建构起来。
在《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吴定宇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整合的四个时期,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他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一直在进行着整合:“所谓文化整合,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交流时,所经历的一个协调、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文化会对弱势文化进行选择、适应、调整、吸收、创新,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最终使弱势文化成为强势文化的一部分。”[1]在此基础上,吴定宇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文化整合:第一次肇始于春秋,基本完成于西汉;第二次起于魏晋,经南北朝而止于初唐;第三次发端于北宋,完成于明;第四次则始于鸦片战争,经近现代而至于现在,并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文化整合的视野出发,人们可以很容易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整合的必然性,“这就规定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整合的性质也是从传统到现代,任务是通过中外文化的整合,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现代文化。”[1]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整合与历史上的文化整合的差异,吴定宇先生作了如下描述:“这次文化整合由于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去兼容统摄西方现代文化,居于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固有的特质也因落后和不合时宜而会被淘汰,习以惯常的传统价值观念被撞碎,某些千百年‘从来如此的’规矩和风俗遭到破坏,旧有的文化习惯被打破,民族自尊受到损害,注定了整合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非常艰难,甚至是非常痛苦的历程。”[1]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对于中西文化以何为主体的争论不绝于耳,中体中用、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儒学复兴等概念均有着明显的局限。为此,吴定宇先生明确指出:“我们不可能停留在过去对‘体’‘用’的理解和研究水平上。既然现代化的文化整合在中国文化土壤中进行,就应当以中华民族及其优秀民族精神为体,传统的与外来的文化为用,在新的基点上整合形成一种既是世界性的、又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1]吴定宇先生从文化整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外文化相互撞击、选择和融合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及转型期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于吴定宇先生而言,作家作品专论、史料发掘与转型期文化整合的研究是相互依存的、由具体而抽象的关系。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他撰写了许多作品分析,通过微观的深入探究和个案分析的方式,考察了单个作家作品的文化价值,丰富了他对于文化整合具体形态的感知,也使其对于现代文学史有了新的认识。像《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光——论巴金<家>的文化价值》《论女神的文化价值——兼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中西文化交融的最初硕果——<女神>与<尝试集>文化价值比较》等论文,就代表了吴定宇先生此类研究的特色。《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相撞击的火光——论巴金<家>的文化价值》从人类文化学的方位审视巴金小说《家》中人物心理,充满了文化探究的创新精神。该文从新旧时代转型期的异质环境与小说人物文化心理的嬗变着手,分析了五四时期中外文化碰撞的文化背景对于作品形象塑造的影响。文章认为小说中家族悲剧的根源,在于家族宗法制的钳制和封建文化在心理上的积淀,这种病态文化心理造成了青年一代的畸形、羸弱性格。而作家论则体现了吴定宇先生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价值的追求,他基于中外文学发展历史的了解形成了以文化立场解读文学的研究方法。吴定宇先生在文化的视角中分析、评论作家作品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观念和研究风格,《巴金创作的文化意义》《巴金与宗教》《论郭沫若与巴金》《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与文化研究》等文章即属于此类。其中《巴金与宗教》一文从宗教角度敏锐地捕捉了巴金思想的微妙变化及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了吴定宇先生学术研究的严肃与锐利品格。在他看来,虽然巴金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也一贯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但是他又赞成和接受部分基督教教义,因而对于宗教呈现矛盾而复杂的文化心理。吴定宇先生认为:“考察巴金的文化心理,不难看到,他在人生征途的跋涉中曾遇到许多艰难险阻。这种种复杂的经历,激发了巴金文化心理深层的‘宗教感情’。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也在他心中涌起一种为信仰而奋斗的神圣感和庄严感。所以,尽管巴金不是宗教信徒,但在这种‘宗教感情’的驱动下,对基督教某些教义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显示出他的宗教文化心理的另一面”。[4]这种创见确是发人所未见。在论及巴金作品中的原罪意识时,吴定宇先生指出:“巴金在向人民赎罪的同时,也对内心进行自我审察,从而萌生出忏悔意识。巴金的忏悔,不是向基督教的上帝忏海,而是向他自己的上帝——人类进行忏悔。因此,直到耄耋老年,他在写作中都一直坚持‘把心交给读者’。”[4]不难发现,吴定宇先生是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考察现代作家的创作活动与作品的,他彻底摆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浅层次的直觉批评,而是把握住了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内在品质,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着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命运及价值。这种具体作家、作品文化价值的探究,可谓视为吴定宇先生文化整合研究的有益积累和补充,为他的宏观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台湾业强出版社同期推出了吴定宇先生的学术评传《学人魂——陈寅恪传》。作为国内第一部由学术界专家撰写的陈寅恪传记,《学人魂》立足于文化整合的理论,通过对历史现场的还原和文献资料的爬梳,为读者重新展现了陈寅恪这位史学大师的学术风采和人格魅力。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不仅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文艺、文化、音乐出版社十大优秀图书,而且还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评价。该书凭借宽广的学术视野、文化整合的理论维度和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叩问,再现了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不安与文化氛围的变迁的氛围中,如何坚守文化的信念与学术的精神,勾勒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与命运浮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学人魂》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分析,勾稽史料,还原历史现场,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陈寅恪的某种似是而非的印象。过去人们通常认为陈寅恪是最反对政治干涉学术的,因而认为他只倡导精神之自由、人格之独立,对于政治毫无感兴趣,这是与历史不符的。对于陈寅恪于1931年春进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学习的原因,该著认为“他之所以挑选这所学校学习社会经济,恐怕与他读过《资本论》之后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不无关系”,[5]34-35从而纠正了人们关于陈寅恪不问政治、厌恶政治的错误认识。事实上,陈寅恪对于政治并非没有追求:“应当看到,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思想濡染的陈寅恪,一直服膺儒家的伦理纲常,儒家的‘内圣外王’的人格设计、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影响了他的文化心理深层,成为他处世行事的准则。他不是没有萌发过治国平天下的志向”,[5]57只是由于时代、机遇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使陈寅恪将学术研究作为了自己的终身事业。吴定宇先生将该书命名为“学人魂”是有其深意的。此魂不惟指读书人的品性、追求、学问,更指其学术灵魂得以形成且贯穿人生的成因、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陈寅恪学人魂的形成,既是他沉浸于传统文化、为其所化的结果,又是他超脱于外,以理性精神对其进行批判扬弃的产物。无须讳言,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使得中国文化缺少一种独立的、自由的终极关怀,而陈寅恪的学人精神显然具有弥补传统文化缺陷的重要作用。正如著名学者、当代学术大师杨义先生所评价的,该著“紧扣‘学人魂’的命题之处,是它在探寻传主人生踪迹之际,分阶段地、相当系统地剖析其学术渊源、治学动因和形成学术体系的关键所在,这就把‘学’与‘人’融为一体,而以一个‘魂’字点醒其精神特征了”。[6]
在完成了对于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究之后,吴定宇先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现代文学史上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郭沫若。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便开始了对于郭沫若的研究,相继撰写了《论<女神>与<尝试集>的历史地位》《论女神的文化价值——兼论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心态》等文章。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新世纪初,吴定宇先生对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陆续撰写和发表了十余篇研究郭沫若的文章,内容涉及中西文学、乡土文化、历史研究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成果被收录入《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一书中。他从郭沫若与中外文化的关系着手,系统地阐释了宗教伦理文化、乡土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墨家文化以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对于作家创作的不同影响,以郭沫若为个案,分析了中西文化整合在其思想与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吴定宇先生将郭沫若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置于中外文化整合的视野中进行思考,从作家面对不同文化时的吸收、转化、冲突、变异的细微思想入手,揭示了中西文化整合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冲突、调整、平衡、吸收、代换及创新过程。不难发现,吴定宇先生对于文化与文学整合的研究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作家作品研究是增进了他对于现代文学史的认识,并从微观方面积累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材料与知识,那么到了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则是其文化整合理论的形成、定型阶段,《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代与未来》等文章从宏观上考察了中西文化与文学整合的可能途径与新质的产生。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的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则意味着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经历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渐进式发展之后,重新开始朝着具体的文化整合方向进行研究。他不是从宏观上勾勒中西文化整合的途径与类型,而是从微观上考察不同文化对于中国作家可能产生的或明或隐的影响。这既是对于这一研究方法的不断实践,又是对于文化整合理论的补充和探索。
2004年,吴定宇先生发表了《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一文,这可视为其对文化与文学整合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实际出发,结合语言符号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新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学科称谓进行了论析,认为它们不具有惟一确定性和不可再现性,因而也无法明确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特质。在吴定宇先生开来,人们最为常用的“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从时间坐标看,由于‘现代’这个符号能指的时间维度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法正确描述这一阶段文学的起讫;第二,由中国古典文学时期之后的中国文学实况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着新旧文学共存的局面,用‘现代’标称之,未能涵括其全部;第三,‘现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无法定位具体时空。”[7]与此相似地,他还对“新文学”、“某某年之文学”、“新中国文学”、“共和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厘清。作为替换,吴定宇先生主张采用“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来指称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认为该指称同时具备理论模式和历史视域:“我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异于中国传统文学,根本在于其拥有异于传统的文学,拥有新的观念、规范、标准和惯例”;[7]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创作客体来分析,都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用一个词来概括其共性,即‘转型’。亦即,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处于一种将定未定的混沌状态。”[7]这种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概念的探究,显现了吴定宇先生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他从中外文化的碰撞、适应、选择和融合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异质文化整合的可能与途径,并使之与文学史的编撰、教学及学科设置联系起来,对于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位严谨、求新的转型期文化学者,吴定宇先生始终对学术研究保持了一份可贵的热情和虔诚,他高度关注着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动态,不停地翻阅着相关研究专著和期刊论文,并抓紧时间对其著作《学人魂——陈寅恪传》进行大幅度地补充、修订,并与学术界同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吴定宇先生的学术研究已经沉淀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学术研究史的一部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他缜密严谨的学术风格,博采众家之长的智识,优美流畅的文章辞藻,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与忧患,已融会入他的学术研究血脉之中。作为中国转型时期文学和文化整合领域的研究者,吴定宇先生的学术成就、研究方法、治学思想以及学人精神,值得后来者学习和研究。
[1]吴定宇.文化整合:中国的过去,现代与未来[J].上海文化,1993(1).
[2]吴定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3).
[3]吴定宇.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4]吴定宇.巴金与宗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3).
[5]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M].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
[6]杨义.稳健博识铸学魂[N].光明日报,1996-10-31(7).
[7]吴定宇,陈伟华.为“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名[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On Cultural Exploration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Inquiry of Intellectuals Spirit——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Characteristics of Wu Dingyu
LONG Qilin
(Department of Chines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Wu Dingyu's academic research is with distinc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His judg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a unique concept of“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China”,and the study of Ba Jin,Guo Moruo and Chen Yinque,are all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ies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whit a new perspective.Wu Dingyu promots the ideas of cultural integration,pays attention to the study the independent and free spirit in literary phenomenon,which could input the intellectual vigor and freedom of consciousness into contemporary scholars.
Wu Dingyu;academic research;cultural integration;learning spirit from the scholars
I02
A
1674-117X(2012)01-0107-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19
2011-04-28
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立项课题(08JDXM75004);广州大学人才引进项目(LQL1-2111)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教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中外文学比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