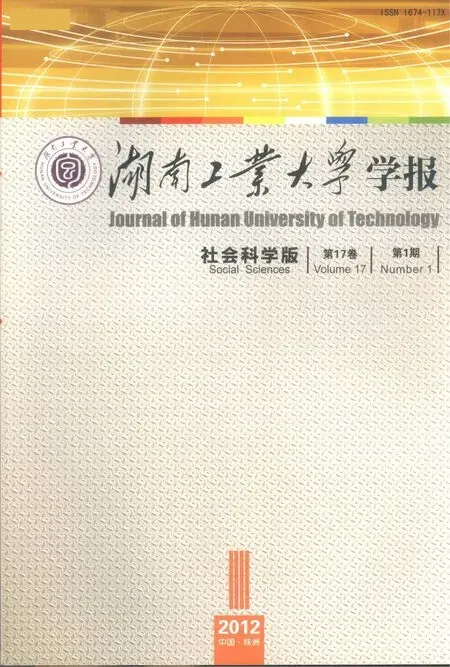当代神话及其美学特征*
颜翔林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15)
当代神话及其美学特征*
颜翔林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15)
当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终结,而神话和神话思维却以变形的方式潜藏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活动之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在当代社会中,神话的典型表现是科技神话、国家神话、民族神话、英雄神话等样式,它们承袭了传统神话的符号和结构形式而有所变异发展,对文艺依然施加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审美影响。
当代神话;神话思维;国家神话;民族神话
一
神话和神话思维作为人类精神的原初形态,对于文明和文化的诞生与发展产生过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主体世界的逻辑思维、抽象思辨等实证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强化,神话和神话思维的某些功能逐渐弱化和转换。因此,“神话消亡论”者普遍认为,神话已经沦落为精神场景中的夕阳余辉,实用理性的日臻强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它构成消解性的势能,它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已经黄鹤一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织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1]
这段为知识界耳熟能详并且援引过若干次的有关神话的论述,甚至被不少学者作为“神话消亡论”的理论依据。诚然,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对于神话本质的如此阐释,的确包含着一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合理性。然而,在当今的思想场景,我们不能满足于把马克思的这段话作为思考“神话”的逻辑前提,而忽视对“当代神话”的深入探究。在后现代的历史语境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所生活的工业时代,这是否意味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完全解构和消亡呢?答案是否定的。神话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说:
我们知道,神话本身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同一个神话从一种变体到另一种变体,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相同的或不同的神话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有时影响构架,有时影响代码,有时则与神话的寓意有关,但它本身并未消亡。因此,这些变化遵循一种神话素材的保存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任何神话永远可能产生于另一个神话。[2]
在斯特劳斯看来,神话仅仅在空间上消亡,而在时间上则不会消亡。因为神话的基本元素和基本结构是恒定的,一则神话在进入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后,它的构架、代码、寓意必然发生变异,但是神话的基本要素、结构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它在历史时间中不会消亡,而只会在某个地域消亡。斯氏的看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然而,斯氏的神话理论毕竟限定于相对狭窄的逻辑范围,而我们关注的理论焦点是在现代性的历史背景中,以往的神话和神话思维如何转换和变异为“当代神话”并对意识形态产生何种影响。在此,简略描述当代神话理论,沿循它的思维路径而进一步探究。
“当代神话”理论是指承认神话和神话思维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并对其特性、结构、功能、表现、传播等方面进行研究的理论。当代神话理论认为,“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甚至在后现代社会中依然不会消亡,只不过它改变了与以往神话不同的存在形式和象征符号,有时候以现代科技作为神话的构成元素和面具伪装。美国当代神话学家戴维·利明和埃德温·贝尔德在《神话学》中阐述了对“当代神话”的精湛见解:
但是当代神话并不只是在童年和上教堂做礼拜时才有,在成年人的世俗世界中也是不乏证据的。比较明显的例证之一是电视广告,因为广告家只有使用众所周知的神话语言,才能做好广告。当某一演员扮成友善的家庭医师出现在屏幕上时,他在人们面前就是一个当代的神话人物了。
……
纳粹神话含有传统神话的许多方面。它大多起源于在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中得到再生的德意志传说。在瓦格纳的故事和纳粹神话里,有两个主题格外重要:一个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崇拜,另一个是对神圣土地的崇拜。瓦格纳笔下的金发碧眼的西格弗里德在纳粹看来就等于是要去统治一个已经清除掉犹太人的世界的超人英雄的模型。这些新一代英雄的领袖具有神一般的、超英雄的无限威力和不可战胜的品质。纳粹分子为了给自己树立根据,强调普鲁士英雄的神话般的传承:从西格弗里德到弗雷德里克,再到俾斯麦、兴登堡,最后到希特勒。[3]
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神话在现代社会没有消失只是改变了存在形式而已,它广泛介入到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之中。“当代神话”改变了古典神话某些特征以适应现代语境,某些神话元素、象征符号、叙述模式、表现形态有所修改,但是其根本的思维方式和无意识的心理结构所构造的神话文本和审美意象,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挥潜在的功用,深刻地影响着市民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代神话呈现的重要特性之一是“象征”,这个“象征”我们借助于波德里亚的话语来阐述:“象征不是概念,不是体制或范畴,也不是‘结构’,而是一种交换行为和一种社会关系,它终结真实,它消解真实,同时也就消解了真实与想象的对立。”[4]当代神话是在交换行为和以经济为主要关系的社会活动之中,确立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意义的。因此,当代神话的政治、经济的色彩要远远高于古典神话,消费意识也超越传统神话的审美意识而成为接受者的主导性意识。同时,当代神话消除了真实和想象的对立,“仿真”和“模拟”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当然,当代神话依然热衷于虚构理想中的“英雄”或“武士”,在电影与电视等现代科技手段所组成的叙事舞台上出场,它们感性化的符号形式更能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当代神话更加重视符号的虚构功能,西方先锋电影艺术家,借助于科技手段,在电影里构建光的“寓言”,“这个寓言处于观众的眼睛和光的超自然力量之间。影片《人工湖》则是另一个极端,它对超自然光进行了直接的暴露,并成功实现了与光合二而一的渴望。当片中形象与光融合时,观众在知觉上有了个人视觉与超自然光融合的相似体验。”[5]从虚拟的光的“寓言”诞生的审美符号,显然具有纯粹虚构的神话意义。而像007邦德、兰博等形象,既产生刺激而震撼的娱乐效果,又为国家主义、民族正义等等意识形态对受众的潜移默化而发挥作用。在塑造英雄人物的手法上,当代神话则放弃采用传统神话中的英雄不死或者死而复活的生命循环的模式,让现代观众能够在理智上接受。叙事意识上,明显的趋向是,“当代神话”一般不再采用传统神话的完整的故事叙述方式来打动接受者,它对结构化的叙述失去了兴趣,而热衷于某些意识碎片的衔接与组合。也就是说,当代神话的“故事性”降低而被代替为某些意识形态的片断连接,或者某些心理情绪的变化伪装。例如“国家神话”仅仅醉心于将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包装起来,“民族神话”则将“民族”虚拟为一个完善的合乎理想的乌托邦存在,“阶级神话”和“政治神话”就以神话思维的终极世界的许诺来唤起社会革命的暴力热情,或者建立一个虚假的价值王国和伦理世界。田兆元在《神话与中国社会》指出:“国家的神话是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神话,而民族神话是一个民族共同信仰的神话,二者的合流是自然而然的。……国家利用民族神话宣扬国家意志,于是国家的神话披上了民族神话的外衣,散布到大众心灵中去。所以,进入了国家制以后,没有一种民族神话不浸染着国家神话的成份。”[6]就现代社会而言,从表层看,现代人类的神话意识由于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似乎被淡化了削弱了,然而,神话与神话思维仍然牢固地存在于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并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同时对于文艺创作、传播和欣赏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倘若辨析神话思维的概念,也许有助于对“当代神话”的深层理解。首先,从思维方式划分上看,以往学术界所谓“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逻辑划分存在着误区,它本身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投影,也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产物,并非符合人类思维方式多样化、渗透性和复杂性的客观实际。其次,以往西方人类学家所描述的“野蛮的思维”、“原始思维”、“神话思维”等等思维方式并非单向度隶属于土著民族、“野蛮民族”,它们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民族。从时间之维看,在现代社会存在者的精神结构中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神话思维,因为它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必然存在于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生命个体之中。因此,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神话和神话思维的心理土壤。最后,西方学者习惯于将人类思维区别为野蛮人的思维和文明人的思维,强硬给这种人类思维的丰富的整体性存在划分出逻辑鸿沟,并且按照时间逻辑为古代人和现代人武断地划出思维方式的界线。例如维柯探讨原始民族的“形象思维”,否认他们有任何理智性的思维,他还将“形象思维”与推理能力截然对立起来,在《新科学》中认为:“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7]克罗齐在《美学史》中就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再如,斯特劳斯所称之的“野性的思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思维”或“前逻辑思维”,卡西尔讨论的“神话思维”等等,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站在欧洲中心论立场上对其它民族表达出的文化谬误和文化偏见。其实,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圈、不同历史语境里的存在个体,既禀赋着相同相似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多种思维方式的交叉渗透的现象,而且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不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差异。就以维柯的“形象思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和布留尔的“原始思维”而言,它们都可以归纳为“诗性思维”,表现为反逻辑、反常识、反经验、反表象等等特征。然而,正是这类思维,它呈现出想象力的自由和直觉领悟的延展,蕴含着超越日常经验和机械逻辑的审美特性和智慧生成,反倒比所谓一般的逻辑思维更具有认识意义和美学意义。因此,神话思维恰恰可能是高于逻辑思维的思维形式,属于更高精神梯度的思辨形式。例如,胡塞尔现象学所推崇的“本质直观”(Wesensschau)、“意向性体验”、“本质地看”等等高度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不正和我们曾经贬低的那些古人的或野蛮人的思维有着潜在的相通之处吗?也许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我们曾经认定的低级思维恰恰应该高级的思维,至少是有其自身价值与意义的美学思维和艺术思维,而这些思维,又可以归纳为“诗意思维”。正是本源于上述对神话思维的探究,在这样一种理论前提下,有理由认为,无论在现代历史语境里,还是延续至将来,神话和神话思维都不可能中断,它们必定施展着强大的精神作用,并且影响人类文化的进程和走向。
卡西尔对当代神话同样做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他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就对国家主义的神话进行探究,认为它构成了当代神话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还肯定了神话思维对于文化的积极作用:“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无一不被神话原理支配着、渗透着。难道我们能够说,所有这些文化(巴比伦的,埃及的,中国的,印度的和希腊的),都完全是人的‘原始愚昧’的诸多面具和伪装,以至于从根本上否认它们的一切价值和意义吗?”[8]问题还在于,我们能否承认神话和神话思维在现代科技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语境里的积极作用,能否认同它对现代心灵的深刻影响及其对文化艺术的审美功能。这样,我们就进入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逻辑层面。
二
当代神话以不同于古典神话的存在方式和表现特性,对社会思潮和文化艺术构成一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程度和作用机制还没有获得广泛和深入的认识和揭示。在此,试图从逻辑分类入手,探索当代神话的某些特性并初步揭示它对部分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
现代社会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它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神话式”的改变。当科技力量满足了人的部分本能欲望的同时,也刺激了潜在的更多更大的欲望诞生。于是,人的欲望对于科技工具的无界的享乐追求就构成了感性和理性的无限循环,也必然催生出对科技的崇拜意识从而导致“科技神话”的诞生。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隐喻了启蒙时代对于理性工具的激情式追求,那么,“科学万能”的口号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科学”所抱有的梦幻式的寓言?它是否也象征着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准“科技神话”?而置身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语境,科技已经成为类似宗教式的“图腾”,所有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都需要它来承担,人们对它寄予了无限的厚望。科技水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于个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尺度,成为一种超越文化的精神性指标。科技在改变我们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信仰。如此而已,现代心灵对于科技的膜拜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宗教和神话。科技神话的传播者往往由科技活动的承载者来担任,而它本身则呈现出与宗教相互渗透的特点。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确观察到了科技神话的身影。首先,我们对于科技作用产生了理性主义的“迷信”,相信它能够解救所有的社会问题,就像原始人相信面临危难的时刻,必然会出现神秘的“英雄”来解救自己一样。我们对于科技的过度信赖和依赖,必然导致一种科技神话的产生。其次,在商品与消费所构成的现代社会的经济链条中,由科技手段所制造的商品往往成为科技神话的直接象征。于是,每一个存在者又都作为“消费者”感受和参与科技神话的传播和再制造,我们由对科技的迷信转移到对商品的迷信,科技的神话当然也就转换为商品的神话。例如许多高科技成果的商品被现代传媒以“广告”的形式扩散,而广告往往又凭借语言和图象、音乐等符号化活动达到对商品的修辞夸张,进一步对它们进行神话意识的包装,于是我们这些消费者就被科技神话所征服。再次,作为科技神话的变种——“信息神话”正在悄然无声地向我们走来,它是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神话象征品。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被一种看似神秘而又极其简单的无所不在的“信息”异化了,“信息”奴役了每一个存在个体: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传播信息又同时被信息所传播,它似乎成为凌驾我们精神之上的神灵,被我们尊崇为“至尊神”。我们固然不能否定科技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欲望满足,然而我们必须对科技神话抱有怀疑主义的理性警惕,也必须看到科学技术给人类精神存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重视科技对人类所构成的现实性的和潜在性的巨大危害与危险。“科技神话”也许就是造成新的历史悲剧的潘多拉的匣子。最后,科技神话在文艺领域表现样式之一,就是科幻影视中的“异形形象”(Alien)。诚如所言:“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说,异形的形象是一个漂浮的能指。这就是说,异形的视觉形象只有在参照异形的其他视觉呈现方式而且不关涉到‘真实的’宇宙空间时,才能被如此解释。”[9]这些异形形象,往往是天外怪兽,机器人,古代神灵,或者多种生物混合品,它们被现代科技所包装或武装,以科技和神话的混合形式展示一种漂浮的能指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给以现代困顿疲乏的审美心灵以感性的刺激,另一方面表达创造者的意识形态。
国家神话构成当代神话的另一个侧面。如果说,科技神话更多禀赋个体的欲望本能的因素,它和意识形态保持疏远的距离,而国家神话则更多包含着群体的理性结构,和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关系。“国家神话”使整个国家的民众相信,这个国家是神圣和合理的,它接近于神话境界的完美和理想,哪怕它是在从事侵略和杀戮的非正义暴行,例如纳粹德国就曾经制造过这样的“国家神话”。因此,国家神话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爱国主义的概念范围,容易变异为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导致历史悲剧的产生。当然,国家神话的有益一面在于,它能够激发和调动整个国民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使个体存在服从于国家利益,从而有利于国家的进步和繁荣。例如像美利坚合众国,可以看作为一个典型的制造“国家神话”的国家。无论历史上美国民众对于华盛顿、林肯、肯尼迪等人物的崇拜情感,还是当今奥运会上的狂热飘摇的星条旗,还有好莱坞的电影和各种商品的广告,都隐喻地说明了美国的“国家神话”的普遍存在和强大势能。在此我又一次援引两位美国神话学家的一段精湛之论:
当然,国家主义的神话采取了众多的外在形态。比如“美国方式”、“美国梦”、“美国人知道怎么办”这些话,就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形态(美国神话)的产物。这种神话中的英雄是戴维·克罗克特或丹尼尔·布恩(他们是边疆的开拓者),历史学家和讲故事的人把他们的事描绘成无所不在的神话。他是个由贫致富的英雄霍雷肖·阿尔杰,或者是个用自己的足智多谋胜过了旧世界老谋深算的说大话的粗汉。然而最重要的或许是,他是个美国总统,人们希望他体现那些决定并鼓舞美国文化的东西。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讲过华盛顿这位“美国之父”的神话。本世纪也造就了一位总统,不过他的命运是以极其悲剧的方式变成神话的。肯尼迪是本世纪出生的首要的总统,人们希望以他那新的想象力改变世界。人们把他的施政与亚瑟王的朝政相比,他的死成为持久的、极度痛苦的和英雄的典礼。而且,当美国各阶级和各政党的人守望着这种神话般的丧葬仪仗队穿过华盛顿时,这位年轻总统的死便产生了一种全美国的团结感,即美国神话的再次诞生。[10]
遗憾的是,冷战后的这位唯一的超级大国,仍然在制造虚幻的国家神话,尽管它并没有给整个世界带来福音和新的公正与秩序。悲哀的是,我们无数第三世界的或者说是“后殖民文化”时期的个体存在,依然被“美国神话”所迷醉,将它看作是当今世界上完美无缺的国家形式。其实,在迄今为止的历史里,绝不可能存在着一个完美的或理想的国家形式和政权制度,因为人类的文明历史也许刚刚开端,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的符合理想的境界。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神话”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精神的致幻剂和有害的麻醉品。从美学意义考虑,它客观地构成对审美活动的压抑和损害,甚至极大程度地遮蔽主体的精神自由和想象力。
需要补充论证的是,国家神话往往暗中转移为一种“阶级神话”,它由对国家主义的信仰转变对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体的某个阶级的信仰。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鼓惑民众相信,存在着一个先进的和革命性的阶级,它代表历史发展和进步的积极力量,你们属于这个阶级或者应该努力地融入这个阶级,这样就可以使国家产生巨大的推动力,由此促进历史的变革和向着美好的未来演进。例如,法国大革命就缔造过这种“资产阶级”神话,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则创造一个“小资产阶级”神话。
与国家神话密切关联的是民族神话,它同样构成对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传统的神话观念无疑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占据为任何一种神话传说的内容之一。在现代社会中,尽管民族神话的外观似乎不再呈现十分明显的无理性色彩,然而其深处仍然隐藏着强烈的非理性情结。“雅利安神话”和“纳粹神话”可以看作为现代历史上的最不幸的民族神话的典型象征,它必须为我们所批判和否定。
迄今为止,民族神话顽固地停留在历史进程之中,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流血冲突的悲剧原因之一,就是“民族神话”的阴影投射给这两个民族心理之上带来的恶果。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以及某些阿拉伯人,他们都是民族神话或种族神话的牺牲品。当然,在众多的虚假的意识形态中,民族神话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常常演变了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的实践行为,给这个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麻烦的因素。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来讲,民族神话更可能导致东西方世界的多民族的意识形态甚至暴力形式的对抗,亨庭顿的忧思不是毫无道理的杞人忧天,不过他的《文明的冲突》也许无意识地隐含了民族神话的意识。在这个世界上,民族神话比国家神话也许更具有潜在的危险性,它不仅仅构成对历史与现实的危害,也构成对人类的普遍的审美精神的危害。
当代神话中的英雄神话,属于传统神话在现代历史语境中的正常延续,所不同的是,它与传统神话中的“英雄神话”相比,更多地包含着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因素,较多地添加了实用观念和工具功能的特性。传统的英雄神话又称之为“元神话”,英雄的生平经历成为神话的基本框架,一般划分为8个部分:出生、成年、隐修、探索、死亡、降入地府、再生、神化。这8个部分构成了英雄神话的故事结构,从而为英雄形象的确立和升华奠定了感性基础。在古典神话中,神话英雄的再生与复活的模式具有普遍性,或者说,英雄的死亡与再生成为古典神话的一个基本主题。英国神话学家里查德·P·亚当斯在《弥尔顿〈利西达斯〉中死亡与再生的原型模式》一文里精湛地揭示了神话中的英雄“生活、死亡和再生的模式”。[11]而在当代神话中,英雄生平不再采用以往的基本结构,神奇的出生方式被扬弃了,如弗雷泽曾经注意到的传统神话中的英雄往往于处女孕育,出生后遭遇到被抛弃于大自然的命运,而救他们的往往是下层民众或者是动物。另外,传统神话中的英雄的奇特经历,如屠龙、打败妖魔、神秘的隐修、探险、奇遇、死亡和复活等故事因素也往往被当代神话所舍弃。而现代的英雄神话,在观念形态上采用实证主义,放弃了一些非现实性的虚构叙事,而采用适度的人物夸张和情节修辞,更多借助于先进的科技手段来实现古代神话中的某些英雄所要达到的目的。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的好莱坞电影《真实的谎言》,故事里主人公——那位由斯瓦辛格扮演的现代“神话英雄”,完全以高科技作为神话的道具演绎了一个在基本结构上类似于古代英雄传说的虚拟故事:英雄斗恶魔而拯救民众和国家的传奇。
对当今艺术中的“英雄神话”问题,姚文放教授曾有精湛之论:“当代英雄神话是一种同质性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说,不管它们在人物、情节、场景以及表现手法上有多大的差异,在其内部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结构。”[12]揭示了当代文艺中的英雄神话的一个特征。尽管英雄神话被不同样式、不同地域的创作者以文艺形式所表现的时候,难免会呈现某种意识形态和写作策略的差异,然而其稳定的文化特征和神话结构相对不变。如果我们将英雄神话延伸到文艺之外,在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里,无论是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精神信仰;也无论是政权控制下的新闻传媒,还是大众流传的日常话语,都不乏“英雄崇拜”的情结流露。只不过官方利用它来维护政权的稳定和合法性,确立一种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道德准则;而民众则希冀利用“英雄”来达到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所不可能完成的铲除非道德的恶势力的目标,尤其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制度中的民众,这种对维护神圣正义的“英雄”的需要就是一种迫切的政治幻想的恰当体现。而对审美而言,“英雄神话”尽管被寄寓了虚幻的乌托邦内容,然而它毕竟为生活于平淡无味的历史语境中的人们提供一种超越平淡的有限的快乐和有限的美感。
总之,当代神话以不同于古典神话的感性样式表达出和古典神话相同的对于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和对于文学艺术的积极的审美作用。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13.
[2]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陆晓禾,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259.
[3]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M].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46-150.
[4]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206.
[5]威廉·维斯.光和时间的神话[M].胡继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76.
[6]田兆元.神话与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0.
[7]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98.
[8]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范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9]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42.
[10]戴维·利明,埃德温·贝尔德.神话学[M].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48-147.
[11]约翰·维勒克.神话与文学[M].潘国庆,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248.
[12]姚文放.当代审美文化批判[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62.
Modern Myths and Their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YAN Xianglin
(School of Humanities,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 325015,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does not mean the end of myths and mythic thinking.However;they conceal in human physical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activities,and play important functions by transformed ways.In modern times,typical myths are myth of technology,myth of state,myth of ethnics,myth of heroes.They follow the symbols and structure forms of tradition myths and have their own variations as well.They still exert certain positive function and aesthetic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modern myth;mythic thinking;state myth;ethnic myth
I01
A
1674-117X(2012)01-0093-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17
2011-12-22
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神话的美学研究”(11YJA720032);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神话与文艺生产”(09CGZW004YB)
颜翔林(1960-),男,江苏淮安人,温州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文艺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