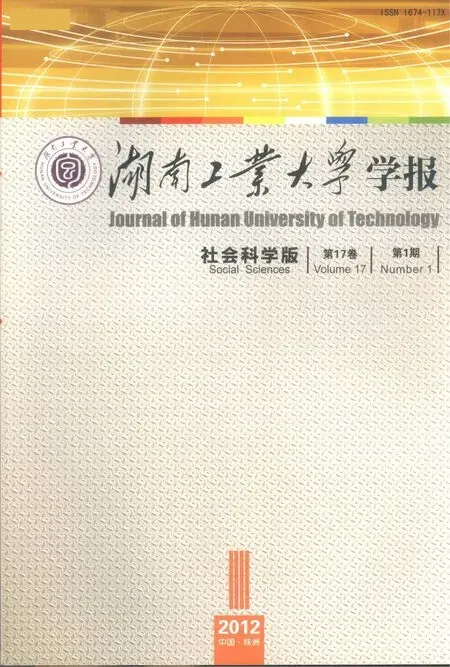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八溪洞”人的合理生活与《山南水北》的叙事策略*
王青,姚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八溪洞”人的合理生活与《山南水北》的叙事策略*
王青,姚海燕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用一种拼贴的结构建构了“八溪峒人”的合理生活;用一种虚构的真实,让读者目睹了情感对异化的治疗功效;以一种充满哲思的叙事,对现代社会单一的生活模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为文学发挥其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功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
韩少功;《山南水北》;八溪峒人;合理生活;叙事策略
继《马桥词典》之后,文体杂糅已成为韩少功作品的主要特色。虽然学界对文体的研究已走出了“文学体裁”的苑囿,[1]而将文体视为“文学作品的体制、体式、语体和风格的总和”,[2]甚至认为是“文化存在方式”,[3]但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跨文体写作”只定义了韩少功不囿于文体的创作态度,并未解释他对“跨文体写作”青眼相加的原因。纵观韩少功的创作历程,“真实”几乎贯穿了韩少功的整个文学时空。他视文学为生活的报告人,消息的传递者。[4]传统的小说往往通过戏剧化的情节来表现生活,但真实的生活却有别于戏剧。现实生活往往没有三一律的恒定模式,既少有因果的必然性,亦缺乏科学的可验性,更不具备真理的唯一性,常表现为事件的偶发性、行动的妥协性及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的小说是通过营造真实性来表现生活,而跨文体写作是通过反思真实来再现生活。在真实性与真实之间,韩少功选择了跨文体作为再现生活的写作方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真实的生活首先应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利用多样的存在反抗单一的现代模式是合理生活的一项重要指标。韩少功将质疑的叙事态度、双声的叙事声音和拼接的叙事结构组合为《山南水北》的叙事策略,通过建构“八溪峒”人的合理生活来反映生活的真实。
一 “八溪峒”人的合理生活
八溪峒是一个被韩少功虚构出来的场域。八溪峒人可以用“一只老虎的笑,一只青蛙的笑,一只山羊的笑,一只鲢鱼的笑,一头骡子的笑”来赞美自己的合理生活。[5]24他们的奔放无拘绝非因为不知魏晋,卫星信号早已覆盖这里的村村寨寨。他们的生动缘于可以利用场域优势,以合法的名义逃离话语的规训。八溪峒人的生活指南不是现代性话语,而是一个融传统、自然、情感于一体的多元话语。
(一)情欲之合理
生活在契约里的现代人总喜欢用追求真理的方法对待生活,但生活往往以悖论的姿态嘲笑人类的“认真”。生活方式是否必须象概念一样被定义,像条文一样被规范呢?当情与法冲突的时候,八溪峒人将如何选择呢?在《天上的爱情》里,一对私奔的贼男女不仅在八溪峒的山顶安了身,而且“山下有些山民替他们说情,说这对痴男女也可怜……”;最后“乡干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也就不了了之”。[5]209本是破坏计划生育的黑户却在山民的庇护下过起了安稳的日子,这种宽容缘于八溪峒人对生活的阐释。生活因为有人才生动,人因为有情才鲜活,所以因情而私奔的生活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当然,生活并不会因为有情人的存在而充满人情味,令人向往的爱情是飘荡在天上并非生长在天堂,单纯的爱恋仍要面对现实的世故。所以,当龙老师动员他们让孩子入学时,女主人会红了眼圈说“谁说不是呢?我们这一辈子,反正也这样了,只是娃崽……”[5]210这也是合情的合理性体现,即追求自由所需的成本高,逃避自由所需的成本低。《带着丈夫出嫁》更是摆出一副将婚姻制度挑战到底的姿态,从题目到内容都与现代性的婚姻条文相冲突。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并未发展成为一个文学“△”,而是按照三角形最稳定的数学逻辑缓缓推进。本应兵戎相见的两个男人到头来却要“吃肉时留一口,喝酒时留一盅,这个男人对那个男人也越喊越亲,不但‘大哥’变成了‘世矮子’,而且干脆变成了‘野老倌’……”;最后,“村民们也对这种隔山笑骂已习以为常。”。[5]228这种“拉帮套”的生活方式曾作为传统的婚俗在民间有相当的市场,但随着现代性话语合法地位的逐步确立,这一婚俗便作为压迫妇女的封建糟粕,被依法取缔。民俗本是一种民众自觉,“拉帮套”婚俗的形成必有其生存的民间土壤,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不难发现这一习俗降低了组建家庭的成本,挽救了濒临破产的家庭,对性资源起到了均衡的作用。现代性话语在放大女权的同时,也遮蔽了其适应生活的合理性一面。《非法法也》是一篇直接用悖谬来命名的叙事,通过“我”的介入引出现代性话语与情理之间的矛盾。两个后生的死亡本与供电公司无关,但是,为了能让事故中受牵连的家庭维系下去,村民们(包括受过现代启蒙的“我”)放弃了求真而选择了求情。虽然“我”明白“活脱脱造出了一个假案。但山民们认为此事办得天理昭昭无可置疑。他们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胡言乱语,乡村干部也不约而同不假思索地两面三刀”。[5]198虽然“我”“不大能接受这种胡来和恶搞,但三个贫困家庭(受害两家加肇事者一家)由此免了灭顶之灾,在没有工伤保险的情况下能继续活命,又不能不说是各种结果中最让人心安的结果。我能说什么?”[5]198用无奈来反抗现代性的求真,是一种拥抱了土地的同情;用利益来反抗现代性的求真,是一种生长于土地的狡黠。无论动机如何,情欲之合理都是两者考量的重点。
(二)观念之合理
八溪峒人对生活的思考往往“因地制宜”,生活空间决定了他们思维的起点,他们不愿为现代性话语所左右,更愿意定点于传统的坐标。比如他们不愿做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人,在处理经济问题时,不是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而是将面子视为经济操作中的最大收益,并不计成本地孜孜以求。在《豪华仓库》一文中,韩少功描写了这种不计收益的经济观念:“很多房主并不太习惯这样的新楼,于是在新楼旁边用木板搭起了偏棚,以解决烧柴、养鸡、养猪、圈牛一类现实问题……他们的新楼经常白白地闲着,充其量只是当作仓库”。[5]229虽然,乡民们也抱怨房子不实用,但“这咬牙切齿的抱怨里还是透着欢喜……不论新楼如何不合用,也不论主人为此欠下了多少债,但新楼至少有一条好处——主人从此做得起人了”。[5]232当然,也可以将面子解释为一种收益,但这收益的内在属性为精神,已超出现代性话语所限定的经济范畴。这种违背经济学原理的经济观虽不合法但却合理。面对无法逃避的电闪雷鸣、莫名其妙的瞬间白日以及流窜于山间的荧荧鬼火,山民们大多偏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迷信观念。韩少功将“上帝”作为质疑理性、质疑知识谱系、质疑科学观念的象征。《山南水北》中的花鸟鱼虫、风雨雷电都是“上帝”。由于神祗在场,《非典时期》的八溪峒人,更愿意用迷信的方法来解读这次人瘟,并试图用鞭炮赶走这吃人的“SARS”,就连学习了“三个代表”的党员干部们,也动员村民们用鞭炮驱瘟送鬼。面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最后出场的贺乡长竟用迷信来破除迷信,他义正辞严地说“放鞭炮有卵用!你要是命里有,不放鞭炮也不会死。你要是命里没有,放再多的鞭炮也白搭。”[5]188这番极具讽刺意味的补充说明,正是八溪峒人对神秘自然的“科学”解读。“家里的五件电器全遭摧毁,一个文明世界顷刻间瓦解,一片死寂”。[5]80这段文字并非描述外星人入侵地球,而是叙说房子遭《雷击》后的惨状。“乡下人没有城市楼群的掩体,暴露在茫茫旷野,暴露在雷电的射区之内,成了大自然随时可以轰击的靶标。如果穷得连避雷针都装不起,人们很大程度上只能听天由命”。[5]81于是,山民们怀着对天地的无比敬畏,企图用道德行为来取悦雷神,甚至不惜将孝道演变成一种表演,比如问候长辈的“声音一定要宏大,宏大到让老天爷能听到;其动作一定要张扬,比如紧急切肉最好在门外大张旗鼓进行,让老天爷一眼看个明白。”[5]81八溪峒的空间特点决定了这些夸张表演的合理性。
(三)经验之合理
自“现代等同于先进,传统等同于落后”的话语被合法化后。知识与经验便不再可以等价交换,由逻辑推演出的定理价值连城,被实践反复印证的经验则一名不文,知识的帽子只能戴在符号的头上,感性的生活被逐出知识的殿堂。八溪峒人却无视这些宏大叙事,他们仍将经验视为生活的挚友。《卫星佬》是一个叫毛伢子的杀猪佬,满是泥点的裤脚让“我”将其错当成了卖鱼人,就是这样一个无法用符号定义其职业的汉子,“既不需要定向仪,也不需要用量角器,只是抬抬头,看看太阳的位置,甚至是太阳在云中可能的位置,……很快就校准了卫星方向”。[5]108几个月前,这项工作却是由两位技师带领着一队人马,兵分两路,依靠定位仪、监测器、电脑、对讲机等一系列高科技工具,忙活了大半天才完成的。对生活来说,经验与科技哪一个更合适呢?作为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业余炮手,每次打炮眼前,华子都“事先围着目标走一走,抠块石头捏一捏,撒泡尿,挠挠脑袋,就能定出最刁的打眼角度,打出恰到好处的深度……因此他用药少,炸掉的石方反而多”。[5]249这样成本低廉、程序简单的经验难道不是知识?那个酷似杂技表演的挖土机师傅老应,开着挖土机在峭壁上表演悬空杂技时,无人不替他捏把汗,而他却“只靠一边履带着地,任另一边履带悬空,硬是把挖土机开了过去”。[5]253这种技巧哪本培训书籍里曾有教授?知识系统的专业化、细致化在提升人类总体能力的同时,也降低了个体的技能。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常常用结果来否定经历,用功利来否定趣味,但生活恰恰由体验和感觉组成,任何能够用“迷”来命名的行为,都无法用目标加以限定。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农痴》中那个年过半百的余老板,为何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跑到农村来挑粪桶。整天忙碌于为农民打米、为鸡鸭诊病,以至于“他的家倒像个叫化子窝”,[5]178这样一个农痴,甚至连农民也无法理解。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5]179“迷”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现实给予体验者的回馈。只有用游戏的态度去体验生活,才能沉迷于生活且乐不知返。现代性话语可以定义各种知识,但却无法让人们用游戏的态度去学习知识,离开了感性谈理性,隔离了他者谈自我正是现代性的硬伤。
二 《山南水北》的叙事策略
八溪峒的自在不同于桃花源的怡然,同属虚构的两个文学空间,却承载了完全不同的时间类型。桃花源的时间是停滞的,八溪峒的时间是流动的;一个是心之所向的净土,另一个是身之所向的沃土;桃花源是心灵层面的空间,是归隐的精神乐土,是一种境界,八溪峒则是世俗层面的空间,是鲜活的物质家园,是一种生活。陶渊明采取“缘溪行,忘路之远近”的方法开启了桃花源的叙事,韩少功又是采用何种技巧建构出八溪峒人的合理生活?
(一)后现代式的叙事态度
《山南水北》的叙事态度颇有“后现代”之风。这里的“后现代”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之后,也不是对现代性抛弃,更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而是一种后现代精神,是指一种不轻易下结论的态度,一种质疑话语的精神,一种用理解之同情进行文学创作的思维路径。“合理”是针对合法提出的概念。“法”并非限定在法律层面,而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秩序的广义场域。在现代社会中,全球化、一体化用其不容置疑的合法性规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本土与多元几乎没有话语权,人类被消费主义的单一价值模式不断异化,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作为一个挑战合法性话语的概念,“合理”应理解为一种自由的生活态度,一种不被规训的生活方式,一种多样化的生活状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后现代的叙事态度与合理生活之间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两者相互支持共同反抗现代性的话语强权。后现代叙事为合理生活提供了话语权,合理生活为后现代叙事提供阐释权。后现代叙事通过强调异质为多元张目,通过设置相对来反对绝对,通过折衷思维来肯定合理生活;与此同时,合理生活通过生动的具象为对话提供依据,通过多样的存在为拼贴提供可能,通过真实的感受为解构提供支持。韩少功通过《山南水北》中的《雷击》强调了迷信的合理性,用文学的方法论证了“存在就是合理”的哲学命题;在《山南水北·开会》中,读者见识了“歪理邪说”的正义性;在《山南水北·十八扯》中,读者看到真实与虚构在生活中的相互缠绵。《山南水北》用质疑的态度、双声的叙事、拼贴的结构,成功地营造了一个生动、合理的现世,让读者透过隐藏在文字中的悖论,触摸到生活的真实。
(二)双重身份的叙事声音
在《山南水北》中,作为文本的作者,韩少功是故事的叙述者,作为故事的人物,他又是被叙述的叙述者。这种作者兼人物的双重叙事身份,让《山南水北》的叙事声效足可以假乱真,甚至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因为这种叙事声音暗含一个逻辑:“我”在讲自己亲历的故事,有什么值得怀疑呢?
1.双重身份的发音。韩少功在《山南水北》中的双重身份可以从现实、创作、叙事三个角度来定义。自2000年起,韩少功就在海口与八景乡之间迁徙。为了防止文学创作上同性繁殖,有着30年城市生活经验的韩少功从知识圈中出走,来到他当年插队的区域,在这片曾经挥洒青春的土地上,自盖宅院,种菜种瓜,用劳动来为自己定位。如果《山南水北》是偶尔客居乡野的城里人用来赞叹“林泉之志”的凭证,那么反抗城市、质疑现代就注定成为一个可疑的命题。就此而论,与其说韩少功选择了《山南水北》作栖息地,还不如说《山南水北》选择了韩少功作代言人。让一个当过作家的农民来质疑现代,反观传统,其说服力之强是不言而喻的。现实身份的双重体验必然会影响到作者的文学创作,精英的血统让韩少功意识到农耕文明的某些“恶”,草根的精神又让他无法漠视现代文明的某些“罪”。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之间穿梭的韩少功,选择了用观察员与行为人的两重身份创作《山南水北》,正如韩少功这样描述自己,“我非常清醒我不是真正的农民,……但是我的确和旅游者、访问者差别大一些。因为我的乡村生活是和农民搅在一起的。”[6]这种现实经验表现在叙事里就是作者以“看”与“被看”的身份同时出场。在卷首文《扑进画框》中,作者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5]1这说明“我”原不属于这片湖水,但湖水之美撩动了我的心弦,因此,尚未落草于此的“我”决定通过观察员的眼睛来“看”这片湖水。可是当“我”站在彼岸反问自己:“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5]3肯定的答案让我理直气壮地逃离了“现代的鼠疫和麻风”,远离了“水泥的巨晰和恐龙”,“扑通一声扑进画框里来了”。[5]4“扑”的甜蜜与“框”的边界,让“我”从一个观画人变成了一个画中人,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因此,从“我”将这里命名为“八溪峒”的那一刻,叙事声音便开始出现了交叠。作者用《特务》来描写乡民对“我”迁居山野的猜测,此时,“被看”的身份溢于言表。八溪峒人庆爹用一个不明来历的女尸案,解释“我”迁居此地的原因,由此引发了“我”对失踪者的臆想。“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他们毫无理由舍弃自己的家,却事实上舍弃了。他们也许像山上那位神秘来客一样,被一座远方的大山召唤而去,在罕见人迹的密林里选定了归宿……她也许是命定的漫游者,是上帝派来的特务,对大地进行某种隐秘的调查,对自己的神圣使命守口如瓶。”[5]29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失踪者”,用双重身份来隐藏真实的自己,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用“失踪者”的声音来叙事。
2.平等对话的语调。韩少功认为:“我的整本书(《山南水北》)都牵扯到农村问题,但我从来不认为歧视是一种批判。歧视带着一种冷漠心态,意味着没有热情与尊重去了解。农村的问题很多根子上还在城市,我们抱着城市人的优越感去看就很不对。”[6]由此可见,在《山南水北》中,韩少功试图用平等的叙事语调与乡民对话。全书呈现一种生活流的叙事态势,看似无章可寻,但如果用“对话”作关键词来扫描这99篇文章,就会发现文章的排列组合颇费心机。从《扑进画框》到《回到从前》,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展开的对话,商谈的结果让作者义无返顾地选择在八溪峒遥望星空。面对璀璨的星空,叙述者将频道调到过去,在《残碑》里与历史对话,询问那些被宏大叙事湮灭的亡灵,革命是否被曲解,被粉饰过?用《拍眼珠及其他》的习俗与古老的道德对话,话题是现代文明如何制约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最后在假想的《智蛙》里完成了对文化遗产的反思。接下来,作者开始气定神闲地与生态对话。从《村口疯村》到《再说草木》,种种怪象让人不由感叹自然的神奇,书写万物有灵不是为了证明神灵的无所不在,而是为了批判现代人为满足欲望不惜驱逐良心的恣意妄为。正如作者在《月夜》里所悟:“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5]47八溪峒的生物对情义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城市里的人群。从《养鸡》到《忆飞飞》,从《诗猫》到《感激》,作者将原属人类的感情附加在动物身上,无论是家蓄还是飞禽,他们都实践着人类曾有的温情。在生物界,这些美好的情义不会因现代社会的到来而终结,但面对物质诱惑的人类会怎样对待这些情感呢?情义在欲望面前将被判缓刑还是死刑?这是作者留给读者的思考。作者用《红头文件》《每步见药》等文章与劳动对话,用《雷击》《守灵人》等文章与科学对话,用《一块钱一摇》《瓜菜》等文章与观念对话,用《开会》《各种抗税理由》等文章与制度对话,用《你来了》《时间》等文章与灵魂对话,用《相遇》《秋夜梦醒》等文章与回忆对话,借助对话韩少功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船老板》到《意见领袖》,从《认识了华子》到《蛇贩子黑皮》,一个个江湖隐士在人们目瞪口呆表情中,阐释着“知行合一”的文化内涵。从《墙那边的前苏联》到《野人另一说》,作者用赞美甚至羡慕的语调来描绘八溪峒人的情真意切,以至于感叹到“哪一天农业也变成了工业,哪一天农民也都西装革履地进了沉闷写字楼,我还能去哪里听到呼啸和山歌,还有月色里的撒野狂欢。”[5]176
在《山南水北》中,我们很难看到对错分明、非此即彼的结论,似乎每篇文章有一个开放的结尾,无法定论。比如:乡干部们为了搞活经济,默许在乡间开设赌场,后被公安部门查处。警察在八溪峒围捕了三天,在《兵荒马乱》之中,“我”也不置可否地放掉了两个避祸的城里人,“我”为什么要知其不对而为之呢?实在是身不由己,情非得已。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是决定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我们认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宁愿承担作伪证的风险,也不愿大义灭亲地说出真相。进入现代社会后,契约精神被合法化。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做一个有情有义的良民,是现代生活之于中国人的难题。这样的难题在《山南水北》中唾手可得。这种无法给出正确答案,只能给出最佳选择的叙事声效,正是生活中两难境状的真实表达。
(三)拼贴化的叙事结构
进入20世纪后,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对应混乱,世界变得让人无法捉摸,因此,蕴涵因果关系的封闭体系已无法准确描述现实,文学应尝试使用一种开放的叙事策略再现生活。《山南水北》用笔记体实践了一种拼贴结构的叙事。这种拼贴结构首先表现为无因果逻辑叙事。因为,“人们讲话有时候不在于讲出什么道理和事实,只是找个乐子,满足自己对惊叹、想像、愉悦、紧张等等的需要。”[7]所以,无论文本形式,还是情节内容,《十八扯》都无法与因果逻辑发生关联。当然“即使是荒诞的《十八扯》,它内在的逻辑亦有真实的一面,比如说某头牛是人的转世,看来荒诞不经,但人们对转世者的同情,含有现实中真切的感情因素,也折射出现实中真切的时代背景。”[7]因此,无因果逻辑叙事并非无逻辑叙事,只是这个叙事逻辑不是因果而是情感。八溪峒人不喜欢用刨根问底,追根溯源方式解释生活,他们喜欢用情感来解释生活现象,并将合情合理作为阐释的最高标准。比如《庙婆婆》中那个90多岁,儿孙已先她离世的老婆婆这样解释自己和后生们一起捕捉老虎的故事:“罪过啊,罪过。连老虫都克死了,还能不克人么?我不知前世作了什么孽,摊上了这么个毒八字”。[5]213这个本可如武松打虎般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却在庙婆婆的叙述里显得凄楚无奈。其次,这种拼贴的叙事结构还表现为多种叙事形式共存于同一文本。比如:《红头文件》浑然一副应用文的姿态,不仅题目直接标明文体,内容也用表格、数据统计等工具,图文并茂地向代表现代话语的GDP宣战。《CULTURE》是一篇用英文命名的文章,作者的本义是一语双关地说明农耕与文明的如影随形,但文字的中英混杂还是表现了拼贴的结构特征。《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一文,因为只有题目没有内容,引得不少读者满腹狐疑。可以说,无辜的泪水让作者找不到文字来记录与描述;也可以说,面对无语的生灵,文字显得太过苍白,还可以说,这是作者玩弄的后现代技巧。这篇文章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叙事形式,为多元阐释提供了可能。《很多人》抄录了一段家谱。有名的,无名的,拥挤在一起,看似很多人,实际却没几个人。因为有太多的人只有符号没有故事,更有太多的人连符号也没有留下,所以,作者留在篇末那不起眼的注释:“至此女性开始上谱”听起来是如此振聋发聩。这种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小说文体是一种丰富和补充。作者采取了披露小说创作动机的手法来叙述《土地》,用一种“戏中戏”的结构来编织文字,韩少功认为这种结构:“不光写故事,而且写故事的产生,这种从舞台进入后台的方式也是有意思的。”[7]这种有意思的文字游戏,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生活的丰富性,也使文章的前后段落形成一种紧张和对峙的关系,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韩少功用拼贴的叙事结构,在《山南水北》中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文学世界,虚构了一个真实的八溪峒,带着理解之同情,用心倾听八溪峒的一切声响,最终用对话的语调完成了哲思式的叙事。这个发现了天空不“空”的叙事者,最终这样定义自己的叙事策略:“我游到岸边,回到家里,回到来串门的两位邻居面前。我像一个小气的暴发户和守财奴,对自己的突然发迹秘而不宣”。[5]311
[1]丘文辉.向杂文学传统致敬——韩少功《山南水北》文类文体透视[J].文艺评论,2011(11):98-99.
[2]陈剑晖.文体的内涵、层次与现代转型[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108-114.
[3]张毅.文学文体概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43-45.
[4]胡俊飞.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0-81.
[5]韩少功.山南水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6]孙小宁.韩少功谈“隐居生活”:乡村里的灵魂之思[N].北京晚报,2006-11-21.
[7]季亚娅.韩少功季亚娅对话:有关《山南水北》[DB/OL].[2008-03-11].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65283/.
Analysis between Baxidongs Reasonable Life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Shannan Shuibei
WANG Qing YAO Hai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The problems of modern society have attack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According to Karl Maxs,“all that is solid melts to air.”Social people use social rules to regulate their own behavior.Rational person explains all phenomena with the science.Facing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Han Shaogong has made a valuable example for literature.He makes the audience witness affection therapy to alienation and intends to criticize and self-examine the sigle life patfern of modern society.He builds a reasonable life of Ba Xi Dong with a narrative,and resists the alienation with the emotion in Shan Nan Shui Bei.
Han Shaogong;Shannan Shuibei;Baxidongs;reasonable life;narrative strategies
I207.425
A
1674-117X(2012)01-0035-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07
2011-11-25
王青(1975-),女,吉林前郭人,华南农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姚海燕(1971-),女,湖南长沙人,华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