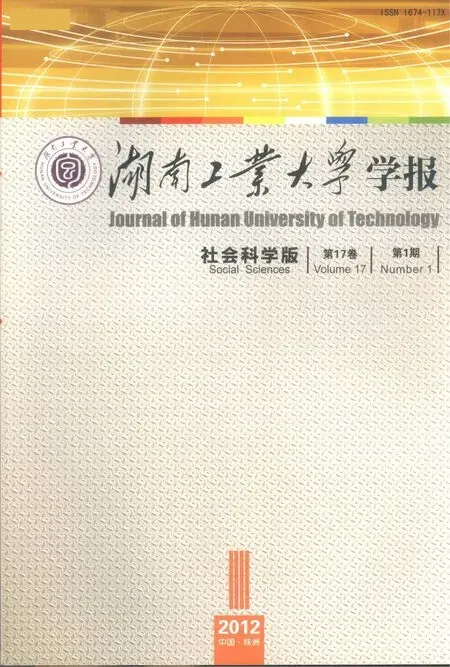在昆德拉与韩少功之间
——兼与陈思和先生商榷*
胡俊飞
(1.长江师范学院文学新闻学院,重庆涪陵4081001;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在昆德拉与韩少功之间
——兼与陈思和先生商榷*
胡俊飞1,2
(1.长江师范学院文学新闻学院,重庆涪陵4081001;2.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马桥词典》和《暗示》是韩少功在“寻根文学”陷入内外夹击后,为缓解危机所做出的创作转型,其转型明显受到昆德拉小说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对此,陈思和先生认为《马桥词典》是受昆德拉“误解小辞书”创作经验的启发之作,而非模仿《哈扎尔辞典》的低劣之作,但他认为这种影响仅限于借鉴辞书之形。事实上,《马桥词典》不仅借取词典式结构之形,而且深得昆德拉“误解小辞书”意义内蕴之实。《马桥词典》及之后的《暗示》借用词典式小说的叙事结构,以崭新的体察方式,成功道出言语背后藏匿的与日常体验相抵牾的人生体悟,实践并拓展了昆德拉的小说文体思想观念。
昆德拉;韩少功;《马桥词典》;《暗示》;小说文体
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既称得上重要作家,在品质上又属上乘的作家并不多,韩少功可算其中一个。韩少功不属于盛产型作家,虽早于上世纪80年代初便在文坛崭露头角,但迄今为止,其创作量甚至比不过许多上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的新生代作家。然而,我们并不能据此泯灭韩少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毫不讳言,将来无论谁来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会为韩少功留下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少功以伤痕反思性作品为文坛所熟识,如《月兰》《西望茅草坪》等。80年代中期,他在创作上做出重要转型,毅然擎起文学寻根的大旗,《爸爸爸》《女女女》是这一阶段收获的果实。80年代末寻根文学面临来自文学内外批评者的夹击,韩少功创作进入一个漫长的反思期,直至1996年,推出令人为之一震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马桥词典》以及随后问世的长篇笔记体小说《暗示》。纵观韩少功的创作生涯,他的作品明显地呈现出由密切关注现实,到沉入历史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层,再到对人类生命本体存在作哲学沉思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走向。韩少功创作之所以会呈现如此形态的轨迹,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小说观念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 《马桥词典》与外来文学思想源头
《马桥词典》甫一问世,便在沉寂良久的文坛和批评界掀起波澜,褒扬与贬抑之声,不绝于耳。贬抑之论中,声势之巨者莫过于“二王”的抄袭之说。当时王干与王彬彬分别著文,直指《马桥词典》属剽窃《哈扎尔辞典》的抄袭之作。由此而起的“马桥风波”,一度愈演愈烈,从文学事件演变为法律诉讼,最终以二王败诉才草草收场(关于事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文人的断桥——〈马桥词典〉诉讼纪实》一书)。有感于此,现代文学兼比较文学学者陈思和先生专门撰文,阐述自己鲜明的“挺韩”态度与立场。陈思和本着科学、严谨的学术精神,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从主题思想、创作风格和叙事技巧等方面,将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发表于《小说界》1996年第2期)与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译文发表于《外国文艺》1994年第2期)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马桥词典》并非是《哈扎尔辞典》的简单摹拟抄袭之作。不仅如此,陈思和在文中还高度肯定和评价了韩少功文学创作中的独创性精神,称《马桥词典》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1]陈先生上述所论,方法得体,言而有据,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我完全赞同。但陈先生在分析《马桥词典》受昆德拉小说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受《哈扎尔辞典》的启发时,将两者等量齐观,认为“无论是米兰·昆德拉还是帕维奇,其自称的‘误解小辞书’,‘词典小说’之名,只是代表了用词条形式来展开情节的叙事形式之实”,指出昆德拉“仅将词条展开的叙事形式夹杂在一般小说叙事当中,作为一般小说叙事的组成部分”,帕维奇“只是借助词条形式展开小说”,而有别于《马桥词典》的“小说的一般叙事服从了词典的功能需要”。[1]陈先生所说的这些,都隐秘地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昆德拉给韩少功的影响与韩少功受《哈扎尔辞典》的启发,恰似两只萤火虫发出的微光,亮度不相上下,凭感觉无法分辨出孰亮孰暗。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种种事实与迹象可以表明,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和文学创作给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施加的影响,远非《哈扎尔辞典》可以比拟。《马桥词典》受《哈扎尔辞典》影响的深度与广度,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只是停留于借用《哈扎尔辞典》“将词条展开形态融入一般小说叙事,以丰富原有的小说叙事方式”上,这样一种影响程度,与昆德拉给韩少功的教益相比,显然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为了更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我将运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法论,从《马桥词典》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者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内在关联,以及词典式叙事结构在两部小说中的实际功能两方面分别展开比较阐述。
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翻译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带有浓郁哲思性的小说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从而在中国掀起一股“昆德拉热”,以致在未逝世且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中,昆德拉是国内译介研究得最充分完整的一位。稍有当代文学常识的人便知晓,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热心并擅长将哲学思考与生存体验等理念性的内容融入小说实践中的作家,韩少功是其中禀赋突出的一个。试想这样一位对生活时刻保持敏感的作家,怎会放过从外国同行作品中汲取创作经验、获取创作灵感的机会?选择翻译昆德拉,便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为自己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译本所作的长篇序言中,韩少功毫不讳言自己对昆德拉的欣赏和赞许。需要特别指出的,韩少功对昆德拉的高度评价并非停留于浅薄的感性认同,而是建立在深入、全面且理性的理解与剖析的基础之上。韩少功在自己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长篇序言中,全面介绍了昆德拉其人其文,并且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对作品思想主题的理解,评论了昆德拉的小说艺术观念对当代小说文体发展的建设性价值。[2]韩少功对昆德拉的认识深度与广度,由此可见一斑。
二 《马桥词典》:昆德拉小说理论的实践
大量的事实材料可以佐证,韩少功谙熟并钦慕昆德拉深刻的小说文体思想和高品质的文学创作实践,这为前者在小说写作中向后者取法求经提供了便利和坚实的基础,何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的韩少功正处于文学生涯漫长的彷徨求索期。取法于外,是中外文学史上作家寻求突破的常见现象。事实也正如此,从文体观念和思想主题表达上看,韩少功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文学创作,均程度不一、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昆德拉的小说思想和创作。尤其是受到韩少功亲自翻译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影响和启示。《马桥辞典》以及后来的小说实践,清楚地表明他正沿着昆德拉指引的小说创作的前景,执着地踽踽前行。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通过对马桥——一个偏处湖南的村庄,抉取其日常词汇中有代表性的100多个词条予以阐释。这种阐释,或为一段关于乡间僻野琐事的回忆,或为作者头脑中因某物象的触动而引发的思绪表达,或仅为一幅人物剪影的素描图,以此实现他在《马桥词典·编撰者序》中希望实现的创作意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清理一些词在实际生活中地位和功能,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存在的密切关系,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3]。韩少功的这种创作意图付诸小说文本中的实践,正好与昆德拉一贯的小说创作理念,存在着某种惊人的契合。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一般不是源自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原型,他们“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简单说来,那隐喻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人类可能性,在作者看来他还没有被人发现或没有被人扼要地谈及。”[4]与此相契合,《马桥词典》中各种人物形象无不是依据作家头脑中闪现的情境、意象、隐喻等,加以选取、调遣和安排的。人物的活动,自然环境的状态,无不服从于对情境、隐喻等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往往表达了作家特殊的人生体悟与哲理玄思。为了揭示语言在马桥人生活中的惊人实践力量,韩少功选取“嘴煞(以及翻脚板)”这一意象,结合自己的人生体验进行了形象地阐释。在此词条中,复查因为骂了罗伯一句“你这个翻脚板的”,而犯了马桥弓的嘴煞,从此便长时期失魂落魄,最后几乎失去生存能力。为了挖掘语言背后隐藏着的马桥人的顽固心理结构与集体无意识,韩少功选取“科学”这一语汇进行了形象说明。马桥人因马桥弓出名的懒人马鸣,将省时省力的劳作称为“科学”,从而使他们深信“科学便是偷懒”这样外人难以理解的解释,以致在马桥人遇见科学的产物——公路上停车修理的大客车时,便不可抑制地产生不将大客车用扁担敲瘪则誓不罢休的冲动。马桥的每条特定词汇,都联系着一个特定的人,一个特定的场景,甚至关联着一个深刻的哲学思考。韩少功用故事的方式,在小说中发现了人们在日常体验中难以发现和揭示的秘密,这种小说观念与昆德拉可谓不谋而合。
当然米兰·昆德拉所倡导的小说哲思化理念,也被他身先士卒地在创作中进行了试验与探索,而且这些实验与探索中的某些细节,实可视作为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的契机。在韩少功参与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主人公托马斯与妻子特丽莎驱车到一个以出产矿泉水闻名的小镇游玩,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镇的街道、旅馆、疗养院等公共场所的名称在苏联入侵捷克后,被完全变更,几乎全部俄国化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虽然面对的仍是原来物质形态的小镇,但他们对往昔小镇的记忆和印象似乎因小镇各场所名称的变更而被统统没收,以致他们无法在小镇上过夜。物质形态上没有纹丝改变的小镇,因名谓的变更,便让小镇上的居民以及故地重游的旅客陷入了一种混沌而无所适从的状态。小说借助这一细节清除了人们头脑中认为语言只是虚空符号的狭隘观念,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语言的强大力量足可以令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维特根斯坦“人只能活在语言之中”的语言哲学理论,就这样被昆德拉创造性地用小说的叙事方式,给予了生动而形象的阐释与说明。昆德拉这样的大手笔不会不给当时已钻进寻根文学死胡同,正欲寻求新的途径,去缓解寻根文学危机的韩少功以莫大的启示。面对继续通过对僻壤民风习俗的展示,发掘传统民族文化的有限深度和广度;面对以方言俚语为突破口,揭示语言表层底下深藏的集体无意识和长期积淀而成的民族心理结构的无限光明前途,何去何从,聪明的韩少功自会做出决断。韩少功没有让我们久等,《马桥词典》以及随后问世的《暗示》告诉了我们他的选择。在这两部作品中正呈现出了韩少功借鉴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和创作实践,而做出的表现主题上的积极而有意义的探索与嬗变。[5]
其实,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还有其它一些情节表明,昆德拉正在进行用小说文体论证现代语言学某些理论命题。笔者认为,昆德拉的这种探索与尝试,被韩少功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小说创作予以了充分的发挥与拓展。昆德拉经常为人物活动设置特定的场景和境遇,以演绎自己对语言的独特理解。例如在《轻与重》中,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他对语言语义的理解:“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回展现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与新的意义混为一体”[2]。综观韩少功近十几年的创作,昆德拉在其小说里所进行的这些探索与实验,对他小说表现主题的转换和嬗递,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正如王晓明所言,韩少功正好借鉴了昆德拉身上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的部分,“那就是他(昆德拉)的那种沉入自己人生体验深处的创作态度”。[6]可以说,韩少功今天在文坛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正是奠基于他将文学的矛头沉入坎坷人生,尤其是他经历的那段刻骨铭心岁月的深层,并以开掘语言的内蕴与外延为突破口,传达其对传统民族文化与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与表达。
三 韩少功对昆德拉小说观念的拓展
事实上,在《〈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世界性因素之一例》一文中,陈思和只是从叙事结构上理解《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辞典》和昆德拉小说作品之间的影响与借鉴关系,那么,关于它们在表现主题上的传承启迪关系,便应在文章的主体论述之外。但这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陈文对韩少功与昆德拉之间关系所做的结论便稳妥可靠了呢?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仍然有其偏颇之处。即使是单从叙事结构层面上分析,《马桥词典》受《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影响,也绝不能简单界定在陈思和所说的,“《马桥词典》仅借用了昆德拉‘误解小辞书’形式之实”的狭窄框架内。在此,笔者无意忽视韩少功创作中的创造性因素,但当我们真正沉入词典式叙事结构在《马桥词典》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价值和功能的分析比较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便从屏障后面凸显了出来。
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部作品中的词典式叙事结构都是旨在有助于澄清文本中隐喻和意象背后隐匿着的与常情不相一致的深沉人生体验。前面已经提到,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仅仅源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昆德拉将源于情境、句子和隐喻的各种人物形象置于各种活动场景中,并让他们去尽情表演。他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挣脱作者主体意识的羁绊,他们的活动甚至成为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4]由作者已经历过的情境衍生出来的人物及其活动,却成为作者“没有意识到的种种可能性”。唯一可以解释这一点的是,昆德拉是在他的小说中,解读出连他本人也没有清楚意识到,但却真切隐匿在他意识暗区的深层人生体验,是在探究未受意识干扰的生命本体存在的秘密。明确这一点后,再去理解“误解小辞书”的形式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功能便会少却许多困难。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误解小辞书中的词条,如“女人”、“游行”等,实非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全可以仅仅视为帮助理解全书的补注,而将其置诸篇末。但作者非但没有这样轻率处理,与此相反,还郑重其事地将其融入整部小说的中心结构之中,担负起澄清隐匿作者心灵深处的人生体验的重任。只不过到了《马桥词典》中,词典式叙事结构作为澄清作者的人生体验的功能和价值,更为明确且更成系统地表现出来了。关于这一点,如不仔细辨析,是很难理解得到的。我想,陈先生之所以会做出《马桥词典》只是借用了昆德拉词典式结构之形的结论,大概渊源于此吧!实际上,韩少功新世纪以来的中短篇小说,从不同方面探索着昆德拉尚未实践的小说创作理念,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成为中国作家推动小说文体向宽广前景延展的成果,令其成为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当代作家。[7]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韩少功并非跟随昆德拉亦步亦趋,其创作表现出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创新价值。
[1]陈思和.《马桥词典》: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之一例[J].当代作家评论,1997(2):36-42.
[2]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韩少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2-11,89.
[3]韩少功.马桥词典[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2.
[4]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35.
[5]胡俊飞,李倩.寻根文学式微途中的自我调适——对《马桥词典的换位阐释》[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3):78-82.
[6]王晓明,夏中义.关于昆德拉与“昆德拉热”的对话[J].书林,1989(5):65-71.
[7]胡俊飞.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6-89.
Analysis Between Kundla and Han Shaogong——Comments from Chen Sihe
HU Junfei1,2
(1.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Yangtze Teachers College,Fuling,Chongqing 408100,China;2.School of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Maqiao Dictionary and Hint are Han Shaogong's transformation works which faced deep crisis from root-seeking literature's inner and outer.The invention transformation of Han Shaogong is apparently influenced by Kundla's novel theory and creation.Chen Sihe thinks Maqiao Dictionary,which elaborates learning from Kundla's dictionary of misunderstanding,is considered as one enlightening work.In fact,Maqiao Dictionary not only takes shape of Hazaer dictionary,but also fully understands connotation of dictionary structure.Maqiao Dictionary and Hint draw lessons from dictionary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successfully interpret life experience behind languag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daily experience,finally practice and develop Kundla's novel style conceptions.
Kundla;Han Shaogong;Maqiao Dictionary;Hint;novel style
I207.425
A
1674-117X(2012)01-0031-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06
2011-10-18
胡俊飞(1982-),男,湖北汉川人,长江师范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