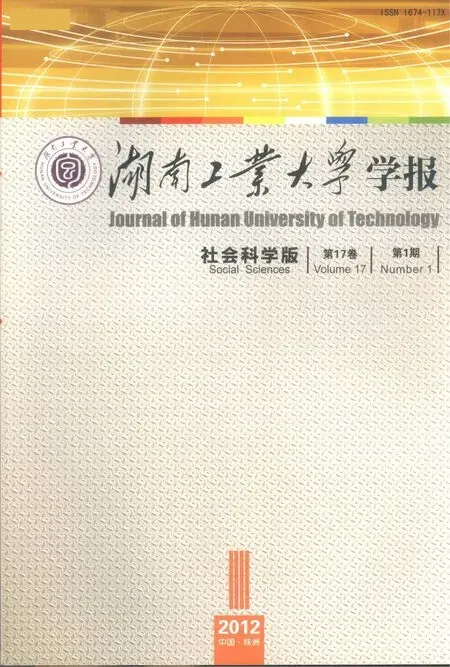从线性叙事到片断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文体探索*
龚政文
(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长沙410003)
从线性叙事到片断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文体探索*
龚政文
(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长沙41000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以《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对以跨界、杂糅、片断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型文体进行了自觉的、不懈的探索。这类韩式文体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散点结构、片断表达、自由组合、系列叙事、第一人称视角等共同特征,打通了短篇与长篇的界限,以主题一致、人物关联、独立成篇又相沿成列的方式,构成分散而又完整、看似无关实则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长篇系列作品。
韩少功;文体探索;散点结构;片断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中对文体进行了自觉的、不懈的探索。之所以说这种探索是自觉的,是因为韩少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与自觉的追求,这见于他的一些随笔和与王尧的对话之中;说这种探索是不懈的,是因为从《马桥词典》到《暗示》再到《山南水北》,体现探索成果的三部重要作品,跨越时间长达十余年。《山南水北》之后的一些作品,仍然体现出这种探索的势头。这种新型文体,其主要特点是跨界、杂糅、片断化。其跨越于小说与散文之间,杂糅哲思、叙事、抒情等多种文体要素,故事精彩又议论风生,人物鲜明又思想深刻;它打通短篇与长篇的界限,以主题一致、人物关联、独立成篇又相沿成列的方式,创造出分散而又完整、看似无关实则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长篇系列作品。用韩少功自己的话说,这种文体,是“在描述中展开思考”,“在碎片中建立关联”,[1]感性与理性,片断与整体,是有机统一的。本文仅从叙事方式上对此进行粗略的分析。
《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是三部长篇作品,但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三部与传统长篇小说、长篇散文面貌迥异的作品。传统长篇小说讲究人物一贯到底,情节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主线副线分明,中国古典小说和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大都是这种模式,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绝大部分也是这种写法,读者对长篇小说的心理预期和接受习惯也是如此。当前出现的一些长篇散文,如韩作荣的《城市与人》、贾平凹的《老西安》,都讲究整体性,结构紧凑,情绪连贯,一气呵成。韩少功的三部长篇与此完全不同。它们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散点结构。所谓散点结构是与焦点结构相对而言的。传统长篇有焦点人物和核心情节,作者始终以一种固定距离来塑造焦点人物,铺陈核心情节,再围绕焦点人物和核心情节来进行环境描写、背景烘托、次要人物塑造和副线展开,如同西方宏大的历史题材油画,焦点是清楚的,画面层次感是很强的,光线对比、景深安排都很讲究。但在韩少功这里,这一传统长篇的经典模式遭到了颠覆。《马桥词典》有焦点人物(绝对主人公)吗?没有,书中陆续出现了二三十个人物,都是主要人物,没有男一号女一号。这些人物有的着墨较多,有的一笔带过,有的形象鲜明,有的面目模糊,但作者对待他们的态度,并没什么分别,不存在哪个是哪个的陪衬,哪个又君临天下主宰一切。书中有核心情节吗?也没有。书中以词条的形式讲了很多故事,大都发生在马桥这个地方,以“文革”年代为主,但往上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往下可延伸到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一条核心的情节线,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与故事。这些人物与故事随手拈来,不经意中消失,没有精心铺排和气氛烘托,完全是随意的、即兴的、散碎化的,因此全书完全是散点结构。《马桥词典》如此,《暗示》同样如此。且不说全书对人生、社会、语言中的诸种现象的阐释与解读是分散的、随意的,一些篇章中出现的知青人物虽也构成一种谱系,一个群体,但没有哪一个是中心人物;这些篇章中所叙述的故事也大多只是为了用形象化的方式说明作者的理论观点,没有多少关联性、连贯性。可以说,《暗示》比《马桥词典》更散点化、平面化,更反结构、反中心。至于《山南水北》,本身是一部笔记体的散文作品,记录的是韩少功乡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当然更不会以焦点结构的面目出现了。
这种反线性叙事的散点结构,是韩少功刻意追求的。创作小说多年,他越来越反感那种有头有尾、起承转合的传统式小说。他不愿意按线性思维模式在一个统一的主题框架里演绎历史,他“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有很多出口和入口,读者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进来,也可以从任何一个门口出去。你经历和感受了这个公园,这就够了”。[2]可以说,《马桥词典》和《暗示》,就是这样的小说式公园。
2.片断表达。与散点结构相应的,是片断化的表达。韩少功思想缜密,学问渊博,表达能力出类拔萃,他并非不能写作较长篇幅的单篇作品。20世纪80年代的《西望茅草地》《爸爸爸》,21世纪的《兄弟》《山歌天上来》《报告政府》,都是很长的中篇小说。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随笔,动辄上万字;与王尧的一次即兴式对谈,整理后成了一本书。但在《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中,他有意对篇幅作了控制,一般也就几百千把字,长的不过万字。《马桥词典》115个词条,28万字,平均每个词条仅2 400字;《暗示》113篇,32万字,平均每篇2 900字;《山南水北》99篇,23.5万字,平均每篇2 400字。从这一统计数据来看,韩少功写的都是些超短篇,遵奉的是简约主义的原则,其中有些篇章堪称极简主义。如《暗示》的《电视剧》一篇仅一句话40余字:“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的很多电视剧,不过是一种有情节的卡拉OK:爱国与革命搭台,金钱与美女唱戏。”《山南水北》中的《待宰的马冲着我流泪》更是只有标题没有正文。蔡翔将韩少功的这种写作路数称为“片断化”,有人把它称为“微小叙事”(张均),韩少功自己也多次在与别人的对话中称这种叙事方式为“片断体”或“散碎叙事”。这表明,他是有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的。
古往今来,采用片断化风格的名作并不少见。例如以《论语》为代表的语录体,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对话体,以奥勒留的《沉思录》和纪伯伦的《沙与沫》为代表的格言体,以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代表的絮语风,以鲁迅的《野草》为代表的散文诗体,等等。韩少功的简约主义写作吸取了这些作品的长处,而又不是对其中任何一种的简单模仿,有着自己的独特风格。总的来说,他不以制造格言警句为目的,不刻意呈现那些高深莫测、云山雾罩的哲理,不特别追求诗化的风格和漂亮的文字,而是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世相的体验与思考。
韩少功沉迷于这种片断化、简约化的表达中,与当下某些作品的越写越长、越写越繁琐形成了鲜明对比。但总的来说他也并未刻意求简以至伤害陈情立意,而是当长则长当短则短。有些意思实在无法一篇表达清楚,有些故事实在无法一篇讲完的,他就采取续篇或系列化的方式表达。如《马桥词典》的本义系列、兆青系列、志煌系列、魁元系列,《暗示》的知青系列、“智识者”系列(大川、小雁等),《山南水北》的神医、剃头匠、野人、猫与狗等,都用了两篇的篇幅来叙述。
3.自由组合。三部长篇作品的每个单篇,其排列组合似没有一定之规,没有逻辑必然。据韩少功自述,《马桥词典》原来是按各词条的首字笔画多少排列的,这当然既没有逻辑联系也不可能体现故事脉落,后来,“为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落,也为增强一些可读性”,改变了排列顺序。现在的排列顺序体现的思路是:大体上前面几个词条是介绍马桥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习俗,中间部分是马桥“文革”中若干主要人物的系列故事,排后面的几篇是改革开放后的马桥人物。这种排列有了一定的时间线索和故事脉落,但也很难说是非此不可、不可移易的。最后两篇又回到了本义的故事和知青们刚进马桥时的情形,就是证明。除了少数几个系列故事有前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外,其余大多数词条都可以打乱排列,甚至象扑克牌那样洗乱也无不可。法国作家马克·萨塔曾经创作过一部扑克牌小说《隐形人和三个女人》(江伙生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每一页如同一张扑克牌,可以不断洗乱阅读,每洗一次呈现的面貌都不一样。《马桥词典》当然未走这么远,但词条的前后顺序是可以自由组合的。《暗示》虽分四卷:“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每卷有若干篇目,但其实这种归纳有点勉强,概念并不清晰,边界有点模糊。“人生”和“社会”能截然分开吗?全书其实每一篇都是对诸象隐秘信息的揭示,因此其前后顺序完全无关紧要,其自由度甚至比《马桥词典》还要高。《山南水北》也是如此,当然前三篇《扑进画框》《地图上的微点》《回到从前》是交代八溪峒的地理位置、风景特点和作者的回归缘起,但这三篇之下就没有多少固定顺序可言了。乡居的劳动、生活、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是片断式的、即兴的,并没有逐步深化不断递进的关系,因此也大可自由组合。
4.系列叙事。前面我们已指出,虽然总体上韩少功是片断化表达,但三部作品中也仍然存在不少系列化叙事的现象。这是因为韩少功作为一个小说家,虽然力图打破传统传统长篇小说的因果锁链和单一线索之弊,但他终究觉得人物和情节是小说的基本要素,终究控制不住讲故事和塑造人物的冲动。而其中一些故事和一些人物不是一个二三千字的片段能完成的,于是他将它们打碎安排在若干片段之中,细心的读者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阅读,便可得出完整的人物印象。
在这一点上,《马桥词典》的系列化叙事更多一些也更明显一些。其中的主要人物,都在不止一个词条(故事)中出现;而每一个稍微完整的故事,也都几乎不止一个人物在活动。万玉的故事,出现在《觉觉佬》《哩咯啷》《龙》《龙(续)》《下》中;马疤子的故事,出现在《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打醮》《打起发》《马疤子(续)》《荆界瓜》中;铁香、三身朵的故事,由《汉奸》《冤头》《红娘子》《渠》组成;志煌的故事,分散在《宝气》《宝气(续)》《双狮滚绣球》《三毛》《挂栏》《梦婆》中;兆青的故事,有《莴纬》《破脑》《津巴佬》《怜相》《朱牙土》《罢园》《飘魂》《懈》《黄茅瘴》;复查的故事,以《嘴煞》《结草箍》《问书》《白话》等篇为主。魁元的故事最为完整,也是唯一一个以改革开放后(或曰后知青时代)的马桥为主要背景的系列故事,包括《压字》《懒》《泡皮》《民主仓》《亏元》《开眼》《企尸》《嗯》等8篇。
当然,所谓系列性不光是以人物为线索,有时也可以表现主题或现象类别为线索。如《马桥词典》里的等级秩序观(《话份》《格》),性别秩序观(《红花爹爹》《小哥》《撞红》《煞》《月口》《不和气》),时间观生死观(《一九四八》《走鬼亲》《放转生》《贵生》《贱生》《散发》《火焰》《归元》《肯》)等等。《暗示》的主题线索更明显而人物线索更隐晦,因为韩少功本就把它定位为“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3]但通读全书,我们仍可以从人物的角度将之系列化。例如著名的独眼老木,就有《军装》《裸体》《红太阳》《鸡血酒》《生命》《母亲》《怀旧》《卡拉OK》《广告》《文明》《暗语·小姐》《潜意识》《伪善》《麻将》等十多个篇目,将他从小作为资本家子弟的被边缘化,到成为知青后的受伤成为独眼,到“文革”时的偷渡香港未遂,到改革开放后的发财、放浪形骸,为富不仁又善于作秀,事业成功而家庭不幸(妻子病死,儿子冷漠),再到组织参与知青返乡和知青聚会时的真情流露,将一个独特的知青形象生动丰满地树立起来了。小雁这个女性形象也在书中出现得比较多,《声调》《铁姑娘》《精英》《党八股》《商业媒体》《M城》《教堂》《暗语·革命》《医学化》等篇都是写她。从中我们收获了这样一个形象:曾经是铁姑娘,“文革”中发愤学英语,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成为知识精英,染上了精英病,但又不失女性的脆弱善良。天资聪明、风云一时但最终一事无成的大川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少一些,但形象也很鲜明(《朋友》《聪明》《观念》《学潮》《领袖》《消失》《麻将》)。其他如鲁少爷、大头、易眼镜等人物,也有系列化叙事来表现。不过与《马桥词典》不同,《暗示》的系列化完全散乱了,破碎了,需要仔细梳理和打捞才能理出一个大致线索。
5.第一人称视角,也就是“我”的视角。如果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都有一个且只有一个贯穿人物的话,那就是“我”。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综合三部作品,可以大略看出“我”是一个什么人:童年遭遇变故,下乡知青;后来回城,成为作家,经常参加知青活动;再后来因为对都市生活的厌倦和对乡村的喜爱,又皈依乡土,回到从前,季节性居住在距当年插队之地不远的地方,与明月为伴,与土地亲近,与农民笑谈,成为人们所熟悉的“韩爹”。“我”既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又是许多事情的参与者,即亲见、亲闻、亲历、亲为者。总的来说,“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叙述者,比较低调,不事张扬,甚少介入到事件当中,作品中很少直接对“我”的言行与心理活动揭示。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情况逐步有所变化。在《马桥词典》中,“我”直接出场并有所行动的,只有因为与兆青、房英、志煌、魁元发生过关系而不得不出场的少数几篇。其中对兆青、志煌的感念是因为“我”一次差点从楼梯上摔死看到兆青害怕着急得哇哇大哭,多年后我给了志煌婆娘一点钱而志煌居然背一段木头到乡政府来感谢我;与房英发生的故事在当年修战备洞的狭小空间里(其实没什么故事),但艰苦劳动中的青春期的“我”还是记得房英的呼吸、关心、出嫁时的失落与如今为兄弟伸冤的执着;魁元与我发生关系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他来到海口,不喜欢“我”为他找的工作反而惹事生非。在《暗示》中,“我”出场时候多些了,尽管仍然不是主角,但在许多知青活动中(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我”都是参与者、见证人,在美国还与小雁一起参加了一次迟到的街头革命,并由此与小雁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冲突。而《山南水北》,直接就是“我”在八溪峒的日常生活记录。
那么“我”究竟是谁?是韩少功?还是仅仅是第一人称?还是二者的结合体?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山南水北》中的“我”,当然基本可以和韩少功划等号。《马桥词典》和《暗示》中的“我”却有所不同。从两部作品中“我”的身份和经历来看,与韩少功高度契合,他有时在书中也借别人之口指称“我”就是“韩同志”,这表明,“我”有很大的自叙传的色彩。“我”的观点、思想、立场、情感,可以说就是韩少功的;“我”的事迹行状,则一方面杂取了诸多知青人物合而为一,另一方面又化身为诸多知青人物共同承担。韩少功曾在《暗示》的《附录一:人物说明》中作出这样的交代: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物都出于虚构和假托,如果说有其原型的话,原型其实只有一个,即作者自己。书中人物是作者的分身术,自己与自己比试和较真,其故事如果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曾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或者差一点发生在作者自己身上。何况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任何故事,包括某些作者观察所得,都受制于作者的理解、记忆以及想像,烙上了作者的印痕,无法由他人来承担全责。[4]
这里可能有某种规避法律风险的考量,但我相信也是韩少功创作时的真实想法。这在古今中外的大量第一人称叙事中,是非常独特也非常有意味的。在《暗示》中,一方面,韩少功放弃了单个知青形象作为表现主体的写作模式,转而将某单一主体分解为老木、大头、大川、小雁、鲁少爷吴大雄、“我”等为指称的主体碎片。“我”与老木们实为一体又不尽相同,后者是“我”的分身术,是“我”的影子,是如同毕加索立体主义绘画中人像的不同侧面,这可以极大地丰富知青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通过“我”与老木们的角色分设,作者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因为“我”既是当年的知青,又是现在的叙述者;既是诸多知青故事的参与者,又是知青群体前世今生的观察者、思考者;既神龙见首不见尾,又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分解后的主体恰恰形成了多个不同的视角和叙事载体,为文学表达提供了新的空间。韩少功可以通过主体分设后的不同视角来反观自身(也是反观整个知青群体),从而解决了单一角色的统一叙述可能带来的简单化、片面化、独断论问题,获得了韩少功所希望的既真实又扑朔迷离、既简约又富有张力的叙事效果。
为什么要采用片断体的叙事方式?韩少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表述。原因有三:一是对宏大叙事的怀疑。“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种‘宏大叙事’受到怀疑,这就出现了一种散碎化叙事,大概从罗兰·巴特就开始有了。现代主义小说不规不矩,把平衡美、完整美这些古典观念抛到一边,与读者的阅读习惯拧着干。但我并不能说‘片断体’是唯一正道。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采用片断体,恰恰可能是因为我还缺乏新的建构能力,没办法建构一种新的逻辑框架”。[5]二是对独断论的反对。“当然,这里也隐含着宁可犹豫、不可独断的一种态度。历史可能就是这样整合、破碎、再整合、再破碎,交替着向前发展”。[5]三是对焦点化叙事的不适应。“焦点结构……在众多历史现象中筛选出一个线索,筛选出一个主题,然后在这样的框架里演绎历史。也许我比较低能,经常觉得这种框架特别拘束、僵硬、封闭、不顺手,有些想写的东西装不进去,有些能装进去的我又不想要。一个贪官出现了,就必须把这个贪官挖出来,才能算完。一个将军成了主角,其他人物就只能成为配角,想喧宾夺主不行。情节主线之外的很多东西,顶多就只能作为‘闲笔’,点缀一下,没办法展开。这样,实际是小说在控制你,而不是你在控制小说。故事有它本身的逻辑,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滚,很可能构成一种起承转合模式。”[5]
韩少功在这里表达的,其实不只是一种个人偏好,他实际上指出了宏大叙事、焦点结构的一个重大缺陷。用传统的方式筛选主题、演绎历史、解释人物,隐含着独断论,同时又消解着作者的主体性,使作者也只能成为某种解释框架和小说逻辑的奴隶。甚至,这种文体的模式化强制,导致了作者的精神残疾,“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6]作为一个有着独立立场的知识分子,韩少功不愿意这么做。其实,中国最早的小说也不是这种面貌。韩少功在与崔卫平的对谈中指出:“古代笔记小说都是这样的,一段趣事,一个人物,一则风俗的记录,一个词语的考究,可长可短,东拼西凑,有点像《清明上河图》的散点透视,没有西方小说那种焦点透视,没有主导性的情节和严密的因果逻辑关系。”[7]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也有意反传统而行之,并深深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形成一波探索小说、实验小说的浪潮。到了90年代,文学界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作家向传统回归,向宏大叙事靠拢;另一部分作家继续走自我路线和探索风格。韩少功引为同道的史铁生创作了许多片断化的长篇随笔,如《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张承志创作了同样文体的《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等长篇系列散文,王安忆、莫言等也在不断进行文体探索。韩少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文体探索、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解决了食洋不化、凌空蹈虚、为实验而实验、为探索而探索的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一批实验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你可以不喜欢不习惯韩少功的这种文体,但你不能不承认,马桥是真正活生生的、原生态的中国南方乡村,《暗示》所指涉的,是“文革”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现实,而《山南水北》则可以从中可以闻到泥土的芳香、瓜果的清新,看到农人朴实的笑脸。
迄今为止,韩少功的文体探索仍在进行当中。他曾经宣示,“如果我不是太弱智的话,肯定也不会永远停留在某种叙事方法上”。确实,除了三部长篇的片断体外,进入新世纪以来,他陆续发表的一些中短篇都文体各异。《兄弟》《山歌天上来》《报告政府》三个中篇是传统式的;短篇《801室故事》通篇只是关于801室的两个文件,一个是装修方案,一个是搜查报告,却讲述了一个被害女人的故事;《方案六号》是一篇第二人称小说,通篇是叙述海外闯荡的某画家提供的自杀方案。这些都十分特别。2008年以后发表的几篇新作又有新的尝试,其中发表于《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8年第8-9期合刊的《第四十三页》是一篇希区柯克式的小说——当下的时髦球星阿贝阴差阳错地登上了一辆二三十年前的列车,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故事,过去和现在交错,小说和生活混淆,被批评家称为“颠覆常识的写作”。
我们期待着韩少功继续他的文体实验,有朝一日拿出更有份量的作品,让我们再次大吃一惊。
[1]韩少功.大题小作·文化透镜[M]//韩少功系列·大题小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28.
[2]韩少功.大题小作·文体开放[M]//韩少功系列·大题小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84.
[3]韩少功.我的写作是“公民写作”[N].南方周末,2002-10-24.
[4]韩少功.暗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93.
[5]韩少功.穿行在海岛和山乡之间[M]//韩少功系列·大题小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36-137.
[6]韩少功.文体与精神分裂症[M]//韩少功系列·在后台的后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41-342.
[7]韩少功.关于《马桥词典》的对话[M]//韩少功系列·马桥词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367-368.
On Fragment Expression from Linear Narrative——Style Exploration of Han Shaogong since 1990s
GONG Zhengwen
(Hunan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TV stations,Changsha,41003,China)
Since the 1990s,Han Shaogong uses new style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hybridity,fragments to pursue a conscious,unremitting exploration with a series of works,such as“Ma Bridge Dictionary”“Suggestion”,“Shannan Water North”.This Korean style,with feature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of scattered points,fragment expression,combination freedom and narrative series,first-person perspective,breaks through a boundaries of short and long novels and composes the dispersed and complete form,seemingly unrelated but in fact an inherent logical structure of a long series of works by a style of consistent theme,characters associated with a separate chapter and bent along the way into the columns.
Han Shaogong;style exploration;scatter structure;fragment expression
I207.425
A
1674-117X(2012)01-0025-06
10.3969/j.issn.1674-117X.2012.01.005
2011-12-02
龚政文(1966-),男,湖南益阳人,湖南广播电视台研究人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评论及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