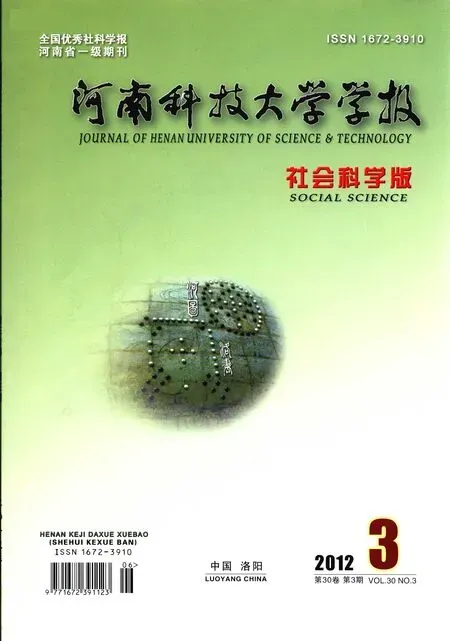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张文静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河洛文化】
杜甫陇右诗与盛唐晚期审美文化风尚
张文静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甘肃 天水 741001)
杜甫陇右诗在主题趣味和艺术风貌上展示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与诗人的现实经历与处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息息相关。杜诗里诗学精神的变化也对中晚唐乃至宋代的诗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甫;陇右诗;审美风尚
杜甫创作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冬的117首陇右诗,是整个杜诗中相对独立的模块。其中呈现了杜诗思想艺术的重要新变:内容上,此前杜诗注重对外在社会生活的反应与干预,流寓陇蜀期间则更多地转向了对文人内在宇宙精神、心理感悟的表达;艺术形式上,陇右诗呈现了意象怪异、意境险绝、音韵折拗、风貌多样等特点。这些变化固然与诗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个人身世遭遇有直接关系,也与当时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文化风尚有间接关联。
综观中国传统社会,审美文化风尚的根本转变在中晚唐时己经浮出水面,至宋则全面凸显。中晚唐时,文学艺术审美精神逐渐由开放外向转为收容内敛、由阔大转为精细,各类艺术普遍呈现出注重心灵感悟的内在追求。因此,整个文艺思想也突出地展示了审美风尚的变迁趋势。李泽厚说:“(中晚唐)它不像盛唐之音那么雄豪刚健、光芒耀眼,却更为五颜六色、多彩多姿。各种风格、思想、情感、流派竞显神通,齐头并进。所以,真正展开文艺的灿烂图景,普遍达到诗、书、画各艺术部门高度成就的,并不是盛唐,而毋宁是中晚唐。”[1]144杜甫流寓陇蜀期间,正是盛唐的辉煌走向没落之际,他早年感受到的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豪壮的意境正在渐行渐远。因而其陇右诗所呈现的精神内容与意境,与开元年间、天宝初期完全不同,除了外在的社会原因,审美风尚的变化也是其内在的变迁趋势。盛唐晚期独特的时代审美风尚催生了一些经历过盛唐巅峰时刻的作家作品内涵的变化,杜甫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得风气之先的诗人。其作品中涌动着盛唐普遍的时代精神与艺术精神,乾元间的陇右诗和入蜀后的诗歌里面,也明显呈现出了盛唐诗歌美学向中唐诗歌美学的新变。
一、陇右诗的艺术新变
杜甫于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离开陕西华州西向秦州。此时诗人经历了现实的种种苦难,早年强烈的外向型现实精神渐变为对社会问题、自我命运、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其陇右诗,在主题内容、意象选择、形式结构、审美风格方面均有明显的变化,除了与诗人的经历、年龄、现实处境相关外,本质上也是一种美学性的变化,它与盛唐晚期追求的注重内心体验的独特审美风尚有间接关联。此时的唐诗艺术中,盛唐余波虽在,然而部分诗人的作品在主题内容、艺术风貌方面都已有了新变,尤其是杜甫,其陇右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呈现出的变化是具体而鲜明的。
(一)主题趣味的新变
流寓陇右的三个月,是杜甫一生中极为艰难的时期,在饱经战乱、内忧外困的间隙中,诗人对自己多年来的思想经历、自我追求、以及社会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整理。因此,陇右诗中展现了杜甫复杂、矛盾、动荡的内心世界。从题材上看,杜甫陇右诗主要有咏物、纪行、遣兴抒怀、寄赠怀亲等类型,诗人在对外在社会现实进行把握的同时,更多地通过诗篇发掘与探索复杂多元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咏物诗,选材趋于琐细、凡俗,意象审美趋于心理体验,逐渐呈现出以小见大的审美思路,与前期诗歌主题直呈现实、壮阔大美有着明显不同。
如《铜瓶》、《蒹葭》、《促织之二》这三首诗所选取的意象虽很细小,但以小见大,隐喻意味比较突出。“铜瓶”承载了诗人对国破家亡的无限哀婉,寄托着自己的历史兴亡和身世遭遇;“蒹葭”柔弱且遭秋风侵袭,但洁身自好,末句隐含着浓郁的宇宙之叹;弱小而平凡的“促织”哀音声声,与诗人悲痛的内心世界十分吻合。这些诗歌感情抒发深沉内敛,含蕴着一种高洁、兀傲的审美情绪。再如《苦竹》《新月》《废畦》《病马》等咏物诗,在主题意象上均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转型,即通过日常凡俗的题材,表达精细幽微、复杂深曲的美学趣味。其中“苦竹”“废畦”“病马”等意象复杂多元的象征意味耐人寻味,呈现出了与前期诗歌完全不同的审美风貌。
《佳人》以深居幽谷、遗世独立的“佳人”为核心意象,具有深远的隐喻性。在整体隐喻中又有修竹、翠柏等局部的隐喻,将自己的遭遇、体验、叹息深深地融入其间,诗意结构中呈现了一种由外而内、由浅而深的思维特点,十分符合当时艺术领域内意蕴浓重、寄托深远的美学趣味,与早年所写的直抒胸臆的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作于天宝七载,是杜甫长安困守时期求人援引的一篇作品。诗中融入简洁的叙事与直接的抒情,虽也将自己的身世经历融入其中,但没有深曲、宛转的暗示与象征,尤其结尾句气势雄壮、恰如一峰突起直截了当,风格清晰透彻,与盛唐时豪迈、自信、灵动的时代审美风尚完全契合。而陇右诗所呈现的主题趣味的变化,与当时社会大变迁时所追求的个性、怪诞、深邃、繁缛息息相关。它渐渐影响着诗人的审美理念,审美风尚渐渐潜形于这个发生巨变的时代,当许多作家还没有来得及品味和琢磨时,杜甫已经从容地在诗歌中体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二)艺术风貌的新变
杜甫陇右诗中延续了天宝年间的“诗史”式思维,在复杂特殊的地域、历史人文环境中,呈现出更为险怪奇绝的艺术风貌与深蕴的悲剧情调。诗歌通过独特迥绝的转化,走向了折拗、深曲、险绝之境。这是历史环境与审美风尚催生的产物,一些诗句的锤炼也鲜明地呈现出美学精神的新走向和新风貌。
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人以精心锤炼的诗句表达了对外在景物与自我精神状态的奇异体验,“微、瘦、干、腻、萧萧白、片片黄”等语虽然生新、突兀,但极为细腻深曲地表达了作者的独特体验,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直抒胸臆相比,体现了陇右诗独特的审美风貌。再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仪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等,诗中以拗健的描绘和深曲的典故,将内心遭遇和对朋友诉说时的心灵激荡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与王勃、陈子昂、李白、王维、孟浩然等人相比,此时的杜甫深深地触摸着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焦灼与痛苦,不再外向热烈地高歌,只是内敛深沉地低吟。陇右诗中的“遣兴诗”与此前纪实、直陈社会现实的作品相比,更多地通过写景咏物或感兴自然、宇宙、历史来抒发内心情怀。诗人将文人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和对自我和宇宙时空的感叹交织在一起,使诗的内在意义更为凸显。
在《遣兴五首》中,诗人不是咏物或写历史,纯粹是表达一种内心的感觉或感叹。“兰摧白露下,桂折秋风前”的寒凉引动的愁绪,“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中古人的遭遇牵动的感叹,“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的时事悲慨激荡的痛苦,都使诗歌的审美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这些诗歌是作者对一时一地瞬间情绪的全面把握,至夔州所写的《秋兴》八首,便将这种感兴自然和命运的感觉与深沉的心理思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种诗学精神的变化,使杜甫陇右诗中的意象意境发生了连锁反应。这种变化归根结底是在时代政治变化与审美风尚变迁的双重影响下完成的。稍后韩愈、孟郊、李贺等人诗歌精神的质实、意境的怪谲、句法的奇异、审美的峭拔等,都是源自杜甫。
杜甫的陇右诗,一方面气势恢宏,如乾坤、天地、日月、百年、万里等词语的常用,表达了盛唐精神的巨大内涵;另一方面,作品选材出现了新的倾向,如物象渐趋琐细、渺小、残破等,表达了时代变化中新的气象和审美风貌。这便是李泽厚所说的“不一样的盛唐”,也是本文所说的盛唐晚期审美风尚主导下的诗风变迁。
二、审美文化风尚对陇右诗的影响
杜甫陇右诗呈现出来的审美新变与盛唐晚期的审美风尚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大动荡的年代,渗透着盛唐时代的恢宏壮丽,又迸发了中晚唐艺术精神的精致、复杂,内敛。因而,杜甫陇右诗中的审美新变是在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凸显出来的。
唐代的历史分期与文学文化史的分期之间稍有差别。文学史上一般认为,盛唐时期指开元初至唐代宗大历初年(公元713-766年),这一阶段是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走向全面繁盛但同时又潜伏变化趋势的时期。在文化发展走向上有研究者认为,武则天光宅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684-755年),是唐代文化最繁盛的时期。[2]然而,在审美风尚变化的过程中,无论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社会发展以及杜诗变化的表象等角度,都可将杜甫生活的后一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后至流寓陇蜀之间的阶段称为盛唐晚期。整个时代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渐露头角的新的审美气息得以凸显,这种气息与盛唐的恢弘壮阔接续起来,形成了盛唐晚期独特的审美面貌。它清晰地体现在雕塑、建筑、服饰、乐舞、诗歌、绘画等艺术门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新唐书·五行志一》云:“元和末,妇人为圆环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3]中唐时期审美风习呈现出来的鲜明变化,其实在盛唐晚期已经崭露头角,盛唐前期各类艺术中展现出来的雄浑、壮阔、简洁、浪漫的审美气息,渐变为精细、尖巧、繁缛、质实。作为诗歌艺术,势必会受到这种审美环境改变的影响。杜甫开元年间与“安史之乱”前后诗歌风貌的变化,不仅与诗人的年龄、经历相关,更与审美环境的微妙转型相关。有学者认为:“尽管‘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社会的转折,但是千仞高峰并不会在瞬间便跌入万丈低谷,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绝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经一个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抱负和理想……由于信念未泯、真气犹在,因此审美文化的创造反倒因时代的激变而摩擦出耀眼的光芒。于是,在玄宗、肃宗、代宗三位皇帝所统治的70年里,我们不仅看到了雍容典雅的盛唐,一个色彩斑斓的盛唐,而且看到了一个临危不乱、沉郁雄强的盛唐。”[4]48
的确,同是盛唐时代但前后期的精神状貌是有区别的。杜甫陇右诗创作所呈现的审美变化,也是审美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当某种风气发展到一定限度时,必然要寻求新的突破以重立规范。李泽厚认为:“(李白诗歌)达到了盛唐浪漫主义的极峰,它只是一个相当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典范阶段。那就是以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其实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1]131而陈炎则认为:“杜甫诗虽不及李白诗的宏伟瑰丽,不及王维的含蓄、隽永。但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在危难面前从容不迫的阳刚之气。所以,我们不能接受那种将杜诗排斥在‘盛唐之音’以外的做法,而应将其看成是‘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4]145这里所说的“另一种盛唐”和“盛唐之音的第三重旋律”也都明确地表达了盛唐时代不同阶段的不同审美风尚对杜甫诗歌的影响。
具体而言,杜甫流寓陇蜀期间诗歌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由外在描绘转向内在感悟的变化,在稍晚的诗人作品中也有鲜明体现,如岑参、元结、刘长卿、顾况、李益、韩愈、孟郊等的部分咏物、纪行诗。杜甫得风气之先,敏锐地捕捉了艺术的变化,因而陇右诗中呈现出杜甫诗学美学精神的变迁,由对社会历史的描绘转向了对社会历史、自我人生内在精神体验的审视。反过来,追求个性、怪诞、深邃、繁缛的审美倾向渗透在杜甫的诗歌中,杜甫积极敏锐地将它展现了出来,这两者相依相辅,体现了审美精神由外而内的沉潜。诗人在盛唐由盛转衰的变迁中,自觉积极地通过诗歌实践呈现着时代审美的种种变化。
三、杜诗新变对后世诗学精神的影响
作为得风气之先的诗人,杜甫陇右诗中呈现的诗学精神变化不仅与盛唐晚期审美风尚的变化有关系,并对中唐审美风尚进一步改变具有开启意义。中唐是一个动荡不安、文化裂变的时代,当盛唐自然、清新,充满活力与浪漫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寻求新的审美突破,在动荡的外部条件下,艺术家们试图让自己的内在情绪在认可与反思中找到一条合理的途径,因而别致、怪诞、精细便成了中晚唐艺术家共同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精神在杜甫安史之乱后与流寓陇蜀的部分诗歌中都有呈现。那么,杜甫的陇右诗自然具有了承前启后的特殊性:盛唐气象犹在,中唐精神初始。裴斐在《杜诗八期论》中对杜甫陇右诗的分水岭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窃意当以秦州划线分前后,前后又各析为若干期,共计八期。”[5]这种诗学美学精神变迁的主要意义在于,杜甫以自己敏锐独到的对社会人生的体察能力,全面地总结了一个繁盛年代恢弘壮阔、浪漫自由的艺术精神,而又积极地探索着新的创作规范和艺术风气,因而他又开启了另一时代所追求的新鲜、独特的诗歌艺术审美风尚。
从这个意义来说,杜甫便是盛唐向中唐转型过程中承前启后的大诗人,其诗歌艺术中意境生新、音韵险绝的审美风尚更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从中唐诗歌至宋代江西诗派出现的漫长过程中,杜甫一直是宋代诗人、尤其是江西诗派所尊崇的诗家之祖宗,而追求险绝、瘦硬、生新一直是宋及宋后诗歌艺术家的创作倾向,诗人们对一些琐细、凡俗、狭小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进行把玩与吟咏,对格韵高绝的艺术境界击节叹赏。如韩愈、孟郊、白居易、李贺、王禹偁、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人的诗歌,在选材的琐细和诗风的险绝程度上是盛唐诗人所无法实现的。这种诗歌艺术结构的变迁在杜甫陇右诗中的一些咏物诗和纪行诗如《初月》、《萤火》、《促织》、《废畦》、《除架》、《空囊》中,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此外在诗歌体式上,杜甫陇右诗《秦州杂诗二十首》《遣兴五首》和大量的五言排律,以及著名的《同谷七歌》,这种组诗、连章体例对中晚唐及宋代诗人的影响也很直接。如元稹曾作《春深二十首》、白居易则作《和春深二十首》,姚合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皮日休作《太湖诗二十章》等,以及元稹的《代曲江老人百韵》、《梦游春七十韵》,刘禹锡的《游桃源一百韵》,白居易的《东南行一百韵》等一批长律,宋代范成大《使金纪行诗七十二首》、《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等等。
在新的审美风尚影响下,诗歌艺术也渐趋复杂繁缛,从内容到形式,杜甫陇右诗均呈现出这种变化。时代审美风尚对杜诗的习染是偶然的,但也是时代精神、诗歌精神与审美精神多重酝酿变化的结果。正因如此,李泽厚所说的“不一样的盛唐”,也是本文所说的在盛唐晚期审美风尚主导下的诗风变迁。这种变迁的承上启下意义确定了杜甫在整个盛唐诗坛,乃至中国古典诗坛中的地位与价值。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144.
[2]李斌城.唐代文化: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五行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71.
[4]陈炎.中国审美文化史:唐宋卷[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48.
[5]裴斐.杜诗八期论[J].文学遗产,1992,(4):27-39.
Du Fu’s Longyou Poem s and the 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of Late Tang Dynasty
ZHANGWen-ji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 741001,China)
Du Fu made some important changes in his Longyou poems on the theme of taste and artistic style.These chang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his real experience and situation,and to the unique 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s well.The changes in Du Fu’s poetic spirit have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rt of poetry in the late Tang and even in the Song Dynasty.
Du Fu;Longyou poems;aesthetic culture fashion
I206.2
A
1672-3910(2012)03-0013-04
2011-12-08
张文静(1975-),女,甘肃天水人,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