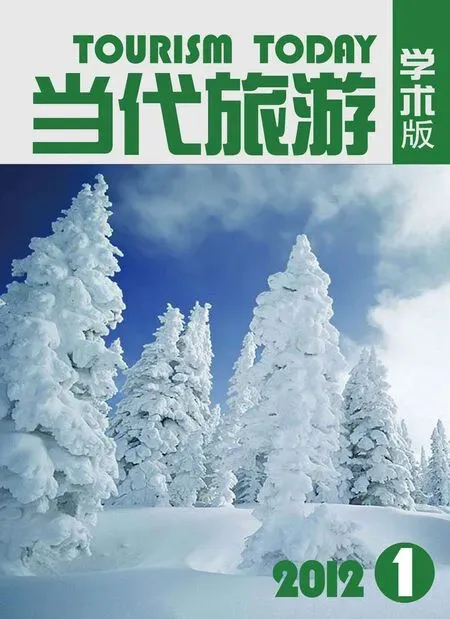清至民国人口流动背景下的黑龙江地区饮食文化考察
郑南
清至民国人口流动背景下的黑龙江地区饮食文化考察
郑南
人口流动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同族群间文化交往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自然也是如此,这种交往既有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今日中国版图内部的,也有域外族群与地域相互间的。清至民国的垦荒移民、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大规模"闯关东"移民;二十世纪初以来,欧洲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十余个民族上流人群的移入,犹太人的避难迁徙;日本关东军与开拓团的进入以及对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因此,可以说战争、掠夺、俘虏、移民、殖民所带来的人口流动是历史上黑龙江地区文化交流的典型特征,忽略这些历史因素,对黑龙江地区的饮食文化就无法深刻理解和准确说明。
饮食文化,黑龙江,人口流动,移民,殖民
一、清至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的人口流动
(一)黑龙江地区多民族杂居的历史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黑龙江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自古以来,黑龙江地区就是少数民族的杂居地,也是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地,如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先民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鲜卑、契丹、满等。这些民族曾经数次在中国的版图内建立过割据的地方政权,并有两次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对中国的近现代社会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数民族人口的不断南下,对于中原地区带来的影响不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故此省略。
黑龙江自古以来的多民族杂居,是形成区域文化多元特征的历史因素。这种多元性在黑龙江居民的饮食生活中同样表现的非常鲜明。
黑龙江地区的少数民族以游牧为主,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一直是相伴而生的。在生存压力并不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但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和虽然缓慢但仍然不断增长的人口使生存压力变大时,则战争与掠夺就成为其获得生活资源最为便捷和省力的方式。按照中国文字史记录,若不将夏、商、周三代考虑在内,则自秦始皇创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之后,中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民族历史是在政治分裂和军事对抗状态下度过的。即便是在大一统的王朝中,北方草地民族和平与对抗形态的南进也是频频发生的,故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一直是北中国,甚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势。
战争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战争的进行,胜负只是历史瞬间的事,而文化之间的交流却具永恒性。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进行的战争使得一方面中原地区的文化吸收了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为自身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另一方面,对于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在与中原地区进行战争的同时,也是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的过程。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原地区进行的战争最多、接触的也最多,而被同化的也最彻底。这种情况直到两宋时期经济文化中心转移到南方后仍然在继续。
(二)关内汉族移民的移入与文化的不断融合
相对于中原而言,黑龙江作为边疆地区,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人口迁移相当频繁,总的趋势是北部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南下,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北上。
汉族人口何时迁入黑龙江地区,史料上没有过明确的记载,但通过近年来对黑龙江地区移民史的研究得知,汉族人口迁徙黑龙江的历史至迟可上溯至辽代。1956年,在黑龙江省泰来县塔子城出土的一块辽大安七年(1091)的刻石的残存部分上记有四十七个汉族人的姓氏,证明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就有一定数量的汉族人聚居在黑龙江地区。
从清至近代内地汉族向东北的移民几乎没有中断过,并经历了清末、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三次移民高峰。清末的移民高峰主要是伴随清政府开禁放垦而来的。一方面,华北各地人地矛盾凸起,旱涝虫灾多发,山东、河北灾民闯关谋生者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清政府为移民实边抵御沙俄侵略和依靠民垦增加收入,从1860年开始陆续开禁放垦黑龙江和吉林的一些地区,吸引了大批移民。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移民高峰,其主要原因是1920~1930年间,关内人口压力不断增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加上1927、1928、1929关内发生罕有的灾荒,而此时东北作为“新大陆”,其农业和工矿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所以河北、山东、河南灾民纷纷到东北谋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永久占有东北,实行抑制关内人口流入东北的政策。直到1938年随着战局的改变,日本急于开发东北的战备资源,迫切需要劳动力,方才鼓励乃至强迫关内人口迁入东北,形成又一个移民高峰。
1840年时,东北地区的人口为300万人左右。从1840年至19世纪末的近60年时间里,东北人口数翻了一番,达到600万人。①参见《中国人口(辽宁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中国人口(吉林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清末做过的一次全国人口统计显示东北三省人口总数为1977.7万人。[1]比十九世纪末,人口数增加了两倍多,十几年间净增1300多万人。到1930年东北人口数达到3008.68万人。与清末的1977.7万人相比,又经过20年的时间增加了1000万人,平均每年净增50万人。到1940年时,三省合计人口数超过3600万人。与1930年相比,经过10年净增600万人,平均每年净增60万人。1945年的三省合计数显示三省人口数已达到了4000万人。近代从1893年到1945年的50年左右的时间,东北三省的人口数增长了近6倍,平均每年净增人口65万人以上。可以看出,东北近代人口变动的特点是人口持续猛增。近代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猛增,移民人口数量多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殖民统治背景下的外国移民
1.俄国的进军中国东北与移民
独占中国东北、与日本争夺朝鲜、称霸远东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的最高目标。为此,沙俄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强行割去中国东北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迫满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俄国趁机调动数十万大军保护边境和西伯利亚铁路。1896年6月3日,沙俄与清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密约》,使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取得了一系列特权,为俄国移民创造了客观条件。
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以十月革命为分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月革命前,是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及其延续;十月革命后,主要是大量溃逃到东北的俄国政治难民。
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己经进行了长期的殖民渗透。沙俄在强取了修筑穿越中国东北并南伸至大连的中国东北铁路及地段内的行政主权后,将路段视为其殖民地。到1900年前后,已有近5000名俄国武装以护路为名,进驻黑、吉、辽三省重要的交通在线,这中间还包括一定数量的俄籍犹太人,加强对中东铁路沿线的保卫。[2]俄国军事部门在中东铁路沿线筹建了士兵村,给予各项优惠政策,以鼓励退役士兵移民士兵村。[3]1903年7月,中东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在客观上为黑龙江地区外国移民的迁徙带来了便利的条件。进入东北地区的大批俄商不断创办工商企业,使这一地区的俄资加工业得到急剧发展。同时,沙俄对中东铁路沿线的林业、矿产资源大规模的破坏性开采,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大量俄人纷纷到来。
由于沙皇政府的积极支持和中东铁路当局的配合,俄罗斯人移居路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义和团运动之后至日俄战争爆发期间,移居路区的俄国居民仅3.4万人(不包括军人),但日俄战争以后至十月革命前的几年内,路区俄国居民猛增至20万人。[4]如在哈尔滨,1912年俄国移民为43 091人,是年哈尔滨的总人口为68 549人,俄国移民占63.7%。[5]1916年哈尔滨约有7万名居民,其中俄国人就占了3.4万名,将近一半。[6]
另外,俄籍犹太人迫于俄国的排犹政策而逃离俄国,寻找能够改善其生活环境及实现到远东处女地淘金愿望的处所,中东铁路的修筑及沙俄的对外扩张政策无疑为俄国犹太人移居中国东北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17年,十月革命后,东北地区的犹太人迅速增加。至1919年哈尔滨的犹太人增至1.5万人,达到鼎盛时期。大批的犹太商人活跃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广大地区,从事木材、大豆、矿业、油料、毛皮等商业行业。当时的哈尔滨成为远东犹太人聚居的中心。[7]
1920~1922年,被俄红军击溃的白匪残部、家属及一些其他俄国公民通过陆路及海路两个方向进入中国。数千名难民经满洲里进入黑龙江地区,其过境后就定居在中东铁路沿线一带。
进入中国的俄国难民中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中,俄罗斯人占86.5%。[8]在俄侨中,沙俄时代的高级军官、大商人、高级文职官员及其家属能占移民总数的2.35%,在满洲里俄国移民中,贵族及沙俄高级官员、大商人、大企业家占到5.95%。[9]据伪满洲国警察部门统计,到1940年底,中国东北地区共有俄侨61403人,其中男性侨民有31 020人,女性30 353人。[10]
2.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和移民政策
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对中国东北原属俄罗斯国的殖民利益和特权,逐步开始了对中国东北这个新殖民地的一系列统治措施。移民始终是日本的“满洲政策”重心之一。日本通过《通商行船续约》(1903年)、《东三省事宜附约》(1905)、《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1909)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将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地相继开放,准许日本商人在这些地方居住和贸易。日本不仅在实际控制区完全掌握了殖民权力,而且在非实际控制区也渗透了殖民势力,为下一步的殖民扩张和移民做好了准备。
殖民初期的移民构成主要是农民和商人。据统计,1914年黑河镇就有日本人开设的药铺、理发所、旅馆、成衣铺、妓院31家。漠河镇也有日本妓院13个、理发所1个、医院2个。在满洲里、安达等地也都有日本移民经商。1924年,满铁在黑龙江开设的“北满贸易馆”,分支机构遍设于齐齐哈尔、海拉尔、海伦、宁安、依兰、牡丹江、佳木斯、富锦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移往东北的人数,1911年达至79,763人,1912年升至85,406人,至1913年10月则为90,548人。至1915年,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数增为101,565人,到1919年,在“关东州”和南北满各地共有日本人181,000人。[11]另据1928年的统计,当时在东北定居的日本人总数近20万人,而农业移民仅1061户,约3000人,这个数字仅占当时东北人口的1.5%。[12]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据英国学者克尔比在《满洲国的经济组织》中得出结论为整个东北是24万人左右。[1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全境,开始大规模的向东北地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的移民。1936年“20年向满洲农业移百万户计划”正式启动。到1936年7月,日本共组织了五次移民。从地理分布上看,大部分集中在北满的三江省和滨江省。
3.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向中国东北的移民
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历史上,来自于朝鲜地区的移民一直不断,但这种移民基本上是自发形式的,此外,包括一部分战俘和“被掳掠者”迁入的。日本实施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后,移民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阶段的朝鲜移民作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服务于日本对最新殖民地的开发政策,将“老殖民地”人口向“新殖民地”有组织、有规划的迁徙。这其中,被迫和被动的移民是主流,自然流动和主动移民也依然存在。
(1)“自发”移民
日本吞并朝鲜后,有大量的朝鲜人因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不甘心当亡国奴,迁入东北。据不完全统计,1910年迁入鸭绿江以北的朝鲜族有98657人,迁入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族也有93883人,共计192540人。1911年有256900人,1912年增至27万左右,1917年达358000人,1918年达到402969人。1919年朝鲜爆发“3.1”运动后,又有一批反日志士为躲避追捕移民东北,致使在东北的朝鲜移民迅速增加。1929年中国东北有朝鲜族597677人,到1931年增长到630952人。[14]
朝鲜人自发迁入东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国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启动了开发高潮,为朝鲜移民的大规模移入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和广阔的地域空间。在日本彻底占领东北以前,民国政府极力提倡和鼓励督垦,使得东北新垦区对劳动力的需求猛增,大批朝鲜移民便涌入东北。
(2)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移民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了把朝鲜移民培养成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尖兵,有利于帝国对满蒙的国防、经济上的统治,便于为日本国民开拓满蒙处女地打下良好基础,日本殖民政府一直奖励朝鲜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把东北彻底变成了殖民地,日本人对朝鲜移民的态度更加明确和积极,强迫朝鲜国内人民有组织的迁移到东北,成为这时期的主要移民政策。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殖民地统治矛盾的激化,朝鲜本国的统治者也倾向于把朝鲜人输送到东北。为了把朝鲜国内的矛盾向外转移,日本殖民当局大批将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制定出15年内移植100万户朝鲜人的移民计划。朝鲜总督府和伪满洲根据《在满鲜人指导要纲》,强迫朝鲜破产农民移居东北,并设立“满鲜拓植株式会社”以管理朝鲜移民工作,并确定东北境内的30个县为移植区,计划从1937年开始每年从朝鲜移民1万户。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4年,被日本强制移民到东北的朝鲜人达30856户、147744人。[15]这是东北朝鲜移民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45年,东北的朝鲜移民增长状况大致是:1910~1918年为21000人左右;1919~1930年为17000人左右;1931~1936年间为41000人左右;1937~1945年间为147744人左右。[16]
殖民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领域的渗透,使东北地区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从小区规划到城市建筑、从宗教信仰到民间习俗等各方面,无不渗透着殖民侵略的色彩。哈尔滨成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及开埠后,便由一个古老的村镇迅速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城市转化。又如安东县开埠通商后,除“韩日外侨,欧美接迹而来者,各有其人”,[17]1907年4月有日本人1 533户,4 895人;中国人2 680户,6 238人;其他国家12户,18人。1909年调查安东新市街有宅地173 000余坪,农工用地68 000余坪;人口共3204户,7 239人。有日本领事馆、警察局、陆军经理部、小学校、实业学校、幼儿园、清语研究会、同仁医院及医学校、布教所、日本基督教会等。[18]可见,清末东北多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结构的形成,是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又受外来文化熏习的结果。
二、17世纪中叶以前的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记录
据《后汉书·挹娄传》载:肃慎、挹娄“有五谷,……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19]《三国志·挹娄传》、《通典·挹娄》记载略同。说明肃慎、挹娄的食物来源除来自采集、游牧、渔猎外,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与发展水平的的农业生产。肃慎、挹娄时期的人们已能饲养马、牛、猪,尤其养猪为挹娄人所擅长。此外,因“土无盐铁”,故先民们采用“烧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20]的方法来自制盐。其方法是选取含盐分较高的树木,砍下来,将其烧成灰,然后用水浸泡,将其中的盐解析出来食用。
《魏书·勿吉传》载:勿吉、靺鞨“其国无牛,有车马……有粟及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酿酒,饮能至醉。……善射猎”。[21]《北史·勿吉传》载:勿吉、靺鞨“所居多依山水……其国无牛,有马……土多粟、麦、穄,菜则有葵。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亦有盐池。其畜多猪,无羊。嚼米为酒,饮之亦醉。……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22]《通典》亦有同样的记载。
勿吉、靺鞨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进步。这一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麦和穄。粟在我国的农作物种类中曾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我国早期种植的主要作物品种。而“麦”,则应该主要是荞麦。荞麦是一种耐高寒的作物,在东北地区和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均为常见农作物。“穄”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糜子。与肃慎、挹娄不同的是,勿吉、靺鞨居地内已有了池盐。这是因为勿吉时期的人开始沿松花江溯流而上,进入了松嫩平原的今哈尔滨地区和肇东境内,故这里指的盐池应该就是今肇东一带的沿江盐池。金代时肇州盛产土盐,供胡里改路和上京路食用。20世纪中叶,海盐紧张时,哈尔滨市民还曾食用过这种土盐。除池盐外,勿吉、靺鞨人所居的山林里还盛产一种“食盐树”,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记载的源来。现今在吉林和黑龙江省交界的张广才岭的余脉,仍然生长着这种“食盐树”。每到雨后,在这种树干的表皮上便凝结了一层盐霜,酷似今天的食盐,可以食用。
女真人的饮食主要来源于渔猎、农业和家畜饲养。女真“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禽有鹰鹞‘海东青’之类,兽多牛、马、麋、鹿、野狗、白彘、青鼠、貂鼠”,“其人勇悍……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23]《大金国志·饮食》载:“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24]《三朝北盟会编》载:辽金女真人“其饮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米为饭,葱韭之属和而食之”,“炙股烹脯,以余肉和羹捣烂而进,率以为常”,“下粥肉味无多品,止以鱼獐生食,间用烧肉,冬亦冷饮”。[25]金初宋人许亢宗在咸州一带所见,女真人的食物还有“馒头、炊饼、白熟、胡饼之类”以及一种“面食以蜜涂泮,名曰‘茶食’”的食品。[26]由于女真人地区盛产马、牛、羊、猪,且河流较多,肉类和水产品在其饮食结构中仍然占据着很大的比重。女真人的肉食主要来自于其牧养的马、牛、羊和家养的鸡、鸭、猪等,还有射猎而获的鹿、麋、狍、獐、山鸡等大量野生动物。而牛主要是用于农耕,马主要是用来作战,因此,女真人餐桌上常吃的肉类还是羊和猪以及射猎所获野味。上京会宁府每年贡猪二万头,大定二十五年始罢。[27]《大金国志》中还记载的招待宋使许亢宗的“花宴”,则应是一种比较“讲究”的礼节性的招待宴。此外,饮酒和饮茶也是金代女真人的两大嗜好。
后金建国,天命元年(万历四十四年、1616)“始行元旦庆贺,制朝仪。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行新定朝仪,此班朝所繇始,崇德改元,定元旦进表笺及圣节庆贺仪。”[28]“元日宴,崇德初,定制,设宴崇政殿,王、贝勒、贝子、公等各进筵食牲酒,外藩王、贝勒亦如之。”[29]满族入主中原之前朝仪初创时贵族食制的特征是以习俗为基础的,并一直在制度上维系到顺治十年(1653)。“食肉之会”是满族根植于东北文化生态的传统,“凡满洲贵族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识与不识,若明其礼节者即可往。……客至席地盘膝坐垫上,或十人一围,或八九人一围。坐定,庖人则以肉一方约十斤,置二尺径铜盘中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中一大铜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铜盘,径八九寸者,亦无酰酱之属。酒则高粱倾于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呷之,以次轮饮。……”[30]由于优厚的经济支撑与民族文化再造需要,“食肉之会”传统一直维系到帝国的最后,“自用御刀割析,诸臣皆自脔割,遵国俗也”。[31]
三、移民与殖民背景对黑龙江地区饮食文化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地区或政权与中原相对峙或分立的状态下,其饮食文化交流在物质层面主要有官方互市、民间交往(往往是违背官方法令的)和往来使节等形式。自三代以下,东北地区就一直维系着与政治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央王国的“朝献”、“岁贡”、“奉献”、“入献”、“交市”、“贡献”、“朝贡”等官方性质的经济往来。三国时代(220~265),东北地区的濊貊、扶余、肃慎、乌丸等自魏立国之始的黄初元年(220)以下,均先后服属或贡奉不绝。魏国“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32]“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33]至于更深一步的居处相接、习尚濡染,则使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更为活跃,其意义也深刻得多。十六国之后,北中国一直是少数民族活跃的舞台。其中,鲜卑族北魏(386~581)、契丹族辽(907~1125,西辽1124~1211)、女真族金(1115~1234)、蒙古族元(1271~1386)、满族后金·清(1616~1911)等时期,少数民族更成为舞台的主角。
我们不仅应当关注中国封建制时代各民族饮食文化交流史上的一般性规律现象,更应当深入研究这一规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确切地说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别与个性。比如,汉族同北方广阔草原文化带上的游牧骑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汉族同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有不同程度的狩猎等辅助经济成分)少数民族的交流,无论就具体的历史文化内容和交流方式都有明显的区别。汉族与草原民族的饮食文化交往,属于农耕文化与游牧狩猎文化两种类型差异较大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反差大、互补性强,而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伴有激烈的震荡和尖锐的冲突。而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基本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同类型文化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故差异不大,互补性相对小,而且交流过程相对平和得多。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本质,是过分依赖自然并靠向自然索取的力度与效果来维系人群生存发展的,因此,这种文化具有突出的扩张性,其经济生活的重要的政治表现方式之一便是对其他民族,尤其是农耕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劫掠。农耕民族的一切他们都需要,如粮食、食品、酒、畜禽、釜等饮食器具、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也可作为兵源和力役)、食生产工艺(各种技艺掌握者),以及其他生活数据或有用的非生活数据。劫掠是他们的生产方式,是他们的生活必需,是历史合理的生存需要--虽然对被劫掠者来说是残酷和不公平的,但这不公平是社会的和时代的,即“当时的”,而公平则是历史的,即“超越当时的”。“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34]小农自然经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儒家思想的伦理判断,只能停留于言不及义的行为事象表层。即使如董仲舒(前197~前104)那样的大学者也只能看到草原民族劫掠行为利益驱动的表面,无法揭示其原动力乃是生态制约--生存需要的根本所在,其实质是各游牧狩猎民族历史上食生产--食生活的周期性规律表现。草原牧草再生产能力限制着草原民族生活区内的载畜量,因此限定了可养活人口的数量。在放纵生育的历史上,草原人口的密度短期内很容易便达到天然的极限,随即便是“肉荒”;而频繁出现的黑(无雪致旱)、白(降雪过多)二灾毁灭草原更造成严重的饥荒。于是他们只能将狩猎方式转向于其他人群,于是厚积而又文弱的农耕民族便自然成了攻掠的目标。所以董仲舒建议朝廷对匈奴本着“利动贪人”的原则实行“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的政策,[35]其结果并不能阻止匈奴人的铁骑常突,边境上仍是烽警时至。为此史家班固(32~92)指出,匈奴单于“咸弃其爱子,昧利不顾,侵掠所获,岁鉅万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36]倒是欧阳修(1007~1072)看得更准确些:“自古夷狄之于中国,有道未必服,无道未必不来,盖自因其衰盛”。[37]只要有力量打破防御,草原铁骑便会伺机南下。黄河流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持续不断地冲突交流,构成了数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这是食生产方式、食生活需要的斗争。对于劫掠者和反劫掠者来说,代价都是巨大的(比较而言,痛苦最大和牺牲最多的还是农耕民族),但历史决定人们别无选择。
于是,与中原汉文化交往的日益密切,使得汉文化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地区的文化与风俗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女真人在建国前,没有岁时节日。受汉族风俗的影响,女真出现正旦、元夕、清明、七夕、中秋、重九等节日。其节日活动中有汉族风俗、契丹风俗,也掺杂着女真族风俗等。这样,东北社会风俗杂糅互染,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特色。尤其清中期以来关内移民的大举北上,使东北地区民族人口比例出现变化。如吉林地区的居民,清初还是“满洲居者多,汉人居者少”的状况,但是道光、咸丰以后,已经是“民户(汉户)多于旗户(满洲旗人)”的局面。[38]于是,随着内地移民的涌入,其饮食文化也就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
二十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哈尔滨率先于1907年正式开辟为国际商埠,先后有俄、日、美、法、英、德等20余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领事馆。大批的俄国人进驻哈尔滨。日本占领后,为了深化殖民统治,向“满洲”国移来大量日本人,称之为“开拓民”。开拓团在伪满洲国内,享有自治权。日移民团到来时,开拓科给各团组织共励组合,一起制造大酱、酱油、酒等,开拓科又组织消费组合,共同购买日用品等。开拓科根据基本要纲,设立医科大学,专收开拓民子弟,毕业后使其成为日本殖民政府的专职医生。开拓厅每年举办一次开拓团长会议,主要是解决开拓民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而移民来的一般朝鲜农民大部分是作佃农。他们通过跟汉族地主订年租合同或佃租合同来租种农地。他们“精于经营水田,且富于经验,故东北的水田,几全为韩人所独占。东北水田收获年约200万担,其中85%是由韩侨经营的。”据统计,1921年东北地区的水田面积达48 911公顷,大米产量约为1234 000石。[39]朝鲜移民“平均每户4口人”,“饮食方面是卖掉收获的大米,以之购入廉价的谷子、玉米、高粱等作为主食;以干鱼、葱、白菜、萝卜等蔬菜及辣椒、咸菜为副食。一家4口每月伙食费为银7、8元至12、13元者已算相当不错;更贫穷者则以少量的谷子、高粱、和蔬菜来勉强充饥,一家4口人每月伙食费仅以4.5元来度日者,亦为数不少。”[40]
哈尔滨犹太人的数量最多时占外来人口数的10%,却占从事经济贸易总人员数量的1/2。他们创办了许多商业企业,参与哈尔滨的采矿、冶金、金融流通、林业、面粉、豆油等诸多领域的经济活动,建立了多个经济实体,成为哈尔滨市相当有影响的经济群体。哈尔滨的犹太人建立的邦纳和明达诺维奇面粉厂,华英油坊、哈尔滨老巴夺烟厂、阿什河糖厂等一批著名企业,生产出一批影响久远的名牌产品。1913年,法籍犹太人创建的马迭尔宾馆是当时哈尔滨最早、最高级的旅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07年,犹太人比特克诺夫斯基首次将中国大豆销往欧洲,开创了中国大豆出口欧洲的先河,从此,哈尔滨大豆誉满全球。
正是由于日、朝鲜、俄罗斯、白俄罗斯、犹太、欧美等国家和民族的人口大量聚居在黑龙江地区,故使得黑龙江地区无论是食物原料、加工方法、菜品特色、饮食生活、饮食民俗,还是饮食思想,都深深地打上的异域文化的烙印。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已经渗透到了黑龙江人的血液里,代代相传,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形成了黑龙江独具异域风情的饮食文化。如1900年,由俄商乌卢布列夫斯基在哈尔滨创建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啤酒厂。此后,又有捷克人、德国人相继兴建了几个啤酒厂。从1900年到1935年,哈尔滨就先后建有8家啤酒厂。日本占领后,黑龙江地区的啤酒生产被日本人所垄断。啤酒,至今仍在黑龙江人的饮食生活中占居重要的地位,啤酒的年生产量和消费量均居全国前列。而这还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侧面而已。今天黑龙江地区的饮食文化无处不彰显着其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留下的印痕。
[1]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42-445.
[2]刘爽.哈尔滨犹太人探源[J].学习与探索.2004.5:126-130.
[3]斯科韦尔斯基.黄俄罗斯的士兵村--沙俄在满洲的军事殖民计划[J].东省杂志.1930.4:15.
[4]薛衔天.中东铁路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28-129.
[5]石方.黑龙江地区的外国移民[J].学习与探索.1986.4:126.
[6]Lucy S.Dawidowicz.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M]. Harmondsworth:Pelican Books.1977:216.
[7]张铁江.哈尔滨犹太人的由来[N].黑龙江日报.2000.02.17.
[8]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1128.目录1.卷宗135[Z]:6.
[9]哈巴罗夫斯克国家边区档案馆.全宗849.目录l.卷宗23[Z]:31.
[10]哈巴罗夫斯克国家边区档案馆.全宗849.目录1.卷宗23[Z]:31.
[11]孔经纬.东北经济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202.
[12]赵力群.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侵略始末[J].社会科学辑刊. 1992.2:98.
[13]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日本移民档案·黑龙江省卷[Z].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07.
[14]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33;金元石.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J].民族研究.1993.1:62等.
[15]车哲九.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及其变化[J].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138.
[16]车哲九.中国朝鲜族的形成及其变化[J].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138;金元石.中国朝鲜族迁入史述论[J].民族研究.1993.1:62-63.
[17]王介公修、于云峰簒.安东县志(1931年)[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4:958.
[18]关东都督府陆军经理部.草稿满洲地方志[Z].沈阳:辽宁省档案馆日文资料.1911:2009-2010.
[1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12.
[20]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994上.
[21]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20.
[22]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24.
[23]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1.
[24]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4.
[2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0-35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20.
[26]赵永春.奉使辽金语录[M].长白丛书五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153.
[27]脱脱等.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551.
[28]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21.
[29]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2627.
[30]清朝野史大观[M].上海:上海书店.1981:29.
[31]昭梿.啸亭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377.
[32]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12.
[33]陈寿、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80.
[3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33.
[3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81.
[3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33.
[37]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5.
[38]长顺.吉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510.
[39]孙春立."9·18"(满州)事变前俊におけゐ在满朝鲜人[R].西日本地域研究会报告要旨.2001.6.25.
[40]依田喜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M].卞立强译.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300.
K825.4
A
1671-7740(2012)01-0028-08
郑南(1975-),女,副教授,黑龙江旅游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饮食文化研究。
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0CZS036);2010年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QW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