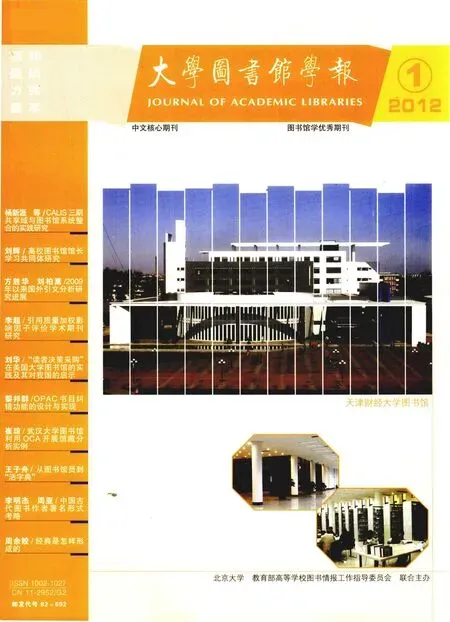《全民阅读推广手册》序
□曾祥芹
2006年4月23日,当全球同庆第十二个“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倡议,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它表明“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有机部分。
与此同时,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王余光教授的倡议和推动下,于当年“4·23世界读书日”,在广东东莞正式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科普与阅读推广委员会”,并邀请时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的我担任学术顾问,副会长徐雁、甘其勋分别兼任有关分支机构的主任、副主任等。这一举措启动了图书馆学与阅读学的学科联姻,宣示了阅读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图书馆阅读推广实践的组织联盟,标志着“汉文阅读学”在“全民阅读”的社会大舞台上“知”与“行”的进一步融合。这一整合,乃是我国阅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此举较二十年前,年富力强的徐雁联络其学长王余光合作主编后来荣获第八届“中国图书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意义。尽管那时,他就已发表过“读书问题,再也不是一个可以局限在象牙塔中自我品味、修身养性的事了,而是成为了一项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乃至在‘地球村’里各个国家之间综合国力争衡的重要标志”[1]的见解。
我认为,在“全民阅读”这一理念旗帜下,覆盖着阅读客体、阅读主体、阅读本体三个重要领域,凸现了“大阅读”观的时代价值。
作为阅读对象的“书”,从媒体看,不外乎“无字书(Wordless-Book)”、“纸本书(Paper-Book)”、“电子书(Eiectronic-Book)”三类。与人类五千年文明史同龄的“无字书”(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之理)是比喻意义上的读物;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纸本书(含报纸、杂志等纸质文献)和只有数十年历史的电子书(含网页、软件)是本体意义上的读物:这三类书涵盖了“书”的演变史,构成了阅读的“外宇宙”。其形体和内涵的丰富多样,给我们提出了“多读书”和“读好书”的阅读推广任务。
作为阅读主体的“人”,是包含广大工、农、兵、学、商、政、教、科、文、卫等不同职业成员在内的读者。这个庞大的阅读群体涵盖了儿童、少年、青年、成年、老年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因此,“全民阅读”的本质意义在于“全社会成员的阅读”和“全人生过程的阅读”。营造“书香社会”,意味着“阅读”是每个现代公民的社会权利。
作为阅读技法的“读”,承继叶圣陶所分的“念诵、默诵、目治”之说,也不外乎“精读、略读、快读”三种。
“精读法”主要追求阅读深度,只有进出文本,跨越读者与文本、与作者、与世界、与自我的四重视界,神游阅读的“内宇宙”,践行“解文、知人、论世、察己”的“读书八字经”,才有资格称为“深阅读”。“略读法”主要追求阅读广度,“快读法”则主要追求阅读速度。
我认为,一个现代人必须养成读书、阅网、观景三结合的阅读生活习惯。这个良好阅读习惯最好在少儿的学龄阶段形成,才可望持之终生。我还曾提出,这个阅读习惯的诀窍在于学会“精读纸本书”,“快读电子书”,“活读无字书”。其中,精读纸本书是基础,必先打好这个底子。
树立了阅读的“外宇宙”、“内宇宙”观和“全民阅读”观,我们才能扩展阅读时空,克服阅读偏见,认同“阅网”、“观景”也是“读书”的“大阅读”理念,恪守“业务读文章,业余读文学”的社会阅读常规,形成自幼到老的终身阅读习惯[2]。这样,对“培育读书人口,营造书香社会”的崇高理想,就会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不至于沉沦在“阅读危机”的愁绪和焦虑之中。
阅读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阅读科学和阅读学科在于揭示共性规律,以求“推广”;阅读艺术则在于体现个性风格,忌有“样板”。健康的阅读要推广到全民,当务之急不是欣赏别人独有的阅读艺术,而是学习和掌握可以共通公用的阅读科学成果。正是从阅读理论和阅读实践相结合的意义上来说,“图书馆学”与“阅读学”两个学科,“阅读学研究会”与“阅读推广委员会”两个学会,应该在全民阅读推广的社会大舞台上分工合作,各擅胜场。
“图书馆学”与“阅读学”是血脉相系的两个姊妹学科。“图书馆学”侧重研究阅读客体(读物、环境、时间),经历了从“经验型图书馆学”到“学院派图书馆学”再到“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如今要进一步建设“学习型图书馆”,就是要为全民阅读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使之变成活跃的“阅读生态园”,而决不能让图书馆沦为沉睡的“图书博物馆”。
“阅读学”侧重研究阅读本体(原理、技法、应用),经历了从“传统阅读学”到“现代阅读学”再到“汉文阅读学”的发展过程,建设中华民族化的现代阅读学,就是要为全民阅读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决不让“汉文阅读学”锁入“象牙塔”,脱离“科学图书馆学”,脱离“网络阅读”和“观景阅读”实践,而要充分开发阅读主体的潜能,使阅读科技转化成激励阅读情志、引导阅读航程、提高阅读效率的阅读教育工程。
如果我国图书馆学界人士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善于汲取“汉文阅读学”的知识营养,能够自觉地运用“科学阅读观”来指导社会大众的阅读实践,同时阅读学界又能深入掌握“现代图书馆学”的专门知识,在全民阅读推广的丰富实践中来进一步发展“汉文阅读学”,那么中华民族阅读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一定大有希望。
当前“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是建设一个“学习型社会”,而“学习型社会”的坚厚之基在于建设一个“书香社会”,因为阅读是“学习之母”,而读书与学习从来是密切不可分的。如今,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中国的网民和手机用户均已超过5亿,居世界第一;随着交通的发展,旅游人群也在与日俱增。他们正用“纸书阅读”、“网络阅读”、“手机阅读”和“旅游阅读”促进着“大阅读”的社会化,而让我们深切体验到“全民阅读”的新时代风貌。但在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的空前加速,也让“爱‘悦读’、恶‘苦读’,喜‘轻读’、怕‘攻读’,只谈‘文学阅读’、不论‘文章阅读’”这种“时代阅读病”,愈来愈严重地侵袭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因此积极探寻“保健阅读”之道,重构书香飘逸的“精神家园”,也就成为了我们所面临的一个紧要的时代课题。
早在2003年,作为知名教育家、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永新教授,就曾创意呼吁我国应尽快设立“国家阅读节”,并建言各级公务人员要“少一点烟酒味,多一些书卷气”[3]。他从2006年起,倡设了“苏州读书节”。
2009年底,《中国新闻出版报》在北京发布“2009十大促读力”代表,赢得“中国文明网(www.wenming.cn)”等大量媒体广泛关注。该报《读周刊》编辑部认为,“民族的精神力量来自阅读”。在“过去的10多年中,在信息海量而复杂的网络世界里,一边是出版繁荣、新书每年大量增长;一边是人们面对书海,无所适从,深度阅读锐减。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推广者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盘点2009年,《读周刊》编辑部推出10个代表阅读推广势力的机构和个人,他们所起的作用对改善国民阅读的状况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他们在社会上所做的努力和坚持是我们向其投注目光的理由。”[4]
为此,发表“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然是美丽的城市”[5]等名论的朱永新,与倡言“不信书香唤不回”,组织策划并主编出版了《华夏书香丛书》、《读书台笔丛》、《书林清话文库》等近十套书系,被评价为是“国民阅读活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如何开展国民阅读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方面,均颇有建树”[6]的徐雁等,榜上有名。
如今,由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江苏省图书馆学会阅读与用户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集结陈亮、江少莉等众多同好友生编成的这部《全民阅读推广手册》,科学布阵九大单元,努力推介古今阅读理论的精华和中外阅读实践的经验,既有给力人生的阅读智慧,又有给养心灵的“阅读疗法”,既有积淀丰厚的藏书文化,又有精彩纷呈的都市阅读,还涉及到阅读机构、导读书目、读书媒体,以及方兴未艾的数字化阅读等有关方面的内容,不仅总结了有关阅读的传统理论和成熟经验,而且展示了阅读实践的新方法和新进展,乃是一部开卷释疑、读之益智的重要工具书。
相信该书于第十二个“深圳读书月”期间,在深圳海天出版社的隆重推出,将为任重而道远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出推波助澜的独特作用。
参考资料
1 徐雁.读书之乐.见:王余光,徐雁.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3
2 曾祥芹.汉文阅读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99
3 朱永新.追随伟大的灵魂.见:岛石.60年中国人的阅读心灵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9:154
4 周翼双.2009十大促读力量本年度阅读推手齐齐亮相.2009-12-18.[2011-08-05].http://www.chinaxwcb.com/index/2009-12/18/content_185974.htm
5 “明星市长”谈读书:少点烟酒味多些书卷气.2007-07-05[2011-08-05].http://13.eduol.cn/archives/2007/296983.html
6 《中国新闻出版报·读周刊》2009年12月18日专文.2009-12-18.[2011-08-06].http://hi.baidu.com/nj_xuyan/blog/item/ce906af32d12615b342acc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