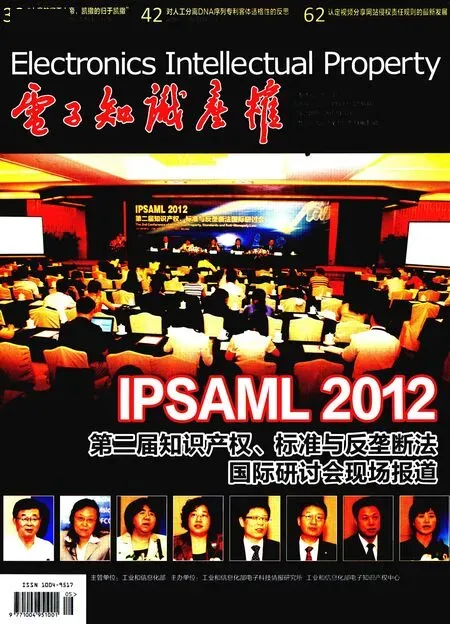认定视频分享网站侵权责任规则的最新发展评Viacom诉YouTube案二审判决*
文 / 王迁 /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认定视频分享网站侵权责任规则的最新发展评Viacom诉YouTube案二审判决*
文 / 王迁 /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在Viacom vs YouTube二审判决中,法院从几方面澄清或发展了认定视频分享网站侵权责任的规则。首先,“知道”是指知道特定侵权内容,而不是指了解网站中存在侵权内容。但“故意对侵权行为视而不见等于知道”的普通法规则与“红旗标准”规则并不矛盾。其次,视频分享网站内部信函可以用于证明:网站经营者知道特定视频是侵权的。最后,判断视频分享网站“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并进而认定其“替代责任”的条件,并非是其已知道特定的侵权行为。同时,也不能仅因网站有能力阻止用户获取侵权内容,就认为其“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
视频分享网站;红旗标准;替代责任避风港
2012年4月5日,在经过近两年漫长等待之后,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举世瞩目的“Viacom诉YouTube案”(以下简称“YouTube案”)下达了二审判决。1与一审判决相比,二审判决的分析更加细致、透彻,特别是对如何适用“红旗标准”、是否在适用时应考虑服务提供者对明显的侵权行为“视而不见”,以及如何认定“替代责任”等疑难和复杂问题,都给出了较为清晰的指引或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我国目前正在修改《著作权法》,最高人民法院也正在起草有关网络著作权侵权的新司法解释,而各地法院审理的指称视频分享网站侵权的纠纷更是数量惊人,其中许多争议焦点与YouTube案是相同的。因此该案的判决结果,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红旗标准”的含义及与“故意视而不见等于知道”规则的关系
YouTube案涉及的主要问题,在于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是否应当为其网站中存储的、由其用户上传的
注 释大量侵权影视剧、音乐电视(MV)和体育赛事节目片断,对Viacome公司等版权人承担间接侵权责任。而要对此作出认定,则必须先判断YouTube能否根据《千禧年数字版权法》(DMCA)第512条(c)款规定的“避风港”免责。DMCA第512条(c)款规定的免责条件包括:“并不实际知晓其网络系统中的作品是侵权的”(也即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明知”),以及“在缺乏该实际知晓状态时,没有意识到能够从中明显发现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也即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应知”或“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对DMCA的报告中将后一免责条件称为“红旗标准”,其指出:“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意识到了从中能够明显发现侵权行为的‘红旗’之后,如果不采取措施,就会丧失享受责任限制的资格”【1】44。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以何种标准去认定YouTube是否“实际知晓其网络系统中的作品是侵权的”或“意识到能够从中明显发现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
1.对于本案一审判决的评论,请参见拙作:《Viacom诉YouTube案:“红旗”何时飘扬?——兼评此案对我国视频分享网站的影响》,《中国版权》2010年第4期。况”(以下简称“明知或应知”)。原告Viacome公司在一审中举证证明:在YouTube网站中存储的所有视频片断中,超过60%都是有版权的,而其中只有10%是经过许可的。这说明YouTube意识到了其网站中有大量视频片断是侵权的。2但一审法院认为:“明知或应知”的对象,应当是对特定作品的特定侵权行为。仅仅一般性地知道网站中普遍存在此类侵权行为是不足以认定“明知或应知”的。3
二审法院支持这一观点,其指出:根据DMCA第512条(c)款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用户上传的内容侵权之后,只要迅速加以移除,仍然可以进入“避风港”免责。这本身就说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应知”的是特定的侵权内容,因为只有知道特定的侵权内容,才可能迅速加以移除。4
Viacome公司在上诉中提出,如果将“应知”的对象解释为“特定侵权行为”,会导致“明知”和“应知”无法区分,也即会使“红旗标准”形同虚设。5但二审法院认为:“明知”一词用于说明“主观上的认识”(subjective relief)。而“(意识到能够从中明显发现侵权行为的)事实或情况”则用于表明“客观合理标准”(objective reasonableness standard)。6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
“明知”标准与“红旗标准”之间的区别,并非在于前者要求知道“特定的侵权行为”而后者仅要求笼统地知道存在侵权行为,而是“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间的区别。换言之,“明知”标准取决于服务提供者是否实际上或“主观上”知道特定侵权内容,而“红旗标准”则取决于服务提供者是否主观上意识到了一种事实,该事实能够使特定侵权内容“客观上”对理
注 释性人而言非常明显。7
二审法院对“红旗标准”的观点,与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解释完全吻合。早在1998年对DMCA的报告中,国会参议院就指出: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意识到了相关事实或情况时,应当采取主观标准。但在判断相关事实或情况是否构成“红旗”时,应当采用客观标准。也即应当以一个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的理性人为标准,根据相同的事实或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明显的侵权行为【2】44。
根据“红旗标准”,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知”侵权行为的前提,是其意识到了相关事实或情况的存在。对此应采用“主观标准”。换言之,即使一个处于相同地位的理性人明显能够发现相关事实或情况,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声称自己确实没有发现。只有确认网络服务提供者意识到了相关事实或情况后,才能采用“客观标准”,从理性人的视角,判断其是否能够从该事实或情况中,发现明显的侵权行为。这其中的“主观标准”可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尽量避免作出任何能够使自己发现相关事实或情况的行为。如根本不去看自己的网页,哪怕一进网页就会发现明显的侵权内容。
对此,美国普通法中有一条“故意(对侵权行为)视而不见等于知道”的规则,其含义是:当一个人意识到了争议事实有高度存在的可能性,却有意避免确认该事实时,其“故意视而不见”或“存心避免知道”的行为等同于知道该事实。8二审法院认为:虽然DMCA第512条(m)款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免责不以其监控网络服务,积极寻找反映侵权活动的事实为前提,但“故意视而不见等于知道”规则并未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监控义务,与DMCA的规定并不矛盾。二审法院据此认为:在适当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故意视而不见等于知道”规则,以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或应知特定的侵权行为。9换言之,该规则可以作为“红旗标准”中“客观标准”的补充,用于判
2.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718 F. Supp. 2d 514, at 518 (S.D.N.Y. 2010).
3.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718 F. Supp. 2d 514, at 523 (S.D.N.Y. 2010).
4.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25 (2nd Cir, 2012).
5.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26-27 (2nd Cir, 2012).
6.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27-28 (2nd Cir, 2012).
7.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28 (2nd Cir, 2012).
8.United States v. Aina-Marshall, 336 F.3d 167, 170 (2d Cir. 2003).
9.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0 (2nd Cir, 2012).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意识到了能从中发现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或情况,因此成为了“避风港”规则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一审法院并没有明确适用“故意视而不见等于知道”规则,也没有说明其与“避风港”的关系,因此二审法院将此点发回重审,要求一审法院查明YouTube是否“故意努力地避免知道(侵权行为)”。10
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对“红旗标准”及其与“故意视而不见等于知道”规则的解释,对我国法院具有参考价值。一方面,不能仅以网站中出现了侵权视频,甚至网站被用户大量用于侵权而推定视频分享网站具有主观过错【2】,而应当首先考察视频分享网站是否已经意识到了涉案视频的存在,随后再根据“客观标准”判断其是否能够认识到该视频是侵权的。另一方面,在视频分享网站声称自己并未意识到用户上传了涉案侵权视频时,应当注意分析其是否故意“视而不见”。当涉案视频的信息存在于专业视频分享网站的显著位置或在“排行榜”的前列时,网站经营者对于自己从来不去查看网站或“排行榜”,因此不知道其中有涉案视频的抗辩,只能被解释为是其努力避免使自己发现明显的侵权视频。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内部信函对认定“明知”和“应知”的影响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章规定了“证据发现程序”,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另一方当事人披露与争议问题有关的各类文件。Viacom公司在上诉中提出,通过“证据发现程序”获取的许多YouTube内部文件都已说明,YouTube对特定的侵权行为是“明知”或根据“红旗标准”是“应知”的。例如,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贾德·卡林姆曾在公司内部报告中指出“今天,下列知名电视剧的片断仍然可以在YouTube中找到:《恶
注 释搞之家》、《南方公园》和《雷诺911》……,虽然YouTube在法律上并没有监控义务,并遵循DMCA规定的通知与移除规则,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主动删除那些极为明显的非法的、极可能招致批评的内容而受益”。显然,卡林姆确认在YouTube中存在这些电视剧的片断,而且相信其是侵权的,因为他本人将其称为“极为明显的非法内容”。11
YouTube的另一名创始人查德·赫利则曾敦促其同事“要开始谨慎地拒绝有版权的或不适当的内容”,并注意到“网站中有当天CNN报导致航天飞机发射的新闻片断”,并提醒如果CNN的人在YouTube网站看到了该视频,可能会带来麻烦。而YouTube的第三名创始人陈士骏则回复到:“我们就把这段内容留在网站中。我并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产生。什么?从CNN来的人会看到它?而他碰巧是一个有权的人?他碰巧想立即删除它?让他联系CNN的法务吧。两周后,我们会收到要求停止侵权并删除视频的信函,到时我们再删除”。卡林姆同意陈士骏的看法,并称“我喜欢CNN有关航天飞机的视频。一旦我们做大了和更为人所知了,再删除它,但就现在而言,留着它没事”。12
二审法院指出:面对上述事实,一个理性人会得出YouTube“明知”特定侵权行为,或者至少“应知”特定侵权行为的结论。由于此案一审作出的是有利于YouTube的“即决判决”(summary judgment,也可译为“简易判决”,但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简易判决”不同),而“即决判决”的前提是双方对关键事实不存在真正争议。二审法院认为,原告Viacom公司所举出的上述证据,已经提出了有关YouTube是否“明知”或“应知”特定侵权行为的事实争议。而一审法院在没有对该事实争议进行仔细审查的情况下就作出有利于于YouTube的“即决判决”,为时过早。因此将该部分发回重审。13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与美国类似的“证据发现程序”,但二审法院的观点仍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在本案中,二审法院要求一审法院重审的
10.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0 (2nd Cir, 2012).
11.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33-34 (2nd Cir, 2012).
12.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34-35 (2nd Cir, 2012).
13.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36-37 (2nd Cir, 2012).重要原因,在于YouTube内部的文件和电子邮件,已经说明YouTube意识到了特定作品的存在,以及其极有可能是侵权的。事实上,根据二审法院对“红旗标准”的解读,在YouTube意识到了特定作品存在之后,是否应知该特定作品侵权,应当根据“客观标准”,由处于同等地位的理性人加以判断。即使YouTube管理层声称自己虽然看到了视频,但自己并不认为其是侵权的,也只能说明其不“明知”,却不能由此确定其不“应知”侵权行为。而我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要求所有“为他人提供上载传播视听节目服务活动”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提供者”建立“有健全的节目安全传播管理制度”,以确保包括用户上传的视听节目不得含有违反宪法、法律和损害社会公德的内容。14为了符合该规定的要求,国内各大视频分享网站均设有人数众多的“审片组”,负责对用户上传的视频进行审核。
那么,“审片”机制能否影响对视频分享网站“应知”侵权视频的认定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起草《关于审理涉及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时,曾经在草案中规定“视频分享网站有对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事前人工审查的义务。用户上传的视听作品系专业制作且节目完整,或者处于档期或者热播期间的,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定其有过错”。但因担心此条被误解为要求视频分享网站承担著作权审查义务,在最终稿中并未将其纳入。对此,笔者认为:根据“红旗标准”,在认定“应知”时,需要经过两个步骤的判断:(1)是否发现了被控侵权内容;(2)发现之后,能否根据“客观标准”判断出其是侵权的。是否“发现了被控侵权内容”,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判断,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有法定义务去审查著作权毫无关系。无论是像YouTube管理层那
注 释样在无任何法定义务的情况下主动发现,或偶然发现,还是出于阻止黄色、反动内容等与著作权无关的目的发现,都在所不问。当然,视频分享网站通过“审片”程序,“发现了被控侵权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就“应知”该内容侵权。这取决于该内容对于一个处于同等地位的理性人而言是否明显侵权。但如果一方面承认视频分享网站有义务去“审片”(虽然不是出于审查著作权的目的),从而能够“看到”所有用户上传的视频,另一方面又认为其虽然肯定会“看到”明显侵权的视频(如由用户匿名上传的、热播期内的完整电影),却并不“应知”该视频侵权是侵权的,显然是违反事实和法律逻辑的。例如,如果用户上传了一部正在热播之中的完整的影视剧。而审片人员在对全部视频进行合法性审查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这部影视剧的存在。此时,任何一个理性人都会意识到,影视公司是不可能自行或许可他人以匿名用户身份在视频分享网站免费传播这部影视剧的。此时,无论视频分享网站是否有积极审查著作权状况的法定义务,由于其已意识到了侵权视频的存在,当然有义务立即删除。
三、对“替代责任”的认定
YouTube二审判决中最为新颖的观点,也是最值得我国立法者和法院思考之处,莫过于其对DMCA中“替代责任”的解释。
DMCA第512条(c)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要进入“避风港”免责,就不能从用户的侵权行为(即上传侵权内容的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但条件是网络服务商对该行为是有权利和能力加以控制的。15通说认为,该条体现的是美国版权判例中的“替代责任”——如果对他人的侵权行为具有监督的权利和能力,同时又从侵权行为中获得了直接经济利益,即使其不知道他人的侵权行为,也应当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16如美国著名版权法专家Nimmer认为:该条是将“替代责任”的两个构成要素都法定化了【3】。美国国会参议
14.参见《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第2条、第8条、第16条。
15.17 USC 512(c)(1)(B).
16 . Gershwin Publishing Corp. v. Columbia Artists Management, Inc., 443 F.2d 1159, at 1162 (2d Cir. 1971); Polygram Intern. Pub., Inc. v. Nevada/ TIG, Inc., 855 F. Supp. 1314 (D. Mass. 1984); Melvile B. Nimmer& David 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Chapter 12.04 [A][2] (2006).院在对DMCA的报告中也认为,“避风港”规则可使“符合条件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免于因……替代责任而进行赔偿”【1】20。但是,究竟如何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具有“控制的权利和能力”,美国法院众说纷纭,迄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4】。
在本案一审中,原告Viacom公司认为YouTube不但具有直接控制用户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也从用户上传的侵权内容中获得了广告收益这一直接经济利益,因此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但一审法院认为:认定YouTube“有权利和能力控制”侵权行为的前提,必须是其知道特定的侵权行为,因为“服务提供者只有知道特定的侵权行为,才可能去控制它”。17
二审法院则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由是它将会使这一免责条件变得毫无意义。根据一、二审法院都认同的观点,“明知”和“应知”的对象,就是“特定的侵权行为”。如果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了“特定的侵权行为”,却没有及时移除侵权内容,就已经无法进入“避风港”免责了。此时再规定“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特定的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如果有权利和能力去控制它,并且从中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就不能免责”,不就成了多此一举了么?既然法律解释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使法律中的规定变得多余,一审法院的观点不能成立。18
与此同时,二审法院也不赞同将以往判例中对“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的解释照搬到DMCA中。一些法院曾经认为:“阻止他人获取侵
注 释权内容的能力,就是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的证据”。19二审法院认为,这与DMCA对“避风港”的规定是冲突的。因为根据“通知与移除”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享受免责,应当在收到通知后迅速移除被指称侵权的内容。但“移除”的结果,就是“阻止他人获取侵权内容”。这不就意味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从而无法享受“免责”了么?
为了避免这种“第22条军规”式的解释20, 二审法院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DMCA第512条(c)款规定的“对侵权行为具有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并非是对“替代责任”认定标准的法定化,而是对它的背离,21因此不能仅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能力移除用户上传至其网站的侵权内容,或防止他人获取该侵权内容,就认定其“对侵权行为具有控制的权利和能力”。22但对于究竟该如何认定,二审法院也没有给出具体标准,只是将此点发回重审,要求一审法院考虑“原告是否提交了充分的证据,以使理性的陪审团能够得出YouTube具有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并且从该侵权行为中获得了直接经济利益”。23
笔者认为:YouTube案二审对此问题的讨论,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否将DMCA第512条(c)款中与“控制的权利与能力”及“直接经济利益”有关的免责条件解释为“替代责任”的法定化,该免责条件直接来源于美国版权判例中的“替代责任”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中的“替代责任”仅仅是指用人单位对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责任。24除此之外,并未像美国那样在著作权法中确立广泛的,而且是以“无过错责任”形式存在的“替代责任”。而《信息网络传
17.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718 F. Supp. 2d 514, at 527 (S.D.N.Y. 2010).
18.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3 (2nd Cir, 2012).
19.A&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 at 1023 (9th Cir. 2001).
20.《第22条军规》是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的代表作。在小说中,一名想逃命的飞行员找到一个军医帮忙,想让他证明自己疯了。但军医告诉他,虽然按照“第22条军规”,疯子可以免于飞行,但同时又规定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如果本人一旦提出申请,便证明其并未变疯,因为“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这样,这条表面讲究人道的军规就成了耍弄人的圈套。“第22条军规”就由此象征人们处在一种荒谬的两难之中。见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22%E6%9D%A1%E5%86%9B%E 8%A7%84,2012年4月10日访问。
21.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4-45, 47 (2nd Cir, 2012).
22.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7 (2nd Cir, 2012).
23.Viacom International v. YouTube, 2012 U.S. App. LEXIS 6909, at 49 (2nd Cir, 2012).
24. 见《民法通则》第43条,《侵权责任法》第34条。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将“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的免责条件设定为“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应是直接移植DMCA上述条款的结果。这一移植似缺乏本国法律基础。而美国法院至今还未弄清DMCA中该条款在美国如何适用。因此,这一移植显得并不成熟。
其次,根据DMCA第512条(c)款的规定,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利和能力控制侵权行为的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用户的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后,才不能进入“避风港”免责。换言之,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不具有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即使其从用户的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仍然可能享受免责。相比之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却没有规定“控制侵权行为的权利和能力”这一前提,如果按字面意思实施,将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比在美国还要严厉的责任,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最近引起广泛关注的“苹果商店侵权事件”中,美国苹果公司“苹果商店”中一些付费下载的应用程序侵犯了他人著作权(如将作家的小说制成电子书应用程序)。如果“苹果商店”是自动接收并发布第三方上传的侵权应用程序,同时苹果公司与应用程序开发者进行分成,就意味着苹果公司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了经济利益。如果仅以苹果公司不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规定的免责条件为由,要求其承担责任,等同于宣布任何与上传者分成为基础的商业模式从此走向灭亡。这一结果似乎并不合理。
第三,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统一各巡回上诉法院认定“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及“直接经济利益”的标准之前,美国的案例无法在这方面为我国法院提供参考。此时较为合理的做法,应是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2条规定的各项免责条件,视为“免责的充分但非必要条件”,也即:如果“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完全满足该条规定的所有免责条件,当然不承担责任(免责的充分条件),但如果不满足其中的一项(如不满足“未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条件),不必然承担责任(免责的非必要条件)。其是否承担责任,转而根据《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以过错为基础的侵权认定方法加以判断。换言之,应将“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作为其是否履行了相应的注意义务,是否有过错的因素来对待【5】。这样,既避免了对“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施加过于严厉的责任,也符合过错责任的基本要求。
【1】US Congress. Senate Report on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of 1998【R】.Report 105-190. 105th Congress, 2d Session:44.
【2】王迁.视频分享网站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08(4):42-53.
【3】Melville B. Nimmer and David Nimmer.Nimmer on Copyright【M】. § 12B.04【A】【2】,New York:Matthew Bender,2001.
【4】王迁.网络环境中的著作权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225-229.
【5】王迁.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J】.法学, 2010(6):128-140.
*本文是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技术措施的保护与规制》的初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