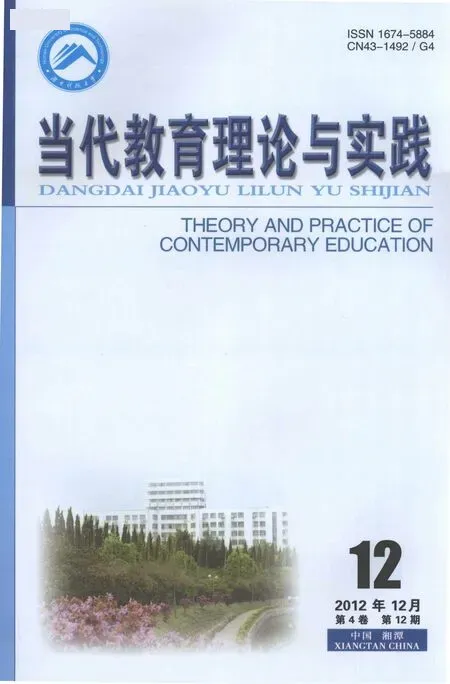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基督教隐喻翻译研究*——以《哈姆雷特》为例
赵 明
(湖南理工学院公共外语部,湖南岳阳414006)
文学作品中基督教词汇与隐喻的有机结合给人以博大精深的文化享受,其含义深刻,奠定了文学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戏剧中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隐喻颇多,而《哈姆雷特》堪称莎剧隐喻的集大成者,凸显了主人公难以决断但最终采取复仇行动的原因:哈姆雷特笃信基督教,从骨子里、到头脑里乃至行动上无不映射出基督教隐喻的背景、思想与准则。然而,宗教差异以及隐喻理解的难度往往会导致基督教隐喻为译者忽视,其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流失。因而,译者如何有效传译基督教隐喻的内涵,不失其宗教色彩,颇具研究价值。
一 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现状研究
国内外学者认为人们使用隐喻是为了用隐喻思维,对于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研究集中于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域和文化特征,相关隐喻的生成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基督教隐喻的翻译等方面。关于隐喻及隐喻翻译的观点主要有:Richards(1936)指出“隐喻不仅是词语之间的类比,而且是思维之间的借用与转换”;Lakoff和Johnson(1980)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认知心理学家Earl MacCormac解释“人脑能够合并不太相关的概念而形成新的概念,在分辨两个概念的相同与不同的过程中,新的理解就产生了,用语言来说这就是隐喻。”(转引自Walter:125)另一些学者则坚持“隐喻是用一个范畴的认知域去解释或建构另一个范畴”,“当人们用基督教的基本范畴去表达和解释其他认知域的范畴时,便形成了基督教隐喻认知。”如徐莉娜(1999)围绕张力与语境、系统与生成、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问题,探讨了隐喻语翻译的原则。她建议从语用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隐喻语的诸特征和动态技术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语用价值。武柏珍、沈荃柳(2010)则建议“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已开始将隐喻视为概念域,此类概念域具有较强的心理凸显性和稳定性,与图形—背景理论的凸显性原则基本一致。
二 图形—背景理论
图形背景理论是基于凸显性原则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其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同时符合空间组织与语言组织的基本认知原则。凸显性原则认为人们观察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不自觉地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如人们看到小船漂在水上时,习惯将船视为图形而将水视为背景。因此,绝大多数人会说“水面上有一条小船”,而不说“水在一条小船的下面”。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也认为,一些小的、运动的物体常常被识别为图形,大的、静止的物体则为背景。
最早提出图形和背景概念的丹麦心理学家Rubin认为,图形是有完整结构、能引起自觉者注意、从其它事物中凸显出来的前景,背景是烘托前景的其他事物;图形一般比背景显著,更容易辨认和记忆。根据突显程度,Langacker建立了与图形—背景理论一致的射体和界标理论:从印象上看,情景中的图形是次结构,在感知上比其他部分更显眼。而Lakoff建立了“类属层”、“具体层”概念,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其根本属性就是相似性。类比作为理解隐喻的常规方法,通常将不同领域的相关特性凸显作为图形,而把不相关的特性降为背景。因此,图形—背景理论是对隐喻进行认知理解的最基本理论,对于隐喻翻译从源语向目的语映射的过程具有良好的阐释能力。
笔者通过相关理论分析与大量的翻译研究实践发现,将图形—背景理论运用于翻译符合人类共有的认知规律,能从篇章、句序凸显原作隐含的意图。《圣经》赋予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基督教背景,主人公的基督教隐喻在基督教背景中得以凸显,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相近的教义给读者以相似感,产生宗教的篇章隐喻义;教义的变化则隐示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等。如果基督教隐喻义接近,就可直译,图形—背景对等;如果基督教隐喻义冲突,图形—背景可随译者视域转换为新的图形,但翻译时应保持目的域读者和源域作者隐喻义的基本一致。笔者以《哈姆雷特》为例,从篇章隐喻和句式转化两个角度探讨图形—背景理论在基督教隐喻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
三 图形—背景理论与《哈姆雷特》基督教隐喻翻译
《哈姆雷特》以基督教为基调,对“上帝”、“神”、“上天堂”的信仰以及“人生来有罪(原罪)”、“人来源尘土,而归于尘土”等基本教义在该剧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的基督教隐喻不仅蕴含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合理诠释了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极大地渲染了基督教背景,同时使读者感受到圣洁、看到哈姆雷特复仇力量的源泉。笔者尝试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将《哈姆雷特》剧中的基督教隐喻分为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哈姆雷特对复仇思索的基督教隐喻以及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基督教隐喻,来探讨文学作品中基督教隐喻的翻译。
(一)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翻译
众所周知,英美读者很容易接受和认同基督教隐喻,然而东方读者的基督教文化背景缺失,较难理解剧中的基督教隐喻。海伦·加德纳(1989:73)认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确以最为优美动人的形式表现了显然的基督教观念……它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理解相联系的……。”李伟民(2009)指出,“《哈姆雷特》隐喻中的基督教信仰背景、生活习惯背景,反映了主人公和他的周围浓重的基督教文化心理以及好的基督教价值取向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发现基督教精神家园构成了《哈姆雷特》隐喻的背景,译者正确理解哈姆雷特所处的基督教背景是成功翻译的关键。在第一幕第一场,厄耳锡诺城堡前的露台上,勃那陀来接弗兰西斯科的班,当时背景如下:
The nights are wholesome,then no planets strike,
No fairy takes,nor witch hath power to charm,
So hallowed,and so gracious,is that time.(Evans 1143)
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朱生豪等233)
该句中的3个具有较强基督教隐喻意义的词汇wholesome、hollowed、gracious加上名词 nights绘出一幅“清静、圣洁、美好的夜晚”图形。它置身于前面,使哈剧一开始就弥漫着基督教式的背景。其中,“夜晚”同为图形与背景;“夜晚”暗指当时暗无天日的社会,“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暗指哈姆雷特思想的单纯。译文“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概括出该基督教隐喻的意义,呈现出一幅基督教式的隐喻背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大量的人物对话都隐喻着《圣经》中的人与事。对“人”的隐喻使读者获得对基督教的认同感。如悲剧开始时,鬼魂说:
(The leprous distilment,)whose effect
Holds such an enmity with blood of man
……
All my smooth body.(Evans 1150)
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地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里,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立刻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癞病似的满布着可憎的鳞片。(朱生豪等248)
most lazar-like,with vile and loathsome crust all my smooth body隐喻《圣经》里两位乞丐拿撒路浑身的“疮”,虽形象不佳,但结果很好:一位死后进入天堂,一位被耶稣复活。鬼魂的话语隐喻了他被弟弟杀死后必将进入天堂。笔者认为上述译文没能将这一丰富的基督教隐喻义翻译出来,无法让读者领略其魅力。根据图形—背景理论,此处应增加基督教式隐喻背景--“拿撒路身上害的疮”并提前,而将“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布满鳞片”看作背景图形延后。改译为:
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我全身光滑的皮肤就像拿撒路身上害的疮一样,布满可憎的鳞片。
隐喻有时不足以解释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莎士比亚会直接将基督教与非基督教进行对比,哈姆雷特在城堡的厅堂里与几个伶人的对话体现了他意识深处基督教的正统意识,如:
O,there be players that I have seen play—and heard others[praise],and that highly—not to speak it profanely,……they imitated humanity so abominably.(Evans 1162)
啊!我曾经看见有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把他们极口捧场,说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又不会学着(基督徒、异教徒、甚至)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目。(朱生豪等279—280)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但这些伶人的形象如此恶劣,好像是上帝的雇工造的。根据图形—背景理论,“上帝的雇工造人”是“什么造化(即上帝)”这一基督教隐喻背景所凸显出的图形,其隐喻这些伶人是异教徒,天生比基督徒低人一等,从而深化了基督教隐喻的背景内涵。此外,哈姆雷特嘴边常说的“上帝”、“神”、“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等都是他渲染圣洁、采取行动的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不但给他为父报仇披上了一层基督教式背景的神圣面纱,而且从世俗层面也符合当时社会观众的认可,从而增加了撼人心魄的戏剧性和艺术效果。所以说,理解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有助于正确地进行翻译。
(二)哈姆雷特对复仇思索的基督教隐喻翻译
哈姆雷特常被比喻为“优柔寡断的人”,他的优柔寡断在于他对复仇的思索。虽然鬼魂敦促他采取行动,但他内心却缺乏相应的动力,如果不是国王要除掉他,哈姆雷特可能永远拖延下去。在第一幕第二场中,克劳迪斯劝解哈姆雷特不要沉溺于悲痛:
Tis sweet and commendable in your nature,Hamlet,
To give these mourning duties to your father.
……
“This must be so.”(Evans 1144)
哈姆雷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头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朱生豪等236)
克劳迪斯将哈姆雷特丧父看作自古以来人们必须面对的主题,corse是双关,既指 course,也指 corpse;因而 the first corse可理解为丧父的“第一个例子”或“第一具尸体”。the first corse让哈姆雷特不难想到亚当(第一位父亲)和亚伯(第一具尸体),并将克劳迪斯谋杀国王的罪行与该隐弑兄弟行为联系起来。但面对父亲突然去世、叔父篡夺王位、母亲再婚嫁给叔父,听到鬼魂讲述父亲被谋杀的经过,看到心爱的姑娘与他断绝恋情等等不幸,他苦于找不到有效途径为父报仇,内心十分矛盾,在第三幕第一场的这段独白显示了他对复仇的思索:
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
Devoutly to be wish’d.(Evans 1160)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朱生豪 等275)
“生存还是毁灭”、“默默忍受与挺身反抗”这两对矛盾隐喻了哈姆雷特遵循或违反基督教原则,具有很深的哲理意蕴:生存和忍受、毁灭和反抗代表符合或违背基督教教义。对于复仇,哈姆雷特多次权衡“忍受”与“反抗”,最终选择了忍受。此处“睡眠”隐喻“死亡”,映射哈姆雷特的厌世倾向,为他不采取行动提供借口。而且,哈姆雷特面临伦理难题:身为王子、儿子、民众心中美德的化身,他意识到鬼魂命令的正义性,但他对罪的憎恶和对抽象正义的要求否定了它,因此他拖延复仇的计划。哈姆雷特害怕死后下地狱,想找到既能为父报仇,又能使自己的灵魂上天堂的最好途径,也正是他对复仇思索的结果。可以说,哈姆雷特对复仇的思索始终没有跳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三)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基督教隐喻翻译
哈姆雷特对复仇的思索在3次刺杀中得到充分体现。第一次刺杀:
…And am I then revenged,
To take him hi the purging of his soul,
……
Up,sword,and know thou a more horrid hent:(Evans 1167)
他用卑鄙的手段,在我父亲罪孽方中的时候乘其不备地把他杀死;虽然谁也不知道在上帝面前,他的生前的善恶如何相抵,可是照我们一般的推想,他的孽债多半是很重的。(朱生豪等293)
此时国王正在祈祷,毫无防备,最好下手。但哈姆雷特居然相信克劳迪斯利用祷告可逃脱惩罚,认为此时杀他只会送他上天堂,因而放弃了行动。他在等候一个更惨酷的机会:“当他在酒醉以后,在愤怒之中,或是在荒淫纵欲的时候,在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的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朱生豪等293)
第二次在母亲寝宫,哈姆雷特叫道:How now?A rat?Dead,for a ducat,dead!(怎么!是哪一个鼠贼?要钱不要命吗?我来结果你。)(朱生豪等294)他利用疯癫的假相将普隆涅斯(他以为是国王)当作一个鼠贼杀了,推卸自己良心的重负。
最后,心爱的姑娘与母亲已死,自己遭国王暗算,在临死前哈姆雷特痛斥国王,奋起反抗:Here,thou incestuous,[murd’rous],damned Dane,Drink [off]this potion!(好,你这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的丹麦奸王!喝干了这杯毒酒!)最终哈姆雷特与国王同归于尽。当然,与其说哈姆雷特的行为是为父报仇,不如说是他的绝地反击。
四 图形—背景理论对基督教隐喻翻译的指导意义
由于中英文化差异,本来隐蔽性就很强的基督教隐喻使译者、读者更多地关注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特征,而忽视他所处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基督教意义的行动原则。利用图形—背景理论翻译《哈姆雷特》作品中的基督教隐喻,一方面应进行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促使读者理解隐喻的蕴含并运用到对普通情景的理解,另一方面应注意基督教隐喻的句式转换,使主语与主题凸显出来。
(一)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
在语篇生成和理解过程中,人们往往用类比方式将隐喻的某些方面映射到所描述的事物或情景上。通过延伸隐喻概念,使隐喻具有建构语篇的功能,从整体上映射语篇的基调和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哈姆雷特》随处可见基督教隐喻(图形),译者将之置于《圣经》背景中进行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就能较好地翻译这些基督教隐喻。
第三幕第二场中,当哈姆雷特得知父亲是被叔父害死时,气愤地说:I would have such a fellow whipt for o’erdoing Termagant,it out-Herod Herod,pray you avoid it.熟悉《圣经》的译者会因此联系古犹太希律王(他曾为扼杀耶稣,差人将伯利恒城和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斩尽杀绝),中世纪欧洲许多剧本把他演作暴君。莎士比亚创造“Outherods Herod”隐喻“比暴君还暴君”。如将此隐喻与《圣经》进行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该句应译为:我可以把这种家伙抓起来抽一顿鞭子,因为他把妥玛刚脱形容过分,希律王的凶暴也要对他甘拜下风(朱生豪等279)。
第三幕第三场中,国王祈祷O,my offense is rank,it smells to heaven,… My stronger guilt defeats my strong intent.国王表面道貌岸然,内心却充满淫欲,不惜弑君;虽无法摆脱罪孽感与自我谴责,但又不愿放弃用罪恶手段获得的一切。此段隐喻《创世纪》中亚当的长子该隐杀死其弟亚伯,受上帝诅咒。经过与《圣经》进行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可译为: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升于天;我的灵魂上负着一个元始以来最初的诅咒,杀害兄弟的罪行!我不能祈祷,虽然我的愿望像决心一样强烈;我的更强的罪恶击败了我的坚强的意愿。(朱生豪292)
翻译基督教隐喻时,由于中西思维的差异,译者对图形背景的区分以及隐喻理解上可能产生错位。“文学作品中隐喻式的语言决定了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直线翻译,它需要心理空间的填补、连接和转换,这是认知结构、文化心理、语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胡东平106)译者基于对图形—背景理论,有效融合基督教隐喻(图形)与《圣经》(背景),从而尽可能达到隐喻翻译的形神兼备,这正是基督教隐喻翻译的难点也是关键所在。
(二)英汉语的句式转换
汉语通常是信息单位话题和评说语言,具有话题凸显特征;其主语非不可或缺,且句子结构也不稳定。而英语属主语凸显语言,主语和谓语不可随意缺省。在认知模式上的差别也明显,汉语主题句一般从背景到图形,主题提供背景,述题表示图形;而英语则从图形到背景,主语占凸显地位。因此,翻译基督教隐喻文本时,译者往往发现隐喻文本富于宗教文化色彩,奠定了作品的背景色,或凸显了图形的对立色,构成连贯的篇章隐喻。不同文化概念域的基督教隐喻可能带来不同的文化和情感意义,英译汉时需要从篇章隐喻角度关注句子的凸显。否则,没有把握好凸显部分就难达到基督教篇章隐喻的效果。
按照图形—背景理论,译者应遵循句式转换的最佳映射;如不能直接按源语图形背景出现的顺序进行对等映射,则应调整语序,或凸显重点、或部分的差异。《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说:A mote it is to trouble the mind’s eye。该隐喻源自《圣经》中的“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有一粒灰,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吗?”原文中的A mote属于图形,the mind’s eye则属于背景。由于英汉图形—背景的差异,翻译时调整语序,译为:那是扰乱我们心灵之眼的一点微尘。
五结语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剧中基督教隐喻多,富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凸显了主人公对复仇的思索和对复仇采取的行动。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基督教隐喻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无法为译者完全移植,容易造成译本和原作的翻译差异,让丰富的基督教文化流失,甚至对读者产生误导。为了使基督教隐喻的文化意义不流失,不误导读者,笔者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探讨基督教隐喻翻译,认为需要同时关注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和基督教隐喻的英汉句式转换。其有效翻译不仅可以缩小双语文化间的差别,深化对作品的整体认识,而且可以促进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1]Evans,G Blakemore.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M].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74.
[2]Lakoff,G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Langacker,R W.Concept,Image,and Symbol:The Cognitive Bas is of Grammar[M].Berlin:Mounton de Gruyter,1991.
[4]Walter,Virginia A.Metaphor and Mantra:The Function of Stories in Number the Stars[J].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1996.
[5]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6]胡东平,汪 珍.基于图形—背景理论的颜色隐喻英译研究[J].三湘译论(第十辑),2011.
[7]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8]莎士比亚全集[M].朱生豪等译.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97.
[9]徐莉娜.隐喻语的翻译[J].中国翻译,1999.
[10]武柏珍,沈荃柳.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