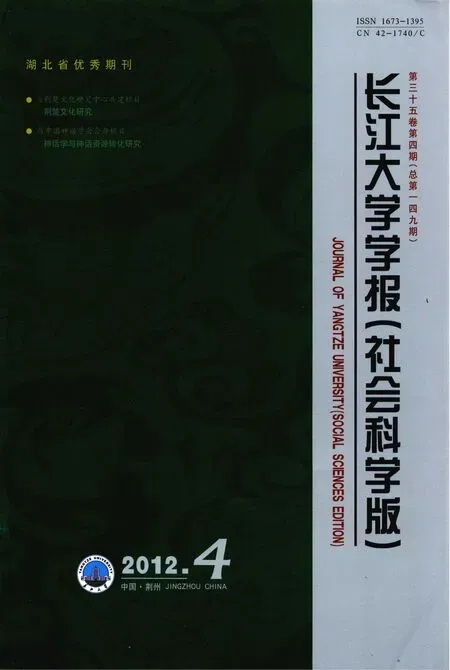诗歌翻译中“三化”理论的应用
——以《江城子· 悼亡妻》两种英译文为例
姜丹丹
(晋中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诗歌翻译中“三化”理论的应用
——以《江城子· 悼亡妻》两种英译文为例
姜丹丹
(晋中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在汉诗英译理论体系中,许渊冲的“三化”理论是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对许渊冲和徐忠杰的《江城子· 悼亡妻》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三化”理论指导下,许渊冲的译文不但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境,还给译入语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
江城子· 悼亡妻;“三化”理论;诗歌翻译
中国古诗词的英译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最初,翻译中国古诗词的主要是英美学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将古诗词译成英文,80年代以后,中国古诗词英译的中心由欧美转移到中国。理论的不同使得译诗活动被分为很多派别,其中,格律派(以诗译诗)的代表人物是许渊冲,他独特的翻译理论和思想为我国翻译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理论知识框架:“三化”理论
许渊冲从事文学翻译实践60余年,他不仅有大量的译诗问世,而且还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化”理论,该理论已被广大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所认同。许渊冲认为,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1](P82)。在《唐宋诗一百五十首》英译本中,他提出了诗词翻译的“三化”问题,随后又在《文学与翻译》一书中,对“三化”作了进一步阐述:“翻译甚至可以说是‘化学’,是把一种语言化为另一种语言的艺术。大致说来,至少可以有三种化法:一是‘等化’,二是‘浅化’,三是‘深化’。这三种化法,都可以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2](P11)等化包括形式的对等、意思的动态对等、词性转换、句型转换、正话反说、典故移植等,当原文与译文审美格局接近时,才能实现等化。深化包括特殊化、具体化、加词、分译、无中生有等。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译、化难为易、以音译形等。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强调,译论要注重实践和创新,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翻译的实际服务;译者要基于译论,但又不要过分地拘泥于旧有的理论。他的译诗理论,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单一“忠实”标准,也有别于西方语言学派一味追求的“对等”,而是一种更加灵活的翻译理论。
二、《江城子· 悼亡妻》两种英译文的对比分析
《江城子· 悼亡妻》是苏轼悼念亡妻的作品,原作充满了作者对亡妻的思念以及对现实的无奈,所以译者在英译文中要力求传达出作者失去爱妻的悲痛和对自己命运不济的感慨。笔者拟对许渊冲和徐忠杰的英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来探讨“三化”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先看词牌名“江城子”。“江城子”之名,取自五代十国中的蜀国词人欧阳炯的词: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后来,“江城子”慢慢演变成为固定的词牌名。对于该词牌名,许渊冲(以下简称“许”)译为“A riverside town”,他将典故之意挑明,这种做法虽然稍减美感和文学底蕴,但照顾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鉴赏习惯,还传递了客观的历史文化信息。这种“深化”法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歌所蕴涵的感情和意境。徐忠杰(以下简称“徐”)将“江城子”译为“Jiangchengzi”,用汉语拼音表达词牌名,这样翻译并没有照顾到译入语读者的理解能力和鉴赏习惯,从而带来了阅读障碍。
“十年生死两茫茫”,生者与死者都在长期相互怀念,但却音信不通,彼此音容渺茫了。“两茫茫”许译作:the living of the dead knows nought,此为倒装句,其正常顺序应是:the living knows nought of the dead.许的译文本着“浅化”的原则,“浅化”的使用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简化,使得译入语读者能充分理解“两茫茫”的含义。此句徐译为:Between us is an impenetrable haze,其中“an impenetrable haze”对“茫茫”的词义造成伤害和损失。这种译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汉诗英译时的“因韵害义”。
“不思量,自难忘。”许译为:Though to my mind not brought,Could the dead be forgot?此句为倒装句,并省略了一些句子成分。复原以后应是:Thought(she was)not brought to my mind,could the dead be forgot?他的译文采用等化中的句型转换法(让步从句和倒装),将原句从陈述句转换成问句“难道我会忘了你吗”,这样的转换很好地传达出“自难忘”的刻骨铭心。徐译为:To my mind have constantly come thoughts of you:Things I can’t forget,loving you as I do.从中可以看到加词,例如“constantly”,“loving you as”等,并且他采用的是陈述语序,这就远不如许的译文中的多种表达方式,因为,正是这多样的变化表达出苏轼“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铮铮誓言。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这是从想象中的死者的反应方面来描写作者十年来所遭遇的不幸和世事的巨大变化。比较中英文,对于“相逢”一词,许深化、加译了“revived”一词,突破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生者与死者得以“相逢”,这样处理不仅有利于译入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词的感情和意境,而且也起到了明确主旨的作用。“尘满面”许译为“worn with care”,浅化了作者十年来宦海沉浮的痛苦际遇,揉进十年的岁月与体态的衰老,形象地表达出原文的意境。徐的译文“My face is overspread with dust and soot”中的“dust and soot”具体化了原词的意境,这让译入语读者很是疑惑,他们不知道诗人因何会满脸油污,难以体会到诗人在这十年间几经沉浮,生活上困难到食杞菊以维持的境地。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其中“梳妆”一词,许译为“Before her mirror with grace”,浅化、抽象化了具体动作,尤其是“grace”一词,更是神来之笔,仿佛使读者想象到新婚时,作者在王氏身旁,看着她沐浴晨光对镜理妆,心里满是蜜意柔情。徐译为:With your quiet dignified,lovable air,Engaged in dressing,with grace and ease,your hair,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来试图表达苏轼眼中昔日的美好时光,但描写得过于浅化、具体化,缺乏诗给人的联想。“惟有泪千行”,许译为:from our eyes tears gushed;徐译为:tears flowing down in streams.前者用了动词“gushed”,明显比后者的“flowing down”要精准得多,这种“浅化”是在钻入原作深层,领悟作者精神后才做到的“去其粗,取其精华”,是典型的“浅中有深”法。
三、结语
通过对《江城子· 悼亡妻》的两种英译文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在“三化”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许的译文不但很好地传达了原作的意境,还给译入语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翻译难,译诗更难,尤其在翻译中国古诗词这一方面,不仅要求译者尽量准确地再现原诗的风貌和意味,来弘扬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而且还要兼顾译入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习惯。其二,虽然译者总是本着为读者提供最好的译文的原则,采用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法,但译者主体性原则的运用,使得译文往往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就要求译者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把握好“化”的程度。
[1]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许渊冲.文学与翻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H315.9
A
1673-1395(2012)04-0108-02
2012-02-12
姜丹丹(1982-),女,山西榆社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