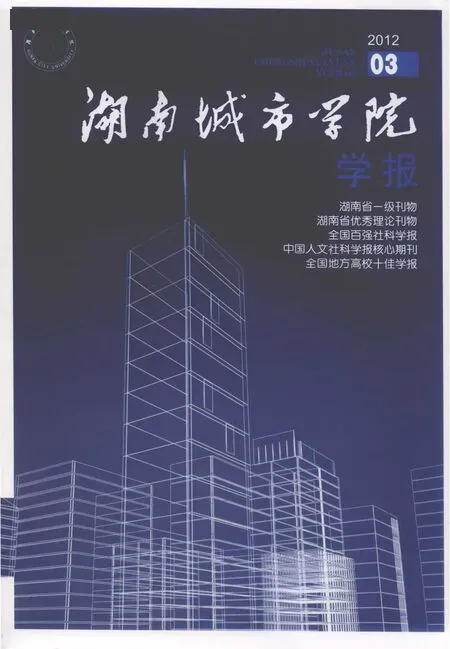认知语言学中的比喻
王莉莉
比喻研究是语言问题同时也是心理学问题,因为比喻这一现象是人类通过各种语言性手法向对方传达并使对方理解其在认知构造中感知到的心象。所以比喻研究的重点是,使用或发明语言性手法的发送者的精神性认知构造及其投影出的语言表现形态之间的问题。并且通过语言表现和语义之间的联系实现接受者在精神性认知构造过程中与发送者保持同样的感知和理解。
对于比喻这一认知语义学范畴中的中心研究课题,本文在鸟瞰比喻研究的历史的同时,撷取介绍认知语言学中隐喻的重要地位。
一、比喻研究的历史
比喻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创立期。该时期与古希腊以Aristotle为代表的修辞学的黎明期相当。第二个时期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语言哲学中的比喻研究时期。第三时期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符号学和语言学对其的侧面研究。其中这一时期比喻研究的兴盛令人瞠目。出现如此的盛况原因有二。其一,得益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认知心理学阐明了人类认知构造中的意义处理结构及相关的知识构造。因此,认知心理学中的比喻研究是把人类进行的比喻处理看作是认知处理的过程,或者说它着眼于在语言处理过程的框架下,人类生成、理解意义的知识构造。这对过去的比喻研究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其二,受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认知语言学的影响。Lakoff 和 Johnson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可以说是使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比喻的先驱之作。书中 Lakoff 和Johnson极力主张比喻支撑着我们的认识和概念构造。他们不仅把隐喻和明喻作为研究对象,还涉及了过去少人问津的换喻和提喻。首次提出隐喻性映像和图像架构的认识与语言表现化的问题。他们的研究使比喻研究和认知构造方面的概念研究、范畴研究联系到了一起。[1]
以上的比喻研究中特别受到重视的是支撑比喻的语义构造方面的内容。尤其相似性、语义构造和语言表现化的关联性更是研究的中心。并且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人类的知识构造在比喻理解可能性方面起到的促进和制约作用都是认知构造中的组成部分。
语言是人类和世界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并不是被人类概念化分离出来的世界客观性属性,必须置于与认知作用的关联性中进行考察。因此,语义现象是以人类的记忆和经验为基础的。语义研究也应把意义放到语言使用者的客观认知中理解。Lakoff 和Johnson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比喻对于我们日常语言的语义认识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它所产生的语言现象及语义理解,已经成为认知语义学的中心课题之一。而在认知科学中,主要从范畴和隐喻的视点来理解语义现象,认为隐喻性认知活动是人类五感、空间认识、运动感觉等身体经验的反映。隐喻产生的语言现象和语义理解也成为认知语义学的中心研究课题。
二、隐喻的本质
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和A is like B/A is as...as B这样的明喻比喻形式不同,它直接采用A is B这类断定性表达形式,B表示的意义内容被添加到A中。比如,“She is my lover”这种字义性表达可隐喻为:“She is my sunshine”。在人类的语言活动中把未知领域的事物比喻为已知领域的事物,通过这两种领域间的某种相似性来理解未知事物,这种相似性的联想认识就是隐喻。濑户贤一这样定义隐喻:它是理解世界的认知装置,同时也是再构筑世界的理性策略。[2]再看「人生は航海である」这样的表现,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发生的大小事视作航海,从起点到终点,漫长的迂回曲折和喜怒哀乐。让人更易体味出人生的艰辛和坚持。还有把男人比作狼和羊,其间性格的微妙差异一目了然。当然,类似的比喻语言表现是不能反映全部的语言机能的,我们只是把它作为理性策略,便于认识世界,或者说便于理解特定指示的内容。
隐喻原本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它也包含有语义学的问题。对它的研究可分为两大论别,“比喻论”和“相互作用论”。“比喻论”就是指相似性的表达,认为隐喻就是省略掉“A is like B”中“like”的明喻表现形式。而持“相互作用论”观点的一方认为,隐喻的本体和喻体在内容上相互作用。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仅仅只把隐喻现象当成语言问题,单从人的认知和概念构造等方面是无法阐明隐喻现象的,这只有以修辞技法的角度在诗和文学作品等艺术文章中进行研究才能得以实现。
于是,对以上两种论别持有怀疑态度的Lakoff 和Johnson,在两人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中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活动,它已深深渗透到人的思考、行动样式,甚至日常生活中。人类认知的大部分概念体系都由隐喻性要素支撑。因此必须站在认知性的立场来研究隐喻的机能和表现。[1]
Lakoff 和Johnson把隐喻分为四个种类,“构造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s)”、“方向性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存在性隐喻(Ontological Metaphors)”、“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s)”。[1]
三、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
(一)构造隐喻
构造隐喻是指某个概念以其他概念为基础借用隐喻构造其概念的现象。关于这个问题,Lakoff和Johnson举了战争概念表现争论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如:“議論は戦争である”“彼は私の議論の弱点をことごとく攻撃した。”“私は彼の議論を粉砕した。”“私は彼との議論に一度も勝ったことがない。”[3]
Lakoff和Johnson认为争论在现实中有胜负之分,把争论的对手看作是敌人,攻击对方争论的立脚点(=阵地),守卫己方。审时度势,转换战略。当眼看己方争论立足点(=阵地)不保时适时放弃另辟战线。这不是武力战斗,但却是语言的战斗。争论中进行的行为虽然是部分性的,但都可以借助战争这一概念构造起来。争论中的攻击、防御、反击在战争的隐喻中得以构造并诠释。所以说,隐喻是语义认识构造的基础。Lakoff等认为人的大部分概念构造都是由构造隐喻形成的,这种说法一点也不为过。
(二)方向性隐喻
方向性隐喻是指概念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整体性概念体系的现象。当中大部分是由指示空间的方向性概念构成。比如上—下(up-down)、内—外(in-out)、前—后(front-back)、到—离(on-off)、深—浅(deep-shallow)、中心—周边(central-peripheral)等。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Lakoff 和Johnson引用了William Nagy “空间关联性的隐喻”中上下方向性隐喻的研究成果。如:“HAPPY IS UP;SAD IS DOWN”、“I’m feeling up.”“My spirits rose.”[1]15
除此之外 Nagy还提示了其他隐喻性认识的语言表现:意识为上,无意识为下;健康和生命为上,生病和死亡为下;具有支配力的为上,被支配的为下;多的为上,少的为下;高位的为上,低位的为下;好的为上,坏的为下;德行为上,恶行为下;理性为上,感性为下等。总的来说,人类认识构造的语言表现中,把肯定性概念隐喻性认识为上,否定性概念隐喻性认识为下。这种围绕语词周边的感觉性语义概念用方向关系来表现的现象,被称为“方向性隐喻”。另外,Lakoff等认为离开经验理解隐喻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恰当表现也不会被认同,而且该如何理解经验为基础的周边语义概念问题,也已经成为认知语义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
(三)存在性隐喻
方向性隐喻中的概念理解肯定有所界限,所以存在性隐喻提示了比方向性更广范围的理解形式。它是指把自己的经验看作是物体或物质。换句话说就是感情、思想、活动、事件、社会现象等无明显界限的抽象概念视作物理性存在物或内容物。Lakoff 和Johnson在这里举了“通货膨胀”的例子,他们把“通货膨胀”视为一个存在物,对其进行数量化和识别,这种更广范围中进行的认识就是存在性隐喻。另外,Lakoff等还把人的精神以及心理视为机器和易碎的物体。如:「彼は故障した。」「彼は砕けてしまった。」[3]43
存在性隐喻通常是把非物质体的对象物视为物体,这使得现象和语言表现的认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化。
(四)容器隐喻
容器隐喻是利用内外方向性的区别界线来认识事物。这里所说的容器主要指视界、土地领域、事件、活动、状态等。Lakoff 和Johnson在他们的著作中阐述了容器隐喻中产生的语言表现及其认识的关联性。
“视界”是把映入自己眼中的物体看作是存在于视界这一容器中的内容物。这个隐喻发生在限定的视界范围领域中,如:「その船がだんだん視界の中に入ってきた」。“土地领域”把房间、家、森林、土地看作是容器。「部屋の中に(外に)」、「開拓地の中に(外に)」「森の中に(外に)」这样的语言表现自身就具有内、外方向性。“事件”在人们看来,存在性隐喻是理解事件和行为、活动和状态的框架,事件和行为是物体的隐喻,活动是内容物的隐喻,状态是容器隐喻。我们以“竞争”为例,假设“竞争”是一个事件,那么它在空间和时间中就有一个明确的界线。所以把“竞争”看作是“容器”,那当中就会有参加者、有开始、有发展活动、有结束等事件。“活动”是将使众多活动及行为成立的其他活动视为盛载的容器,主体进行的活动也隐喻性地包含了主体本身。“状态”是把主体的被放置状态看作是容器,被放置当中的主体看作是内容物。
认知语言学是以认知、解释、语义、共性为取向的,这是语言研究史上的重大发展。隐喻形成的语言表现及其理解,强烈暗示了隐喻由来于人类基本的普遍性的经验。另外,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隐喻不仅具有构成概念的性质,同时也是扩展语言表现及其语义认识可能性的手段,对隐喻的进一步研究将会更有利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和奥秘。
以上对Lakoff 和Johnson比喻相关理论的再梳理与认知,不仅为我们提供认识比喻的视角,也为比喻所产生的语言表现及其理解方面提供了相关研究的依据。
[1]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 瀬戸賢一.認識のレトリック[M].海鳴社, 1997:35.
[3] 渡部昇一,楠濑淳三,下谷和幸 訳.レトリックと人生[M].東京:大修館書店, 1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