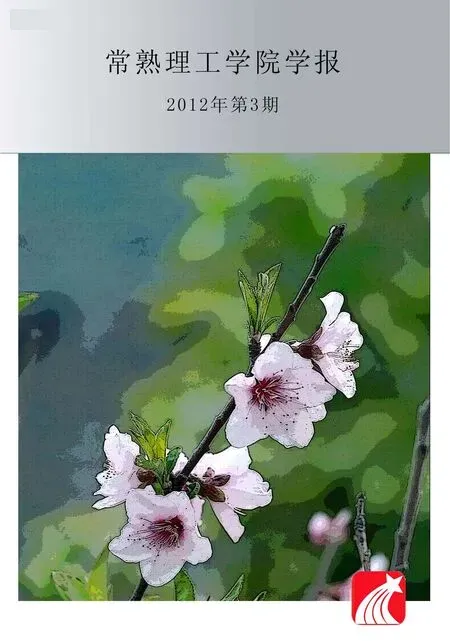贝克的“自反现代化”论
钟一军
(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昆明 650500)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现代性一直是该学科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现代性有其时代内涵,毕竟,经典社会理论提出的现代性在当代起了变化。在当代研究现代性的社会学家中,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自反现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理论①现代性指现代社会特征,指向一种状态。与其相对应,现代化则是走向现代性的一种过程,二者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所以,贝克的“自反现代化”理论可看作是对一种生成中的现代性的研究。独具特色,本文试对这一理论作一番系统解读。
一、现代化的“自反”内涵
贝克提出的“自反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在于现代化的“自反”(reflexive)特性,理解“自反”内涵成为理解贝克理论的关键。关于“自反现代化”概念,贝克至少在两处作了较为明晰的说明。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贝克指出,“自反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的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化的道路。”[1]6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他写到:“正如现代化消解了19世纪封建社会的结构并产生了工业社会一样,今天的现代化正在消解工业社会,而另一种现代性则正在形成之中。”[2]3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贝克指出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特征,即“自反”特性,这种“自反”既是一种转型机制,又是一种转型过程。
(一)作为转型机制的“自反”
贝克眼中的这种“自反现代化”转型非常独特:它“(首先)指自我对抗(self-confrontation)。现代化……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动力之后,采用的是隐性副作用的模式。”[1]9这段话集中反映了“自反”独特的转型机制:(1)转型的动力。贝克指出,“现代化利用自主的现代化的力量挖了现代化的墙角”[1]224,现代化转型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自身,进一步说,是源于自身的激进化②贝克认为他的这一观点不能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是其自身掘墓人”的观点等同,在他看来,马克思笔下资本主义转型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阶级斗争,而他认为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是资本主义胜利的成果以及非暴力的进一步的现代化。。(2)转型的方式。与上述的自我动力相联系,因为是“自挖墙角”,所以是在不易被察觉、在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贝克称之为“隐性副作用”①贝克和吉登斯、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一起提出了相近的概念,即“reflexive modernization”,但理解各有侧重。前者主要强调“自反”,即在不被察觉下的自我消解、自我对抗,贝克也称为“隐性副作用”;而后二者则主要强调“反思”,即在认知层面上的自我反思。。(3)转型的后果。现代化在经过上述一番不可思议的“自我对抗”后,产生了一系列自身的后果,这种后果体现在后文要讨论的“个体化”对工业社会制度的消解和现代风险对科学技术的消解中。
(二)作为转型过程的“自反”
“自反现代化”也是贝克对现代化转型过程的一种判定。(1)进程的界定。与后现代主义者不同,贝克认为当前社会并不是对现代化的背离而进入另一个时代,它仍然在现代化轨道上运行。贝克指出:“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现代性的开端——这是一种超越了古典工业设计的现代性。”[2]3正因为如此,贝克又将自反现代化称为“再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2)特征的双重性。转型的自反现代化意味着新旧重叠的两重性,一方面旧式的工业现代性正在被消解,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新的现代性正在形成之中,尚未定型,新旧因素同时并存。(3)预示着现代性的重建。进行中的第二次现代化暗示着一种现代性重建的努力,表现为一种应对,乃至一种超越。在这一点上,贝克与另一位社会学家吉登斯达成了一致,“吉登斯和贝克承认现代社会已达到了极限。但他们认为现代工程并没有陷落,它只是变得激进化并得以重建。”[3]232
二、工业社会模式的“自反”:加速中的“个体化”社会
贝克指出,“自反现代化”体现在一种“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的社会生活状况中。吊诡的是,这种“个体化”在工业社会内部生成,现在,它又转而动摇着工业社会传统生活模式的根基——工业社会正在进行着一场“自反”。
(一)自反的动力:制度化的个体化
贝克对于当代“个体化”现象的理解,既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个体概念,也不同于个性化和个体互不依赖的观点,也与18、19世纪作为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统治的形式出现的个体化现象相区别。他提出了“制度化的个体化”概念,认为“个体化”现象是工业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促成这种现象的直接“马达”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化的劳动力市场。他进一步指出,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三个因素加速了“个体化”进程。(1)教育。教育的时间在延长,对教育的重视重塑了传统的目标取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有向上流动的预期,“学校和大学的正规教育为个人提供了资格证书,使他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个体化的职业机会。”[4]38(2)流动。劳动力市场通过职业流动、居住地变动、雇佣关系变动及其初始位置的变动,使人们独立于传统的行事方式,成为个体化的动力源。“由于独立于传统的纽带,人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特征,这第一次使个人命运体验成为可能。”[4]38(3)竞争。劳动力市场迫使人们为自己做宣传,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加速了个体化。尽管人们可能有共同的竞争资源(如相似的教育、经历与知识),但这种共同体已在相互竞争中被削弱,竞争“导致同质性社会群体中个体的相互隔离。”[4]38
(二)自反的后果:“个体化”对工业社会模式的消解
“个体化”在加速进行,它反过来消解造就它的工业社会的“参数”,正如贝克所言,“‘教育扩张’政策最初并无意瓦解家庭,也无意使劳动市场灵活化”[5]71,这种政策的后果是非预期的。贝克认为,这种非预期的自我消解突出表现在:(1)阶级的消解。在阶级社会中,雇员必须受制于劳动法以及社会政治范畴的相关规定。但在当前转型期,社会认同、社会不平等、社会冲突等问题已经脱离了传统范畴,而必须在个体意义上加以理解,我们正通向一个“雇员的个体化社会”。(2)社会文化的转变。与遵循特定轨道的阶级文化不同,个体化带来一种“自我文化”,它不再以阶级为根基,而是崇尚一种“为自己而活”的文化。这“意味着标准化的人生轨迹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人生,人们可以选择‘随自己意愿而过的人生’、充满风险的人生、破碎的人生等。”[4]28(3)生活的全球化。人们的生活开始跨出国界,这是一种生活轨迹的全球化,一种旅行生活和跨国生活。(4)个体能动性增强。个体化意味着个人越来越挣脱集体生活的束缚,人们为了生存要迫使自己去思考、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的能动性和反思能力得到增强。(5)家庭领域的变化。一方面是女性角色的变化。妇女生活处在从“为他人而活”迈向“一点属于自己的生活”的矛盾进程中,其前景既饱含机会又充满风险。另一方面是家庭模式的变化。家庭由基于团结的义务而结合在一起的“需要共同体”,正在变成一种基于个人生活设计逻辑的“选择关系”。如跨国跨文化的夫妻组成的文化多元家庭,就意味着一种个体的联合。
(三)自反的应对:自我发明和社会再造
贝克指出,指向一种“自主人生”的个体化具有双重面孔,体现为“不确定的自由”。“机会、危险和人生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此前已经在家庭纽带和村庄共同体中被事先规定好了,或是被社会等级或阶级规则事先规定好了,如今却必须被个体本身所感知、解释、决定和处理。”[4]5思考、计算、计划、适应、协商、定义、取消,这些都是“不确定的自由”的要求,它正在掌控着生活。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更自由了,但个人生活却变得难以适从。如何应对这种个体化社会的不确定性?贝克指出,可能的四条社会重新整合道路——民族主义的复归、超验共识基础上的价值整合、建立在共同物质利益上的整合、国族意识——并不可行,他认为至少还有另外一种整合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是“首先必须对这种状况(个体化——笔者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次,人们在面对生命中的重要挑战(失业、自然灾害等)时必须能够被成功动员与激发。”[4]21在此基础上,“在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蒸发’的地方,必须对社会进行再造。”[4]21-22这种再造如何实现?贝克从科尼格那里受到启发,认为“如果说这种社会还可能整合,那就只能凭借其自我解释、自我观察、自我发现、自我开放来完成,即通过自我发明来完成。”[4]22而社会自身的开拓能力和创造能力是衡量其整合度的标尺。当然,贝克认为这种自我发明只是一种可能,成功还未有定数。
三、科学技术的自反:形成中的风险社会
在贝克那里,“自反现代化”也体现在不断呈现的现代风险中。科学技术的成功已经使得自己不再可靠,原先被遮蔽的风险开始凸显,科学开始了一边解决风险又一边制造风险的历程,风险社会正在形成。现代社会风险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却与科学的预设——确定性、进步性背道而驰,科学开始陷入自我对抗的矛盾之中。
(一)自反的动力:科学制造风险
贝克认为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而这种风险根源于科技。“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有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互重叠。”[2]15贝克将科学产生风险的逻辑归纳为两个阶段:(1)初级科学化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的发展逻辑“依赖于一种被截削的科学化,在其中,对知识和启蒙的科学理性吁求仍旧排除了科学怀疑论的自我应用。”[2]190人们对科学信仰不疑,“人们遭受的疾病、危机和遭难”被归因为“野蛮的不可理喻的自然和牢不可破的传统的强制”[2]195,而很难被归因为科学,从而使科学免遭批判,进而使其超稳定地发展,而错误和风险却正在悄无声息地生成、积累。(2)自反科学化阶段。但是,随着科学的成功,风险越来越暴露,科学不得不接受外来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科学进入自反科学化阶段,其逻辑是“基于一种完全的科学化,它同样将科学怀疑论扩展到科学自身的固有基础和外在结果上。”[2]190于是科学的自我反思开始了,“科学自身是它们要去加以分析和解决的现实和问题的产物和生产者。以这种方式,科学不仅被当作一种处理问题的源泉,而且是一种造成问题的原因。”[2]191一方面,面对风险,只有科学能去解决,这种解决推动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科学又是造成风险的始作俑者,其越发展,制造的风险越多,从而形成了“风险推动科技,科技产生风险”的不断循环。
(二)自反的后果:现代风险对科学预设的消解
科学产生的现代风险意味着危险的不确定性,这无疑是对科学预设的进步性、确定性的自反。这种自反可以从贝克对风险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说明,突出表现在:(1)风险的不确定性。风险“使这个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标准的计算基础——事故、保险和医疗保障的概念等等——并不适合这些现代威胁的基本维度。”[2]19换句话说,风险产生的后果是不可计算的,因此也是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的。(2)风险数量的无限性。“饥饿和需要都可以满足,但文明的风险是需求的无底洞。它们无法满足,是无限的和自我再生的。”[2]21(3)风险的灾害性。风险不仅是一种生态威胁,也是一种社会威胁。它不仅带来关于自然和人类健康的问题,还带来市场崩溃、资本贬值等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后果,“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2]22(4)风险范围的全球化。风险具有全球蔓延的特征。“9.11”事件后贝克指出,“全球风险社会的新涵义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6]72风险越是增多、越具灾难性、越是扩散,其不确定性也越加呈现出来,对科学预设的消解也就越是深入。风险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科学自反的过程。
(三)自反的超越:亚政治和生态民主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自反”,科学产生的全球风险越来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如何超越风险社会?贝克提出了两个方案:(1)现实性超越——亚政治。随着风险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这种风险意识激发了一种政治上的爆发力。“在哪里现代化风险被承认……在哪里风险就发展出一种难以置信的政 治 动 力 。”[7]93贝 克 称 这 种 新 型 政 治 为“ 亚 政 治(sub-politics)”,它与传统的议会政治相比有两个特征:一是直接性。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绕过代表性的意见形成的机构(政党、议会)。”[7]50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力量。二是全球倾向。“其‘全球性’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道德或意识形态方面并不排斥任何人或者任何事。”[7]51这是一种“无敌政治”。贝克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就是一种“亚政治”形式,该组织成功地使壳牌公司将它的废弃石油装置在陆地上处置,而不是在海里。(2)规制性超越——生态民主。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制造了一种技术专家政治,这是“一种‘删节’的民主,其中社会的技术变迁问题是政治议会决策永远束手无策的。”[7]91也就是说,技术专家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人们对技术的伦理诉求难以奏效,风险难以制止。对此贝克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扩展协商机制的“生态民主”,对科学的扩张起到真正的规制。一方面,要实行权力划分,即解除科学对自身的垄断权威,实现“危险制造者和危险评估者之间权力的分离”[7]91;另一方面,创造可以对科学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只有一场强有力的、充分的、用科学的论据‘武装’起来的公众讨论,才能够将科学的麦粒从糠壳中脱出。”[7]92
四、结 论
作为一种社会转型理论,贝克的“自反现代化”论以“自反”为逻辑起点,对当代社会的新变化进行了精辟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时代特质,即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产生它的确定性进行着对抗。这种自我对抗在“个体化”中表现为一种“不确定的自由”,在“风险社会”中表现为难以预测的现代风险。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M].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陶传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乌尔里希·贝克,伊利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M].李荣山,范譞,张惠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6]乌尔里希·贝克.“9.11”事件后的全球风险社会[J].王武龙,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
[7]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