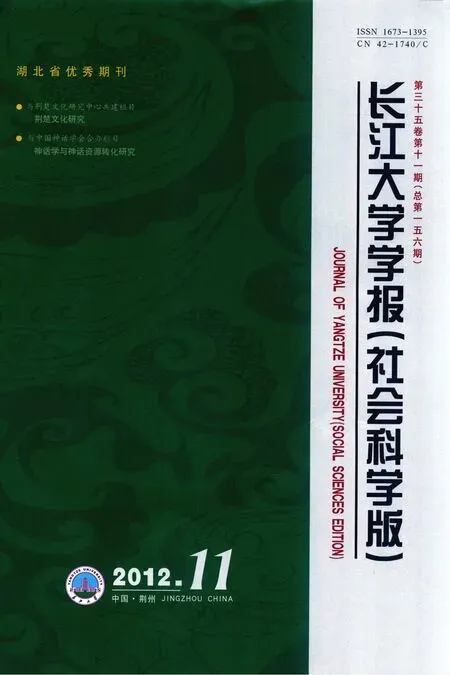爱因斯坦科学发现模式中的非逻辑思维
王龙海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是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者。相对于其辉煌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留给人类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思想也毫不逊色。他是直觉假设主义科学发现模式的思想先驱,特别是他关于科学发现中的非逻辑思维的独立而睿智的思想,对于现代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爱因斯坦在《关于思维同经验的联系问题——1952年5月7日给 M·索洛文的信》[1](P541)中,描述了他的科学发现模式:由公理体系A导出命题S(如S1、S2、…),命题S接受直接经验的检验。公理体系、导出命题以及直接经验,构成了科学发现的三个层级。在他的科学发现模式中,非逻辑思维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ε——A:直觉和想象
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讲道:“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1](P284)他在解释由ε到 A 的过程时,指出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只是一个“直觉的(心理的)联系”。也就是说,科学理论体系的发现和建立,并不是从经验事实逻辑推导得到的,而只是由“直觉”和“思维的自由创造”得到的。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过程的非逻辑性质,“要走向理论的建立,当然不存在逻辑的道路,只能通过构造性的尝试去摸索,而这种尝试是要受支配于对事实知识的缜密考察的。”[1](P566~567)“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是要得到那些普遍的基本定律,……要通向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才能得到这些定律。”[1](P102)“理论观念的产生,……它也不能通过纯粹逻辑的程序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它是由创造性的行为产生出来的。”[1](P497)关于 A,爱因斯坦称之为“公理体系”,也就是由科学概念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不是单个的经验定律这一层次的东西,而概念其实也是思维的“自由创造”。根据爱因斯坦关于直觉在ε——A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谓的直觉有这样一些特点:
其一,直觉与归纳相对立。亚里士多德和以培根为代表的古典归纳主义所倡导的科学发现模式都认为:从经验事实到具有普遍性的科学定律、科学理论的过程,是一个归纳过程,即是一种逻辑过程,是一种逐步抽象、概括从而上升的过程,逻辑思维是这一过程的主导。逻辑思维是按一定逻辑的格和式,严格遵循思维的逻辑规律和规则,运用一定的逻辑方法,从前提通过逐步推理的程序得出结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程式化的思维,是逐步、连续、渐进、步骤明确,一步步接近目标。而爱因斯坦则一反传统,强调公理体系的产生不是归纳的产物,而是直觉的作用。直觉是人的一种突发性的、对展现在面前的新事物或新现象极为敏锐准确的判断和对其内在本质的理解的思维类型,属于非逻辑思维,具有猜测的性质。如他所说:“理论越向前发展,以下情况就越清楚:从经验事实中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比如,引力场方程或量子力学的薛定谔方程。”[2](P490~491)爱因斯坦对用纯粹归纳的方法建立理论的做法提出批评,这本身是符合现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特点的,因为归纳法的确是适应近代实验科学的兴起而提出的,它在寻求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爱因斯坦的批评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创新的精神。
其二,直觉是一种非逻辑思维,同时携带了逻辑思维的颗粒。爱因斯坦所谓的直觉,几乎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是一种理性思维,是广义的逻辑思维。首先,直觉是以ε(直接经验的各种体现)为基础的,而不是空洞的异想天开。由于从经验材料中不能归纳和演绎出概念公理体系,即ε与A之间没有逻辑的道路,必须要有基于经验材料的“大胆”的想象和直觉。其次,思维自由创造概念本身也是一个有意识的理性思维过程。爱因斯坦说:“从知觉材料到达‘实在’,到达理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理智构造的途径。”[1](P512)这里的“无意识”,是指心理方面,即“直觉”;而“有意识”则指逻辑方面。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本人也从逻辑方面看待思维自由创造概念这一“直觉”过程,在此,逻辑的意义就被扩大了,用来刻画理性思维过程。再次,思维自由创造概念的原理存在于数学之中。爱因斯坦认为数学方法是一条从经验抽取理论公理基础的正确道路,思维自由创造概念的方法是数学方法。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直觉就是思维利用数学方法自由创造概念的过程,显然,直觉已不再是单纯的非逻辑思维,它打上了数学思维的烙印,有了逻辑的影子。
二、ε——S:直觉
爱因斯坦在解说他的科学发现模式时,认为S与ε相联系的这一过程可以用实验加以验证,“然而,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是属于超逻辑的(直觉的)”,原因是“S中出现的概念同直接经验ε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他进一步解释:“S同ε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比A同ε的关系要不确定得多,松弛得多(比如,狗的概念同对应的直接经验)。如果这种对应不能可靠无误地建立起来(虽然在逻辑上它是无法理解的),那么逻辑机器对于理解真理将毫无价值(比如神学)。”[1](P542)他认为ε与 S 的关系更加“不确定”,甚至用虚线来连结二者。
爱因斯坦认为,直觉是由经验事实检验理论的活动中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一理论的检验过程中,超逻辑似乎比直觉更容易理解,因为检验理论的方法是实验验证,而把实验验证说成是直觉的,似乎有点混乱。由此可以看出,爱因斯坦是在“必然性”这个意义上谈论逻辑的,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只用虚线连结ε与S。不过,在非必然性意义上,把实验验证看成是超逻辑的(直觉的),这仅是一个方面,而更为重要的是,选取哪个或哪些个别的经验来验证由基本原理演绎出的可检验性结论S,却需要借助直觉。因为通过这种选择,“单个经验同理论结构的相互关系,必须使所得到的对应是唯一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1](P384)。在这里,爱因斯坦无疑是持有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即理论之结论的证实要“令人信服”,而这是归纳法所达不到的。在选取适当的观察和实验来验证表示为理论之结论的经验内容时,有时会运用到直觉的方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也并非如此,典型化方法、统计归纳方法等也是可以选择的重要方法。如果仅靠直觉来把握这种选择的话,无疑会使理论检验的偶然性大大增加,这是不符合科学史的事实的。由此可见,爱因斯坦关于在理论检验过程中的直觉的意义,基本上是逻辑思维性质的。
爱因斯坦的直觉假说主义的科学发现模式非常注重直觉这一非逻辑思维形态的作用,他所谓的直觉,既有非逻辑的一面,又有可把握的逻辑因素,不能一概而论。爱因斯坦敏锐地洞察到了现代科学的到来,现代科学方法论要注重科学理论的建构,而不再像近代科学一样只围绕科学基本定律展开。直觉在把握科学理论方面比传统的逻辑方法更有说服力,因为它与“创造性”这一概念密切相关。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许良英,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